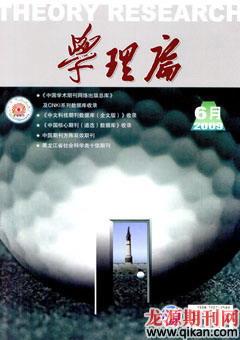重審啟蒙
曹 峰
摘要: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通過對啟蒙概念的深入分析,重新審視了啟蒙運動的思想資源。他們揭示了“啟蒙退化為神話”的啟蒙概念自身所蘊涵邏輯結果,從而對由啟蒙帶來的以工具理性為主導、以人的異化為特征、以世界性災難為必然的現代性世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這對克服工具理性的負面效應、重塑價值理性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關鍵詞: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啟蒙;批判;重審
中圖分類號:B565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09)14—0054—02
二戰以后,面對現代化浪潮在全球的廣泛展開所帶來的一系列的世界性“浩劫”這一社會現實,西方思想界對此進行了追根溯源的考究和分析,最后多數思想家認為肇始于近代的啟蒙是這些現代性問題產生思想根源,從而展開了對啟蒙的廣泛、持久的批判,而這其中又數法蘭克福學派的主將霍克海默和阿多爾多的批判最為深入、影響也最大。本文主要以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合著的《啟蒙辯證法》一書為文本依據,對兩者的啟蒙觀進行較為深入分析,并返回兩位作者對啟蒙批判的基礎內部,試圖揭示他們對啟蒙精神重審的邏輯根據與現實依據。
值得注意的是: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對啟蒙的分析和批判不同于一般人或流于形式的鞭撻、或側重于現象的否定等等諸如此類的純粹外部審視和考察,而是通過深入到啟蒙精神的源頭處,分析得出“如同神話已經是實現了的啟蒙一樣,啟蒙也一步步深深地卷入神話”[1]9是啟蒙內在辨證邏輯發展的必然,并對這種啟蒙辨證的發展后果進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揭露與批判,從而為20世紀一系列世界性的現代性問題癥候找到了重要的思想病源。
一、啟蒙的內在邏輯
“就進步思想的最一般意義而言,啟蒙的根本目標就是要使人們擺脫恐懼,樹立自主。但是,被徹底啟蒙的世界卻籠罩在一片因勝利而招致的災難之中。”[1]1這是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在《啟蒙辨證法》中開篇對一直被視為進步運動的啟蒙的嚴肅拷問。也就是說,啟蒙了的世界為什么會走向其原初宗旨的反面而使這個世界重新陷入野蠻的狀態呢?這既是現代性問題的焦點,也是當代世界需要迫切解決的重大理論問題。經過深入啟蒙思想源頭的研究,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發現:以上這些現代性災難的發生,是啟蒙的內在邏輯發展的必然——啟蒙和神話具有天然的親緣性。從某種意義上講,啟蒙與神話猶豫一個硬幣的兩面,它們之間同根同源、形影相隨、難分彼此。也就是說,神話發展成啟蒙(從古希臘到近代啟蒙運動)和啟蒙倒退為神話(從近代啟蒙運動到當代一系列現代性問題出現)一樣,都是啟蒙自身的邏輯使然。啟蒙的邏輯主要體現在啟蒙與神話的以下兩個方面的關聯上:
1.神話已經是啟蒙。換句話說,就是近代啟蒙的一切特征在古希臘的神話中均已有萌芽或者隱喻。眾所周知,啟蒙的最核心的概念是“祛魅”,使人擺脫恐懼和外在支配,樹立人類自身的主體性。正如康德所言:“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2]24作為“脫離不成熟狀態”之“祛魅”的目的又是要使人類的自我意識覺醒,這在啟蒙運動的口號:“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2]23中得到了集中表現。而在喚醒人類自我意識過程中,最根本的手段就是用知識替代幻想,正如近代“經驗哲學之父”培根所言“知識就是力量”一樣,知識(自然科學知識)成了啟蒙運動以來人們的根本追求和渴望。對知識這種力量的崇拜,是建立在人類思維(理性)自身和外界(包括自然、社會和人類自身)對立的基礎之上的。從此以后,世界的一切都被人類的理性對象化、固著化了。通過對古代神話的考察,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認為近代啟蒙所具有的這種典型的對象化思維已經在神話中雛形初具。因為在荷馬史詩中,“眾神與物質元素區別開來,并成為它們的總體性。自此時起,存在就分解為邏格斯(這種邏格斯隨著哲學的發展而被歸結為單子,歸結為單一的指謂項)和外部的萬事萬物。這種對自身存在與實在的區別壓倒了其他一切的區分。”[1]6也就是說,神話中的諸神就已經有意識地將它們區別于其身外的世界,確立自身的主體性。與此同時,“許多神話人物都具有一種共同特征,即被還原為人類主體。”[1]4所以,這樣一來,在神話中的諸神就和近代啟蒙中的人類相通了。除此之外,神話世界里的諸神等級制、人類因對陌生事物的恐懼而將之神化等等都和啟蒙中人類用理性對身外之物進行分門別類、對陌生之物窮根究底并最終順從于其(所謂客觀規律等等)有不同程度的契合。一言以蔽之,近代啟蒙的一切都可以在神話中找到原型。
2.啟蒙倒退為神話。啟蒙發展到極致后,最終使自身變成一種神話成為一種必然。為此,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強調說:“被啟蒙摧毀的神話,卻是啟蒙自身的產物。”[1]5“如同神話已經是實現了啟蒙一樣,啟蒙也一步步深深地卷入神話。啟蒙為了粉碎神話,吸取了神話中的一切東西,甚至把自己當作審判者陷入了神話的魔掌。啟蒙總是希望從命運和報應的歷程中抽身出來,為此它卻在這一歷程中實現著這種報應。在神話中,正在發生的一切是對已經發生的一切的補償;在啟蒙中,情況也依然如此:事實變得形同虛設,或者好象根本沒有發生。”[1]9也就是說,啟蒙的精神本來的目的是要以知識代替幻想與幻象、以理性反對神話與蒙昧,并力圖使人類從無知、愚昧和野蠻的狀態中擺脫出來,成為一切身外之物(自然、社會等)的主人。然而,啟蒙在發展的過程中卻走向了反面,創造了理性的神話。隨著啟蒙運動的不斷推進,啟蒙精神越來越深地和神話交織在一起了。于是,可以說:啟蒙用以抵抗、祛除一切神秘力量的原理,就是神話本身所包含的原理,或者說啟蒙自身退化為神話。也就是說,人類在不斷運用自身的理性這個工具來追求支配外部世界、試圖獲取自由的“祛魅”啟蒙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將理性奉為了可以主宰一切的神明。從而導致了主體理性的勝利是以主題對理性和現存事物為代價的,即當人們用理性來考量一切時,人的思維也就完全受到了理性邏輯的擺布,這樣,“啟蒙就是徹底而又神秘的恐懼”[1]13。可見。這跟神話中的人受制于各種神秘事物本質上講是一致的,不同只在于兩者的表現形式罷了。
二、啟蒙辨證的邏輯后果
在分析啟蒙內在的辨證邏輯發展的同時,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也對啟蒙所帶來的一系列可怕的后果作了精當的分析和批判。綜觀《啟蒙辯證法》一書,可以看出,對啟蒙所帶來的種種現代性危機,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不同的角度來把握:
1.哲學角度。啟蒙思想的實質,是對作為“支配”和“統治”的“主人精神”推崇和無限制拔高。這種精神在哲學領域里主要表現為一切唯理性馬首是瞻,理性在把握和統治世界的過程中,將整個世界絕對地和自身對立起來,從而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自然與人類、物質與精神、肉體與靈魂的二元對立。同時在理性不斷試圖用自己的標準去把握和統攝一切外部世界時,同一性的形而上學恐怖也將不可避免地時有上演。正如“啟蒙對待萬物,就象獨裁者對待人”[1]7一樣,整個世界都成為了理性的奴隸。
2.宗教學角度。如果我們可以將宗教理解為人類精神最后的避難所(人生終極意義的生產地、生命最高價值的寓所)的話,那么啟蒙最可怕的后果就是將這個避難所徹底地粉碎。啟蒙在反對“神義論”,不斷張揚“人義論”的時候,也將“神義論”中所蘊涵的價值之維一起拋棄。在追求知識“祛魅”之時,將知識(科學)這個“工具”抬高到了“目的”的地位,這直接導致了人類價值維度的缺失,這時西方的“虛無主義”時代就不約而至了。正如尼采所說“虛無主義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最高價值的自行貶值。沒有目的,沒有對于目的的回答。”[3]280的一樣,當人的“工具(手段)”和“目的”顛倒過來時,意義世界便蕩然無存了。即啟蒙“在通往現代科學的道路上,人們放棄了任何對意義的探求。”[1]3
3.社學會角度。啟蒙在推崇工具理性、發展自然科學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對社會領域產生了重大甚至決定性的影響。一切運用于自然科學領域的規則:強調量化、整齊劃一、同一性、整體性等等都被社會的管理者理所當然地運用到社會的治理上面來。這樣,社會中的人徹底地就成了社會總體的奴隸,同時“隨著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步地增長,制度支配人的權力也在同步增長。”[1]36這種情況在以資本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里體現得更加淋漓盡致。在工業發達的西方國家里,“廣大群眾被馴養成一支失業大軍。在廣大群眾的眼中,他們已經被徹底貶低為管理的對象,預先塑造了包括語言和感覺在內的現代生活的每一個部門,對于廣大群眾而言,這是一種必然性。對于這種客觀必然性,他們除了相信之外無能為力。這種作為權力與無力相對應的悲慘境地,連同要永遠消除一切苦難的力量一起得到了無限的擴大和增長。每個人都無法看清在他面前林林總總的集團和機構,在這些集團和機構內,從最高的經濟指揮階層到最低的職業行當都各自維護著各種既存地位。”[1]35由此,在強大的經濟機構面前,人的主體性徹底地化為烏有。
4.政治學角度。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指出,啟蒙世界里,在人們對工具理性(其本質是技術)抬高到無與倫比的位置這一帶有“極權主義”性質的“造神”運動過程中,為別有用心的獨裁者統治、壓迫甚至殺戮大眾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合理化”借口。這“合理化(理性化)”的掩飾下,極權者便可以為所欲為了,“他(即領袖——筆者注)在現實生活中體現出來的正是他禁止他人所做的一切。”[1]207而更為可怕的是,這種極權性質的統治是與人類啟蒙的程度同步發展的,而不是相反。按照這樣的邏輯,人類在20世紀所遭受的災難就是一種必然了。正如鮑曼所言:“正是人類不斷增長的力量,以及人們不受限制地決定把這種力量應用于人為設計的秩序這兩者之間的結合,才使得人類的殘酷打上了獨特的現代印記,而使得古拉格、奧斯維辛和廣島事件成為可能,甚或不可避免地會發生。”[4]283同樣,納粹德國正是在一種特殊的歷史境遇下,利用啟蒙所推崇的“純粹”、“絕對”等宏大概念來制造極權制度和推行其意識形態罷了,反猶主義、大屠殺只不過是這些宏大概念所表現出來的冰山一角而已。
綜上所述,通過對啟蒙內在邏輯的分析和考究,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對近代以來一路高奏凱歌的啟蒙精神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并從不同的角度對在啟蒙精神推動下成型的現代社會的種種弊病之本質和現象進行了釜底抽薪般的鞭撻和針砭,從而實現了對啟蒙精神的嚴肅、深入的重新審視。也許他們對啟蒙的批判在某些方面有過激之處,但是作為一種“社會批判理論”,它們是深刻、真誠、中肯而又可貴的。其為陶醉在啟蒙勝利氣氛中的現代世界敲響了警鐘,為對工具理性過分張揚的現代世界重建價值、人文理性、克服片面工具理性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參考文獻:
[1]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啟蒙辯證法[M].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3]尼采·權力意志[M].張念東,凌素心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4]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M].楊渝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
(責任編輯/石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