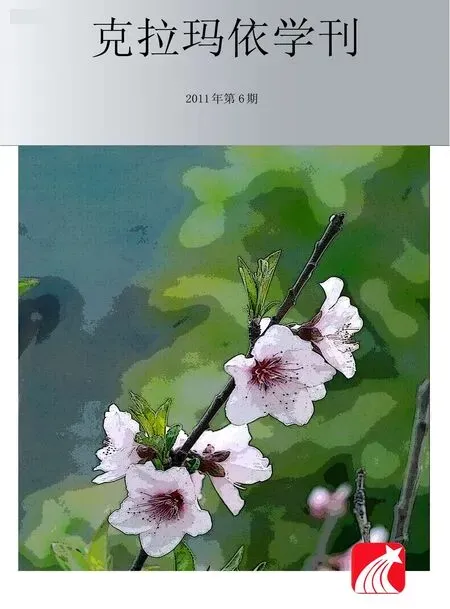論保險利益原則的適用范圍*——人身保險領域不適用保險利益原則
劉靜波
(新疆大學法學院,新疆烏魯木齊830046)
我國傳統保險法理論認為,保險利益原則是保險合同法的基本原則,保險合同均須有保險利益存在。否則,保險合同即歸于無效或失去效力。[1](P.31)
財產保險利益為世界各國保險立法和學說所公認,而對人身保險利益卻存在爭議,兩大法系中,英美法系國家多堅持保險利益原則,而大陸法系國家多不采用保險利益原則而采用同意主義。我國1995年6月30日《保險法》的頒布及2002年10月28日《保險法》的修訂,均將保險利益的相關規定置于保險合同的通則部分,①表明立法采用英美法系的保險利益原則。目前學界存在對立意見,臺灣的江朝國教授和大陸多數保險法學者主張人身保險領域仍應適用保險利益原則,而認為應當在人身保險領域采用同意主義的學者屬于少數派。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對《保險法》進行了修訂,最新修訂的保險法仍堅持保險利益原則適用于所有保險合同 ,②表明問題仍然存在。筆者認為人身保險領域堅持保險利益原則弊大于利,應該以同意主義替代保險利益原則。
一、人身保險領域不應適用保險利益原則
根據《保險法》第12條:人身保險是以人的壽命和身體為保險標的的保險。其實質是以被保險人本身作為保險事故發生對象的保險。人身保險合同與財產保險合同之分類是我國保險合同法之基本立法體例。根據傳統保險法理論,保險利益原則具有避免賭博、防范道德風險、限制賠償額度等功能。由于人身保險多為定額給付保險,原則上不可能發生不當得利,因此人身保險利益也就不存在限制賠償額度以防止不當得利的功能。但基于人本身的尊嚴和價值,以人本身作為保險事故發生對象的人身保險當然比財產保險更有必要避免賭博和防范道德風險。筆者認為,在人身保險領域堅持保險利益原則存在諸多弊端,具體理由如下:
(一)人身保險利益的主體分析
保險利益是法律對保險合同投保方③的要求。問題是,為實現保險利益原則的規范功能,保險法應當要求投保人、被保險人還是受益人具有保險利益。
1.要求投保人應當具有保險利益分析。我國最新修訂《保險法》第十二條規定,人身保險的投保人在保險合同訂立時,對被保險人應當具有保險利益。然而問題在于:其一投保人不是當然的受益人,并不當然享有保險金請求權④。在投保人不是受益人的情況下,其不具有以人身保險合同作為賭博方式和從事道德風險活動的動力,法律要求“投保人應具有保險利益”也就不能實現防止賭博和道德風險的功能;其二,保險利益原則適用于人身保險的結果是,對被保險人具有保險利益的特定投保人的不經被保險人同意而以其生命、身體投保,這反倒充滿了道德風險,美國有些州和我國立法不得已而采用雙重標準⑤即為保險利益原則不足以防范道德風險的明證;其三,這一規定限制了投保人的范圍,導致在人身保險領域難以適用無因管理和贈與,從而限制了人類相互救助精神的發揚,更不利于保險業的發展。可見,若法律要求投保人對被保險人應當具有保險利益,則不但不足以除弊,反而有礙興利,實不可取。
2.要求被保險人應當具有保險利益分析。我國臺灣地區保險法專家江朝國先生認為,“人身保險之保險利益系指被保險人對關系連接對象——自己的生命、身體、健康、醫療費用等——所產生的利益關系”。[2](P.26)然而這種認識是沒有意義的,它只是對社會生活事實樣態的客觀表述,而不具有規范功能。人們固然是根據對社會生活的邏輯認識來制定法律規范,但是生活事實不等于法律規范,法律規范是人們意識過程中的思想抽象,是邏輯的、觀念的和理性的,其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對人的有用性,即其唯一價值在于其具有規范功能。倘若法律要求“被保險人對自己的生命、身體、健康應具有保險利益”,這是沒有實質意義的大實話,因其不具有任何規范功能。有意義的倒是投保人以他人的生命、身體、健康投保時的合法性問題,這才是所謂保險利益原則所要解決的問題。正因如此,“美國在長期的保險法律實踐中形成了一個普遍承認的原則:投保人以自己的生命投保時不適用保險利益原則,即保險利益原則僅適用于以他人之生命投保的生命保險契約”。[3](P.41)
3.要求受益人應當具有保險利益分析。根據《保險法》第18條,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險合同中由被保險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險金請求權的人,因此,受益人具有以人身保險合同作為賭博方式和從事道德風險活動的動力。但人壽保險的保險單具有轉讓性,若以保險利益限制受益人的范圍,勢必使得保險單只能在對被保險人具有保險利益的特定人之間進行轉讓,這種對保險單轉讓的限制顯然不合理,因為人壽保險單不僅是保險合同的書面憑證,它還是“由投保人投資所產生的財產(property)。”[4](P.29)。為了保障保險單的可轉讓性而把“被保險人同意轉讓”擬制為“受讓人具有保險利益”,這實屬迫不得已,難以自圓其說,因為保險利益是客觀存在的一種利益關系,不能由“同意”來創造。其實,放棄復雜的人身保險利益概念,直接規定“由被保險人指定和變更受益人”,并且“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才能轉讓或者質押保險單”,即可有效防范受益人賭博和道德風險。綜上所述,無論法律規定投保人、被保險人還是受益人應當具有保險利益,都不足以實現保險利益原則所應有的規范功能,這說明在人身保險領域適用保險利益原則缺乏充分的理由。
(二)人身保險利益的規范方式和認定標準的分析
在英美法系國家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中,總體而言,人身保險利益的規范方式是采用法定主義的方式,即通過立法與判例明確規定,只有與被保險人具有法定關系的人方具有保險利益,才能作為合格的投保人。這種法定關系包括兩大類:
1.人身上的法定經濟利益關系:主要包括債務人對自己的身體所享有的以其債權人為受益人的保證保險利益,債權人對債務人的人身享有的信用保險利益,作為自然人的雇主和雇員相互對對方人身享有的利益。[3](P.216-219)這種法定經濟利益關系的客體是被保險人的人身,其利益性質均為具體的經濟利益,反映了英美法系對保險利益的本質認識:“保險利益必須是金錢上的利益,而不能僅是一種精神上的利益”。[5](P.39)
2.法定人身關系:一般包括本人與其配偶、子女、父母之間的關系。[6](P.221)其對被保險人所享有的利益為抽象的精神利益,屬于例外承認的保險利益。在英國,法定人身關系的范圍相對狹窄,除了夫妻之間互享保險利益而無須舉證外,其他情況下的投保人必須證明自己對被保險人的生存具有現實的金錢上的利益,才能構成保險利益。[7](P.39-40)
筆者認為,英美法系對人身保險利益所采用法定主義的規范方式不足以為我國效仿。
其一,法律明確列舉的范圍很難恰到好處,從而存在過寬或者過窄的問題。比如,英國法中狹隘的保險利益范圍經常導致法官在司法實踐中認定父母與子女相互之間不具有保險利益,從而一直受到批評。[8](P.89-90)
其二,僵化的法定關系標準并不能有效防范賭博和道德風險。比如,依據信用保險利益和保證保險利益,債權人能夠成為以債務人人身為保險對象的保險合同受益人,則在合同成立后,若債務人長期無力償還債務,久而久之,債權人難免產生“與其等待其還債,不如想辦法取得保險金”的念頭,很容易產生針對債務人人身的道德風險。正因如此,“現在美國部分州的法院以及立法,給予了被保險人同意權,明確要求有保險利益的投保人在投保他人之生命保險時必須征得被保險人本人同意,未經被保險人本人同意的,保險契約無效”。[9](P.42)也正因如此,基于人身上的法定經濟利益關系的人身保險在我國過去的保險實踐中均不存在,其理由固然可能是基于“人身保險即保護人身關系的保險”的狹隘認識,這些險種本身的不道德性可能也是重要原因。
其三,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確定保險利益存在時間的困惑,到底應當要求訂約時還是保險事故發生時具有保險利益?人際關系是可變的,尤其在社會變革和動蕩時期,手足成仇、夫妻反目者并不罕見。把應當具有法定保險利益的時間限制在“保險合同訂立時”能否完成防范道德風險的功能?對保險利益的存在時間若不加以限制則對保單持有人顯失公平,限制了又不足以防范道德風險,這反映了保險利益原則在人身保險領域適用的尷尬。
其四,在理論上存在構建統一的保險利益概念和理論的困難。在英國之所以出現債權人對債務人具有保險利益而父母對其子女不具有保險利益的怪現象,就是因為英國對保險利益概念持統一的經濟利益說,認為人身保險利益也是金錢利益。
總之,在人身保險領域適用保險利益原則,不僅不足以防范賭博和道德風險,而且給理論和實踐帶來諸多難以解釋的問題。
二、以被保險人同意規則替代保險利益原則的可行性
與財產保險合同一樣,人身保險合同也存在賭博和道德風險問題,而且以人身為對象的賭博和道德風險更為社會一般秩序和社會公德所不容。但這并不意味著在人身保險領域一定要采用保險利益概念。如上所述,在人身保險領域貫徹保險利益原則存在諸多弊端,這使得我們不得不考慮替代辦法,即以被保險人同意主義替代保險利益原則。
(一)“被保險人同意”在保險法上的地位分析
由于英美等國的傳統保險法奉行保險利益原則,有保險利益,合同即有效,所以“被保險人同意”在英美傳統保險法上不具有重要性。“被保險人同意”在當今各國保險法中的地位存在三種不同的立法例:
1.同意導致合同有效。以大陸法系的德國、法國、瑞士、日本保險法為典型。德國《保險契約法》第159條第2款規定:以他人之死亡事故訂立之保險且約定之金額超過一般喪葬費用者,須經他人之書面同意始能生效。第179條第3款規定:以他人所受之傷害為投保人自己之利益訂立保險合同者,須得該他人書面同意始能生效。[10](P.58)
2.同意即有保險利益,合同有效。以我國《保險法》第31條的規定為典型。“投保人對下列人員具有保險利益:(一)本人;(二)配偶、子女、父母;(三)前項以外與投保人有撫養、贍養或者扶養關系的家庭其他成員、近親屬;(四)與投保人有勞動關系的勞動者。除前款規定外,被保險人同意投保人為其訂立合同的,視為投保人對被保險人具有保險利益。”
3.同意且有保險利益,合同才有效。美國部分州采此種立法例。《紐約州保險法》第146條第3項明確規定,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保險合同,須“保險利益與被保險人同意同時具備始生效力”。[11](P.93)我國《保險法》在第 31 條明確要求保險利益后,第34條第1款規定,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未經被保險人同意并認可保險金額的,合同無效。可見,我國保險法對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采用雙重要求,同意且有保險利益,合同才有效。
筆者以為,以上三種立法例中第二種立法例把同意擬制為具有保險利益,這有欠妥當。其一,保險利益是客觀存在的一種利益關系,不能由“同意與否”來創造或消滅它。其二,同意的原因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非法的原因顯然與保險利益的宗旨不協調。[12](P.28-29)第三種立法例采用雙重要求,似無必要。依據我國《保險法》31、34條,被保險人同意投保人為其訂立合同的,視為投保人對被保險人具有保險利益;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必須經被保險人同意。這意味著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保險合同實質上只需要被保險人同意。先要求具有保險利益(可以通過“同意”擬制),再要求“同意”,疊床架屋,實無必要。正因如此,美國有些州已經放棄了把保險利益當作保險契約絕對要件的立場,弗吉利亞州實質上已經改采同意規則,投保人即使對被保險人的生命不具有保險利益,但只要征得被保險人本人的同意,并且由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同樣可以就該被保險人的生命投保。[3](P.42)實質上,我國《保險法》和美國部分州采用所謂雙重要求的法律適用結果同大陸法系的同意規則是一致的,即以他人的死亡或受到傷害為保險事故的發生所訂立的保險合同,須經他人的書面同意始能生效。
(二)同意主義的功能分析
綜觀大陸法系保險法制,其同意主義的核心內容包括:訂立以他人之死亡或傷害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應當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并認可保險金額;受益人應由被保險人指定或經其同意。英美法系保險利益原則與大陸法系同意主義的本質區別在于以法定(即強制)手段還是自治手段調控保險合同效力的問題。筆者認為,以同意主義替代保險利益原則具有合理性:
1.能夠完成私法防止賭博和防范道德風險的任務。
在人身保險合同中,法律對合同關系合法性的調整包括兩個層次:先通過適用同意規則對合同的訂立進行程序控制,“訂立保險合同應當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并認可保險金額,受益人由被保險人指定或者經其同意”,從而積極防范道德風險于事前;再通過受益權喪失、道德危險拒賠、自殺條款等進行結果控制,消極防范道德風險于事后。這樣既靈活機動地完成了私法在較低程度上防止賭博和防范道德風險的任務,也較好地兼顧了個體自由與公共秩序,讓個人的自由意志保有了最大的伸展空間。因為每個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看護人,通過個體自治的“同意”方式實現對公序良俗的維護,既充分尊重和保護了被保險人的人格尊嚴,又“具有確定性、靈活性和可操作性”,[14](P.72)避免了適用保險利益原則的復雜和混亂。
2.能夠避免因適用保險利益原則而產生的問題。
若保險法規定“人身保險的受益人應由被保險人指定或者經其同意”,“訂立保險合同應當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并認可保險金額”,則這樣標準明確的立法,既便于保險實踐和司法實踐操作,又簡化了保險利益的理論,能夠避免不必要的理論紛爭;既能適度地防范道德風險,又為拓展保險業務范圍留有充分的余地,這是最明智之舉。至于同意主義存在的不能完全禁止賭博和道德風險的問題,筆者認為,保險法作為私法,其規范性質是裁判規范,它的根本任務是給法官裁判保險合同糾紛提供裁判依據,而不必積極督促和強制保險方、投保方增進公共利益。因此,保險法根本就不應當負擔積極禁止賭博和防范道德風險的“公益性”任務,實際上它也無法完成這一任務。英國法官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點:“每個案件中要求有可投保利益的理由都是相同的,即避免賭博,并在較低程度上清除造成被保險損失的誘因”;人壽保險要求保險利益的目的“不是除去每個特定保險合同中的投機性,而是限制公眾以他人的生命為對象從事買賣保險單的投機生意”;[15](P.80)“道德風險主要是刑事法問題”。[16](P.102)而且,不僅同意主義,就是保險利益原則也同樣不可能從根本上防范賭博和道德風險。要從根本上防范賭博和道德風險,主要得仰仗公法對違法和犯罪行為的及時懲處以及社會公眾道德水平的提高。在這方面,以理性經濟人假設為前提、不具有懲罰功能的私法規范實在不如具有強大威懾力的刑法規范和道德規范有效果。法律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因此,法律對社會生活的調整手段應當盡可能妥當,盡可能既除弊又興利,不能動輒因噎廢食,甚至導致弊大于利。每個部門法、單行法乃至法條都具有其特定的功能和使命,他們有機協作,共同調整社會生活。不恰當地賦予一個法律過多、過重的使命和任務,這未必是好事情。把賭博和道德風險的防范完全系于保險合同的效力,這實在是保險合同法不能承受之重。合同法的基本任務是保護合同當事人的信賴利益和履行利益,而沒有積極促進公共利益的任務,即使有,也只是通過保障合同當事人的利益來間接促進公共利益的。
三、對《保險法》相關條文的修訂建議
基于以上研究所得,筆者試擬《保險法》相關條文的解釋和修訂意見如下,作為本文的結論,并供學界探討和立法修訂之參考:
第12條第1款“人身保險的投保人在保險合同訂立時,對被保險人應當具有保險利益”為倡導性規范,而非效力性強制性規范,即不能據此判定保險合同的效力。
第31條⑥是對人身保險合同中保險利益的規定,為避免保險利益法定主義的僵化,以有效防范賭博和道德風險,并對被保險人的身體健康權和生命權予以同等程度的尊重,建議將第31條和第34條⑦合并規定為:
投保人訂立以他人死亡或傷害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且認可保險金額,保險合同不生效;非由被保險人指定和變更受益人,受益人對保險人無保險金請求權。
按照以死亡或傷害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所簽發的保險單的轉讓或質押,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產生保險單轉讓或質押的法律效力。
對本條第一款的書面同意,被保險人有權隨時撤銷。
注釋:
①我國1995年《保險法》第11條、2002年修訂之第12條。
②2009年最新修訂之《保險法》第12條、第31條。
③投保方指與保險人相對應的投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一方。
④根據《保險法》第39條規定,人身保險的受益人由被保險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時須經被保險人同意。
⑤即投保人即使對被保險人具有保險利益,仍需要征得被保險人同意才能投保生命保險。
⑥《保險法》31條規定,“投保人對下列人員具有保險利益:(一)本人;(二)配偶、子女、父母;(三)前項以外與投保人有撫養、贍養或者扶養關系的家庭其他成員、近親屬;(四)與投保人有勞動關系的勞動者。除前款規定外,被保險人同意投保人為其訂立合同的,視為投保人對被保險人具有保險利益。訂立合同時,投保人對被保險人不具有保險利益的,合同無效”。
⑦《保險法》34條規定,“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未經被保險人同意并認可保險金額的,合同無效。按照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所簽發的保險單,未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轉讓或者質押。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險,不受本條第一款規定限制”。
[1]溫世揚.保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2]江朝國.保險利益之研究[M].保險法評論(第一卷),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
[3][5][6][7][9][13]王萍.保險利益研究[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
[4][12]曾東紅.我國保險利益制度的法理分析[J].政治與法律,1998,(3).
[8][15][16][英]Malcolm A.Clarke,何美歡、吳志攀譯.保險合同法(第3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10]楊芳.可保利益效力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11]樊啟榮.死亡給付保險之被保險人的同意權研究[J].法學,2007,(2).
[14]張秀全.人身保險利益質疑[J].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6).
——與林剛先生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