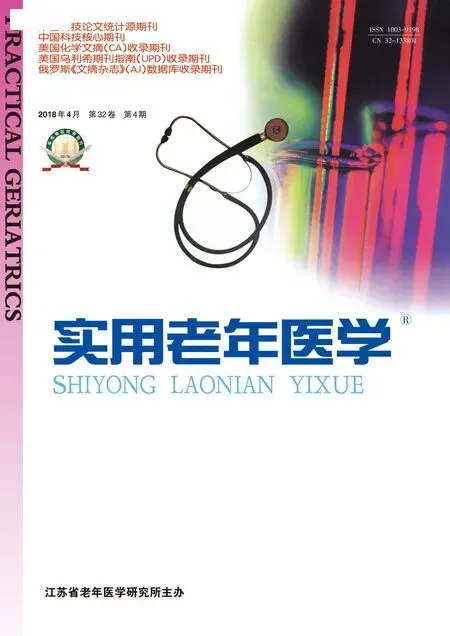實用老年醫學
臨床研究
- 血清miR-27b在老年左心室肥厚病人中的表達及診斷意義
- 老年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與老年性癡呆的相關性分析
- 卡培他濱節拍化療在老年轉移性乳腺癌維持治療中的臨床療效
- 盆底重建術治療老年婦女子宮脫垂的療效及對病人生活質量的影響
- 七氟醚復合麻醉對老年關節置換病人術后氧代謝及認知功能的影響
- 老年人膳食多樣化與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癥的關系
- 目標劑量螺內酯聯合曲美他嗪對老年慢性心力衰竭病人心功能和炎癥因子的影響
- 通心絡膠囊聯合曲美他嗪治療老年心肌缺血的臨床研究
- 老年橈骨遠端骨折病人應用萬向掌側接骨板治療的療效及對生活質量的影響
- 百泌達對老年2型糖尿病病人的降糖效果研究
- 應用無創心排量監測指導老年膿毒癥休克病人早期液體復蘇的臨床研究
- 不同劑量右美托咪定對老年腹腔鏡膽囊切除術病人圍術期血流動力學及心功能的影響
- 血脂水平與老年原發性腦出血的相關性
- 老年血液腫瘤病人住院營養狀態研究
- 老年病人呼吸機相關肺炎發生情況與危險因素調查
- 腦梗死急性期病人并發多臟器功能障礙綜合征的影響因素及臨床轉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