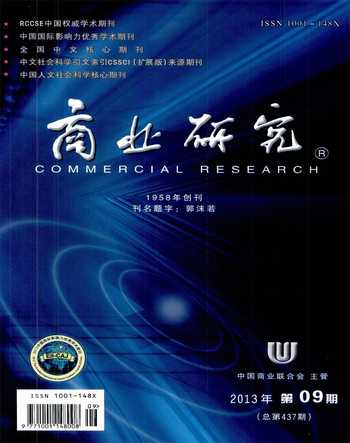機構投資者、信息披露質量與公司績效
彭丁 楊長虹
摘要:本文以深交所信息披露考評結果作為信息披露質量的替代變量,從信息披露的視角考察了機構投資者在我國上市公司的持股行為和治理效應,研究發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對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決策具有正向影響,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在信息披露質量較好的公司顯著高于信息披露較差的公司,隨著信息披露質量改善,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增加;機構投資者的治理作用因信息披露質量存在顯著差異,隨著信息披露質量提高,機構投資者對公司業績的改善逐漸凸顯出來,而在信息披露質量很差的公司其治理作用受到限制。換言之,機構投資者的治理作用受制于公司信息環境的影響,改善公司信息披露質量對促進機構投資者發揮其應有作用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關鍵詞:機構投資者;信息披露質量;公司治理
中圖分類號:F83091;F2766 文獻標識碼:A
作者簡介:彭丁(1984-),男,成都人,西華大學管理學院教師,管理學博士,研究方向:資本市場財務與會計;楊長虹(1980-),女,成都人,西南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業管理。
基金項目:西華大學校重點科研基金項目“我國上市公司機構投資者治理行為影響因素及經濟后果研究”,項目編號:ZW1221505。 一、問題的提出
自我國證券市場成立以來,機構投資者在國家政策培育下逐漸成為資本市場的新興力量。從1997年《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的推出、1998年南方基金管理公司和國泰基金管理公司的成立,到2002年QFII制度實施、2003年社保基金入市,直至2004年《證券投資基金法》等一系列相關制度措施的頒布與實施,機構投資者在經歷了早期探索、試點發展和快速發展三個階段后逐步形成了具有相當規模的專業投資者。截止到2010年末,包括證券投資基金、全國社保基金、保險公司、證券公司、QFII等各類機構投資者持有的已上市流通A股股票市值達到了70%以上①,成為資本市場的重要投資主體。
作為新興的治理機制,機構投資者能否依靠自身的專業能力、資源優勢通過對上市公司的持股參與公司治理,提升上市公司治理績效?在上市公司國家控股、股權高度集中的制度背景下,相對于董事會、薪酬激勵等內部治理機制,機構投資者的相對獨立性能否使得其在外部治理機制中發揮更為積極的股東作用?圍繞這些因素,一些文獻立足于機構投資者本身進行了探討,但由于我國機構投資者的發展時間不長,這方面的文獻較少且沒有得出較為統一的結論。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作為解決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信息不對稱的有效途徑,歷來受到我國監管部門的高度重視;同時,提高上市公司會計信息質量也是我國政策制定者致力解決的難題。機構投資者雖為專業的投資者,比普通投資者具有更強的信息獲取能力,但作為外部股東,加之內部人控制問題,機構投資者同樣會為獲取私有信息付出高昂的成本,而這些軟約束可能間接地抑制機構投資者對公司治理的參與程度。因此,上市公司不同的信息披露質量可能導致機構投資者的治理作用產生差異,那么,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決策是否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而不同?會計信息披露這一制度安排是否會對機構投資者的治理效應產生影響?所以本文擬從會計信息的視角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二、理論分析及研究假設
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是資本市場監管的重要目標,作為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制度安排,其目的不僅在于提高公司的透明度,也為治理機制各方通過較好的信息質量提高對公司資源配置的效率。
作為外部股東,一方面,會計信息質量高低成為機構投資者持股決策的重要信息標準,機構投資者通過信息質量決定持股計劃以降低股價異常波動帶來的交易成本(Healy 等,1999),較好的會計信息披露將提高機構投資者在二級市場交易的流動性(Diamond和Verrecchia,1991);另一方面,機構投資者在公司治理機制中的有效程度也取決于會計信息質量,機構根據信息質量改變對公司權益金額的持有數量及時間長短(Bushman,2001)。Bushee和Noe(2000)以AIMR指數評級作為信息質量因素,研究發現更及時的會計信息披露有著更高的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不同類型的機構投資者對信息質量的敏感程度及披露要求存在顯著差異,激進型、指數型機構投資者更加重視信息質量,而長期機構投資者則會較少倚賴會計信息。程書強(2006)的研究表明盈余及時性與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正相關。在我國機構投資起步較晚的背景下,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會依靠信息披露作為重要的標準。換言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的差異會對機構的持股行為造成影響。為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2013/09假設1: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而存在顯著差異,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隨著信息披露質量的提高而增加。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機構投資者在公司治理中是否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已有的國外文獻形成了兩種競爭性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機構投資者通過對公司研發投資的監督、薪酬管制及提高自愿信息披露能有效地改善公司治理狀況(EI-Gazzar,1998;Hartzell and starks,2003;Bushee,1998);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機構投資者也是短視的投資者(Myopic Investors),其持股行為的短期化和與公司之間的利益糾纏并不能改善公司治理狀況(David,1998;Smith,1996)。機構投資者作為公司治理機制,重要的一面在于機構的相對獨立性,其對公司治理效率取決于機構的投資遠見、信息獲取能力及對公司治理的參與程度(Bushee和Noe, 2000)。
關于我國特殊的制度環境是否會對機構投資者的治理效應產生影響,薄仙慧和吳聯生(2009)的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的治理作用在國有和非國有公司中存在顯著差異,隨著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增加,非國有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顯著降低,而這一治理作用在國有公司中受到限制。張純和呂偉(2007)檢驗了機構投資者持股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融資約束和融資能力的影響,結果表明機構投資者的參與能顯著降低民營企業所面臨的融資約束,但機構投資者并不能降低國有企業的融資約束問題。翁洪波和吳世農(2007)以“自由現金流”假說和“利益輸送”假說為依據,驗證機構投資者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響,發現機構投資者不會通過影響公司的股利政策而降低代理成本,但機構投資者能抑制公司的“惡意派現”行為。李維安和李濱(2008)發現,機構投資者在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范海峰等(2009)以社保基金和證券投資基金為對象,發現機構投資者的異質性對提升公司價值產生了不同的效應。
綜合國內外現有文獻,機構投資者在公司治理中已經發揮了“用手投票”的監督作用,但不同的公司治理狀況也會對機構在治理中的參與程度產生影響。在我國股權高度集中的制度背景下,公司內部人及控股股東往往具有信息優勢,而作為外部股東,機構投資者會因獲取更多的決策信息付出較高成本。信息披露作為解決機構投資者與公司之間信息不對稱的有效機制,會對機構投資者的治理作用產生積極影響。收益與成本的權衡是機構投資者能否發揮治理意愿的重要因素,相對于信息披露質量不佳的公司,高質量的信息披露更能降低機構投資者與公司之間的代理成本與利益沖突,其更有動力發揮積極的股東行為。為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2:同等條件下,相對于信息披露質量較差的公司,機構投資者在信息披露質量較好的公司中的治理作用更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業績。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主要考察信息披露質量是否會對機構投資者持股決策及治理作用產生影響,所以異于上市公司本身的第三方考評更能客觀體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按照深交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辦法》中規定的及時性、準確性、完整性及合法性標準,本文選取2005至2008年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公司為樣本,并對數據做了以下處理:(1)剔除任一變量缺失的上市公司;(2)剔除金融行業的上市公司;(3)將資產負債率(LEV)大于1的公司作為異常值予以剔除,最后得到2 099個觀測樣本。為了控制極端值的影響,本文對可能存在極端值的連續變量在1%的水平上進行了winsorize處理②。除了信息披露考核從深交所搜集外,其余數據全部來自國泰安研究服務中心的CSMAR數據庫。本文所有的數據處理與分析采用Stata100軟件,為了保證數據的可靠性,本文對數據進行了隨機核對。
(二)變量設計
1.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的衡量。深交所的信息評級是比較權威的第三方考評,能夠較客觀地反映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質量。本文根據深交所的考評結果,依次將“優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賦值為4、3、2、1,用有序變量DISC表示,分值越高表明信息披露質量越好,同時采用虛擬變量DISC_Dum衡量兩類信息披露質量不同的公司。若考評結果是“優秀”和“良好”的公司,賦值為1,并將其定義為信息披露質量較好的公司;而“合格”與“不合格”的公司則取值為0,將其定義為信息披露質量較差的公司。
2.機構投資者。本文用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中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之和(INST)和機構投資者是否持股的虛擬變量(INST_Dum)衡量機構持股決策的變量③。根據中登公司結算統計報告,證券投資基金、社保基金、證券公司、保險公司、QFII和其它法人機構都作為機構投資者。但由于其它機構投資者沒有統一標準且持股數量非常有限,所以本文不將其納入研究對象。
3.公司績效的衡量。公司績效的衡量主要基于會計績效(ROA)和市場績效(Tobins Q)兩方面。Ferreira和Matos(2008)指出,Tobins Q并不是一個測度公司市場價值的有效指標,加之我國資本市場有效程度較低及非流通股、限制流通股長期存在,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存在很大誤差,Tobins Q并不能真正體現公司市場價值。基于此,本文采用會計績效(ROA)指標。
4.其它需要說明的控制變量。假設1是檢驗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是否會受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除此之外,公司特征也是機構主要考慮因素。Bushee和Noe(2000)的研究發現,資產負債率(LEV)、成長性(GROW)會影響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公司規模(SIZE)、總資產凈利率(ROA)和分析師盈利預測(ANAL)也會對機構持股造成影響(Ferreira和Matos, 2008)。考慮到上市公司國家控股和股權分置的問題,本文還控制了股權性質(STATE)和流通股比例(SHARE)。假設2是考察機構投資者對公司業績的影響(ROA)是否受制于公司信息披露質量,根據以往的研究(Ferreira和Matos, 2008;李維安和李濱,2007),公司規模(SIZE)、公司成長性(GROW)、資產負債率(LEV)、行業(IND)及年份(YEAR)都有可能成為影響公司業績的因素,為保證結論的可靠性,本文對這些變量加以控制。同樣的,在此檢驗中控制了股權性質(STATE)和流通股比例(SHARE)可能造成的影響。各變量的符號表示和詳細定義如表1所示。
(三)模型構建及解釋
根據前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設和對相關變量的定義,本文構建以下三個模型,其中模型1、模型2用來檢驗假設1,模型3用來檢驗假設2。模型3中INST的系數β1表示在信息披露質量較差的公司機構投資者持股對公司績效的影響,交互項INST×DISC_Dum的系數β2表示相對于信息披露較差的公司,機構投資者在信息披露質量較好公司中的持股比例對公司業績影響的差異。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及分析
從表2Panel A的基本描述性統計可以看出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NST)的平均值為3%,這個比例遠遠低于美國上市公司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均值的657%(Ferreira和Matos, 2008),表明雖然我國近十年來機構投資者發展迅猛,但總體規模仍然偏小。同時,INST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0和029,顯示機構投資者持股決策出現了明顯的分化。根據深交所的誠信檔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DISC)的均值和中位數分別為2733和3,這客觀地說明上市公司總體信息披露質量達到較高水平。總資產凈利率(ROA)的平均值為0027;財務杠桿(LEV)的均值為05,說明中國上市公司的融資比例仍遵循西方的最優資本結構范圍;此外,樣本公司規模(SIZE)的平均值為2127,國家控股(STATE)達到了57%,表明國有企業在我國上市公司仍占據很大比例;而流通股比例(SHARE)的平均值和中位數分別為0529和0513,表明截止到2008年末仍有50%左右的限受股還沒有流通解禁;上市公司營業收入增長(GROW)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出現顯著差異,分別為-073及3315;分析師對上市公司盈利預測(ANAL)的平均值為8162。
Panel B對兩類公司當中機構投資者持股決策的差異性進行了比較。檢驗結果表明,在信息披露質量較好的公司,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NST)和機構是否持股的虛擬變量(INST_Dum)的平均值和中位數均顯著高于信息披露較差公司的平均值和中位數,t值和Z值都在1%水平上顯著,這初步驗證了本文的研究假設1,即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存在顯著差異。
(二)相關性分析
表3報告了各變量之間的Pearson和Spearman相關系數。INST與DISC顯著正相關,表明信息披露質量對機構投資者持股具有正效影響;在公司特征方面,INST與ROA、SIZE、SHARE、GROW顯著正相關,顯示機構投資者更加偏好盈利能力強、規模大、流動性高與成長性較好的公司;此外,分析師盈利預測次數(ANAL)也是影響機構投資者的重要因素,Pearson與Spearman相關性分別達到了0497和0671。影響公司業績的變量LEV、STATE、SHARE與ROA負相關,SIZE、GROW與ROA正相關。在本文的回歸模型中,各自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不高,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三)實證檢驗與分析
表4為驗證假設1的實證結果。在模型1a和1b中,無論是信息披露質量的有序變量(DISC)還是虛擬變量(DISC_Dum)均在1%的水平上與INST顯著正相關,t值分別為423和295,支持了本文的假設1,表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是機構投資者持股決策的重要影響因素,隨著信息披露質量的提高,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增加。在控制變量方面,總資產凈利率(ROA)、公司規模(SIZE)、分析師盈利預測次數(ANAL)與機構持股比例顯著正相關,這與Ferreira和Matos(2008)的結論相一致,顯示機構投資者偏好盈利能力強、規模較大、分析師非常關注的公司;但公司成長性(GROW)對機構持股的影響不顯著,表明機構投資者并不太關心公司盈利增長的持續性,這也說明我國機構投資者持股可能只關注公司某個會計年度的業績,而持股周期并不會太長;流通股比例(SHARE)的估計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流動性也是機構持股的考慮因素,這也符合機構持股規模較大的特點。在其它控制變量方面,股權性質(STATE)的系數在模型1a與1b中均為負,但都不顯著,表明股權性質不是機構投資者持股的考慮重點;而公司財務杠桿(LEV)在模型1a和1b中都與INST正相關,雖然LEV的系數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但可以看出我國機構投資者可能偏好于一些高負債、虧損重組的ST公司。此外,本文控制了行業(IND)、年份(YEAR)因素可能造成的影響,模型的調整可決系數說明模型的整體解釋能力較強。
模型2a和2b采用Logistic模型進行回歸,同樣的,DISC和DISC_Dum的估計系數分別在1%和5%水平上顯著為正,Z值分別為281和213,這進一步證明了信息披露質量對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具有顯著影響,同時也說明本文的結論較為穩健。其它控制變量與模型1a、1b的結果基本一致,ROA、SIZE、ANAL、SHARE與INST正相關;STATE的系數在2a中顯著性有所提高,符號為負,說明從某種程度上機構投資者更偏好非國有公司;GROW對INST的影響仍然不顯著。檢驗中唯一的變化在于財務杠桿對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的影響,LEV的系數在模型2a與2b中均在5%水平上顯著為負,而在模型1a和1b中LEV的估計系數為正,但都不顯著。Bushee和Noe(2000)也發現,資產負債率(LEV)對機構投資者的持股影響存在一定差異,而在本文的研究中,采用Logistic模型對資產負債率(LEV)的估計較OLS估計更具顯著性,表明機構投資者更加偏好財務穩健的公司。
表5報告了信息披露質量是否對機構投資者的治理效應有所影響的回歸結果。在模型3a中,本文所關注的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信息披露質量的交互項INST×DISC_Dum的估計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t值為292,支持了本文的假設2,表明公司信息披露質量的確對機構投資者的治理作用產生不同影響。同等條件下,在信息披露質量較好的公司,機構投資者對公司業績的影響比在信息披露較差的公司高出176%,這一結果在統計上非常顯著。通過對業績變化的計算,信息披露質量差異導致機構投資者對公司業績的增量影響是信息披露較差公司業績的876%⑤,這一變化也十分明顯。此外,本文對INST與INST×DISC_Dum的系數之和的線性約束進行了檢驗,系數之和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機構投資者在信息披露質量較好的公司更能提升公司業績。其它控制變量均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資產負債率(LEV)、國家控股(STATE)與公司業績負相關;公司規模(SIZE)、營業增長(GROW)與業績正相關,這些結果都與預期一致且符合經濟意義。
考慮到股改期間非流通解禁可能對公司業績產生影響,模型對流通股比例(SHARE)進行了控制,研究發現SHARE對公司業績影響為負。本文認為,股權分置之前,由于大量非流通股受制于政策約束,導致二級市場定價扭曲,非流通股東沒有話語權參與定價行為。而隨著股改的實施,基于有限理性的解禁股東通過自身標準判斷公司是否存在投資價值,對高估溢價采取退出機制;同時,我國上市公司交叉持股嚴重,大小非拋售成本低廉,造成大量非流通股在流通后進行減持,惡化了治理行為,對公司業績產生負效影響。
為了進一步考察機構投資者在不同評級公司的治理作用,模型3b將考評結果的4種評級作為衡量信息披露質量高低的標準。研究發現INST×DISC_Dum1的估計系數為負,并且在10%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在評級結果為“不合格”的公司,即在信息披露質量很差的公司機構投資者并不能改善公司績效,機構投資者的治理作用受到限制。而在考評結果為“合格”、“良好”和“優秀”的公司,機構投資者均能顯著提升公司業績,模型的估計系數非常理想,分別為0235、0351和0439,這一逐步遞增的結果說明隨著信息披露質量提高,機構投資者更能發揮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其它控制變量的結果與模型3a完全一致,故不再贅述。
注:DISC_Dum1、DISC_Dum2、DISC_Dum3、DISC_Dum4分別表示信息披露結果為“不合格”、“合格”、“良好”、“優秀”的虛擬變量,若公司信息披露結果為“不合格”,則DISC_Dum1取1,否則取0,DISC_Dum2、DISC_Dum3、DISC_Dum4賦值方法與DISC_Dum1一樣。變量INST×DISC_Dum1、INST×DISC_Dum2、INST×DISC_Dum3、INST×DISC_Dum4分別表示機構投資者在信息披露“不合格”、“合格”、“良好”、“優秀”公司持股比例對公司績效的影響。***、**、*分別表示在1%、5%、10%水平上顯著。
(四)穩健性檢驗
由于我國機構投資者的類型并不太多,而證券投資基金無論在持股比例與管理市值上都占據絕對規模,所以本文進一步用上市公司證券投資基金持股比例(FUND)作為機構投資者的替代變量,同時用凈資產收益率(ROE)衡量公司業績,對上述研究進行穩健性檢驗。穩健性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主要變量的回歸結果與前文一致,表明本文的結論是可靠的。
五、結論
本文以我國2005-2008年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以深交所誠信檔案的考評結果作為信息披露質量的替代因素,實證檢驗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對機構投資者的持股行為和治理效應的影響。研究發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對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決策具有重要影響: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在信息披露質量較好的公司顯著高于信息披露較差的公司,隨著信息披露質量改善,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增加;機構投資者的治理作用也因信息披露質量存在顯著差異,隨著信息披露質量提高,機構投資者對公司業績改善的作用逐漸凸顯出來,而在信息披露質量很差的公司其治理作用受到限制。
注:穩健性檢驗采用的方法為Robust regression,在檢驗2中沒有將FUND和DISC的單獨兩項納入模型是因為這樣會造成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分別表示在1%、5%、10%水平上顯著。
伴隨著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以管理規模的不斷擴大,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也越來越受到各方的關注。證券市場管理層寄希望機構投資者以其專業能力和資源優勢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進而提升公司治理績效。但不容忽視的是,我國機構投資者的發展時間相對于西方資本市場機構投資者上百年的發展歷程仍顯短暫,加之我國獨特的制度環境,機構投資者能否真正在公司治理中發揮積極的股東行為受制于諸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等因素的影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是公司信息環境好壞的最終體現,提高信息披露質量對于降低機構投資者監督、治理成本具有重要影響,而這些內在因素共同影響著機構投資者的治理作用。因此,對于監管方來說,加強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監管并促使公司信息環境的改善,對促進機構投資者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注釋:
① 以上數據根據2010年12月前中國證監會主席尚福林在上證法治論壇講話獲取。
② 本文對可能造成影響的連續變量資產負債率(LEV)、總資產凈利潤率(ROA)和營業收入增長(GROW)進行了winsorize處理,即對大于99%分位數和小于1%分位數的值分別按99%和1%分位數賦值。
③ 本文用機構投資者持股占流通股的比例而非總股本的比例是考慮了我國的特殊制度背景,因為在股權分制存在的背景下,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主要是基于流通股,檢驗機構投資者占流通股的比例更能真實體現其持股決策和對公司治理的作用。
④ 分析師預測(ANAL)的計算方法為當年所有分析師對某一公司盈利預測發布的次數,在本文的樣本中存在同一分析師在某一會計年度里對同一公司多次發布預測的情形,本文仍予以加總,考慮的主要因素在于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很可能會因分析師盈利預測的改變而增減,即同一分析師對公司盈利預測的修正可能更具有信息含量。
⑤ 計算過程為:模型3a中估計系數0176/0201=876%。
參考文獻:
[1] 薄仙慧,吳聯生.國有控股與機構投資者的治理效應:盈余管理視角[J].經濟研究,2009(2).
[2] 程書強.機構投資者持股與上市公司會計盈余信息關系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06(9).
[3] 范海峰,胡玉明,石水平.機構投資者異質性、公司治理與公司價值——來自中國證券市場的實證證據[J].證券市場導報,2009(10).
[4] 李維安,李濱.機構投資者介入公司治理效果的實證研究——基于CCGINK的經驗研究[J].南開管理評論,2008(1).
[5] 翁洪波,吳世農.機構投資者、公司治理與上市公司股利政策[J].中國會計評論,2007(3).
[6] 王雪榮,董威.中國上市公司機構投資者對公司績效影響的實證分析[J].中國管理科學,2009(2).
[7] 張純,呂偉.機構投資者、終極產權與融資約束[J].管理世界,2007(11).
[8] Bushee, B. J.,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on Myopic R&D Investment Behavior[J].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8,73(3):305-333.
[9] Bushee, B. J., and C. F. Noe, Corporate Disclosure Practices,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Stock Return Volatility[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0,38(supplement):171-202.
[10] Bushman, R. M., and A. J. Smith, Financi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1,32(1-3):237-333.
[11] Bushman, R. M., Q. Chen, E. Engel, and A. J. Smith, Financi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al Complexity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4,37(2):167-201.
[12] Bushman, R. M., J. D. Piotroski, and A. J. Smith, What Determines Corporate Transparency[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4,42(2):207-252.
[13] David, P., R. Kochhar, and E. Levitas, The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on the Level and Mix of CEO Compensation[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8,41(2):200-208.
[14] Diamond, D. W., and R. E. Verrecchia, Disclosure, Liquidity, and the Cost of Capital[J].Journal of Finance, 1991,46(4):1325-1359.
[15] El-Gazzar, S. M., Predisclosure Information and Institutional Ownership:A Cross-Sectional Examination of Market Revaluations during Earnings Announcement Periods[J].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8,73(1):119-129.
[16] Ferreira, M. A., and P. Matos, The Colors of Investors Money: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round the World[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8,88(3):499-533.
[17] Hartzell, J. C., and L. T. Starks,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J].Journal of Finance,2003,58(6):2351-2374.
[18] Potter, G., Accounting Earnings Announcements, Institutional Investor Concentration, and Common Stock Returns[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92,30(1):146-155.
[19] Smith, M. P., Shareholder Activism by Institutional Investors:Evidence from CalPERS[J].Journal of Finance,1996,51(1):227-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