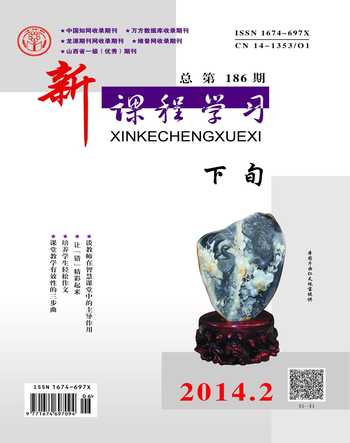讓文學回歸審美,讓語文教學重現(xiàn)生機
王嬪
摘 要:受新課改語文高考的沖擊,文學作品的教學陷入了一種審美缺失的境地,應嘗試從語言和多元解讀的角度,讓文學回歸審美,還語文課堂以生機。
關鍵詞:文學作品;語言;多元解讀;審美
當代著名語文教育家于漪在給楊斌老師的新著《發(fā)現(xiàn)語文之美》的序言中這樣寫道:“崇尚美、欣賞美,會使人變得高尚、優(yōu)美起來。教學中帶領學生學會找到美,評判美,給學生以熏陶感染,正是教師義不容辭的責任。”是的,語文是所有學科中最具審美意義和價值的學科。可是遺憾的是語文卻在現(xiàn)實中被許多一線教師迷失成了功利。自新課改以來,文學類文本閱讀被提到了高考的日程上來,新課改“重過程”的這一初衷被一點點地抹殺殆盡。特別是文學作品的教學更是堪憂,取而代之的教學方式是“生平及背景”“主題思想”“藝術特色”的點段式的教學模式,文學作品本身甚至可以不在場;抑或是把絕佳的閱讀材料當做是訓練學生如何審題、答題的載體。我想是我們被現(xiàn)實迷住了雙眼,以至于看不清語文教學應走的路。語文學科應是目的性價值超過工具性價值,“雖然也要傳授知識,也為人們提供一種生活的工具,但它更是目的本身,是情感、人格的陶冶過程。”所以,我們需要嘗試走出一條既符合課程標準,又遵循文學教育、審美教育規(guī)律的路子,讓文學回歸審美,還語文課堂以生機。
一、讓語言帶動審美
韋勒克說:“語言是文學的材料,就像石頭和銅是雕刻的材料,顏色是繪畫的材料或聲音是音樂的材料一樣。”可見,語言是文學架構的載體,但它又不等同于文學。文學是語言的藝術,透過語言的審美才是真語文。
比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這確乎是一篇寫作技法相當突出的文學作品。對于這一課的教學,相當一部分教師緊緊抓住通感等手法進行大張旗鼓的解說,最后還不忘一番盛情地拓展,學生自然也忙得不亦樂乎,可是最終的結論只有一個:朱自清寫作的高明之處在于用了很多的修辭,我也習得了一些。我無語。我們并不排斥教師對修辭的講解,只是覺得把如此美文解讀成無情的手法習得課而感到痛心。脫離了語言品讀的教學,語文課堂似一潭死水,審美頓失,更談不上什么藝術。
散文是一種書寫靈性的文學樣式,是“集諸美于一身”的文學體裁,是語言藝術文學體裁的典范。因此,教學應該緊緊把握住這一特殊體裁的固有特點,找準語言這一切入口,適時地讓學生進行文學的涵泳。《荷塘月色》總體的基調是帶著淡淡的喜悅與淡淡的憂傷的,而正因了這淡淡的憂傷,才讓這淡淡的喜悅來得如此不易,才讓作者如此醉心于月下的荷塘。文本中的一句“熱鬧是它們的,我什么也沒有”活脫脫展示了作者此時內心的彷徨和郁結,然而這種憂傷既無大起也無大落,達到了恰到好處的審美效果,反復品味其言,所有優(yōu)美的文字都因了豐富的情感而有了它存在的理由,而我們內心收獲的也就不僅僅是技法的東西,還有語言之外的情緒的激蕩,教學的高明之處,我想就是在這所謂的審美中體現(xiàn)出來的。
散文如此,其他的文學作品亦是如此。
《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在“課程目標”中明確指出:學生應在五個方面獲得發(fā)展,其中之一便是“感受、鑒賞”——閱讀優(yōu)秀作品,品味語言,感受其思想、藝術魅力,發(fā)展想象力和審美力……通過閱讀和鑒賞,陶冶情性,深化熱愛祖國語文的感情,體會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追求高尚情趣,提高道德修養(yǎng)。
二、讓多元解讀實現(xiàn)審美
新課標實施伊始,“多元解讀”曾一度被捧為新寵,但隨之而來的極端的探究造成了“課堂鬧哄哄,課后一場空”的病態(tài)局面又讓許多教師嘗試了、慌張了、撤退了。什么多元解讀,那整個就是瞎扯淡。于是乎,“多元解讀”再次被束之高閣。之后,對于文學作品思想的解讀重又回歸到“唯我獨尊”的原始階段那些內涵深沉、內容豐富的文本被衍化成千篇一律的統(tǒng)一結論。那些所謂的正統(tǒng)的、貼近高考高分可能的思想被追捧、被強化,文學作品的解讀只剩下干巴巴的軀殼,無任何的審美可談。于是,教師對教學厭倦了,學生的主體意識被壓抑了,教學的狀貌不堪入目。其實,“多元解讀”并不是胡讀、亂讀,它是有原則的。這一原則便是在忠實文本內容的基礎上進行的多元解讀,也就是“文本至上”的原則,任何脫離了文本的解讀都是無效的。畢竟,一千個讀者就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無論怎么解讀,讀出的終究是哈姆雷特而非羅密歐等。
比如,關于魯迅《祝福》的主題探究,一直以來,人們都局限于以下兩種主體歸納:①揭露“四權”(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對中國婦女的毒害。②揭露了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而人教版語文必修3教師教學用書上也沒有明確的主題說明,只是做了如是概括:小說通過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把批判的鋒芒直指造成其悲劇的社會環(huán)境和封建倫理道德。因此,這也就給了我們極大的解讀空間。但這個解讀空間必須以文本所反映的事實為依據(jù),不能信口開河。比如,有學生認為祥林嫂是作為一個人存在的,可以從人性的角度切入談主題,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學者劉心武曾坦言:“我認為《祝福》的最可貴之處,還并不在于‘反封建‘反禮教或‘控訴舊社會等層面上。《祝福》的深刻還在于表現(xiàn)了人性中的傾訴欲望,并沉痛地呼吁:人類應當懂得他人的傾訴,在相互承接傾訴中,逐步達到人類大同。”學生尚且懂得多元解讀文學作品的主題,最終達到個人解讀的目的。作為教師的我們,何不先邁開步,做好多元解讀的準備,甚至于自身亦可對一些舊說作一番深入的個性化的解讀。
清人沈德潛在《唐詩別裁·凡例》中亦有言:“古人之言包含無盡,后人讀之,隨其性情淺深高下,各有會心。”古人尚且懂得文章不求定解的道理,允許各有會心,我們今人又如何能將多元解讀置之門外,使文學作品美麗的解讀空間被封堵,從而失去了應有的審美,讓課堂失去了應有的活力。
語文學科是一門詩意的學科,在功利化日益嚴重的現(xiàn)今,我們不妨打開窗戶,親近文學經典,卸下應試的包袱,讓文學回歸審美,讓清新的教學之風輕撫我們的面龐,讓語文課堂重現(xiàn)生機。
參考文獻:
[1]袁振國.教育新理念.北京教育出版社,2007:46-51.
[2]薛世昌.魯迅小說《祝福》的主題再探.天水師范學院學報,2006(5).
(作者單位 福建莆田第二十五中學)
?誗編輯 楊兆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