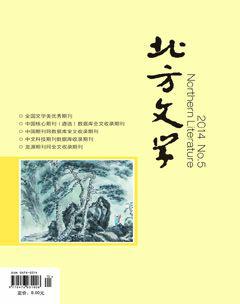生命悲劇隱喻與文化啟蒙符碼的合一
黃莉++
摘 要:蕭紅以獨有的女性關懷堅持不懈地描寫著女性世界,其筆下的女性形象蘊涵著生命悲劇隱喻和文化啟蒙符碼的雙重寓意。這些女性人物,不僅透視出蕭紅對生命悲劇的深刻體認,以及對人的生存的巨大悲憫,而且承載著批判封建傳統文化,呼喚女性的精神解放,從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的寄意。
關鍵詞:蕭紅;女性;生命悲劇;啟蒙
一
蕭紅這位充滿靈性的女作家,從步入文壇開始,就表現出了她的獨異性和邊緣性。與同時代左翼作家相比,她很少正面直接描寫戰爭和階級斗爭,而堅持不懈地描寫著女性世界。其筆下的女性,身處社會的邊緣,是一個被無視被奴役的群體,在生死場上艱難掙扎,甚至走向毀滅。蕭紅的創作富有主體意識,她對文本中的女性人物灌注了某種特殊的情感,用獨特的視角書寫女性肉體上特別是精神上所遭受的巨大痛苦,使得這些女性形象具有豐富而深刻的蘊涵。
蕭紅遠離主導意識形態而始終關注女性存在方式,并非僅僅因為其本身的女性身份,更重要的是在于她對女性生存的獨特體驗和深刻感悟。如所周知,蕭紅是一位性格堅毅剛強卻又命途多舛的女性。她的人生幾乎經歷了一個女人一生所可能遭遇到的所有苦難:幼年喪母,被父親逐出家門,忍受男人的欺辱,孩子不幸夭折,被丈夫殘酷地拋棄。蕭紅渴望自由、解放,追求“溫暖和愛”,卻又不得不依附、借助于男性的支撐,在堅強中透出沉重的嘆息:“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討厭呵,女性有著過多的自我犧牲精神。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長期的無助的犧牲狀態中養成的自甘犧牲的惰性。”[1]
弗洛伊德認為:“現實的強烈經驗喚起了作家對早年經驗(通常是童年時代的經驗)的記憶,現在,從這個記憶中產生了一個愿望,這個愿望又在作品中得到實現。作品本身展示出兩種成分:最近的誘發場合和舊時的回憶。”[2]作家的創作與早年(童年)經驗有著極為重要的關聯。作家的早年經驗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其心理結構和意向結構,并規定了該作家創作的基本走向。所以說,蕭紅的早期人生經驗是觸發其書寫悲劇女性的重要內因。蕭紅孤獨寂寞的早年經歷,不僅讓她切身感受到女性狹小的生存空間,而且使她生成了對女性命運的深刻認識。當這種生存體驗長期積壓在作家的內心深處,便成為其生命動力來源,于是催發了蕭紅對不幸女性形象的書寫。
二
康定斯基說:“任何真正的藝術形式都來自于創作主體‘表達他的內在沖突和體驗的‘內在需要。”[3]蕭紅對女性的書寫,滲透著一種強烈的生命意識,蘊涵著她對生命悲劇的深刻體認。蕭紅筆下的女性形象就包含著作家本人深切的生命體驗。讀者在作品中感受到的女性的卑弱、渺小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都屬于作者自身刻骨銘心的情緒記憶。
每個作家都有獨具個人特色的精神苦旅之路。有些作家學習他人的思想,以此作為洞察人生的利器,如“五四”時期的大多數作家就拿西方先進的文明思想武器來抨擊黑暗現實。有些作家則特別注重自我生命體驗,通過自我體驗來感悟現實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如廢名、沈從文等。蕭紅既沒有經歷過現代高等學府的熏陶,也較少從書本上吸收他人的思想成果作為自己的精神養料。相對而言,蕭紅更多的是憑借自身的天賦來體驗、感悟人生,獲取精神養料。因此,蕭紅是一個特別注重自我生命體驗的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她的文學創作就是對自我生命感受與體驗的闡釋。
細讀文本,我們發現蕭紅的文學作品中所涉及的死亡描寫基本上都是發生在女性身上的。蕭紅在她的作品中苦心經營了一個女性的生與死的世界:《王阿嫂的死》中懷著身孕的王阿嫂產后同新生嬰兒一起死去;《呼蘭河傳》中黑乎乎笑呵呵的小團圓媳婦被活活燙死,馮歪嘴子的女人王大姐生第二個孩子時難產而死;《小城三月》的翠姨在男女有別的社會里憂郁而死;《生死場》中美麗的月英癱瘓之后遭丈夫折磨至死。最觸目驚心的是王婆的“死亡”經歷。王婆得知兒子砍頭后服毒自殺,只剩下最后一點氣息,丈夫趙三便用扁擔去壓。“她的肚子和胸膛突然增脹,像是魚泡似的。她立刻眼睛圓起來,像發著電光。她的黑嘴角也動了起來,好像說話,可是沒有說話,血從口腔直噴,射了趙三的滿單衫。”[4]大家以為王婆必死無疑,便將她裝進棺材,準備釘上棺材蓋。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王婆感到寒涼、口渴,說了一句“我要喝水”便又活過來了。蕭紅就是通過這些逼真血腥、慘不可言的畫面,揭示出中國女性的生命悲劇。其筆下這么多悲劇女性,幾乎每個都像壓在磐石下的小草一樣,見不到陽光,感受不到溫暖,受盡折磨和摧殘,扭曲變形,枯萎而死。這種死亡描寫,已經超越了通常的對生/死的美與丑、偉大與渺小的價值判斷,而凸顯其豐富而深沉的生命體驗。由此,蕭紅的女性書寫使讀者產生共鳴,引起他們對人的生命意義的理性思考。
蕭紅對女性生命悲劇的揭示來源于對生存價值的思考。“在中國現代作家中,也許蕭紅比之別人更逼近‘哲學。”[5]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沒有一個作家像蕭紅這樣,把女性的身體經驗與肉體受難表現得如此真實、慘烈、觸目驚心,表面看這似乎停留在肉體的感官層面,但實際指向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是關于人類存在的哲學命題。蕭紅從人的生命本質的層面去觀照女性,其筆下的生命,都是在命運的簸弄下完成的一個陰暗、悲慘的過程。生命在苦難中降生,又在無法抵御的磨難中走向死亡。人生的運行似乎就是這種生生死死、生死輪回的悲劇過程。可以說,蕭紅對于女性生存的深刻審視,實際上是對人的存在、人的意義的終極思考,在顯示了作家言說自我體驗的欲望的同時,體現出作家博大而深切的人性關懷,隱含著對人的生存的巨大悲憫。
三
“五四”文化啟蒙運動的“自我意識”是文化建設,“目的是國民性改造”[6]。發端于新文化運動的現代文學,一開始就以改造與重建中國文化為己任,并把實現人的現代化作為文化建構的終極目標,開啟了自身的啟蒙傳統。蕭紅雖屬體驗型作家,但其創作依然離不開“五四”精神的影響,總體上繼承了“人的文學”的創作傳統。更重要的是,直接師承魯迅的蕭紅深刻地把握魯迅思想的真諦,把筆觸伸及“改造民族靈魂”,從而使創作富有啟蒙特征。
蕭紅把魯迅改造國民性的文化思路融入到她對女性命運的表現中,在反映舊中國女性卑微處境的同時,從民族文化的深處揭示封建主義對女性的精神奴役,尋求徹底解放她們的出路。但是,她在作品中并沒有像魯迅那樣以啟蒙者的身份出現,而是以一種平等的、深入人物內心世界的平視姿態來觀照人物靈魂的。她有意識地把自己這個敘述者和被啟蒙者放在一起,看成是一種平等關系,在審視被啟蒙者靈魂的同時,也在檢察自身的靈魂。蕭紅如此處理自己與被啟蒙者的關系,除了說明她具有強烈的自省精神外,還凸現了啟蒙的艱難和自我啟蒙的必要,在更廣泛更深刻的意義上強化了其筆下女性形象的啟蒙功效。
在蕭紅文本中,中國底層女性最直接最經常的痛苦是被男性奴役迫害,成為男人的奴隸。在牢固的封建父權制宗法制度控制下的鄉村,女性的生存空間更為狹小、窒息,她們受到更多的奴役和迫害,性別壓迫與歧視無處不在。在男人看來,女人首先是滿足他們情欲的工具,男人可以任意發泄其生理欲望。而一旦女人懷上孩子,男人便又厭惡她們的懷孕、生產,置之不顧,肆無忌憚地實施暴力。男性永遠都是處于統治支配的地位,女人則被動地陷于受壓抑的位置,她們要完全服從于男人的命令,甚至連其基本的生存權利和價值也遭到粗暴的踐踏。麻面婆、月英、金枝等女性只是作為被壓迫的奴隸,就連努力抗爭的王婆也難免活在男權的陰影下。她奄奄一息之際,趙三表現得冷漠、不耐煩,拿扁擔去壓她身子。蕭紅專注于審視具有悲劇色彩的婦女形象,實質上旨在揭示中國女性悲劇的根本原因,強烈批判傳統男性文化對女性的漠視與扭曲。
endprint
蕭紅批判的筆端不僅觸及男性中心文化,而且還伸向了女性本身。對不幸女性不只是純粹的同情與憐憫,而且還涉及到其自身弱點的審視,這是蕭紅女性關懷的一個獨特之處。如果用啟蒙話語來觀照作家筆下的婦女形象,她們本身也不免存在著病態靈魂。“在蕭紅的眼里,女性最大的悲哀不是因為她們經歷坎坷不幸,而是她們對這種不幸的屈從和認同。”[7]金枝盡管痛恨男人,但還是懦弱地忍受著男人帶給她的屈辱;“瓷人”雖感到丈夫的無情,卻依然回到那傷心的家庭去,等等。女性麻木地依附于男性,并且將父權制文化價值取向內化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安于男性指派給她們的地位,于是失去了爭取自由的能動性。這正是女性本身的局限所在。更發人深省的是小團圓媳婦的悲劇。小團圓媳婦本是一個健康活潑的少女,嫁到婆家后,因為不符合封建道德對女性的規范,便遭到婆婆殘酷的折磨,后來更成為了婆婆不順心時習慣發泄的對象,最后還活活被開水燙死了。于苦難中掙扎著的女性,在受到男性木然的漠視、踐踏的同時,也在木然地傷害、壓迫著比自身更弱小的女性。她們首先是自己成為封建男權秩序下的犧牲品,然后又不自覺地成為了這種傳統制度的捍衛者。面對著陰森窒息的生存環境,女性不學會為生活斗爭,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地位,于是只能可悲地成為奴隸,處于生死輪回的悲劇中。這里展現的正是頑強的傳統意識與文化惰性所催生的麻木而扭曲的靈魂。蕭紅直接暴露女性的病態文化心理,旨在昭示徹底批判封建傳統文化的迫切性,呼喚女性的精神解放,從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所以,蕭紅描寫的女性人物,與其說是藝術形象,還不如說是文化啟蒙的符碼。
不可否認,蕭紅筆下的女性,大多以群像和符號化的形象出現,她們較為抽象,是片段式、白描式的。但這不僅不會削弱作家的藝術獨創性,反而恰好體現其“越軌的女性筆致”,增添了創作的獨特魅力。這些人物的描寫并不停留于表面化的性格判斷,而是深入到藏在內部的靈魂。在這里,她們作為一個深刻的人生哲理與巨大的文化內涵相結合的寓意特征。所以說,女性形象是解讀蕭紅藝術文本的一個重要視角,為我們闡釋和呈現了作品蘊含的豐富的藝術價值和思想價值。
注釋:
[1]聶紺弩:《在西安》,見季紅真:《蕭蕭落紅》,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6頁。
[2](奧)弗洛伊德:《作家與白日夢》,見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論美文選》,知識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頁。
[3](俄)瓦?康定斯基:《論藝術的精神》,查立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頁。
[4]蕭紅:《生死場》,見蕭紅:《蕭紅集》,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66至67頁。
[5]趙園:《論蕭紅小說兼及中國現代小說的散文特征》,見趙園:《論小說十家》(修訂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213頁。
[6]李澤厚:《中國思想史論》(下),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頁。
[7]黃曉娟:《雪中芭蕉:蕭紅創作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頁。
作者簡介:黃莉,華南師范大學文學碩士,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