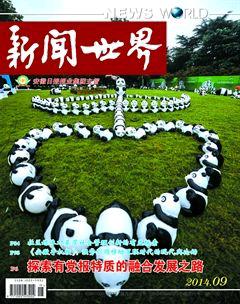技術壟斷文化下親身體驗的缺乏
王菲
【摘 要】《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一書向我們揭示了技術壟斷階段各種“軟”技術的欺騙作用,撻伐所謂的社會“科學”,譴責唯科學主義,它辨析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文學的異同。它為傳統符號的耗竭扼腕痛惜,呼吁人們以強烈的道德關懷和博愛之心去拼死抵抗技術壟斷,并堅決反對文化向技術投降。
【關鍵詞】技術壟斷 體驗 媒介生態
《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是尼爾·波斯曼媒介批評的三部曲之一,其余兩部是《童年的消逝》和《娛樂至死》。對技術發展弊端的批判是一以貫之的主題,在《技術壟斷》這本書里更是達到了論述的高潮。
尼爾·波斯曼是世界著名的媒體文化研究者和批評家,生前一直在紐約大學任教。他在紐約大學首創了媒體生態學專業。直到2003年,他一直是文化傳播系的系主任。2003年10月波斯曼去世后,美國各大媒體發表多篇評論,高度評價波斯曼對后現代工業社會的深刻預見和尖銳批評以及對媒介文化深刻的洞察。
波斯曼是媒介環境學的第二代精神領袖,媒介環境學這個術語的首創者是麥克盧漢,但正式使用者是波斯曼。波斯曼戲稱自己是“麥克盧漢的孩子”,卻又“不是很聽話的孩子”。他繼承了麥克盧漢的很多核心思想,他們都認為“媒介”應該是廣泛的,“媒介是人的延伸”,“人的一切人工制品,包括語言、法律、思想、假設、工具、衣服、電腦等,都是人體的延伸。”因而人類幾乎所有的發明創造,都可以算作媒介的范疇。同樣,本書中的“技術”也是一種泛技術,并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甚至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等同于“媒介”。然而波斯曼之所以稱自己為“不是很聽話的孩子”,因為不同于麥氏對新媒介熱情的贊頌和擁抱,他卻對媒介/技術的發展充滿了悲觀的擔憂和警惕。
書中,波斯曼對技術壟斷從多個角度做了簡明的界定:“任何技術都能夠代替我們思考問題,這就是技術壟斷的基本原理之一……所謂技術壟斷論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藝和技術的統治”。“技術壟斷是文化的‘艾滋病,我戲用這個詞來表達‘抗信息缺損綜合癥。”①波斯曼用技術和媒介的演化來劃分人類歷史。他認為:人類文化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工具使用文化階段、技術統治文化階段和技術壟斷文化階段;人類文化大約也分為相應的三種類型,即工具使用文化類型、技術統治文化類型和技術壟斷文化類型。他認為,技術和人類文化是亦敵亦友的關系,但是他死死地盯著技術的陰暗面,警惕技術對人造成的傷害。
一、醫療技術壟斷中親身體驗的缺乏
通過閱讀筆者深深地體會到,隨著人類文化發展的不斷推移,技術的發展卻造成了人類親身體驗的缺乏,人類與自然界被各種機器隔離開來。在第六章,機器意識形態:醫療技術壟斷中,作者運用許多事例和數據表明,技術壟斷條件下,醫療設備越來越好,醫術卻不一定提高,醫患關系不一定和諧,醫療事故不一定減少。原因就在于,現如今,醫患雙方都過分迷信技術設備,醫生的傾聽和經驗的判斷、患者的主訴、似乎都不再重要了。醫療實踐已經轉入了完全依賴機器生成信息的階段,患者也進入了這樣的階段,如果醫生沒有用盡一切可能的技術資源包括藥物,患者沒有得到一切診療手段,患者就不放心,醫生就容易受到無能的指控。所有疾病的治療只剩下一種方法——技術方法,醫療能力取決于用于治病的機器的數量和種類。
如此,人類已經陷入了技術壟斷的怪圈,這種現象的發生,應該歸根于人類對自身定位的偏差和對技術能力的夸大。人類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技術發明和應用的最初目的是完善人類的生活,它應該是人類創造更多更好文化的輔助工具。而現如今,對于技術的過分依賴,使人們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對于任何事物如果可以通過技術途徑獲得或者解決,人類就不會選擇親身體驗。可是,大多數人并未清楚地意識到,在盲目追求結果的同時,我們忽略了親身體驗過程的重要性。技術應該被人類利用,而不是人類被技術控制。
二、電腦技術壟斷中親身體驗的缺乏
再如,第七章機器意識形態:電腦技術壟斷中提到,在技術壟斷條件下,對機器人的迷信愈演愈烈,這個演變過程的三部曲是:人在某些方面像機器——人幾乎就是機器——人就是機器。文中介紹了電腦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不難發現電腦的“普適性”確實具有一定的欺騙性,導致人類“言必稱電腦”、“迷信人工智能”的電腦崇拜。計算機看似是技術壟斷論中近乎完美的機器,難道它的“思考”功能真的勝過人類的思維能力?筆者想說,人的智能是得天獨厚的,是具有生物性根基的,人類的精神生活是任何機器都無法取代的,機器能夠在某些有限的方面模擬人的精神世界,但絕不可能復制人的精神世界。機器不可能感知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更不可能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些只能靠人類的親身體驗來獲取,這就是人工智能完成不了的任務。
人類往往容易把造成某一結局的責任從自己身上遷移到一個抽象的媒介身上,例如:銀行出納員說無法告訴客戶戶頭上的余額,是因為電腦出了故障。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就等于放棄了對技術的控制權,我們會去追求誤導人的目標甚至是非人性的目標,僅僅因為電腦可以完成這樣的目標,或者說我們幻想電腦可以完成這樣的目標。
面對計算機,人類失去了判斷力和主體性的信心。人們用機械的威力取代了人類關照全局的能力。我們不能盲目地認為技術革新就等于人類進步,而應該認真思考:不用電腦的情況下能夠做什么,并時刻提醒自己,在使用電腦的時候可能會失去什么。
三、隱形技術影響下親身體驗的缺失
在第八章隱形的技術中,波斯曼更進一步指出很多軟性技術也潛移默化地減少著我們對客觀世界的親身體驗,影響著我們對現實的感知。比如語言、統計學就是隱形的技術的代表,尤其是后者的濫用帶來對數字的盲目崇拜。這樣的例子在現實生活中比比皆是。智商測試、性格測試、民意調查、成績排名等等一系列看似客觀的技藝,成為我們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數字取代了定義,程序取代了思考,而這背后則是將一切曖昧不明的現實數量化和操作化的渴望。以電視為例,“好”節目的定義為單純的高收視,“差”節目就是收視率低的節目,而全然不顧節目的內容、形式、內涵、品味、社會意義等諸多重要元素,收視率被當做籌碼來吸引投資者進而出售節目的廣告時間,怎樣才能衡量其廣告時間的價值呢?觀眾評價是抽象的、不具體的,此時收視率冷冰的客觀數字決定了一個節目的生死存亡。電視節目的制作者不需要顧及傳統、審美標準、主題的真實性、品味的高雅,甚至不需要考慮觀眾是否容易看懂,只要找到一個搏出位的噱頭來吸引更多人的收看,這就是成功的表現。可是,盲目追求高收視率的結果,導致電視媒介自身職能的缺失,電視新聞媒體應該親歷社會事務,重視對民眾認知的體驗,切實感知民眾的真實感受與意識取向。親身體驗的缺乏,將媒體從業人員禁錮在自己的幻想世界當中,憑空編造的節目就算吸引再多人的聚焦,對整個社會也是毫無益處反有其害的。
四、文化終究不會向技術投降
我們的生活中充斥了太多的偽科學和唯科學主義,科學已不僅僅是一種研究的方法,還成為組織社會的工具。在這樣的一種邏輯下,技術壟斷已經取代了人們傳統的信仰和價值觀,人們重新確立自己安身立命的理由,以及重新確立自身的生命意義、心靈安寧和道德滿足。人們在“科學”的標簽下,形成一種科學無所不能的幻覺,陷入了技術的深度和整體的控制。波斯曼并不是危言聳聽,人們更多地享受到技術帶來益處的時候,已經忽略了它尚存的弊處,這種忽略在某種程度上會讓文化、傳統、道德關愛、人文情懷遭受到致命的影響。
不少人認為技術的進步就等于人類文明的進步,但波斯曼告訴我們人類依然處于艱難的困境之中。我們生活在一個娛樂化的世界,利用層出不窮的新技術、新媒介,我們雖然暫時滿足了視覺和心理上的需求,但卻逐漸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和親身體驗的機會。我們越來越多地受到了技術的限制和牽絆,毫無防備地淪為了技術的奴隸。面對技術的迅猛發展,無法分辨技術可以為我們提供哪些服務,也就無法阻止技術被利用來破壞我們的生活。因此,我們必須要對技術是否最終有利于人類社會發展作出評判;同時也要思考技術應用的過程中我們是否會失去一些比方便、快捷更為重要的東西,從而不被技術的力量所牽制。
不可否認,現代科技的發展確實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工作、學習、交通、購物等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無不因科技的創新發生著空前的變化。但是這并不代表人類世界只要有技術的扶持就可以正常運轉,技術不可以完全代替人類文化。波斯曼的技術壟斷觀帶有技術悲觀主義色彩,這種對技術的批判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它提醒我們不能只是盲目、樂觀地關注技術的發展,而應樹立一種全新的文化價值觀,文化與科技同步前進,使文化引導科技發展,科技扶持文化進步。如果人類始終保持文化的傳承、思想的獨立,技術就不可能壟斷文化,文化也絕不會向技術投降。□
參考文獻
①尼爾·波斯曼 著,何道寬 譯:《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作者:南京理工大學設計藝術與傳媒學院傳播學研究生)
責編: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