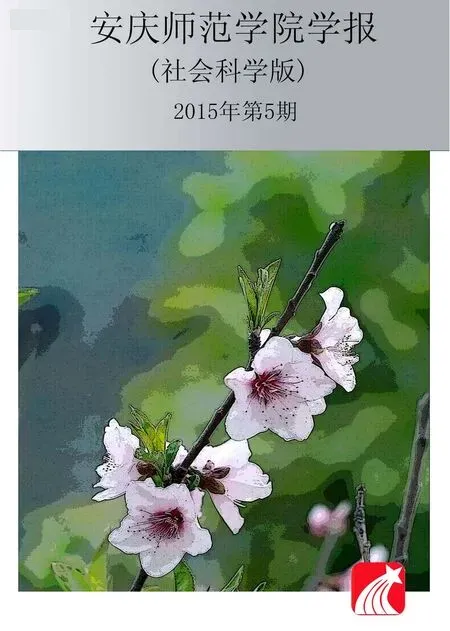方令孺對西方詩歌藝術形式的接受
張 文,郝涂根
(安慶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 安徽 安慶 246133)
?
方令孺對西方詩歌藝術形式的接受
張文,郝涂根
(安慶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安徽安慶246133)
摘要:桐城籍女詩人方令孺在詩歌創作中大膽借鑒、移植西方詩體、詩行、韻律和題材。其詩歌體式移植西方十四行詩的變體十六行體,詩行排列選用法國立體派的壓行式,韻律借鑒意大利彼特拉克體的抱韻格式,在題材選取上極力模仿英國維多利亞中后期詩人克·羅塞蒂的詩歌。方令孺在詩歌藝術形式上所作的有益嘗試,較好地踐行了新月派“三美”主張和“理性節制情感”的美學原則。
關鍵詞:方令孺;西方詩歌;藝術形式
“五四”以后,新月派詩人對一些“自由詩人”忽視詩歌藝術表現形式深表不滿。作為新月派主帥之一,聞一多先生力主新詩格律化,其《詩的格律》一文,是新詩格律化的綱領性文獻,中國現代格律詩派的理論基石。在創建格律詩體時,他提出并實踐了自己的“三美”主張,使音樂美、繪畫美和建筑美在詩歌的寫作上風行一時,也成為新月派詩人遵循的規則。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一個五彩繽紛的時代,正如陳夢家在《新月詩選·序言》里所描述的:“到了這個世紀,不同國度的文化如風云會聚在互相接觸中自自然然溶化了……外國文學影響我們的新詩,無異于一陣大風的侵犯,我們能不能不受她大力的掀動彎過一個新的方面?那完全是自然的指引。我們的白薔薇園里,開的是一色雪白的花,飛鳥偶爾撒下一把異色的種子,看園子的人不明白第二個春天竟開了多少樣奇麗的異色的薔薇。那全有美麗的,因為一樣是花。”[1]226為了實現新詩的形式格律化以及“理性節制情感”的美學原則,新月詩人在詩歌藝術形式上作了有益的嘗試。他們共同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竭力在西方詩歌園地里汲取藝術靈感。
目前,學界就新月派與西方文學之關聯研究主要集中于聞一多、徐志摩、朱湘和陳夢家四員主將,而對另一位隱微的安徽桐城籍女詩人方令孺,尚未深入研究。目前對這位女詩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生平介紹、散文的藝術特色以及散文版本上,至于20世紀30年代初方令孺的詩作,也僅限于評析一首詩(《詩一首》)。由此,筆者在中西跨文化視域下,擬就方令孺對西方詩歌藝術形式的接受和借鑒方面進行深度挖掘,以便能更加清楚地認識這位新月詩人在新詩語言藝術形式方面進行的大膽嘗試,以及為踐行并豐富發展新月派詩歌理論所做出的貢獻。
一、西方詩歌體式的借鑒——十六行體
1923年至1929年,方令孺赴美國留學,在華盛頓州立大學和威斯康星大學攻讀西方文學。深厚的英文功底和西方文學的浸潤,使她日后的詩作涂上了較為濃厚的西詩藝術色彩。
西方十四行詩詩體(Sonnet),聞一多先生音譯為“商籟體”,發源于意大利。一般來說,西方十四行詩體按其格律特點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以意大利詩人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ch 1304-1374)命名的彼特拉克體(Petrarchan Sonnets),簡稱彼體;第二種類型是英國文藝復興時期詩人斯賓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所創立的詩體完美、富于音樂性的斯賓塞體(Spenserian Sonnets),簡稱斯體;第三種類型是以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命名的莎士比亞體(Shakespearean Sonnets),簡稱莎體。十四行詩一般分為前后兩個部分,不同詩體前后兩部分的行數不同。彼體由兩節四行詩(the octet,共8行)和兩節三行詩(the sestet,共6行)組成。斯體、莎體由三節四行詩(共12行)和一節二行詩(共2行)組成,形成起承轉合的趨勢。十六行體一般每首詩限定十六行,包含四組抱韻體(abba),是十四行詩的變式或不規則十四行詩。新月詩人中創作十六行詩的不多,徐志摩的《為要尋一顆明星》和方令孺的《靈奇》可能是僅有的兩首。
為要尋一顆明星
我騎著一匹拐腿的瞎馬,
a
向著黑夜里加鞭;——
b
向著黑夜里加鞭,
b
我跨著一匹拐腿的瞎馬!
a
我沖入這黑綿綿的昏夜,
c
為要尋一顆明星;——
d
為要尋一顆明星,
d
我沖入這黑茫茫的荒野。
c
累壞了,累壞了我胯下的牲口,
e
那明星還不出現;——
f
那明星還不出現,
f
累壞了,累壞了馬鞍上的身手。
e
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g
荒野里倒著一只牲口,
h
黑夜里躺著一具尸首。——
h
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2]
g
徐志摩的這首《為要尋一顆明星》, 共分四個詩節十六行,采用西洋四組抱韻體(abba)。每節第一句和第四句、第二句和第三句字數相等,詩節勻稱,句式整齊。徐志摩以短短四小節十六句,講述了一個尋夢者對光明執著追求的故事。“我”即使付出“荒野里倒著一只牲口,黑夜里躺著一具尸首”的代價,也要“沖入這黑茫茫的荒野”,“為要尋一個明星”。《為要尋一顆明星》乃是作者追求理想的宣言。與徐志摩相呼應,方令孺在新詩創作中同樣接受了西方十六行詩體,她基本上模仿英國19世紀著名詩人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1828-1909)的愛情組詩《現代愛情》(Modern Love)的詩歌體式。
Modern Love
In our old shipwrecked days there was an hour,
a
When in the firelight steadily aglow,
b
Joined slackly, we beheld the red chasm grow
b
Among the clicking coals.Our library bower
a
That eve was left to us: and husband we sat
c
As lovers to whomTime is whispering.
d
From sudden-opened doors we heard them sing:
d
The nodding elders mixed good wine with chat.
c
Well knew we that Life's greatest treasure lay
e
With us, and of it was our talk.“Ah, yes!
f
Love dies!”I said: I never thought it less.
f
She yearned to me that sentence to unsay.
e
Then when the fire domed blackening,I found
g
Her cheek was salt against my kiss, and swift
h
Up the sharp scale of sobs her breast did lift-
h
Now am I haunted by that taste! That sound![3]209
g
梅瑞狄斯共創作50首組詩,全部采用十六行體寫成。這是《現代愛情》組詩的第16首。這首詩的格律采用抑揚格五韻步,全詩分四個部分,共十六行,每個部分單獨押韻,押韻格式為abba cddc effe ghhg。下面是方令孺1931年于青島創作的詩歌《靈奇》。
靈奇
有一晚我乘著微茫的星光,
a
我一個人走上了慣熟的山道,
b
泉水依然細細的在石上交抱,
b
白露沾透了我的草履輕裳。
a
一炷磷火照亮縱橫的榛棘,
c
一雙朱冠的小蟒向前宛引領,
d
導我攀登一千層皚白的石磴,
d
為要尋那鐫著碑文的石壁。
c
你,鐫在石上的字忽地化成
e
伶俐的白鴿,輕輕飛落又騰上——
f
小小的翅膀上系著我的希望,
f
信心的堅實和生命的永恒。
e
可是這靈奇的跡,靈奇的光,
g
在我的驚喜中我正想抱緊你,
h
我摸索到這黑夜,這黑夜的靜,
h
神怪的寒風冷透我的胸膛。[4]207
g
與梅瑞狄斯相似,方令孺的《靈奇》同樣由四個詩節構成,每節四句,共十六行。每節中都是第一行與第四行押韻、第二行與第三行押韻,而且每詩行的一、三句和二、四句字數完全對等:11-12-12-11, 11-12-12-11,11-12-12-11,11-12-12-11。全詩形式整飭,音韻回環。詩中描寫了一個寂靜的夜晚,詩人獨行在山間小道上,努力尋找著她所希冀的東西。她真的看到了希望,石頭上的字開始化成富有生命活力的白鴿,讓她充滿了信心和希望。然而當她正想欣喜地擁抱這希望時,前面出現的“靈奇的跡,靈奇的光”突然間又觸不可及,離她遠去。方令孺16歲時遵從族長之旨、媒妁之言,與志趣不投的安徽陳姓官紳之子完婚,婚后生活很不幸福。1929年從華盛頓州立大學、威斯康星大學學成回國之后,她與丈夫矛盾激化,婚姻名存實亡。不幸的婚姻給她心頭抹上了一層陰影,她想在靜謐的深夜將心靈的苦悶、靈魂的掙扎、骨子里潛藏的欲望釋放出來,對自己進行一次自由的放逐。在黑色的世界里,她吟詠著詩歌來排遣這份孤獨與寂寞。
《靈奇》獨特的十六行商籟體的構建主要由兩方面因素促成。其一,為使新詩在“自由-規范”的辯證統一中完善發展,以聞一多、徐志摩、朱湘為代表的新月派擔負起這一歷史使命。他們提出“理性節制感情”的美學原則,反對詩歌中感情的過分泛濫,主張理性節制感情——不論是抒發個人感情的自我表現,還是對社會黑暗的直接揭露,都應該在節制之列。為了貫徹“理性節制感情”的美學原則,新月派詩人提倡以“和諧”、“均齊”為新詩最重要的審美特征,把詩的感情收納在嚴格規范的形式中。聞一多“三美”中的建筑美尤其倡導“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其二,“在新詩史上,新月派曾大力提倡‘移植’英詩,由于‘桑籟體’(即十四行詩)在分段上雖有其特殊規定,但仍然主要是建立在以四行為一段這一普通的土壤上的。這乃是整個世界詩壇上共同的、最普遍的一種分段法,中國也不例外”[5]。 十四行詩對行數、韻式、音組、起承轉合等方面都有較嚴格的要求,這都為新月詩人追求新詩的形式格律化提供了契機。方令孺大膽并且巧妙地移植梅瑞狄斯的十六行體,并且將西洋抱韻糅合其中,作品詩節勻稱,句式整飭,音韻和諧,比較完美地踐行了新月派所倡導的“三美”主張之建筑美和音樂美。
二、西洋韻律的模仿——抱韻
西洋詩歌一般每四行構成一個詩節,每個詩節通常有四種韻式:交韻、抱韻、隨韻和疊韻。交韻(alternating rhyme scheme)——一、三行押,二、四行押(abab);抱韻(enclosing rhyme scheme),又稱“首尾韻”、“環抱韻”——一、四行押,二、三行押(abba);隨韻(running rhyme scheme)——一、二行押,三、四行押(aabb);疊韻(overlap rhyme scheme)——兩行押韻(aa)。方令孺在詩歌創作中借鑒并模仿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桂冠詩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的抱韻體(abba)。丁尼生1850年出版的懷念其摯友哈勒姆的挽歌集《悼念》(In Memoriam),共收詩作131首,全部運用抱韻韻式,從而形成一種獨特的風格。下面是其中的第22首:
The path by which we twain did go,
a
Which led by tracts that pleased us well,
b
Thro' four sweet years arose and fell,
b
From flower to flower, from snow to snow:
a
And we with singing cheer'd the way,
c
And, crown'd with all the season lent,
d
From April on to April went,
d
And glad at heart from May to May:
c
But where the path we walk'd began
e
To slant the fifth autumnal slope,
f
As we descended following Hope,
f
There sat the Shadow fear'd of man;
e
Who broke our fair companionship,
g
And spread his mantle dark and cold,
h
And wrapt thee formless in the fold,
h
And dull'd the murmur on thy lip.[6]
g
丁尼生的抱韻體是十四行詩的彼特拉克體(Petrarchan Sonnet)中的前八行(the octet)的韻式。意大利詩人彼得拉克一生寫了375首十四行詩,匯集成《抒情詩集》,獻給他的意中人勞拉(Laura)——他心中理想化的愛。詩人以浪漫的激情、優美的音韻和豐富多彩的色調,表達對愛情的追求,抒發甜蜜、痛苦和對愛情的憧憬、思念、渴望等感受。他筆下的十四行詩,每首分成兩部分:前一部分由兩段四行詩組成,后一部分由兩段三行詩組成,即按四、四、三、三編排。其押韻格式為abba,abba,cde,cde或abba,abba,cdc,dcd以及abba,abba,cdc,cdc。這種詩體在押韻的形式上不拘泥于一種,有三種押韻格式可供詩人創作時選擇,使詩歌的形式富有變化并顯得活潑、生動。正是由于意大利十四行詩在形式上有種種優點,十六世紀初被介紹到英國后,很多大詩人將彼特拉克體奉為十四行詩的典范,競相模仿,彼體隨即成為英國文學中十四行詩體的主要形式之一。
方令孺在《靈奇》中巧妙地運用了抱韻(abba)這一意大利體韻式。第一節里的第一行“光”與第四行“裳”押韻,第二行“道”與第三行“抱”押韻;同樣第二節里的“棘”與“壁”、“領”與“磴”押韻;第三節“成”與“恒”、“上”與“望”押韻;第四節“光”與“膛”、“你”與“靜”押韻。這種韻式第一行與第四行構成一個封閉性整體,音韻交接緩慢,給人以聽覺上的寧靜莊重之感,又首尾韻同,具有一種回環效果,極易表達纏綿悱惻的情感。尾韻中多用長元音如“光”(guɑng)與“膛”(tɑng)、“成”(cheng)與“恒”(heng)、“上”(shɑng)與“望”(wɑng),著力渲染了整首詩所籠罩的壓抑、沉重、緩慢以及令人窒息但又難以擺脫的氣氛,使人仿佛感覺到詩人滿腔深沉溫柔的愛與內心的痛苦交織在一起。徐志摩曾說:“商籟體是西洋詩式中格律最謹嚴的、最適宜于表現深沉的盤旋的情緒。”[7]《靈奇》是方令孺在國立青島大學期間的詩作。當時聞一多與方令孺曾在情感上生起漣漪,情形并不太嚴重。這段情感剛剛生出一個蓓蕾就被掐死了,不久之后,方令孺便黯然地離開了青島。這首詩表達了詩人經歷過不幸婚姻后對理想愛情追求的無望與痛苦,欲愛又不能愛的纏裹使她陷入深深的絕望中。而以歌頌愛情、表現人文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彼得拉克十四行詩,形式整齊,音韻優美,回環緩慢,有利于纏綿情調的渲染。這種韻式不僅影響了方令孺,也對當時其他新月派詩人產生過一定影響,聞一多的《忘掉她》,朱湘的《曉朝曲》、《玉嬌》,全都采用了abba抱韻式。
三、法國立體派詩行的移植—— 壓行式
19世紀20年代,以法國阿波利奈爾、西班牙畢加索為代表的法國立體主義流派對新月派產生過一定影響。立體主義將詩歌創作演繹為藝術建筑術,并將建筑美學的藝術構思引進文學創作,主要追求一種幾何形體的美,追求形式的排列組合所產生的美感。阿波利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1880-1918)嘗試創作詩行排列形式像階梯狀的詩歌,稱為“樓梯詩”。它常把一個詩行表現的內容分成幾個詩行,并逐漸壓低來表現,故亦稱為“壓行詩”。
米拉波橋下塞納河水流
相愛難長久
此情可待成追憶
常恨歡樂總在斷腸后
良宵來臨晚鐘幽
流光水逝我獨留
執手相對啊盈盈空佇立
雙臂拱橋底
清波倦眼總凝眸
脈脈千載最能解人意
良宵來臨晚鐘幽
流光水逝我獨留[8]
以上所選的是阿波利奈爾《米拉波橋》中的前四個詩節,詩人通過錯落有致的詩行,描繪出塵封在記憶中的米拉波橋,及其承載的一段純美凄涼的愛情。方令孺的《詩一首》和《任你》兩首詩都極力模仿立體派的樓梯式和參差式。
詩一首
愛,只把我當一塊石頭,
不要再獻給我,
百合花的溫柔,
香火的熱,
長河一道的淚流。
看,那山岡上一匹小犢
臨著白的世界;
不要說它愚碌,
它只默然
嚴守著它的靜穆。[4]206
任你
任你是:天神一樣尊嚴,
或是冰崖一樣凜冽;
千年一現的彗星
能把你毀滅。
任你說:心像月一樣皎潔
或是海水一樣平靜;
可惜這陰云的天
誰信有星辰?[4]209
方令孺首先通過獨特排列的詩行,突出強調每個詞的內容,使詞語獲得最大的感情表現力,以加強詩的節奏感,凸顯豐富的感情層次。參差的詩行表達出詩人百轉千回的情感起伏,繪聲繪色地描繪出愛情的悲涼、企盼等思想軌跡。其次,將主觀情緒化為具體形象。兩首詩并沒有鋪寫觸發這些情感的具體事件,也沒有赤裸裸地傾瀉情感,而是經過藝術的想象,呈現具體可觸的客觀形象:“石頭”、“上岡”、“百合花”、“小犢”、“白的世界”、“冰崖”、“月”、“彗星”、“海水”和“陰云”,等等。這是一位已婚女子對傾慕者委婉的答復。面對求愛者的溫柔、熱烈和淚水, 她仍婉拒對方, 讓人只把她“當一塊石頭”。落寞的心如空花飄零,淡淡的哀愁如潺潺流水,詩人在無可奈何中,將這滿腹心事、一腔愁怨,化作冷冷的月、蕭瑟的山岡、凄涼的水和陰沉的云,在那“白的世界”里,在那“冰崖一樣凜冽”的黑夜里,嚴守著她的“靜穆”。新月派詩人極力倡導客觀抒情詩的創造,他們一方面變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為主觀情愫的客觀對象化,另一方面對個人情感著意克制,努力在詩人自身與客觀現實之間拉開距離。實際上,從這首詩里不難窺見,詩人的寂寞哪里是死寂,實則有一種暗流在奔涌,有萬般不能安撫的情愫在潺湲。這種主觀情感的客觀化,使情感的表現蘊藉而含蓄,具有鮮明的形象性。而且,這也能夠激起讀者更豐富的聯想,從而使其積極地參加審美再創造過程。由于客體與主體之間、外物與內情之間有了象征體作媒介而得以緩沖,情感的激流受到一定的阻遏與制約,再配以參差錯落的詩行,詩也就變得更加含蓄蘊藉了。方令孺借助法國立體派樓梯式的排列,凸顯明晰的意象,使全詩帶有象征主義的詩風。這在新詩抒情藝術道路上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四、英詩題材的效仿——星夜登山
方令孺不僅借鑒、移植和模仿西詩的體式、韻律和詩行排列,在題材的選取上也大膽借鑒和嘗試。《靈奇》就是直接模仿英國維多利亞詩人克·羅塞蒂的《Up-hill》(《登山》)。
Up-hill
Does the road wind up-hill all the way?
Yes, to the very end.
Will the day's journey take the whole long day?
From morn to night, my friend.
But is there for the night a resting-place?
A roof for when the slow dark hours begin.
May not the darkness hide it from my face?
You cannot miss that inn.
Shall I meet other wayfarers at night?
Those who have gone before.
Then must I knock, or call when just in sight?
They will not keep you standing at that door.
Shall I find comfort, travel-sore and weak?
Of labour you shall find the sum.
Will there be beds for me and all who seek?
Yea, beds for all who come.[3]483-484
兩首詩都描寫了月白風清的夜晚,詩人獨自一人登山,沿途的景致引發了內心的感觸。《靈奇》是方令孺1931年在青島所作。當時她的大學校舍后面是青島山,山高128米,昔日這里有汩汩的泉水并形成溪流。這就是方令孺在詩的第一節描寫的情景:“有一晚我乘著微茫的星光,/我一個人走上了慣熟的山道,/泉水依然細細的在石上交抱,/白露沾透了我的草履輕裳。”1930年,聞一多受國立青島大學校長楊振聲之邀來此任教。他先在文登路住過,后因靠海太近,夜晚海浪聲音大,于是又搬到學校的八號樓來住,這個宿舍就是現在的“一多樓”,據說這個樓是當年德國俾斯麥兵營的附屬建筑,聞一多住這里時,樓附近還有墳頭,到了晚上還有鬼火。《靈奇》第二詩節這樣描寫道:“一炷磷火照亮縱橫的榛棘,∕一雙朱冠的小蟒向前宛引領,∕導我攀登一千層皚白的石磴,∕為要尋那鐫著碑文的石壁。”詩中的“磷火”,即俗稱的鬼火。詩人運用了“磷火”、“碑文”、“小蟒”等一系列神秘而恐怖的意象,來表達內心的憂郁情緒。方令孺“乘著微茫的星光”,去尋覓“靈奇的跡”和“靈奇的光”;克·羅塞蒂擔心“夜幕會不會將小屋遮蔽”?(May not the darkness hide it from my face)“那山徑能否一直蜿蜒上升?”(Does the road wind up-hill all the way)像她“這般疲憊”(travel-sore and weak),“可會找到安慰”?(Shall I find comfort)她們孤獨著自己的心靈,徘徊著自己的愛情,蹣跚地走近這憂傷哀婉的結局:一個“摸索到這黑夜,這黑夜的靜,神怪的寒風冷透我的胸膛;”另一位走進上帝為她安排的居所(inn)——天堂。兩位詩人星夜登山時的甜蜜與苦澀、期盼與悵惘,都糅合在詩中。
五、方令孺的西詩借鑒對新月派詩歌理論的貢獻
從以上方令孺借鑒西詩的四個方面,可以看出,她在實現新詩的形式格律化和踐行“理性節制情感”的美學原則上作了大膽而有益的嘗試。首先,《靈奇》一詩借用的是十四行詩的變體十六行,四個詩節大體上體現了一首詩所包含的思想情緒起承轉合的發展關系。其次,該詩運用了適合渲染纏綿情調的回環韻式(abba),再配上勻稱均齊的詩行,十分符合新月派“三美”之“音樂美”和“建筑美”的要求。再者,方令孺的《靈奇》、《詩一首》和《任你》等詩歌都較好地體現了“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與聞一多先生倡導的“一首理想的商籟體,應該是一個360度的圓形,最忌的是一條直線”[9]合拍。方令孺采用勻稱的詩節和整齊的詩行,從一定意義上說,都是這種“圓滿”藝術精神的體現。《詩一首》在內容上不僅是一些平凡的描摹與感慨,而且吸收法國立體派的創作經驗。在詩行排列上大膽移植了法國立體派的壓行式,以錯落有致的詩行凸顯豐富的情感波瀾,留給讀者更多的想象空間。詩人對曾經有過的熾熱情感表現出理性的克制,在“白的世界”里,她只愿“默然地嚴守著它的靜穆”。所以陳夢家稱贊道:“令孺的《詩一首》是一道清幽的生命的河的流響,她是有著如此樣嚴肅的神采,這單純印象的素描,是一首不經見的佳作。”[10]它既契合了前期新月派聞一多的“三美”主張和“理性節制情感”的美學原則,同時又應和了后期新月派陳夢家的新詩理論即詩“是美的文學”[11]122,“詩必須具有其獨具之形象與靈魂,明了這就要使詩有其獨具的要素,那便是詩形,詩韻,詩感……所以詩應當是可以觀賞的歌詠的思味的文學”[11]121。方令孺也較好地踐行了陳夢家《新月詩選·序言》里的詩學主張:詩歌應“本質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謹嚴”[1]230。
可以說,在中國新詩史上,陳夢家、方令孺、方瑋德等后期新月派詩人雖然傳承了“帶著鐐銬跳舞”的主張,但新月后期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創作上都表現出鮮明的西方現代主義傾向,給較為沉悶的新詩壇吹進一股清新的風,有力地促進了新詩創作的繁榮與發展。新月詩人方令孺在新詩創作中對西方詩歌藝術形式的大膽借鑒和實驗,為豐富新詩藝術形式以及構建新詩理論做出了一定貢獻。
參考文獻:
[1]陳夢家.夢家詩集[M].北京:中華書局, 2006.
[2]徐志摩.徐志摩選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59.
[3]何功杰.英詩選讀[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4]徐志摩,卞之琳,等.新月派詩選[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
[5]林庚.新詩格律與語言的詩化[M].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1-2.
[6]羅經國.新編英國文學選讀(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6:162.
[7]徐志摩.徐志摩散文全集(第一卷)[M].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383.
[8]阿波利奈爾.燒酒與愛情[M].李玉民,譯.合肥: 安徽文藝出版社, 1992:3.
[9]聞一多.新月討論:(三)談商籟體[J].新月.1930(3):210.
[10]陳夢家.新月詩選[M].上海: 新月書店,1931:27-28.
[11]陳夢家.夢甲室存文[M].北京:中華書局,2006.
責任編校:林奕鋒
On the Crescent Poet FANG Ling-ru’s Acceptance of the Artistic Forms of Western Poetry
ZHANG Wen,HAO Tu-g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qing Teachers College, Anqing 246133, Anhui, China)
Abstract:FANG Ling-ru, a crescent poet, borrowed and transplanted with audacity western poetic stanza, line arrangement, rhyme as well as subject matter. She borrowed the 16-line verse, a variant of sonnet. She used the uneven lines derived from French Cubism. The enclosing rhyme scheme used in the Pecharchan sonnets was also employed in her poems. She imitated C. Rossetti, a Victorian poetess in terms of subject matter. Her experiments in artistic forms of poetry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ree Beauties principle advocated by the crescent poets and the aesthetic principles of rational emotion.
Key words:FANG Ling-ru; western poetry; artistic forms; acceptance
中圖分類號:I207.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730(2015)05-0098-06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5.023
作者簡介:張文,女,安徽安慶人,安慶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郝涂根,男,安徽安慶人,安慶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
基金項目: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一般項目“維多利亞中后期文學與民族道德的重構研究”(AHSKY2014D110);教育部英語國家級特色專業項目(TS12154);安徽省省級教學研究重點項目(2012jyxm348)。
*收稿日期:2014-10-17
網絡出版時間:2015-11-11 10:42網絡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51111.1042.0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