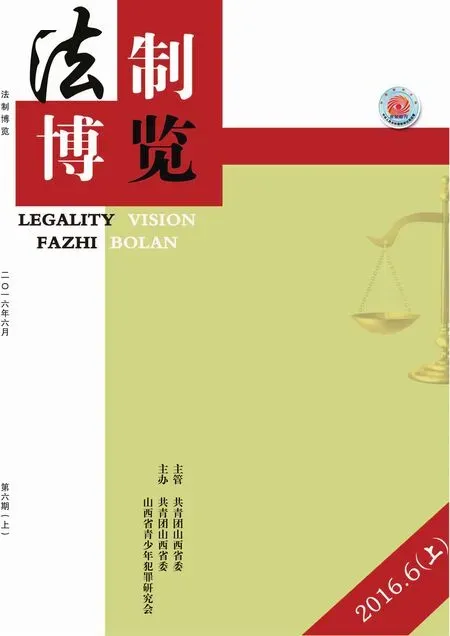論《海商法》船舶碰撞侵權行為之互有過失
宋 雯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3
?
論《海商法》船舶碰撞侵權行為之互有過失
宋雯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湖北武漢430073
摘要:19世紀初起源于西方的“互有過失”制度,最初的性質是侵權行為加害人主張免除全部賠償責任的抗辯事由。由于該原則有過度保護加害人之嫌疑,后來漸漸被更合法合理的“比較過失”制度所取代。我國《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條規定亦借鑒了這一立法例,并保留了“互有過失”的表述。然而它與“共同過失”這一字面相近的表達,卻有謬以千里的區別。基于這兩個法律概念的比較,結合國內外的立法發展,淺析我國“互有過失”制度。
關鍵詞:船舶碰撞侵權行為;互有過失;共同過失;比較;借鑒
船舶碰撞事故的損害賠償責任認定,因各國相關法律遵循的不同歸責原則而迥異。如何合法合理、公平公正地處理這類海上侵權行為,對當事雙方以及第三人均有不可小覷的影響和意義。因此,正確認識“船舶碰撞條款”中的“互有過失”,是維護合法權益、彰顯公平正義的重要前提。
一、互有過失之定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條規定:“船舶發生碰撞,碰撞的船舶互有過失的,各船按照過失程度的比例負賠償責任;過失程度相當或者過失程度的比例無法判定的,平均負賠償責任。
“互有過失的船舶,對碰撞造成的船舶以及船上貨物和其他財產的損失,依照前款規定的比例負賠償責任。碰撞造成第三人財產損失的,各船的賠償責任均不超過其應當承擔的比例。
“互有過失的船舶,對造成的第三人的人身傷亡,負連帶賠償責任。一船連帶支付的賠償超過本條第一款規定的比例的,有權向其他有過失的船舶追償。”
結合上述法律條文,從含義、性質、構成要件等方面,對“互有過失”進行定性。
互有過失,在英美法系國家和臺灣地區有其他表述——與有過失、促成過失、過失相抵或者受害人過錯①,其含義都是原告(被害人)對自己的安全未盡到通常的注意義務而與被告(加害人)各自存有過失。一般地,侵權行為中加害人以原告與有過失為抗辯事由,從而減少或者免除自己的賠償責任。與最初用作絕對的完全免責抗辯事由相比,相對的不完全免責抗辯事由被認為是“互有過失”制度發展完善后的根本性質。在海上船舶碰撞侵權行為中,互有過失是指碰撞船舶雙方在船舶航行或管理方面均未盡通常的注意義務而有疏忽,并以此作為責任認定的原則,對對方或者第三人的財產損失或人身傷亡承擔賠償義務的情形。
進一步來說,海上船舶碰撞侵權行為之互有過失的確定,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構成要件:(一)碰撞發生在船舶之間,且須符合《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款②的規定;(二)涉及二個或二個以上的當事方(一般情況下只有當事雙方,本文僅談論此種情形);(三)碰撞侵權行為發生在海上或者與海相通的可航水域;(四)碰撞船舶雙方在船舶航行或管理方面均未盡通常的注意義務;(五)侵權損害、碰撞事故、雙方過失之間有直接因果關系;(六)不要求共同侵權行為人之間必須有意思聯絡。
二、互有過失與共同過失之比較
失之毫厘,謬以千里。我國《海商法》保留了“互有過失”的表述,而沒有選擇“共同過失”這一社會大眾更為熟悉的表述,實際上當中是有其充分合理的原因的。采取不同的解釋方法得到的區別比較也有所不同。
從文理解釋方法出發,互有過失和共同過失均表現了過失方的多元性,但深層次的內涵無法清楚分辨。這種解釋方法由于有脫離法律的精神實質而發生偏差的嫌疑,仍不足以區分二者。
然而邏輯解釋則是運用邏輯的方法,分析法律規范的內容結構、適用范圍和概念之間的聯系,從而作出確定的解釋。我國《海商法》第五章關于船舶碰撞責任認定的法律規定具體有三條③,根據此立法邏輯,互有過失是與“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能歸責于任何一方的原因或者無法查明的原因”和“一船的過失”相對應的,強調過失責任同時歸于雙方,體現了邏輯上的周延性。而共同過失缺乏明文規定,并沒有類似相對的限定情形,不具有周延性。
論理解釋又稱目的解釋,是指按照立法精神并結合具體案件,從現階段社會發展的需要出發,以合理的目的進行的解釋。根據立法目的,互有過失旨在表明過失的來源是非單一的,“互有”強調多元過失的獨立性、平行性,不要求共同侵權行為人之間必須有意思聯絡;而共同過失旨在表明過失是作為一個不可分的共同體而存在的,“共同”強調過失的不可分性(但不排斥責任分配的比例原則),在是否要求有意思聯絡的問題上模棱兩可。由此看來,“互有過失”這一法律概念是極具精確性的。
三、國外法淵源
(一)英美法系
互有過失制度最早追溯到1809年的英格蘭,意指加害人所為的侵權行為雖造成被害人的損害,但加害人可以被害人與有過失作為絕對的抗辯事由,而主張免除一切賠償責任,且法院應否定被害人的請求權。被害人與有過失,是指在能預見并能即時避免損害發生的情況下,其未盡一般的普通注意義務。此后的半個世紀美國各州和哥倫比亞特區繼受了該制度,同時輔以一些例外情形。
最初,被稱為被告“完全的、要么全有要么全無的抗辯理由”的與有過失制度,因其偏重保護被告的弊端而廣為詬病。隨著侵權行為法的發展,更為合法合理的“比較過失”制度漸漸代替了原本僵化的絕對與有過失制度。美國最先采用這個原則的州是紐約和威斯康星,且從1910年到1992年,46個州先后全部或部分廢除了互有過失制度。新制度在損害賠償責任的分配上有了極大進步和完善:如果原告存在著過失,則要比較原、被告雙方間的過失比例,按該比例分配損害賠償的數額,即原告仍然可以得到賠償,但是他的賠償數額要相應地減少,被告并非完全免除而是適當減少了賠償責任。而過失比例的界定,一般由陪審團來確定。
然而海商法與侵權責任法在立法上又存在著差異。1931年正式生效的《1910年統一船舶碰撞若干法律規則的國際公約》,是有關船舶碰撞民事責任的最早、最重要的國際公約,世界上許多的海運國家都加入了該公約,但美國卻是例外。美國法院在船舶碰撞過失認定標準方面一直采用“賓夕法尼亞規則”,而關于互有過失的船舶碰撞侵權案件中,也是特立獨行地采用“平均分擔損失原則”,與公約規定的比例過失原則背道而馳。而后在1975年的“美國訴可靠轉運公司”一案中,聯邦最高法院雖然首次按過失比例判定責任,但仍未將此上升至成文法高度。
(二)大陸法系
自古羅馬法時期始已有“與有過失制度”的相關原則,后來由德國民法典第二百五十四條明確規定。德國侵權法上的與有過失制度,涉及到侵權責任的分配問題,其本質即當受害人未盡到對自己利益的合理照顧或保護,與加害人共同導致自己損害時,責任如何公平分配的問題。一般地,法院應當找出導致損害發生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但受害人對損害本身也有過錯的,則從當事人雙方的過錯入手來分配責任。對于因第三人的過失造成的損害,德國判例認為當受害人與加害人之間存有債之關系時,受害人應當對其法定代理人或使用人的與有過失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四、國內法比較:《侵權責任法》和《刑法》
我國《侵權責任法》第十、十一、十二條中規定有“二人以上實施”、“二人以上分別實施”等表達,并沒有采用“互有過失”這一表述。而在學理上經常使用“共同過失侵權行為”來區分“共同故意侵權行為”,二者統一構成侵權責任法上的共同侵權行為。共同過失侵權行為,是指二個或二個以上加害人共同侵害他人合法民事權益而造成損害的違法行為。其構成要件包括:(一)二個或二個以上加害人;(二)加害人有主觀過錯,分故意和過失;(三)存在共同侵害他人合法民事權益的行為;(四)產生了損害結果;(五)損害結果與侵權行為間有因果關系;(六)不要求共同侵權行為人之間必須要有意思聯絡。因為不存在意思聯絡,根據一般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侵權行為人只對自己所實施的行為造成的客觀損害結果負責。這些規定和要求,實際上與《海商法》船舶碰撞侵權行為的“互有過失制度”的認定,有異曲同工之妙。
而我國的《刑法》在定罪時否認了“共同過失犯罪”的認定。根據第二十五條規定,共同犯罪的成立不僅要求犯罪主體數量是兩人以上,而且要求共同犯罪的主體之間必須存在意思聯絡而構成共同犯罪的主觀方面要件,并在此共同故意的主觀意圖支配下實施了犯罪行為。因此,共同犯罪只能是共同故意犯罪。雖然《刑法》條文中沒有使用“共同過失”和“互有過失”的概念,但是在司法實踐中,法院依舊會將受害人的自身過錯作為量刑情節加以考慮。
五、互有過失之借鑒與完善
綜合上述對國外法淵源的縱向探究與國內各部門法的橫向比較,可以看出“互有過失制度”有著堅實流長的法律基礎,以及不斷發展完善的不竭動力。羅馬皇帝安托尼努斯曾說:“朕誠為陸上之王,但海法乃海上之王。”我國的海商法起源較晚,后來系統成文的《海商法》是在一系列國際公約諸如《海牙維斯比規則》、《漢堡規則》的基礎上學習借鑒而成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我們應當繼續汲取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立法理念,進一步明確“互有過失”的定性問題,這是后續比例責任分配原則有效適用的前提和基礎。同時,國內各部門法之間也應互為補充借鑒,彼此相輔相成,不斷提高法律條文解釋之準確性和明辨性,推動中國法制發展完善。
[注釋]
①均是對Contributory Negligence的不同翻譯,其實質內涵一致.
②<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款規定:“前款所稱船舶,包括與本法第三條所指船舶碰撞的任何其他非用于軍事的或者政府公務的船艇.”第三條規定:“本法所稱船舶,是指海船和其他海上移動式裝置,但是用于軍事的、政府公務的船舶和20總噸以下的小型船艇除外。前款所稱船舶,包括船舶屬具.”
③是指<海商法>第五章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一百六十八條、第一百六十九條.
[參考文獻]
[1]張湘蘭著.海商法(第二版)[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
[2]徐愛國.“與有過失”與“比較過失”[EB/OL].中國法院網,2002-8-12.
[3][美]G·吉爾摩(Grant Gilmore),[美]C.L.布萊克(Charles L Black)著,楊召南等譯.海商法[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
[4]董琳著.美國海商法中獨特的船舶碰撞責任體系[J].決策與信息旬刊,2010.
[5]何坦著.德國侵權法上與有過失制度研究[D].湖南師范大學,2011.
[6]張明楷著.共同過失與共同犯罪[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3(02).
中圖分類號:D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379-(2016)16-0062-02
作者簡介:宋雯(1995-),女,廣東珠海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2013級法學(民商法方向)本科生,研究方向:海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