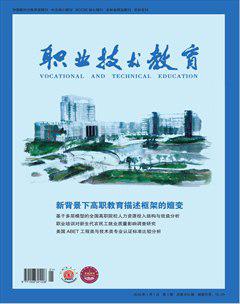高職學(xué)生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對(duì)職業(yè)未決的影響機(jī)制
安蓉 梁娜



摘 要 職業(yè)決策被認(rèn)為是個(gè)人職業(yè)發(fā)展面臨的最重要決定之一。全球經(jīng)濟(jì)及職業(yè)市場(chǎng)的復(fù)雜性,使得人們不得不頻繁地做出職業(yè)決策。這些決策的有效性如何直接影響到今后的職業(yè)生涯發(fā)展。以Jones和Chenery的職業(yè)定向模式作為理論基礎(chǔ),分析高職院校學(xué)生職業(yè)決策的現(xiàn)狀,進(jìn)一步探討高職院校學(xué)生職業(yè)決策中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情感舒適程度、職業(yè)未決的關(guān)系及內(nèi)在作用機(jī)制,通過(guò)對(duì)天津市211名高職學(xué)生的實(shí)證研究發(fā)現(xiàn):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和情感舒適度均對(duì)職業(yè)未決程度有顯著預(yù)測(cè)作用。在這一作用發(fā)生過(guò)程中,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通過(guò)情感舒適度的部分中介而影響職業(yè)未決。
關(guān)鍵詞 高職學(xué)生;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情感舒適度;職業(yè)未決
中圖分類(lèi)號(hào) G718.5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 A 文章編號(hào) 1008-3219(2016)01-0062-06
一、研究背景
職業(yè)決策是個(gè)體職業(yè)發(fā)展過(guò)程中面臨的重要選擇。在激烈的就業(yè)競(jìng)爭(zhēng)和頻繁的職業(yè)流動(dòng)過(guò)程中,個(gè)體隨時(shí)面臨職業(yè)的選擇并做出決策,職業(yè)決策結(jié)果也直接影響著個(gè)體的職業(yè)生涯發(fā)展[1]。對(duì)高職學(xué)生職業(yè)決策現(xiàn)狀及內(nèi)在作用機(jī)制進(jìn)行實(shí)證研究,是基于以下現(xiàn)實(shí)考慮:首先,我國(guó)已經(jīng)處于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形成供大于求的態(tài)勢(shì),畢業(yè)生就業(yè)走向市場(chǎng)化[2]。在日趨激烈的職業(yè)競(jìng)爭(zhēng)中,高職學(xué)生的就業(yè)壓力也與日俱增,職業(yè)決策變得更為艱難。在大學(xué)擴(kuò)招、經(jīng)濟(jì)社會(huì)轉(zhuǎn)型及職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就業(yè)難等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的拷問(wèn)下,反思高職學(xué)生職業(yè)決策和職業(yè)發(fā)展教育十分必要。其次,科學(xué)的職業(yè)決策對(duì)于促進(jìn)高職學(xué)生就業(yè)至關(guān)重要。研究結(jié)果表明,教育工作者了解高職學(xué)生職業(yè)決策的影響因素和面臨的困惑,并開(kāi)展相應(yīng)的職業(yè)定向教育和職業(yè)咨詢(xún),有助于其有效指導(dǎo)學(xué)生個(gè)體掌握科學(xué)的職業(yè)決策方法,增強(qiáng)職業(yè)決策能力,在面對(duì)職場(chǎng)上巨大的壓力時(shí)作出符合自己的職業(yè)選擇 [3]。
不同學(xué)科和研究者對(duì)于職業(yè)決策研究基于不同的角度和見(jiàn)解。Gelatt(1962)認(rèn)為,對(duì)職業(yè)決策的研究有著直接的現(xiàn)實(shí)意義,其通過(guò)評(píng)估可能、權(quán)重結(jié)果來(lái)選擇適當(dāng)決策活動(dòng)的研究結(jié)論是典型的理性范式[4]。Katz(1966)指出決策者在職業(yè)決策過(guò)程中會(huì)使用信息、價(jià)值、預(yù)測(cè)三個(gè)系統(tǒng)。該研究結(jié)果強(qiáng)調(diào)決策者通過(guò)確定可能獲得的職業(yè)并估計(jì)其回報(bào)強(qiáng)度,挑選出能夠具有最大期望價(jià)值的選擇對(duì)象[5]。
然而,盡管上述典型的經(jīng)濟(jì)人理性假設(shè)和效用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可以作為決策的主要依據(jù),卻不足以對(duì)職業(yè)決策過(guò)程作出完整解釋。這是因?yàn)閭€(gè)體的職業(yè)決策不能等同于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的決策,個(gè)體對(duì)職業(yè)的期望與經(jīng)濟(jì)決策的效用是不同的。同時(shí),職業(yè)決策過(guò)程涉及決策個(gè)體復(fù)雜的內(nèi)部過(guò)程,如認(rèn)知的失調(diào)、情感態(tài)度的改變、價(jià)值的澄清等也都能夠?qū)β殬I(yè)決策行為產(chǎn)生重要影響。在心理學(xué)和其他行為學(xué)科思想的影響下,職業(yè)決策理論從另一個(gè)視角被不斷地認(rèn)識(shí)和闡明。Tiedeman和Ohara(1963)研究發(fā)現(xiàn),個(gè)體職業(yè)決策的過(guò)程應(yīng)與個(gè)人心理發(fā)展相適應(yīng),以個(gè)體的整體認(rèn)知能力為基礎(chǔ),強(qiáng)調(diào)職業(yè)認(rèn)同發(fā)展與職業(yè)決策發(fā)展的一致性[6]。Sampson,Peterson和Reardon(1991,1996)提出了認(rèn)知信息加工的CIP理論,并構(gòu)筑金字塔模型,強(qiáng)調(diào)從信息加工取向去解決職業(yè)決策問(wèn)題[7]。上述研究成果為今天研究職業(yè)決策問(wèn)題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理論基礎(chǔ)。然而職業(yè)決策是動(dòng)態(tài)和難測(cè)度的,影響職業(yè)決策的主客觀因素都不盡相同,在實(shí)證領(lǐng)域中對(duì)職業(yè)決策的測(cè)評(píng)結(jié)論也千差萬(wàn)別。只有將理論和研究個(gè)體的現(xiàn)實(shí)背景相結(jié)合,確切了解個(gè)體職業(yè)決策的實(shí)際過(guò)程和更底層的機(jī)制,才能更全面地反映個(gè)體的職業(yè)決策規(guī)律,才能采用一定的方法來(lái)預(yù)測(cè)和指導(dǎo)個(gè)體的職業(yè)決策,改善其決策能力。這也是本研究的努力方向。
基于此,要探討高職學(xué)生的職業(yè)決策,前提是必須摸清高職學(xué)生發(fā)生職業(yè)決策行為所處的高等職業(yè)教育這一大背景的教育特征。首先,高等職業(yè)教育作為職業(yè)性的定向教育,就業(yè)導(dǎo)向這一培養(yǎng)目標(biāo)是顯性存在的[8]。其次,高等職業(yè)教育的課程也呈現(xiàn)出區(qū)別于普通教育的本質(zhì)特征,即職業(yè)定向性。聯(lián)合國(guó)教科文組織(UNESCO)在《國(guó)際教育標(biāo)準(zhǔn)分類(lèi)》(1997)中將高等職業(yè)教育歸為基于知識(shí)應(yīng)用課程,面向“實(shí)際的、技術(shù)的、職業(yè)的”,即“定向于某個(gè)特定職業(yè)”的5B教育[9]。因此,需要在研究與探討高職學(xué)生職業(yè)決策過(guò)程中考慮對(duì)職業(yè)定向性的分析與檢驗(yàn)。
Jones和Chenery(1980)在職業(yè)決策研究中提出多向度的職業(yè)定向狀態(tài)模式,并編制出職業(yè)決定量表(Vocational Decision Status,VDS)[10]。通過(guò)該量表來(lái)評(píng)價(jià)職業(yè)定向的確定及認(rèn)知程度、對(duì)目前職業(yè)定向狀態(tài)的情感舒適程度、職業(yè)未決因素。本文以Jones和Chenery(1980)的職業(yè)定向模式作為理論基礎(chǔ),擬從高等職業(yè)教育區(qū)別于普通高等教育具有職業(yè)定向性這一特征規(guī)律為切入,以高職學(xué)生的職業(yè)定向作為分析起點(diǎn),并結(jié)合高等職業(yè)教育中職業(yè)決策的現(xiàn)實(shí)狀況,試圖做進(jìn)一步的高職學(xué)生職業(yè)決策因素關(guān)系的探究,探討職業(yè)定向的認(rèn)知對(duì)職業(yè)未決行為的影響作用,同時(shí)考察情感舒適度在此過(guò)程中的作用。本研究提出如下兩個(gè)假設(shè),假設(shè)1: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與職業(yè)未決程度呈負(fù)相關(guān),并能顯著預(yù)測(cè)職業(yè)未決程度的結(jié)果;假設(shè)2:情感舒適度在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與職業(yè)未決程度之間起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duì)象
采取方便取樣的方法,從天津市高職院校中抽取部分在校生,共發(fā)放問(wèn)卷250份,實(shí)際回收215份,回收率86%,篩除無(wú)效被試后,共獲得有效問(wèn)卷211份,有效率98.1%。其中,男生60人,女生151 人;獨(dú)生子女70 人,非獨(dú)生子女141人;城鎮(zhèn)學(xué)生96人,農(nóng)村學(xué)生115人。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Jones(1980)根據(jù)職業(yè)定向模式編制的職業(yè)決策量表的中文修訂版[11]。修訂后的量表共33個(gè)項(xiàng)目,包括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情感舒適度和職業(yè)未決三個(gè)分量表。分別探討個(gè)體對(duì)未來(lái)生涯、職業(yè)方向和目標(biāo)所持的確定及認(rèn)知程度;對(duì)目前生涯定向狀態(tài)的主觀感受(測(cè)量對(duì)抉擇狀態(tài)舒適與否的情緒反應(yīng));個(gè)體無(wú)法形成滿(mǎn)意的職業(yè)決定的阻礙狀態(tài)。量表采用Likert五點(diǎn)計(jì)分,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經(jīng)過(guò)集體施測(cè)后,三個(gè)分量表的內(nèi)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數(shù)分別為0.791、0.824、0.861,均較為理想。
(三)數(shù)據(jù)處理
使用SPSS17.0進(jìn)行數(shù)據(jù)統(tǒng)計(jì),并采用描述統(tǒng)計(jì)、相關(guān)分析、回歸分析對(duì)數(shù)據(jù)進(jìn)行處理。Baron和Kenny(1986)提出中介作用需要滿(mǎn)足的三個(gè)條件[12]:當(dāng)自變量分別對(duì)中介變量和因變量預(yù)測(cè)時(shí)作用是顯著的;待檢驗(yàn)的中介變量也能夠顯著預(yù)測(cè)因變量;當(dāng)自變量和待檢驗(yàn)的中介變量同時(shí)進(jìn)入對(duì)因變量的回歸方程中時(shí),若中介變量的回歸系數(shù)依舊顯著,而自變量對(duì)因變量的回歸系數(shù)顯著性下降或消失,說(shuō)明存在中介作用。溫忠麟、張雷、侯杰泰等人在總結(jié)該檢驗(yàn)方法的基礎(chǔ)上,又提出:當(dāng)中介作用存在時(shí),如果自變量對(duì)因變量影響顯著減小至消失,則起完全中介作用;如果影響減小但仍然達(dá)到顯著水平,則起部分中介作用。
三、實(shí)證結(jié)果與分析
(一)高職院校學(xué)生職業(yè)決策現(xiàn)狀
表1列出了天津市高職學(xué)生職業(yè)決策三個(gè)分量表的得分情況。基于量表采用的是五點(diǎn)記分,以下分析取3為估計(jì)參考值。
從統(tǒng)計(jì)結(jié)果可知,情感舒適度題均得分最高,為3.19,略高于總體均值3,表明高職學(xué)生在職業(yè)決策中情感舒適度良好,較為安定,不焦躁,不緊張。職業(yè)未決題均得分最低,為2.70。因職業(yè)未決分量表內(nèi)容所測(cè)皆為負(fù)向描述,測(cè)量的是職業(yè)決策的阻礙程度,分值越高,表示職業(yè)決策的阻礙程度越高,反之越低。該職業(yè)未決結(jié)果低于估計(jì)參考均值3。說(shuō)明高職學(xué)生職業(yè)決策的阻礙程度低,遇到的職業(yè)決策困難較少。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題均得分為2.85,低于參考均值3,未達(dá)到一般水平,說(shuō)明高職學(xué)生職業(yè)定向的有效性并不高,多數(shù)還不能清楚認(rèn)知自己將來(lái)愿意從事或可以從事的職業(yè)方向或職業(yè)領(lǐng)域。
職業(yè)教育的目標(biāo)及課程具有職業(yè)定向性,直接服務(wù)于將要從事的職業(yè)崗位要求。該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的調(diào)查結(jié)果表象上是不符合職業(yè)教育的職業(yè)定向性特點(diǎn)的,實(shí)質(zhì)上恰好說(shuō)明了盡管當(dāng)前高等職業(yè)教育在高職學(xué)生職業(yè)定向上進(jìn)行了引導(dǎo),但高職學(xué)生面對(duì)未來(lái)從事的職業(yè)仍存在盲目性、職業(yè)定向失效的問(wèn)題。對(duì)這一現(xiàn)象作出如下解釋?zhuān)阂皇钦J(rèn)知偏誤。高職學(xué)生通過(guò)學(xué)習(xí)職業(yè)教育課程以及在內(nèi)外群體之間的交流和比較獲得了“我們是誰(shuí)”的身份判定,但是“我們是”并不一定意味著“我們?cè)敢獬蔀椤保憩F(xiàn)出對(duì)當(dāng)前專(zhuān)業(yè)對(duì)口的職業(yè)不接納或不理解,職業(yè)認(rèn)同未得以激發(fā),最終放棄對(duì)該職業(yè)目標(biāo)的探索[13]。二是認(rèn)知不足。獲取信息不充分,對(duì)與自己所學(xué)專(zhuān)業(yè)緊密相關(guān)的行業(yè)形勢(shì)認(rèn)識(shí)模糊,對(duì)如何進(jìn)行職業(yè)決策未能思考明確。
(二)人口統(tǒng)計(jì)學(xué)變量對(duì)高職學(xué)生職業(yè)決策的影響
相關(guān)決策研究顯示,人口學(xué)及組織變量是影響個(gè)體進(jìn)行決策的重要因素。因此,除了預(yù)計(jì)需要驗(yàn)證的研究假設(shè)之外,進(jìn)一步考察人口統(tǒng)計(jì)學(xué)及組織變量是否也會(huì)影響高職學(xué)生職業(yè)決策。本研究擬從個(gè)人、家庭、社會(huì)三個(gè)方面的人口統(tǒng)計(jì)學(xué)變量進(jìn)行選取,包括了性別、家庭所在地、專(zhuān)業(yè)、是否獨(dú)生子女、是否擔(dān)任某種學(xué)生團(tuán)體工作、有無(wú)求職經(jīng)歷等。表2呈現(xiàn)了不同人口統(tǒng)計(jì)學(xué)及組織變量在職業(yè)決策各因子的差異顯著性。
1.性別
表2統(tǒng)計(jì)結(jié)果顯示,男生和女生分別在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程度和職業(yè)未決程度上的比較結(jié)果相對(duì)一致,未出現(xiàn)顯著差異。但在情感舒適度上,男生均值為3.40,女生均值為3.10,進(jìn)一步的獨(dú)立樣本t檢驗(yàn)表明,兩者存在顯著差異(t=2.53,p<0.05)。即女生在職業(yè)決策中情感舒適度低于男生。分析其原因,這一結(jié)果可能是受社會(huì)角色和群體特征的影響。女生普遍存在自卑、敏感、缺乏情緒控制以及風(fēng)險(xiǎn)承擔(dān)和抗壓能力較弱等心理特點(diǎn),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阻礙女生在職業(yè)決策中保持舒適的狀態(tài)。
2.是否獨(dú)生子女
表2統(tǒng)計(jì)結(jié)果表明,在情感舒適度上,獨(dú)生子女的均值為3.34,非獨(dú)生子女的均值為3.11。經(jīng)過(guò)獨(dú)立樣本t檢驗(yàn)(t=2.08,p<0.05),表明獨(dú)生子女和非獨(dú)生子女在情感舒適度上的比較結(jié)果具有顯著差異,獨(dú)生子女在職業(yè)決策中情感舒適度略高于非獨(dú)生子女。具體原因可能是獨(dú)生子女的家庭,能夠較為集中地把精力放在單個(gè)孩子身上。所以,相對(duì)非獨(dú)生子女來(lái)說(shuō),獨(dú)生子女在家庭方面受到的愛(ài)護(hù)及指導(dǎo)可能較多,當(dāng)在職業(yè)決策中遇到煩惱時(shí)家長(zhǎng)更能及時(shí)幫助疏導(dǎo),盡快調(diào)節(jié)不適狀態(tài)。
3.有無(wú)求職經(jīng)歷
求職經(jīng)歷能夠加深高職學(xué)生對(duì)職業(yè)的認(rèn)識(shí)和職業(yè)環(huán)境的了解等,最終啟發(fā)職業(yè)決策行為。考察這一變量在研究職業(yè)決策中十分必要。表2統(tǒng)計(jì)結(jié)果表明,高職學(xué)生中有求職經(jīng)歷的和無(wú)求職經(jīng)歷的在職業(yè)未決程度上存在顯著差異(t =2.09,p<0.05)。從均值來(lái)看,有求職經(jīng)歷的為2.85,無(wú)求職經(jīng)歷的為2.65,表明有求職經(jīng)歷的比無(wú)求職經(jīng)歷的被試在職業(yè)決策中遇到的阻礙程度高。分析認(rèn)為,求職經(jīng)歷在高職學(xué)生職業(yè)決策中是把“雙刃劍”。過(guò)多的求職經(jīng)歷在豐富個(gè)體對(duì)職業(yè)崗位、職業(yè)人際關(guān)系、職業(yè)環(huán)境等認(rèn)識(shí)的同時(shí),也會(huì)給職業(yè)決策造成困擾,產(chǎn)生“信息超載”效應(yīng)或是多趨沖突,反而影響了正常的理解與決策。這表明,求職經(jīng)歷不在于“多”,而在于“準(zhǔn)”。
此外,專(zhuān)業(yè)、家庭所在地、有否擔(dān)任某種學(xué)生團(tuán)體工作等變量未能在任何一個(gè)維度上產(chǎn)生顯著性差異。
(三)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對(duì)職業(yè)未決的預(yù)測(cè)作用
要驗(yàn)證本研究假設(shè),必須滿(mǎn)足所研究的這三個(gè)變量間兩兩關(guān)系顯著。表3相關(guān)性檢驗(yàn)的結(jié)果顯示: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情感舒適度及職業(yè)未決均呈顯著相關(guān)。其中“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程度”與“情感舒適度”呈顯著正相關(guān)(r=0.22,p<0.01),與“職業(yè)未決”顯著負(fù)相關(guān)(r=-0.27,p<0.01)。“情感舒適度”與“職業(yè)未決”顯著負(fù)相關(guān)(r=-0.73,p<0.01)。
采用逐步回歸分析進(jìn)一步考察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對(duì)職業(yè)未決的預(yù)測(cè)作用。因變量為職業(yè)未決,預(yù)測(cè)變量為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納入回歸方程,結(jié)果見(jiàn)表4。
由表4可以看出,模型1顯示了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對(duì)職業(yè)未決的預(yù)測(cè)效應(yīng)顯著(β=-0.27,t=- 4.02,p<0.001),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對(duì)職業(yè)未決有顯著的負(fù)向影響關(guān)系,本研究假設(shè)1得到驗(yàn)證。
(四)情感舒適度在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程度與職業(yè)未決間的中介作用
采納Baron和Kenny及溫忠麟等人的中介作用檢驗(yàn)程序,采用線(xiàn)性回歸進(jìn)行分析。首先,考察了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對(duì)職業(yè)未決的作用。其次,為考察情感舒適度中介作用的存在,分別分析了情感舒適度與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和職業(yè)未決的關(guān)系。如果情感舒適度分別與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職業(yè)未決顯著相關(guān),則表明有存在中介作用的可能。再次,在回歸模型中加入中介變量情感舒適度,觀察情感舒適度是否對(duì)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與職業(yè)未決的關(guān)系產(chǎn)生影響。如果由于情感舒適度的作用,使得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與職業(yè)未決之間的關(guān)系減弱或消失,表明存在部分或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應(yīng)分析結(jié)果見(jiàn)表5。
由表5可以看出,模型1和模型2分別顯示了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對(duì)職業(yè)未決的預(yù)測(cè)效應(yīng)顯著(β=-0.27,t=-4.02,p<0.001),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對(duì)情感舒適度的預(yù)測(cè)效應(yīng)顯著(β=0.22,t=3.30,p<0.001)。此處完成Baron和Kenny(1986)提出的中介檢驗(yàn)的第一個(gè)條件。模型3中,情感舒適度預(yù)測(cè)職業(yè)未決時(shí),情感舒適度對(duì)職業(yè)未決的回歸系數(shù)也是顯著的(β=-0.73,t=-15.30,p<0.001)。此處完成Baron和Kenny(1986)提出的中介檢驗(yàn)的第二個(gè)條件。在滿(mǎn)足了自變量(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可顯著預(yù)測(cè)因變量(職業(yè)未決)和中介變量(情感舒適度),中介變量可顯著預(yù)測(cè)因變量的檢驗(yàn)條件之后,可以進(jìn)一步對(duì)情感舒適度在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與職業(yè)未決關(guān)系的中介效應(yīng)進(jìn)行分析。模型4結(jié)果顯示,當(dāng)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和情感舒適度同時(shí)預(yù)測(cè)職業(yè)未決時(shí),情感舒適度對(duì)職業(yè)未決的回歸系數(shù)仍十分顯著(β=-0.70,t= -14.56,p<0.001),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對(duì)職業(yè)未決的回歸系數(shù)卻大大降低(β=-0.11,t=-2.31,p<0.01),而顯著性仍存在。
綜上所述,中介變量檢驗(yàn)程序?qū)β殬I(yè)定向認(rèn)知、情感舒適度、職業(yè)未決程度三者的關(guān)系進(jìn)行了實(shí)證檢驗(yàn),結(jié)果表明,在引入情感舒適度變量后,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與職業(yè)未決依然呈顯著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但顯著性降低,這一結(jié)果支持了本研究提出的情感舒適度是中介變量的假設(shè)2,且為部分中介效應(yīng)。即在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影響職業(yè)未決的過(guò)程中,情感舒適度起著部分中介作用。
為進(jìn)一步計(jì)算高職學(xué)生職業(yè)決策中情感舒適度這一部分中介效應(yīng)在總效應(yīng)中的比例,在以上回歸模型的基礎(chǔ)上建立三個(gè)標(biāo)準(zhǔn)化回歸方程,結(jié)果見(jiàn)表6。
從輸出結(jié)果計(jì)算得出,情感舒適度的中介效應(yīng)值為-0.17,由0.30×(-0.55)所得;總的效應(yīng)值為-0.29,由-0.12+(-0.17)所得。中介效應(yīng)占總效應(yīng)的比例為58.62%。情感舒適度的中介路徑見(jiàn)圖1。
四、討論
(一)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對(duì)職業(yè)未決有負(fù)向影響關(guān)系
研究結(jié)果表明,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與職業(yè)未決總分存在顯著負(fù)相關(guān),進(jìn)一步的回歸分析結(jié)果表明,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對(duì)職業(yè)未決有顯著的負(fù)向影響關(guān)系。具體表現(xiàn)為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程度越高,那么職業(yè)阻礙越少。反之,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程度越低,職業(yè)決策阻礙越多。這一結(jié)論與Jones 和 Chenery 在研究中的結(jié)論相反,但與臺(tái)灣學(xué)者楊淑珍的研究結(jié)果相一致。在楊淑珍的職業(yè)決策研究中,所測(cè)的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量表與職業(yè)未決量表呈顯著負(fù)相關(guān)(r=-0.77),同時(shí)她還認(rèn)為個(gè)體有焦慮傾向時(shí)會(huì)妨礙其做出職業(yè)選擇或?qū)ι臓顟B(tài)產(chǎn)生焦慮和不適感[14]。因此,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是職業(yè)決策個(gè)體對(duì)于未來(lái)生涯、職業(yè)方向和目標(biāo)等所抱持的確定程度及認(rèn)知狀態(tài),可以作為理解職業(yè)決策中出現(xiàn)職業(yè)未決的一個(gè)重要預(yù)測(cè)變量。
(二)情感舒適度對(duì)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影響職業(yè)未決的中介作用
假設(shè):檢驗(yàn)結(jié)果表明,情感舒適度在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與職業(yè)未決間起部分中介作用,即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一方面會(huì)對(duì)職業(yè)未決產(chǎn)生直接影響,另一方面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對(duì)職業(yè)未決產(chǎn)生的影響有一部分是通過(guò)中介變量情感舒適度實(shí)現(xiàn)的,情感舒適度是有效提高高職學(xué)生職業(yè)決策的重要因素。
首先,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對(duì)職業(yè)未決產(chǎn)生直接影響解釋為: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是個(gè)體對(duì)未來(lái)職業(yè)生涯的一種積極準(zhǔn)備狀態(tài),高職學(xué)生的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程度越高,個(gè)體能更好地認(rèn)知自我的職業(yè)素養(yǎng)、能較為理性地思考與計(jì)劃未來(lái)職業(yè)的發(fā)展,排除職業(yè)決策中的阻礙因素,最終作出恰當(dāng)職業(yè)選擇。其次,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對(duì)職業(yè)未決的影響有一部分是通過(guò)情感舒適度來(lái)實(shí)現(xiàn)的可解釋為:在舒適狀態(tài)下,即使個(gè)體在理想與就業(yè)現(xiàn)實(shí)產(chǎn)生落差時(shí)也依然能潛意識(shí)自我削弱職業(yè)未決時(shí)帶來(lái)的不安感,并專(zhuān)注于找出職業(yè)困難的解決辦法。情感舒適的狀態(tài),使得高職學(xué)生在面臨職業(yè)決策困難時(shí)能更多地激發(fā)出個(gè)體潛在的心理資源,積極樂(lè)觀地去通過(guò)提升自身素質(zhì)獲取職業(yè)信心,不斷從職業(yè)決策遇到的挫折與困難中獲得經(jīng)驗(yàn),主動(dòng)利用各種職業(yè)信息資源進(jìn)行職業(yè)規(guī)劃和探索,克服職業(yè)決策的阻礙。
五、啟示
由于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程度對(duì)職業(yè)未決行為有顯著負(fù)向影響,且該影響還受到了情感舒適度的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在實(shí)際的教育中,要想改善高職學(xué)生的職業(yè)決策力,平衡職業(yè)決策的良好狀態(tài),一方面應(yīng)該加強(qiáng)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教育,通過(guò)職業(yè)定向性認(rèn)知激發(fā)學(xué)生內(nèi)在的職業(yè)認(rèn)同以形成有效職業(yè)決策,另一方面不可忽略職業(yè)決策過(guò)程中情感舒適度的部分中介作用。具體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開(kāi)展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教育,激發(fā)學(xué)生職業(yè)認(rèn)同感
高職學(xué)生相對(duì)擁有較為豐富的專(zhuān)業(yè)理論、技藝技能、操作經(jīng)驗(yàn)等職業(yè)知識(shí),卻沒(méi)能把這方面的認(rèn)識(shí)與職業(yè)結(jié)合起來(lái),導(dǎo)致無(wú)法明晰自己的職業(yè)定向并選擇適當(dāng)?shù)穆殬I(yè)路徑。這啟發(fā)教育者應(yīng)重視開(kāi)展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教育。
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教育的首要核心任務(wù)是幫助學(xué)生完成職業(yè)生涯規(guī)劃,在深度認(rèn)知自我和職業(yè)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職業(yè)定向培養(yǎng)。實(shí)際上,高職院校中大部分學(xué)生職業(yè)路徑的發(fā)展還是依賴(lài)于所接受的職業(yè)教育的,學(xué)校根據(jù)自身特點(diǎn)和市場(chǎng)需求為高職學(xué)生制定的培養(yǎng)目標(biāo)及研究方向會(huì)密切影響到高職學(xué)生職業(yè)方向的確定及職業(yè)路徑的選擇。擬定職業(yè)生涯規(guī)劃時(shí),首先需要讓學(xué)生了解該培養(yǎng)目標(biāo)與自我認(rèn)識(shí)是否一致。學(xué)生個(gè)體只有在學(xué)校和市場(chǎng)需求共同要求的總培養(yǎng)目標(biāo)下,對(duì)自己想要從事的職業(yè)制定系統(tǒng)而行之有效的規(guī)劃,積極參與實(shí)習(xí)實(shí)踐和探索職業(yè)世界,這樣才能契合市場(chǎng)需求,不斷為自身職業(yè)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逐步明確職業(yè)定向。
其次,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教育是轉(zhuǎn)移或強(qiáng)化學(xué)生職業(yè)心理和職業(yè)行為,培養(yǎng)學(xué)生個(gè)體形成職業(yè)認(rèn)同的過(guò)程。職業(yè)認(rèn)同是學(xué)生個(gè)體有意識(shí)地進(jìn)行職業(yè)生涯規(guī)劃的基礎(chǔ),有利于幫助完成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教育。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部分高職學(xué)生因起初的專(zhuān)業(yè)興趣已確立短期的職業(yè)定向。但通過(guò)日常學(xué)習(xí)和實(shí)習(xí)實(shí)踐,獲得了關(guān)于自身未來(lái)職業(yè)的局限性信息,職業(yè)的某一弊端有可能會(huì)因?qū)W生個(gè)體對(duì)該職業(yè)的認(rèn)識(shí)不全面或自我認(rèn)識(shí)不清晰而被放大,造成職業(yè)認(rèn)知偏誤,無(wú)法形成職業(yè)認(rèn)同。教育工作者應(yīng)加強(qiáng)專(zhuān)業(yè)建設(shè)以提高專(zhuān)業(yè)含金量,通過(guò)培養(yǎng)專(zhuān)業(yè)認(rèn)同來(lái)激發(fā)高職學(xué)生的職業(yè)認(rèn)同,以達(dá)到擴(kuò)充高職學(xué)生的職業(yè)認(rèn)知基礎(chǔ),促進(jìn)職業(yè)成熟度,提高其接受和甄別外界職業(yè)信息的全面性和準(zhǔn)確度的目的。
(二)關(guān)注情感舒適度的狀態(tài)變化,幫助樹(shù)立職業(yè)信心
情感舒適度在職業(yè)定向認(rèn)知與職業(yè)未決的關(guān)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在啟發(fā)高職學(xué)生職業(yè)決策行為時(shí),教育者不能僅滿(mǎn)足于學(xué)生個(gè)體做出職業(yè)決策的高效率,更應(yīng)該讓學(xué)生個(gè)體在職業(yè)決策制定與執(zhí)行過(guò)程中體驗(yàn)到舒適感,積極的舒適體驗(yàn)會(huì)產(chǎn)生增力性,由此形成內(nèi)化的動(dòng)力付諸于實(shí)踐,這種內(nèi)化的動(dòng)力是學(xué)生個(gè)體保持長(zhǎng)期有效決策和職業(yè)生涯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必要前提。
具體來(lái)說(shuō),教育者應(yīng)注重高職學(xué)生個(gè)體的心理需求,設(shè)立職業(yè)心理咨詢(xún)中心,建立職業(yè)健康檔案。在進(jìn)行咨詢(xún)輔導(dǎo)時(shí)通過(guò)特定的話(huà)題或情境引導(dǎo)高職學(xué)生,鼓勵(lì)高職學(xué)生表達(dá)自己在職業(yè)決策中的心理障礙,以便把握其情感舒適狀態(tài)的變化,幫助高職學(xué)生緩解挫敗、不安、焦慮、惶恐、緊張、失落等消極心理。
其次,采用以團(tuán)體輔導(dǎo)為主,講座為輔的形式,成立互幫小組。團(tuán)體輔導(dǎo)的基本原理是其呈現(xiàn)一個(gè)類(lèi)似現(xiàn)實(shí)的社交生活情境,使參加者在其中獲得一些生活經(jīng)驗(yàn),并將之應(yīng)用于日常與他人的互動(dòng)中。在團(tuán)體輔導(dǎo)中,一方面讓高職學(xué)生通過(guò)他人對(duì)自我職業(yè)態(tài)度與行為的分析評(píng)價(jià),以“鏡我”的方式加深對(duì)自我的認(rèn)識(shí),明晰自身存在的問(wèn)題以便有針對(duì)性地解決。另一方面讓高職學(xué)生借助集體的力量,通過(guò)傾聽(tīng)、觀察、學(xué)習(xí)、模仿、分享等方式吸收內(nèi)化團(tuán)隊(duì)其他成員多方面的信息和經(jīng)驗(yàn)。這不僅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學(xué)生個(gè)體獨(dú)自承受的心理壓力,并且使高職學(xué)生在團(tuán)體的人際關(guān)系中學(xué)會(huì)自我激勵(lì)和換位思考,樹(shù)立職業(yè)信心。
參 考 文 獻(xiàn)
[1]陳世平,張艷.風(fēng)險(xiǎn)偏好與框架效應(yīng)對(duì)大學(xué)生職業(yè)決策的影響[J].心理與行為研究,2009(7):183-187.
[2]李付俊,孟續(xù)鐸.我國(guó)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升級(jí)下的高校畢業(yè)生就業(yè)——研究回顧與展望[J].人口與經(jīng)濟(jì),2014(6):91-101.
[3]方翰青,譚明.論高校職業(yè)咨詢(xún)保障體系的構(gòu)建[J].教育學(xué)術(shù)月刊,2011(2):83-85.
[4]彭永新,龍立榮.國(guó)外職業(yè)決策理論模式的研究進(jìn)展[J].教育研究與實(shí)驗(yàn),2000(5):45-49.
[5]Ofstaff M K M. A Model of Guidance for Career Decision-making[J]. Vocational Guidance Quarterly,1966,15(1):2-10.
[6]V Germeijs. Indecisiveness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Career Decision-making Process: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and the Mediational Role of Anxiety[J].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2006,53(4):397-410.
[7]S Peterson.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Integration, and the Likelihood of Managerial Retention in Governmental Agencies[J].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Quarterly,2009,20(4):451-475.
[8]仵自連.中國(guó)高等職業(yè)教育回顧與展望[M].徐州:中國(guó)礦業(yè)大學(xué)出版社,2008:148.
[9]張建.職業(yè)教育的追問(wèn)與視界[M].蕪湖:安徽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0:84.
[10]Jones, L. K. & Chenery, M. F. Multiple Subtypes among Vocationally Undecided College Students: A Model and Assessment Instrument[J].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1980(5):469-477.
[11]胡潔.大學(xué)生職業(yè)決策因素量表的編制及標(biāo)準(zhǔn)化[D].南昌:江西師范大學(xué),2007.
[12]溫忠麟,張雷,侯杰泰,劉紅云.中介效應(yīng)檢驗(yàn)程序及其應(yīng)用[J].心理學(xué)報(bào),2004(5):614-620.
[13]石偉平,唐智彬.增強(qiáng)職業(yè)教育吸引力:?jiǎn)栴}與對(duì)策[J].教育發(fā)展研究,2010(4):64-64.
[14]楊淑珍.生涯因素量表之編制[R].臺(tái)灣行政院國(guó)家科學(xué)委員會(huì)專(zhuān)題研究計(jì)劃成果報(bào)告,19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