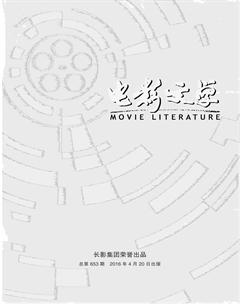新時期國產電影的敘事風格
[摘要]新時期電影是一種開放的敘述,它不會固守電影敘事的種種成規。相比傳統意義上的影片,新時期現實主義影片在戲劇化敘事手法中融入了生活流的松散與真實,使得電影的敘事風格更加貼近于真實生活,也促使影片更具有現實意義。新時期電影在傳統現實主義的敘事慣例與敘事手法基礎上,結合現在網絡文學創作的手法,使生活流與戲劇性這看似對立的兩方,在新時期電影創作中相輔相成,共同建構新時期獨有的現實主義敘事,建立了一種更加靈活、具有彈性的現實主義敘事風格。
[關鍵詞]現實主義敘事;戲劇性;新時期
0
新時期電影在傳統現實主義的敘事慣例與敘事手法基礎上,建立了一種更加靈活、具有彈性的現實主義敘事風格。在網絡文學作品爭相改編成影視作品的背景下,新時期電影的創作沒有墨守成規,從來沒有在電影這一藝術形式中使用過的敘事手段,新時期電影經過改造和挪用,也會用來達成現實主義的風格。
一、戲劇性與生活流
縱觀新時期創作出的現實主義影片,其中不乏堅持傳統戲劇性的案例。例如,王好為作品《瞧這一家子》、謝添作品《甜蜜的事業》、趙煥章作品《喜盈門》等,這類影片按照傳統戲劇性的敘事方式,故事結構采用標準的起承轉合套路,用矛盾沖突的發展將故事主線進行下去,這個過程中不同的影片會遇見某些不謀而合的部分。在這個類型的影片中,電影的敘事風格和故事結構基本是由它的題材決定的,不論是喜劇片還是恐怖片,都有其固定的套路和風格。
除了傳統的戲劇化敘事,在新時期電影作品中,不按套路出牌的生活流作品也不乏經典作品。例如王好為的作品《夕照街》,影片的故事主線是“辦大聯社”,但在電影中卻所占篇幅不多,而電影的主要內容則是靠一些看似散碎的生活化細節撐起來的。故事中吳海波和周燕燕的感情糾葛、老教授王璞的患病、石頭跟人爭吵等一些瑣碎的事情看起來都和故事主線沒有什么關系,故事行將結束的時候,老街坊們集體搬家這樣的大動作,仿佛也和主要矛盾沒什么必然關聯。滕文驥的作品《都市里的村莊》也是如此,采訪勞模是影片的故事主線,但是卻經常被一些無關的小插曲所打斷,影片中的人物結婚生子的情節與主線沒有因果關系,也對推動主要矛盾發展沒有重要意義,卻依然被生動地描繪出來。但正是因為這些生活化的瑣碎情節,使影片更加生動,更有溫度,更貼近生活,影片中所呈現的社會背景更加真實,具有現實意義,這就是本文中提到的生活流敘事風格。
新時期電影中的生活流敘事風格作品與傳統戲劇的敘事邏輯剛好相反,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更接近于小說的敘事邏輯,傳統的戲劇敘事遵循的是因果邏輯,而生活流作品中的敘事邏輯遵循的是時間流線。
二、敘事結構的現實主義
雖然新時期電影在敘事風格上融入了生活化的分散敘事,但也沒有出現類似《偷自行車的人》這樣完全生活化的零散敘事,新時期電影普遍只是將二者進行結合,并未完全拋棄戲劇性的敘事結構。這一時期的電影在戲劇性的因果邏輯和生活化的時間軸之間尋找到平衡,既保留了戲劇的故事框架,又增加了現實生活的意趣。
曾經,在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思潮的涌動下,西方許多影片完全摒棄了戲劇性的敘事結構,崇尚完全寫實的松散結構,但這種影片因為不顧及電影情節應該考慮的沖突和節奏,很難調動起觀眾的觀影情緒。然而,中國傳統文學奠定了深刻的敘事結構理念,起承轉合的脈絡是中國人很難完全拋棄的,正因為如此,新時期的影片依然保留了戲劇的結構特色,保留了影片的可觀性。
雖然新時期的影片中依然保留著因果邏輯,但這種傳統現實主義的敘事風格已經不是重點,重點是將真實的生活用白描的手法展示出來。因此,我們需要注意以下兩點:第一,傳統的戲劇化敘事結構并沒有完全被新時期電影所拒絕,畢竟電影本質上也是一種戲劇,戲劇如果要吸引觀眾就必須考慮觀眾的觀影情緒。然而,新時期電影不會為了戲劇性而做戲,為了保留影片的可觀賞性而背離真實的現實生活。第二,全面真實的寫實現實生活,這雖然是新時期電影的特色,但卻不是其核心內涵。作為一種藝術作品,它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創作者的意識和理念,創作者的思想比起現實背景更為寶貴,而這也正是影片的獨特之處和魅力之處。
在新時期電影中,依然存在虛構的元素,但這并不意味著有了虛構的成分就不再是現實主義影片。藝術是允許虛構的,身為導演是有義務通過部分虛構來使影片主題更加鮮明,使影片更具有可觀賞性的。創作者對虛構程度的把握成為判斷影片是否為現實主義題材的重點,假如對劇情的虛構不具有時代意義及現實意義,甚至完全推翻了現實的本貌,只是為了符合劇情的因果邏輯而生編硬造,這樣的虛構就是毫無價值的。
三、結尾方式的現實主義
在很多現實主義影片中,為了保持自然生活的原汁原味,降低人為設定的刻意感,都會順承情節的發展選擇一個封閉式結局。相反,在現代主義影片中,使用留白方式的開放結局會比較多,給觀眾留下想象的空間。然而,新時期的現實主義影片卻一反常態,在尊重真實生活的情況之下,依然巧妙地設計了一些開放式的結局。與現代主義影片不同的是,新時期電影結局的留白,并不是為了要給觀眾留下想象的空間,而是由于真實的社會本來就存在許多不定性,現實中的未來是不可預估的,故而,選擇開放式結局會更符合現狀。如果說現代主義影片這樣設計是出于戲劇性創作的技巧,那么新時期的現實主義電影則是為了出于尊重真實而進行的一定程度的虛構。
楊延晉的《小街》就是一部開放式結局的代表作品。《小街》中一共出現了三種結局可能,第一種結局可能是男主人公自己想象中的,這個在影片開始已經做了交代,而其他兩個結局都自然地融入了情節之中,讓觀眾誤以為那就是事實,然而隨著情節的發展,敘述者從另一個角度出現,觀眾才會看出這些結局也不過是源于虛構。《小街》屬于現實主義題材的影片,這類影片出現多種結局的可能,乍一看是不符合尊重現實的原則的,但是在電影《小街》中,楊延晉卻讓這種虛構有了憑據。“文革”時期的十年動蕩使一切都成了未知,人的命運如同浮萍一樣,不能預見。所以,在那樣的特殊時代,只有不確定才是真正符合現實生活的。在那個特殊的水深火熱的時代,人們要找的不是結局,而是新的開始。至于影片中主要人物的命運會怎樣,到底是悲還是喜,不如讓觀眾根據自己的際遇或者期望去想象。雖然新時期影片的開放式結局看起來與現代主義影片差不多,但其根本上是完全不同的。或許,未知是最真實的現實。電影《小街》將故事的結局交給觀眾去猜想,本質上是為了更加貼合現實。新時期的導演借鑒現實主義的藝術技巧來使影片更加符合真實,可見,新時期影片的敘事風格充滿了靈活彈性。
吳天明的導演作品《沒有航標的河流》的結局同樣也采用了開放式。一直到整部影片結束,關于盤老五的生死,也沒有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本來我們可以確定,盤老五為了解救所有人而死去,但這個悲觀的結局在影片的最后幾個鏡頭中又被否定,也許盤老五還活著,也許他就在不遠的前面。影片以一種留白式的結局給了觀眾猜想的余地,也給影片注入了一線生機。
很多以“文化大革命”為大背景的影片都會讓整個故事伴隨著十年動蕩的結束而落幕,用當時的大規模平反來為劇中的人物描繪一個確定的結局。例如謝晉的作品《芙蓉鎮》,秦書田和胡玉音最終獲得了圓滿的結局,但這種圓滿并不是源于影片的戲劇性設定,而是由于真實世界中十年動蕩已經宣告結束,所有因“文革”而引發的苦難自然終止。與戲劇性的通常設定不同,影片中反派角色沒有受到懲戒,更沒有被打倒,他們也回歸到了生活的正軌,這是尊重當時時代背景的表現。假如影片《芙蓉鎮》落幕的時候,“文革”還沒有宣告結束,故事中的主要沖突就還要進行下去,整個故事的設定是參照真實歷史的,很難出現什么意外的神來之筆來化解這些矛盾。以李國香為代表的反派人物不會突然收手,停止對他們的傷害,秦書田和胡玉音也不可能突然增加了某種力量戰勝反派,所以故事只有按照實際歷史的軌跡發展下去,才可能獲得合情合理的結局。“文革”結束之后,必然會有一個圓滿的結局。但在影片《沒有航標的河流》之中,十年“文革”還沒有完全結束,整個社會還處于動亂之中,雖然影片的主線已經結束了,然而“文革”沒有結束,整個社會現實還處于一種待定的狀態,所有矛盾沒有得到一個確切的解決方式。假如盤老五已經確定死去了,那整部影片就是一個徹底的悲劇,影片的其他矛盾還一樣得不到答案,假如盤老五沒有死,故事中的矛盾就應該繼續尋找解決方式,因此,吳天明用這種不確定的結局給予影片時間性的停頓,最終沒有給整個故事畫上句號,而是寫上了令人揣測的省略號。
以反映當代現實問題為題材的影片,雖然有時候也采用了確定性的結局,但由于時代一直在發展,角色的命運與現實生活在平行的時間軸上,所以我們不確定社會外因會有什么樣的變化,所謂的確定性結局也并不是純粹的確定。所以,這類影片的結局雖然看起來是封閉性的,但由于大環境存在不確定因素,這種封閉也會存在部分開放性的內涵。
例如,以當代陜北農村生活為背景的作品《人生》,故事的結局,主角高加林沒有實現他的理想,離開了縣城,又回到了家鄉農村,高加林的人生又回到了原點。這個結局看似是封閉性的,高加林的這次走出去以失敗告終,但我們卻不能因此認為以后的高加林也走不出去,高加林以后的命運是未知的,未來充滿了不定性,會發生很多種可能。畢竟,高加林的失敗有時代外因的作用,當時的農村和城鎮幾乎是兩個社會階層,但隨著時代的發展,這個鴻溝自然會消除,所以,高加林以后能否成功走出去,我們有理由產生多種猜想。
多數新時期影片依然會選擇固定的封閉式結局,并且在確定的結局之中加入了現實主義思考。有的影片不以傳統的戲劇性手法來結束故事,而是隨著某個真實的時間點的到來而終結劇情;有的影片雖然整個故事在戲劇性的敘事結構中結束,雖然客觀上結局是肯定的,但主觀上卻對這樣的結局給出懷疑,摻入現實主義的反思。
好萊塢類型電影的敘事結構都是充滿戲劇色彩的,其結局也都是確認的封閉性結局,這類影片用沖突來推動劇情發展,又用戲劇技巧的設計將沖突解決。與之不同的是,新時期影片雖然也采取確定的唯一式結局,故事中的矛盾也都一一得到解決,可是這些矛盾的解決不是依靠戲劇手法的設定,而是依靠時間自然而然地去化解。假如影片中出現無法化解的矛盾,新時期影片便會用開放式的結局留下思考的余地,而不是用人為的戲劇設定來化解。
因此,縱然新時期影片出現了很多封閉式結局,但從本質上來看,這不是在結束這個故事,而是將故事暫時告一段落,讓未來去給它一個現實的結局。故事存在虛構的因素,當故事展現在畫面中的時候是脫離于現實的,故事結尾又將它重新插入到真實的時間軸上,讓它回歸現實世界。
四、結語
新時期電影將生活流的松散敘事融入傳統戲劇性的敘事結構中,兩者相輔相成,形成了現實主義影片中極富有靈活性的敘事特色。在網絡文學作品改編影視劇熱的背景下,我們的新時期電影超越了意大利的“生活流”作品,在崇尚真實生活的基礎上,依然保留了許多傳統現實主義電影的敘事風格。縱然許多新時期電影人崇尚現實,但電影作為一種藝術產品,它雖源于生活,卻又高于生活,新時期的電影人為了使真正的現實更具有觀賞性,依然在影片創作中加以適當的藝術處理,讓電影中的生活比現實中更加繪聲繪色。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16年河南省高等學校重點科研計劃支持基金項目“網絡文學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及對策研究”(項目編號:16A880031)。
[參考文獻]
[1] 王一川.當前中國現實主義范式及其三重景觀——以新世紀以來電影為例[J].社會科學,2012(12).
[2] 張智華.我國當代現實主義電影思潮的變化與發展[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04).
[3] 高明.淺析現實主義電影與類型電影[J].大舞臺,2011(04).
[4] 沈義貞.現實主義視角下的臺灣電影演變[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10).
[5] 呂良.將現實苦難化作夢境的無意識——論超現實主義電影與超現實主義繪畫[J].藝術科技,2014(12).
[作者簡介] 張洪順(1969—),男,河南鄭州人,碩士,黃河交通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及教學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