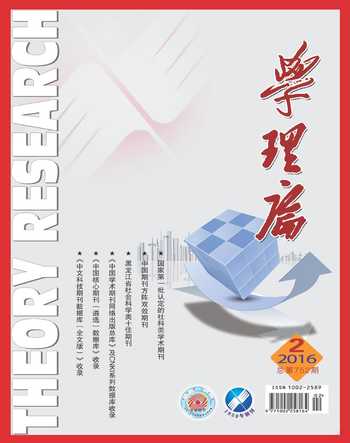淺議20世紀30年代的文化民族主義
劉付承
摘 要:經濟、政治的發展決定文化的發展,文化與政治、經濟、相互交融。五千年來所鑄造的中華民族文化,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之下成為文化民族主義興起的內在動因。20世紀30年代,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新文化運動以來的西化思潮流派逐漸分化,轉而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文化的作用,文化民族主義隨之興起。
關鍵詞:傳統文化;文化民族主義;民族復興
中圖分類號:K26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2-2589(2016)02-0144-02
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是維系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內核紐帶,五千年來歷史文化傳承,不僅塑造了中國人獨有的文化內涵,還孕育了中華民族在民族危機下濃烈的民族主義。九一八事變后,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中國面臨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先進知識分子逐漸改變西化的態度,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文化在實現救亡圖存中的作用,文化民族主義由此興起和發展。20世紀30年代文化民族主義的盛行,是傳統文化自身對外來文化的自覺反抗,對今天仍然具有借鑒意義。
一、20世紀30年代文化民族主義者的內涵
近代以來,在中西文化碰撞中,隨著西學的廣泛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更多被認為是阻礙社會進步的重要原因,漸而被排斥,新文化運動期間,“民主”與“科學”成為時代潮流,西化思潮占據了社會思想發展的主導,傳統文化遭受猛烈批判和打擊。然而20世紀30年代日本侵華,民族危機加深,從中華文化謀求自身救亡成為另一種選擇,“民主”“科學”“西化”等詞語逐漸減少,而對于傳統文化的提倡日漸突顯。從文化發展派別來看,近代以來,文化派別眾多,不僅存在著主張維護傳統文化的文化保守派,還存在拋棄中國傳統文化的全盤西化派,也存在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間派別。九一八事變之后,為了反對日本侵略的需要,文化民族主義興起并逐漸興盛,即使全盤西化論者也有些向此轉變。文化民族主義大力提倡復興中國民族文化,從而實現中國復興。其內涵主要體現如下兩點。
(一)民族文化復興是民族復興的基礎和前提
文化民族主義認為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先要復興中華民族文化,認為民族文化復興是民族復興的基礎和前提。一方面,復興民族文化的目的是要提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識,以挽救民族危亡。要打敗日本侵略,必須要樹立強烈的民族精神和頑強的反抗意志,中國傳統文化所蘊含的愛國主義精神恰恰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源泉,提倡傳統文化有利于培育民族精神,實現民族復興。20世紀30年代中期,王德華在《中國文化史要略》“敘例”中寫道:“中國人之應當了解中國文化,則無疑問,否則,吾族艱難奮斗、努力創造之歷史,無由明了,而吾人之民族意識,即無由發生,民族精神即無由振起。……茲者國脈益危,不言復興則已,言復興,則非著重文化教育,振起民族精神不可。本書之作,意即在此。”[1]顯然,文化民族主義者并非文化保守主義,在時代變化民族危亡之際,從復興民族精神的角度出發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另一方面,民族復興的一個重要的內容是要實現現代化,文化民族主義者認為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可以為中國現代化的實現提供一種價值基礎,因此提倡復興儒學,要求重新審視儒家思想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價值。張君勱認為儒家思想是一種理智的自主,智慧的發展,思考與反省的活動,具有質疑和分析的方式,復興儒家思想足以為中國現代化發展提供一種新的思想方法和原則,從而構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基本方法,這種新的思想方法將是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基礎和先驅[2]。此外,梁漱溟認為,要實現“中國復活”的唯一途徑就是要“昭蘇中國人的人生態度”,而“人生態度”集中體現為文化態度,源于民族文化精神與民族文化傳統,在這里,他指出:“一民族之有今日結果的情景,全由他自己以往文化使然:西洋人之有今日全由于他的文化,印度人之有今日全由他的文化,中國人之有今日全由于我們自己的文化,而莫從抵賴。”[3]文化具有民族性,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由于歷史文化、社會實踐的不同,文化發展各有其特點,而文化的個性也是一個民族國家特有的標志,作為擁有五千多年歷史積淀的中華民族文化更是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內核紐帶。因此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必須要保有自己民族文化的特點。
(二)民族文化復興關鍵是要提振本民族文化自信心,重視傳統文化價值
文化民族主義者通過對傳統文化的審視,指出要實現民族文化復興關鍵在于如何提高對中國自身傳統文化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因此,他們提倡要重新審視自己的文化,把時代精神灌注到傳統文化中,以挽救民族危亡為目的。同時,他們意識到時代要求他們擔當起復興中華文化的歷史責任,毅然以弘揚中國文化為根本宗旨。指出要復興中華文化就必須先樹立國人對民族和文化的自信心,錢穆認為傳統與現代化之間有一線索貫穿其中:“意義價值或生命傳統”。因此,“貴能由傳統中求現代化,非可打倒了傳統來求現代化。”[4]九一八事變后,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文化民族主義者對于傳統文化價值在救亡中的作用認知更加深刻,張君勱在翻譯德國哲學家費希特《對德意志國民講演》時,對費希特闡述的民族復興三個重要原則大為贊同:第一,在民族大受懲創之日,必須痛自檢討過失;第二,民族復興,應以內心改造為重要途徑;第三,發揚光大民族在歷史上的成績,以提高民族自信力。在這三原則中,提高民族自信力又是原則中之原則。所以中國要實現民族和文化復興,就必須提高民族自信力[5]。
二、20世紀30年代文化民族主義者對傳統文化的思考和審視
文化民族主義的興起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民族危機是文化民族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根源,鴉片戰爭后,中國就一直遭受外來侵略和壓迫,面臨著被列強瓜分和亡國滅種的局面。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先進的中國人為實現救亡圖存而不斷向西方尋求救國之路。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開明地主階級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內憂外患,洋務派“中體西用”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甲午慘敗后,資產階級維新派掀起了一場自上而下的維新變法運動;戊戌政變后,資產階級革命派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腐朽統治,建立,“中華民國”……其總體特征都是在向西方尋求救亡路徑,從“技術”到“制度”到“文化”,學習的層次不斷加深。自鴉片戰爭直到九一八事變,學習西方非但不能實現救國,反而民族危機日漸加深,先進中國人對于再向西方學習已經產生了懷疑,再加上此時全國掀起了抗日高潮,再宣揚向西方學習顯然不符合歷史實際,為滿足抗日反侵略的需要,文化民族主義認為傳統文化有自身的價值,能夠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20世紀30年代文化民族主義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重新審視,更多的民族主義者提倡重新認識傳統文化,錢穆主張“回頭重認中國傳統文化之真價值”,對傳統文化要有“新估價”,以兼收并蓄的文化氣度“認識西方文化之真精神”,在中西文化碰撞中達到中西文化“融會調和”。事實上,中國文化自身具有對外來文化接受、吸收、消融的特點和文化傳統,“直上直下,無粗無細,在內在外,兼容并包,如納眾流于大海,泱泱乎誠大平原民族文化應有之征象也”。再歷300年之期,中國文化才能對西方文化“充分接納消融”[6]。事實上,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所固有的文化系統,是維系整個中國民族得以存在和生存的精神紐帶,在抗日戰爭的年代必然有其存在的意義和作用,文化民族主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新認識仍具有現實價值。
值得提出的是,20世紀30年代的文化民族主義并非文化保守主義,也不同于全盤西化派,它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辯證思考,也反對文化復古主義,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存在著許多缺陷和不足,復興中華民族文化,并不是一味地遵循和守護,而是需要進行時代的改造,主張把時代精神融合到傳統文化之中,與時俱進,形成新的民族精神,從而實現民族復興。“貴能由傳統中求現代化,非可打倒了傳統來求現代化”。文化民族主義主張實現現代化,反對文化閉關自守,張君勱說:“文化之改造,非易事也,舍己而求人,是為忘其本根,采他人之方而不問其于己之宜否,是為藥不對癥,心目中但欣羨他國之制,而忘其本身之地位,是為我喪其我。雖欲建樹而安從建樹乎?”[7]同時,在現代化過程中,文化民族主義者認為中國文化也要現代化,要創新,要發展“我們所主張的中國本位,不是抱殘守缺的因襲,不是生吞活剝的模仿,不是中體西用的湊合,而是以此時此地整個民族的需要和準備為條件的創造。”[8]
三、文化民族主義的當代價值和現實意義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紐帶,審視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對于處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歷史節點來說,是具有深刻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的。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一些社會問題也隨之而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從傳統文化中尋找解決途徑,甚至出現了一些新的理論,如“新儒學”。事實上,在發展現代化的過程中,優秀傳統文化與實現現代化的時代任務并不是矛盾的,相反,在某種程度上來講,二者具有契合之處,傳統文化中包含著諸多積極因素,如儒家思想之仁、義、禮、智、信未嘗不可以為解決現當代社會問題提供一種精神范式;“德治”“禮治”等傳統的治國思想與現代所提倡的“民主”“法制”精神并非沖突的,二者可以相輔相成。馮友蘭認為,“中國人的精神力量”或“道德力”有助于中國的現代化。馮友蘭積極提倡現代化,但“認為在基本道德或基本的精神力量這一方面,是無所謂現代化的,或不現代化的。某種社會制度是可變的,而基本道德則是不可變的。可變者有現代化或不現代化的問題,不可變者無此問題”。馮友蘭說的“中國人的精神力量”或“道德力”特別指“墨家、儒家的嚴肅,及道家的超脫;儒家、墨家的‘在乎,及道家的‘滿不在乎”[9]。
總而言之,20世紀30年代的文化民族主義者,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歷史背景之際,結合現代化發展的因素,從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出發,主張繼承和弘揚優秀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培育民族精神,提高民族文化認同感,增強民族文化創造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和競爭力,來探尋實現民族復興、實現現代化發展所需的文化價值支撐點,體現了其民族凝聚、民族認同和民族復興立場上,這是值得肯定的。
參考文獻:
[1]賴希如.中華民族性弱點之改造論[J].建國月刊,1935(5).
[2]單純.民族復興之路·中國精神[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
[3]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4]錢穆.晚學盲言[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2004.
[5]張君勱.歐美派日本派之外交政策與吾族立國大計[J].再生,1933(1).
[6]錢穆.東西文化之再探討[J].華文月刊,1930(3).
[7]張君勱.明日之中國文化[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
[8]王新命.我們的總答復[J].文化建設,1935(8).
[9]馮友蘭.馮友蘭文選[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