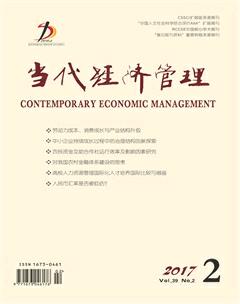基于面板數(shù)據(jù)模型的中國(guó)“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影響因素研究
楊勇++李忠民



摘 要相對(duì)而言,國(guó)內(nèi)對(duì)“四化”同步的研究較多,而對(duì)“五化”協(xié)同的研究處于剛剛起步階段,相應(yīng)的對(duì)“五化”協(xié)同的影響因素的研究還尚未涉及。文章通過(guò)耦合度方法構(gòu)建了“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指數(shù),并對(duì)2001~2013年全國(guó)、三大地區(qū)與各省市區(qū)進(jìn)行了協(xié)同度的測(cè)度,結(jié)果表明,各地區(qū)“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指數(shù)呈現(xiàn)上升趨勢(shì),區(qū)域之間協(xié)同度趨于收斂。在此基礎(chǔ)上,構(gòu)建了市場(chǎng)、政府與社會(huì)三個(gè)維度的影響因素的框架體系,并采用面板數(shù)據(jù)模型對(duì)全國(guó)以及三大地區(qū)的“五化”協(xié)同度影響因素進(jìn)行了定量分析,實(shí)證結(jié)果顯示了人均GDP與人均財(cái)政支出在兩個(gè)維度均高度顯著,人均貸款余額均不顯著,其余各指標(biāo)在不同維度顯著性差異較大。
關(guān)鍵詞“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指數(shù);耦合度模型;固定效應(yīng)模型
[中圖分類(lèi)號(hào)]F124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 A [文章編號(hào)]1673-0461(2017)02-0006-05
一、引言與文獻(xiàn)綜述
從“兩化”融合、“三化”協(xié)調(diào)、“四化”同步到“五化”協(xié)同,這個(gè)系列概念提出的過(guò)程充分反映了人們對(duì)發(fā)展中不斷出現(xiàn)的新現(xiàn)象、新問(wèn)題、新挑戰(zhàn)進(jìn)行的思考與采取的相適應(yīng)的行動(dòng)。理念貼近于現(xiàn)實(shí),更凸顯對(duì)理論進(jìn)行現(xiàn)實(shí)分析的意義,而對(duì)新理念的定量化的研究則可以更好地建立標(biāo)準(zhǔn)化的衡量依據(jù)。“五化”協(xié)同的提出時(shí)間較短,與之相應(yīng)的研究成果較少,更是鮮有對(duì)其定量化的研究。而先前基礎(chǔ)性的研究為我們開(kāi)展“五化”協(xié)同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鑒。如錢(qián)麗等(2012)認(rèn)為基礎(chǔ)教育水平、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以及R&D經(jīng)費(fèi)投入對(duì)“三化”耦合協(xié)調(diào)度的提升具有積極的影響,而農(nóng)村金融支持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對(duì)耦合協(xié)調(diào)度的影響并不明顯;郭振(2013)認(rèn)為不同區(qū)域的自然條件、資源稟賦、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和管理水平對(duì)“三化”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有較多影響;李裕瑞等(2014)認(rèn)為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村的社會(huì)投資、財(cái)政投入及金融支持,以及大中型企業(yè)發(fā)展、道路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居民消費(fèi)等因素對(duì)“四化”同步發(fā)展的影響較為穩(wěn)健;曾福生等(2013)、周振等(2015)則分別利用SBM-HR- Rdgopribit模型和隨機(jī)效應(yīng)有序pribit模型從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角度分析了農(nóng)業(yè)發(fā)展對(duì)“四化”協(xié)同發(fā)展的制約作用;舒季君等(2015)構(gòu)建了面板數(shù)據(jù)模型從全國(guó)、東中西部對(duì)影響“四化”同步發(fā)展水平的主要因素進(jìn)行了定量分析,結(jié)果表明經(jīng)濟(jì)發(fā)展、教育與信息化水平是我國(guó)“四化”同步發(fā)展時(shí)空分異的關(guān)鍵因素,財(cái)政與投資水平、對(duì)外開(kāi)放程度、交通、人口的作用較為顯著。以上主要針對(duì)“五化”同步中的部分內(nèi)容進(jìn)行了分析,或從某一化角度分析了對(duì)整體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影響程度,目前尚未有對(duì)“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的影響因素分析成果,本文基于2001~2013年全國(guó)31個(gè)省市自治區(qū)的面板數(shù)據(jù),構(gòu)建了“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指標(biāo)體系,并利用耦合度指標(biāo)評(píng)價(jià)方法測(cè)度了各地區(qū)“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水平,從市場(chǎng)基礎(chǔ)、政府支持以及社會(huì)資源3個(gè)方面對(duì)“五化”協(xié)同的影響因素進(jìn)行了分析,揭示“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的時(shí)空分異特征,為我國(guó)區(qū)域發(fā)展規(guī)劃與決策提供參考與借鑒。
二、研究方法
(一)指標(biāo)選取與數(shù)據(jù)處理
“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的測(cè)度沒(méi)有一個(gè)公認(rèn)的統(tǒng)一的指標(biāo)來(lái)衡量,因此,我們?cè)诳茖W(xué)性、系統(tǒng)性、層次性、客觀性與代表性的原則下根據(jù)對(duì)“五化”的豐富內(nèi)涵的理解并借鑒前人研究成果多角度構(gòu)建了一個(gè)發(fā)展指標(biāo)體系,綜合反映了“五化”發(fā)展水平,如表1所示。
本文將研究對(duì)象定于全國(guó)31個(gè)省市自治區(qū),數(shù)據(jù)均來(lái)源于《新中國(guó)60年統(tǒng)計(jì)資料匯編》、《中國(guó)區(qū)域經(jīng)濟(jì)統(tǒng)計(jì)年鑒》、《中國(guó)城市統(tǒng)計(jì)年鑒》、《中國(guó)信息年鑒》以及部分省市2002~2014年統(tǒng)計(jì)年鑒,為保證數(shù)據(jù)完整性,缺失數(shù)據(jù)采用插值法進(jìn)行補(bǔ)充。
三、中國(guó)“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指數(shù)的測(cè)度
利用式(1)~(4)計(jì)算得到2001~2013年31個(gè)省市自治區(qū)的“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指數(shù),并且按照東部、中部與西部3大地區(qū)進(jìn)行了分類(lèi),計(jì)算結(jié)果如圖1所示。
為了更好的說(shuō)明“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的程度,借鑒廖重斌(1999)的做法,將協(xié)同發(fā)展度進(jìn)行了等級(jí)劃分,見(jiàn)表2。
依據(jù)上述標(biāo)準(zhǔn),2001年中國(guó)“五化”協(xié)同輕度失調(diào)型地區(qū)有2個(gè),即西藏和貴州;瀕臨失調(diào)型地區(qū)的有1個(gè)為云南;勉強(qiáng)協(xié)調(diào)型地區(qū)數(shù)目最多,達(dá)到12個(gè),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區(qū);初級(jí)協(xié)調(diào)型地區(qū)有8個(gè),東、中、西、東北4大地區(qū)均有分布;中級(jí)協(xié)調(diào)型地區(qū)有7個(gè),幾乎都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qū);良好協(xié)調(diào)型地區(qū)有1個(gè),即北京。而到2013年,各地區(qū)協(xié)同發(fā)展指數(shù)均有所增加,勉強(qiáng)協(xié)調(diào)型地區(qū)僅有西藏;初級(jí)協(xié)調(diào)型地區(qū)僅有貴州;中級(jí)協(xié)調(diào)型地區(qū)增加到11個(gè),大部分分布在中西部地區(qū);良好協(xié)調(diào)型地區(qū)增加到11個(gè),東、中、西、東北4大區(qū)域均有分布;而優(yōu)質(zhì)協(xié)調(diào)型地區(qū)增加到7個(gè),均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qū)。
從各省區(qū)“五化”協(xié)同指數(shù)的均值看,中國(guó)“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指數(shù)呈現(xiàn)出緩慢上升趨勢(shì),從2001年的0.62上升到2013年的0.83,年均增長(zhǎng)2.38%;分階段看,從“十五”到“十一五”,中國(guó)“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指數(shù)均出現(xiàn)增速下滑,再到2011~2013年的發(fā)展階段,“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指數(shù)又出現(xiàn)了增速加快的趨勢(shì)。從各省區(qū)“五化”協(xié)同指數(shù)的變異系數(shù)看,2001~2013年,全國(guó)“五化”協(xié)同的差異逐漸下降,從0.178下降到0.1103,說(shuō)明省區(qū)之間“五化”協(xié)同有趨同趨勢(shì)。西部省區(qū)“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指數(shù)增速加快,且遠(yuǎn)高于東部省區(qū)。2001~2013年間,“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指數(shù)年均增速最快的5個(gè)省區(qū)分別為貴州(5.31%)、西藏(4.2%)、云南(3.81%)、海南(3.34%)與甘肅(3.29%),除海南外均屬于西部地區(qū);而增速最慢的5個(gè)省市分別為遼寧(1.06%)、吉林(1.17%)、北京(1.19%)、內(nèi)蒙古(1.43%)與天津(1.57%),西部?jī)H有1省區(qū),其余為東部與東北省區(qū)。增速最快的貴州與增速最慢的遼寧之間的同步指數(shù)差距從2001年的0.3647降到2013年的0.1478,縮小了一半多。
四、中國(guó)“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的影響因素分析
利用面板數(shù)據(jù)回歸檢驗(yàn)“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度的影響因素,目前有一些研究基礎(chǔ),如張燕等(2006)、劉濤等(2010)、錢(qián)麗等(2012)、郭震(2013)、李裕瑞等(2014)、舒季君等(2015),借鑒以上研究成果并結(jié)合“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需要,本文主要考慮了市場(chǎng)、政府與社會(huì)3個(gè)方面的因素:①市場(chǎng)基礎(chǔ)因素。市場(chǎng)基礎(chǔ)是“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的前提和保證,本文選取了人均GDP(pgdp)指標(biāo)用來(lái)衡量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結(jié)合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的建設(shè)目標(biāo)選取了市場(chǎng)化指數(shù)來(lái)描述市場(chǎng)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市場(chǎng)化指數(shù)(mi)依據(jù)樊綱等1997~2009市場(chǎng)化指數(shù)總得分?jǐn)?shù)據(jù)運(yùn)用回歸方法得到2010~2013年的外插值。②政府支持因素。政府的支持主要體現(xiàn)在財(cái)政與金融支持,財(cái)政方面選取了人均地方財(cái)政支出(pfe)指標(biāo)用來(lái)衡量財(cái)政的支持,金融方面選取了人均貸款余額(fne)指標(biāo)用來(lái)衡量金融機(jī)構(gòu)的支持。③社會(huì)資源因素。主要考慮到人力資本因素與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因素,人力資本(hn)根據(jù)人均受教育年限計(jì)算,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選取公路密度(rd)指標(biāo)。以上數(shù)據(jù)均來(lái)自于中國(guó)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庫(kù)并進(jìn)行簡(jiǎn)單計(jì)算,對(duì)涉及到價(jià)格因素的指標(biāo)利用GDP平減指數(shù)轉(zhuǎn)換為2001年數(shù)據(jù)。為消除異方差性,對(duì)部分自變量進(jìn)行了對(duì)數(shù)化處理。
在回歸模型選擇上,通過(guò)F檢驗(yàn)與Hausman檢驗(yàn)發(fā)現(xiàn),個(gè)體固定效應(yīng)模型最優(yōu),模型的回歸結(jié)果見(jiàn)表3。
表3中的模型一為通過(guò)了檢驗(yàn)后的適合模型,從回歸結(jié)果看,經(jīng)濟(jì)總量和財(cái)政支持通過(guò)了1%的顯著性檢驗(yàn),市場(chǎng)化程度與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均通過(guò)了5%的顯著性檢驗(yàn),而金融支持與人力資本并沒(méi)有通過(guò)檢驗(yàn)。為驗(yàn)證模型的穩(wěn)健性,模型二、模型三與模型四分別剔除了部分變量,回歸結(jié)果與模型一回歸結(jié)果相差較小,待估參數(shù)的方向與顯著性沒(méi)有發(fā)生大的變化。模型五、模型六與模型七分別對(duì)我國(guó)東部、中部與西部進(jìn)行了回歸分析,以更好地進(jìn)行“五化”協(xié)同影響因素的區(qū)域差異分析。
從全國(guó)來(lái)看,人均GDP與人均財(cái)政支出對(duì)“五化”協(xié)同的影響較大,市場(chǎng)化指數(shù)與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對(duì)“五化”協(xié)同的影響次之,人均貸款余額與人力資本沒(méi)有通過(guò)顯著性檢驗(yàn)。模型二、模型三與模型四分別剔除了人均貸款余額、人力資本后并沒(méi)有對(duì)其余自變量的回歸結(jié)果產(chǎn)生較大的影響。人均貸款余額之所以沒(méi)有對(duì)“五化”協(xié)同產(chǎn)生顯著性作用可能的原因有2個(gè),一是多元化的融資渠道大量出現(xiàn)使得依靠貸款獲取金融支持的資金比重在逐漸降低,二是金融在支持“五化”中存在資金分配不公現(xiàn)象,如金融對(duì)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的支持力度遠(yuǎn)不及對(duì)工業(yè)化、信息化、城鎮(zhèn)化的支持,具體從金融機(jī)構(gòu)的貸款對(duì)象來(lái)看,國(guó)有企業(yè)與大型企業(yè)容易獲取較多的款項(xiàng),而中小企業(yè)面臨嚴(yán)峻的融資困境,金融并沒(méi)有一視同仁的支持“五化”的把發(fā)展。從人力資本看,在“五化”中也沒(méi)有很好的分配,如農(nóng)業(yè)與農(nóng)村中人力資本稀缺且相對(duì)水平較低,這已逐漸成為制約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瓶頸。
從地區(qū)來(lái)看,東部、中部與西部人均GDP均對(duì)“五化”協(xié)同的影響通過(guò)了1%的顯著性檢驗(yàn),人均財(cái)政支出通過(guò)了5%的顯著性檢驗(yàn),而市場(chǎng)化指數(shù)、人均貸款余額、人力資本與公路密度通過(guò)部分檢驗(yàn)或者沒(méi)有通過(guò)檢驗(yàn)。如對(duì)東部與中部而言市場(chǎng)化指數(shù)分別在1%與5%的顯著性水平上影響了“五化”協(xié)同的發(fā)展,而西部的市場(chǎng)化水平并沒(méi)有通過(guò)顯著性檢驗(yàn)。究其原因在于東部與中部地區(qū)經(jīng)濟(jì)基礎(chǔ)較為發(fā)達(dá),民營(yíng)企業(yè)發(fā)展水平較高民間資本較為活躍,尤其以環(huán)渤海、長(zhǎng)三角和珠三角為代表,市場(chǎng)環(huán)境較好,因而市場(chǎng)化的發(fā)展在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中起到了顯著性作用(韋倩,2014),相應(yīng)的也促進(jìn)了“五化”的協(xié)同發(fā)展。而西部地區(qū)要么是國(guó)有企業(yè)占比較大,民間資本活動(dòng)范圍有限,要么是市場(chǎng)環(huán)境較差導(dǎo)致民間投資較少,非公經(jīng)濟(jì)發(fā)展緩慢,因而“五化”發(fā)展與“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水平較低。從回歸結(jié)果看,西部地區(qū)的人力資本對(duì)“五化”協(xié)同的影響通過(guò)了5%的顯著性檢驗(yàn),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通過(guò)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yàn),這說(shuō)明了在欠發(fā)達(dá)的西部通過(guò)人力資本的投入增加和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的改善不僅會(huì)提高“五化”發(fā)展水平,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善了“五化”之間的協(xié)同發(fā)展。
五、結(jié)論與啟示
本文利用耦合度方法測(cè)度了2001~2013年間中國(guó)“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指數(shù),并利用基于面板數(shù)據(jù)的回歸模型對(duì)影響中國(guó)“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的因素進(jìn)行了分析,概括起來(lái),主要有以下結(jié)論。
第一,考察期內(nèi)各省區(qū)“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指數(shù)均有較大的發(fā)展,不同區(qū)域之間“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指數(shù)有趨于收斂的態(tài)勢(shì);從指數(shù)增速看,西部省區(qū)的指數(shù)增速快于其他地區(qū),東部省區(qū)指數(shù)增速逐漸趨于平穩(wěn)。
第二,總體上“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的影響因素中人均GDP、人均財(cái)政支出通過(guò)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yàn),市場(chǎng)化程度與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均通過(guò)了5%的顯著性檢驗(yàn),而金融支持與人力資本并沒(méi)有通過(guò)檢驗(yàn)。
第三,分地區(qū)看,東、中、西人均GDP均對(duì)“五化”協(xié)同的影響通過(guò)了1%的顯著性檢驗(yàn),人均財(cái)政支出通過(guò)了5%的顯著性檢驗(yàn),東部與中部的市場(chǎng)化指數(shù)分別通過(guò)了1%與5%的顯著性檢驗(yàn),西部的人力資本與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分別通過(guò)了1%與5%的顯著性檢驗(yàn),人均貸款余額沒(méi)有通過(guò)檢驗(yàn)。
“五化”是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變遷過(guò)程,是社會(huì)轉(zhuǎn)型與結(jié)構(gòu)變遷的5個(gè)方面,為促進(jìn)全國(guó)與各地區(qū)“四化”同步更好的實(shí)現(xiàn)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可以做如下思考:
一是加強(qiáng)信息化與其余“四化”的融合。信息化大發(fā)展不但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生產(chǎn)方式,信息化+工業(yè)化是工業(yè)4.0的基礎(chǔ),信息化+城鎮(zhèn)化形成了智慧城市,信息化+農(nóng)業(yè)產(chǎn)生了智慧農(nóng)業(yè),信息化+綠色化實(shí)現(xiàn)了低碳發(fā)展。信息化不但是促進(jìn)“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的手段,信息化的蓬勃發(fā)展和信息技術(shù)的普遍應(yīng)用,更為縮小區(qū)域差距、促進(jìn)區(qū)域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協(xié)調(diào)、可持續(xù)發(fā)展提供了最大可能,因此,西部地區(qū)應(yīng)該大力發(fā)展信息化,促進(jìn)“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
二是注重經(jīng)濟(jì)總量的提升與財(cái)政政策的實(shí)施。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有利地促進(jìn)了“五化”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水平,而人均財(cái)政支出的增加也對(duì)各地區(qū)“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因此東、中、西各地區(qū)應(yīng)當(dāng)通過(guò)大力發(fā)展經(jīng)濟(jì)增加經(jīng)濟(jì)總量,從而擴(kuò)大財(cái)政支出水平平衡“五化”之間的協(xié)同發(fā)展。
三是針對(duì)不同區(qū)域采取相應(yīng)措施,如東、中部地區(qū)可以進(jìn)一步放開(kāi)市場(chǎng),允許更多的民營(yíng)企業(yè)進(jìn)入競(jìng)爭(zhēng)性領(lǐng)域,而西部地區(qū)則可以通過(guò)提升人力資本水平與完善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來(lái)促進(jìn)“五化”協(xié)同發(fā)展。
總體而言,各地區(qū)在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信息化、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過(guò)程中依然要堅(jiān)持改革開(kāi)放的基本國(guó)策,充分發(fā)揮市場(chǎng)主體的積極作用,進(jìn)一步推進(jìn)要素市場(chǎng)化改革進(jìn)程,并大膽探索政治領(lǐng)域的體制改革,以促進(jìn)我國(guó)市場(chǎng)體系健康發(fā)展,而政府的宏觀調(diào)控要在微觀領(lǐng)域逐步縮減,宏觀層次上要加強(qiáng)調(diào)控和管理,不能讓市場(chǎng)這只“看不見(jiàn)的手”盲目操縱,自發(fā)“決定”。
[參考文獻(xiàn)]
[1] 于瀟,劉義,柴躍廷,等. 互聯(lián)網(wǎng)藥品可信交易環(huán)境中主體資質(zhì)審核備案模式[J].清華大學(xué)學(xué)報(bào)(自然科學(xué)版),2012,52(11):1518-1523.
[2] 錢(qián)麗,陳忠衛(wèi),肖仁橋.中國(guó)區(qū)域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與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耦合協(xié)調(diào)度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經(jīng)濟(jì)問(wèn)題探索,2012(11):10-17.
[3] 郭震.工業(yè)化,城市化,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區(qū)域差異研究——基于中國(guó)1978-2009年省級(jí)面板數(shù)據(jù)的實(shí)證[J].河南社會(huì)科學(xué),2013 (2):44-46.
[4] 李裕瑞,王婧,劉彥隨,等.中國(guó)“四化”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區(qū)域格局及其影響因素[J].地理學(xué)報(bào), 2014,69(2):199-212.
[5] 曾福生,高鳴.中國(guó)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工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及其影響因素分析——基于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視角[J].中國(guó)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2013(1):24-39.
[6] 周振,孔祥智.中國(guó)“四化”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格局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基于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視角[J]. 中國(guó)軟科學(xué), 2015(10):9-26.
[7] 舒季君,徐維祥.中國(guó)“四化”同步發(fā)展時(shí)空分異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經(jīng)濟(jì)問(wèn)題探索, 2015(3):50-57.
[8] 廖重斌.環(huán)境與經(jīng)濟(jì)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定量評(píng)判及其分類(lèi)體系——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為例[J]. 熱帶地理,1999,19(2):171-177.
[9] 張燕,吳玉鳴.中國(guó)區(qū)域工業(yè)化與城市化的時(shí)空耦合協(xié)調(diào)機(jī)制分析[J].城市發(fā)展研究, 2006,13(6):46-51.
[10] 劉濤,曹廣忠,邊雪,等.城鎮(zhèn)化與工業(yè)化及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協(xié)調(diào)性評(píng)價(jià)及規(guī)律性探討[J]. 人文地理, 2010(6):4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