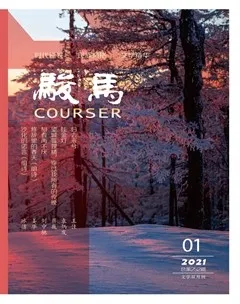眉豆
溫智慧
其實,關于眉豆這個物種,誰不熟悉她呢?彎彎的,綠綠的,可以汆,可以炒,可以涼拌,作為佐餐菜蔬,經常出現在飯桌上。
在河北老家時,我是不知道她還有“眉豆”這個別名的,只曉得她叫豆角。奶奶或媽媽挎著筐出去,一會兒工夫就會摘回一筐來,把角和蒂掐掉和蠟肉燉在一起,很是好吃的。豆角伴隨我的記憶走過了在老家的那段歲月。
那時侯,夏秋的飯桌上豆角的身影是不可或缺的。豆角這個家族有好多成員,“開鍋爛”是一種圓滾滾的豆角,肉很厚。還有一種很扁,很寬又很長的豆角,總要被奶奶和媽媽用剪刀,往返地把它剪成絲,晾開后,儲備到冬天吃,我喜歡聽剪豆角的聲音,咔、咔、咔、咔……清脆脆的,被剪碎的豆角籽粘在剪子上也是很好看的,豆角絲搭在盆沿上,搭滿后,再被掛在屋檐下的晾繩上,綠綠的幾排,一個秋季屋檐下就絢麗成幾行翠綠的風景。
后來到了阿拉善,在煤礦干活,一起干活的人講起買“梅豆”吃(做菜)。我一直不知道“梅豆”究竟是一種什么菜,后來才知道就是豆角,也就附和著呼喊“梅豆”這個名字。
直到一天在一本書上看到了“眉豆”這個詞,我才知道自己一錯就是多年,不是嗎?很簡單的意象,彎彎的“眉豆”,各品種的眉豆就是不同的眉毛呀,像“眉”一樣的豆,詩意浪漫,當時怎么就沒有想到呢?寬寬的掃帚眉,窄窄的柳葉眉,短厚的臥蠶眉,弧彎的初月眉,直帥的劍眉,細細地品味,越發感覺有韻味,有意思。
當一個錯誤,被自己堅持多年,突然發現錯了的時刻,自己的啞然失笑才具備了思考的含義。
在老家時,豆角籽叫“蕓豆”,品類繁多。奶奶和媽媽起了好多名字以示辨別,這些名字在村子里,人們都很熟悉,是通用的,先從色彩上就有紅、黃、黑、紫、白,也有豆青色的、藕荷色的。有一種蕓豆,豆體渾身白色,只是籽芽臍處是黑的(蠻像一粒眼珠),我們叫它“老母豬翻白眼”;還有小面豆,她開著水紅色的花,很鮮艷,一串串的,豆莢較短,每個莢里有三五只豆粒,角的一頭較寬,蒂的一面很瘦,過渡的驟然。一般不吃它的豆莢,只是把粉紫色的面豆煮爛,搗成泥做成豆沙餡是最好的。
還有的蕓豆身上有花紋,好似鸚鵡頭上的紋理,我們叫她“鸚鵡豆”。冬天,奶奶和媽媽要選一些蕓豆種子,把混在一起的蕓豆盛上來倒在桌子上,大家分門別類地挑選飽滿圓潤的做種子,我們小孩子比試著誰挑選的品種最多,大約有二十幾種之多吧,這在每年都是固定的儀式。所以,撿豆種就是童年里冬季開展的最有趣的賽事了。
豆角皮實容易經營,只等待結莢后,摘豆角就可以了。摘下一茬豆角,就會呼啦啦地開一茬花,六七天就再摘下一茬,豆角花泛白、泛粉地裝扮著生長她的那塊土地。
媽媽大鍋里豆角的香味早已彌漫了整個院子,給我們每人盛上一碗來吃,吃得很貪婪,很有滋味,想起一家人聚在炕桌吃飯的歲月是多么的溫馨甜美呀。現在吃飯簡直是刻意描摹,吃相懶散,完全是為了一個儀程而走的形式,難道是日子過得好了嗎?還是別的什么原因,連吃飯都在敷衍,值得去思考了。
我喜歡吃眉豆,尤其是蒜泥眉豆,我很愛吃。飯桌上也許會剩下魚、肉,但是眉豆是不會剩的,即使在宴席或飯局的最后時刻,我也會不失時機地把眉豆菜倒在我的碗里吃掉,拾回那貪婪的感覺。
生活里有好多類似“眉豆”與“梅豆”的故事,一字之間就是兩個意境。關于眉豆,勾陳出許多遠去的回憶,鉆在豆角架下聽牛郎和織女說話,是村童十二歲前必要的演練。因為奶奶說過,過了十二歲就聽不見了。我們迷信著奶奶的說法,每到農歷七月七,小孩子都會鉆在豆角架下面去聆聽,還煞有介事地告訴奶奶聽到了牛郎織女的啜泣聲和隱隱的訴說。
想起來很好笑,我們也會順著千年傳唱的一段愛情故事,沿著豆角蔓的觸角展開編織杜撰,豆角架下那細細的沙沙聲,真是那一對戀人的啜泣嗎?只曉得我們鉆出豆角架后,頭上會帶上一頂花冠,是眉豆花落而成的。
那段歲月濡染了我們幼小的詩心,盡管不會寫詩,但是關于詩的理解還是有的,那就是:豆角架下傾聽遙遠的天音呀。
“眉豆”這兩個字,這一個稱謂,就是一首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