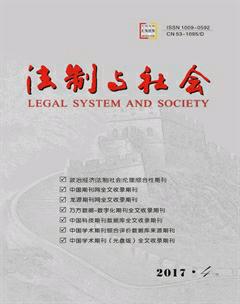“明知他人報(bào)警而等候”型自首在司法實(shí)踐中存在的問題及探討
摘 要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印發(fā)《關(guān)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規(guī)定了幾種新的構(gòu)成自首的情形,其中“明知他人報(bào)案而在現(xiàn)場(chǎng)等待,抓捕時(shí)無拒捕行為,供認(rèn)犯罪事實(shí)的。”的情形在司法實(shí)踐中時(shí)常發(fā)生爭(zhēng)議,本文結(jié)合具體案例,以是否能反應(yīng)投案自首的主動(dòng)性、自愿性為標(biāo)準(zhǔn),對(duì)此問題進(jìn)行討論研究。
關(guān)鍵詞 自首 主動(dòng)投案 自愿性 主動(dòng)性
作者簡(jiǎn)介:王大鵬,天津市西青區(qū)人民檢察院公訴科副科長(zhǎng)。
中圖分類號(hào):D920.5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4.178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印發(fā)《關(guān)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對(duì)認(rèn)定自首問題進(jìn)行了拓展,規(guī)定了幾種新的情形,主要包括:
1.犯罪后主動(dòng)報(bào)案,雖未表明自己是作案人,但沒有逃離現(xiàn)場(chǎng),在司法機(jī)關(guān)詢問時(shí)交代自己罪行的。
2.明知他人報(bào)案而在現(xiàn)場(chǎng)等待,抓捕時(shí)無拒捕行為,供認(rèn)犯罪事實(shí)的。
3.在司法機(jī)關(guān)未確定犯罪嫌疑人,尚在一般性排查詢問時(shí)主動(dòng)交代自己罪行的。
4.因特定違法行為被采取勞動(dòng)教養(yǎng)、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強(qiáng)制隔離戒毒等行政、司法強(qiáng)制措施期間,主動(dòng)向執(zhí)行機(jī)關(guān)交代尚未被掌握的犯罪行為的。
5.其他符合立法本意,應(yīng)當(dāng)視為自動(dòng)投案的情形。
從2010年至今,通過筆者在實(shí)際的辦案過程中觀察,上述規(guī)定的幾種情形中第2條即“明知他人報(bào)案而在現(xiàn)場(chǎng)等待,抓捕時(shí)無拒捕行為,供認(rèn)犯罪事實(shí)的。”是實(shí)踐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情形,并且在實(shí)務(wù)操作過程中存在爭(zhēng)議較大,本文結(jié)合具體案例,對(duì)此問題進(jìn)行一些探討。
一、案例1
2013年5月23日,家住某小區(qū)的犯罪嫌疑人張某和被害人其鄰居楊某因鄰里糾紛引發(fā)矛盾,張某和楊某在小區(qū)樓下空地處先發(fā)生口角然后雙方動(dòng)手相互廝打,在相互廝打過程中,張某將楊某兩根肋骨打成骨折(后經(jīng)鑒定構(gòu)成輕傷),楊某將張某的鼻骨打成骨折(后經(jīng)鑒定構(gòu)成輕微傷),兩人經(jīng)過路人勸解停手后,楊某撥打110報(bào)警,張某見楊某報(bào)警后對(duì)楊某說:你還敢報(bào)警,你把我鼻子都打出血了,我等著警察來,看派出所怎么處理你。后來民警來到現(xiàn)場(chǎng)把雙方帶到了公安機(jī)關(guān)。
該案后以犯罪嫌疑人張某涉嫌故意傷害罪提起公訴并判處,對(duì)案件的事實(shí)和罪名認(rèn)定公訴機(jī)關(guān)和法庭均沒有分歧,但對(duì)法定情節(jié)的認(rèn)定上雙方出現(xiàn)異議,公訴機(jī)關(guān)認(rèn)為該案張某不構(gòu)成自首,法庭認(rèn)為該案張某構(gòu)成自首,并進(jìn)行了判決,該案后來公訴機(jī)關(guān)提起抗訴但因最終判決的刑期和公訴機(jī)關(guān)建議刑期差距小并未改判。
在該案中法庭的觀點(diǎn)是犯罪嫌疑人張某的行為和司法解釋規(guī)定的情節(jié)完全相符,張某明知楊某報(bào)警未離開現(xiàn)場(chǎng),民警到達(dá)后沒有抗拒抓捕的行為,到案后對(duì)于案件事實(shí)進(jìn)行了如是的供述,因此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為自首。公訴機(jī)關(guān)認(rèn)為張某雖然在形式上和司法解釋完全相符,但其主管上不具備主動(dòng)投案的意圖,因此不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為自首。
對(duì)上述兩種觀點(diǎn),筆者同意公訴機(jī)關(guān)的觀點(diǎn),認(rèn)為該案不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為自首。筆者認(rèn)為刑法但凡對(duì)相關(guān)的行為做出規(guī)定,如犯罪行為、自首、立功等,均是既考慮主觀又考慮客觀,以主客觀相一致為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在認(rèn)定主動(dòng)投案問題上也是如此,不能簡(jiǎn)單的只看犯罪嫌疑人的客觀行為而不考慮主觀心態(tài)。在認(rèn)定主動(dòng)投案問題上有兩個(gè)點(diǎn)非常關(guān)鍵一是主動(dòng)性、一是自愿性。所謂主動(dòng)性就是愿意主動(dòng)的將自己歸于司法機(jī)關(guān)控制并處理,這種主動(dòng)性既表現(xiàn)為非強(qiáng)制的、自愿的,同時(shí)也需要犯罪嫌疑人以認(rèn)識(shí)到自己犯罪為前提,即知道自己犯罪或者已經(jīng)可能犯罪,仍然主動(dòng)的將自己歸于司法機(jī)關(guān)控制。回顧本案,犯罪嫌疑人張某雖然明知楊某報(bào)警并且在現(xiàn)場(chǎng)等候民警,但其等候民警時(shí)的主觀心態(tài)是和投案不相符的,其并不是認(rèn)為自己打傷了楊某,可能受到司法機(jī)關(guān)的追究但仍然在現(xiàn)場(chǎng)等候民警。
通過本案的相關(guān)事實(shí)可以看出張某此時(shí)的心態(tài)認(rèn)為自己是被侵害方,自己是受害人,其等候民警的目的是為了讓民警處理對(duì)方而不是自己,既然其對(duì)自己犯罪后者可能犯罪完全沒有認(rèn)知,也就談不到是否有愿意將自己主動(dòng)歸于司法結(jié)果控制的目的了。在法庭調(diào)查過程中,公訴人訊問張某等候民警的目的時(shí)其回答的內(nèi)容更加印證了這點(diǎn),張某回答:打完架后我鼻子破了,流了好多血,我看楊某根本就沒什么傷,他還打電話報(bào)警,我就想你還敢報(bào)警,你把我打成這樣民警來了正好,讓公安局的處理你。
由此可見,張某根本沒有投案的自愿性,更加簡(jiǎn)單的說,所謂“投案”前提是需要行為人意識(shí)到自己涉嫌案件,否則就沒有投案一說了。
二、案例2
2014年7月12日,犯罪嫌疑人董某跳院墻進(jìn)入被害人李某家中,在屋內(nèi)翻找財(cái)物,其在準(zhǔn)備離開的時(shí)候聽見外面大門有開門的聲音,董某連忙躲進(jìn)臥室的床底下。開門進(jìn)來的正是被害人李某和兩名同事,李某進(jìn)入家中后發(fā)現(xiàn)物品有明顯的被翻動(dòng)的痕跡,意識(shí)到可能是家中被盜了,在家中四處檢查的時(shí)候發(fā)現(xiàn)了藏在床下的犯罪嫌疑人董某,李某和兩名同事讓董某從床下爬出來蹲在房間角落里不許動(dòng),然后在現(xiàn)場(chǎng)撥打110報(bào)警,民警出警后從李某的家中把犯罪嫌疑人董某的帶到公安機(jī)關(guān)。
該案后以犯罪嫌疑人董某構(gòu)成盜竊罪提起公訴并判決,該案在認(rèn)定過程中公訴機(jī)關(guān)也和法庭發(fā)生了分歧,法庭認(rèn)為該案董某的行為構(gòu)成主動(dòng)投案構(gòu)成自首,理由也是董某的行為和司法解釋規(guī)定的行為完全相符,其明知被害人李某報(bào)警而未逃走也未反抗,民警出警后將其帶至了公安機(jī)關(guān)。公訴機(jī)關(guān)認(rèn)為該案不構(gòu)成主動(dòng)投案,因?yàn)樵诒缓θ死钅炒螂娫拡?bào)警時(shí),現(xiàn)場(chǎng)不僅有李某還有李某的兩名同事,三人雖然未對(duì)董某采取捆綁等拘束手段,但董某客觀上已經(jīng)處于一種被控制的狀態(tài),在此情況下其等候民警的到來以及沒有了主觀的上的自愿性,因此不能構(gòu)成主動(dòng)投案。該案最終法庭采納了公訴機(jī)關(guān)的意見,未認(rèn)定董某構(gòu)成自首,但雙方確實(shí)產(chǎn)生過明顯的分歧。
對(duì)上述案件,筆者仍然同意公訴機(jī)關(guān)的觀點(diǎn),認(rèn)為董某的行為不能構(gòu)成主動(dòng)投案,進(jìn)而不能構(gòu)成自首。在此仍然涉及到認(rèn)定主動(dòng)投案的兩個(gè)主要條件即主動(dòng)性、自愿性。在此涉及到的主要是自愿性問題,所謂自愿性即自覺、自愿、非強(qiáng)迫的將自己歸于司法機(jī)關(guān)控制。如果是具有強(qiáng)制性質(zhì)的到案顯然不能構(gòu)成主動(dòng)投案,對(duì)此上述司法解釋中規(guī)定的“犯罪嫌疑人被親友采用捆綁等手段送到司法機(jī)關(guān),或者在親友帶領(lǐng)偵查人員前來抓捕時(shí)無拒捕行為,并如實(shí)供認(rèn)犯罪事實(shí)的,雖然不能認(rèn)定為自動(dòng)投案,但可以參照法律對(duì)自首的有關(guān)規(guī)定酌情從輕處罰。”
在此種情況下雖然在量刑上都可以參照自首,但卻不能認(rèn)為為自首正是因?yàn)槿狈ψ栽感赃@一原因,顯然也一點(diǎn)是無法被突破的,否則將根本違背設(shè)置自首的立法目的。
再結(jié)合本案的案情來看,董某雖然明知李某打電話報(bào)警,并且也沒有反抗脫逃的行為,但當(dāng)時(shí)的情況是董某客觀上已經(jīng)處于一種被控制的狀態(tài),在一個(gè)相對(duì)封閉環(huán)境的房間內(nèi),有三人在對(duì)其進(jìn)行看守,董某處于一種想逃而不能的境地,在此種情況下其除了等待民警前來并無其他可行的選擇,對(duì)此到案后的供述中,董某也承認(rèn)自己當(dāng)時(shí)不離開是因?yàn)楸蝗硕略谖葜袩o法離開。
因此在此案中董某就是缺乏構(gòu)成投案的自愿性條件,不能構(gòu)成主動(dòng)投案,進(jìn)而不能構(gòu)成自首。
上述案件的問題因案情原因在認(rèn)定上并不是太困難,但在此問題上在辦案實(shí)踐中還存在一個(gè)相關(guān)問題,在認(rèn)定上有一定的疑難:這個(gè)問題是雖然客觀條件上看,他人報(bào)警后犯罪嫌疑人明顯不具有離開案發(fā)現(xiàn)場(chǎng)的條件,但犯罪嫌疑人供述時(shí)稱自己不離開現(xiàn)場(chǎng)并不是因?yàn)榭陀^上不能而是因?yàn)橹饔^上不想。比如上述案例,如果犯罪嫌疑人董某到案后稱自己不離開不是覺得被三人堵在屋中跑不了,而是因?yàn)樽约簭男睦锊幌肱堋_@種情況在司法實(shí)踐的認(rèn)定中爭(zhēng)議較大,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構(gòu)成主動(dòng)投案的人認(rèn)為該案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能夠體現(xiàn)犯罪嫌疑人主觀上具有自愿性,客觀上的不能拿不是印證其主觀上不自愿的反證,再根據(jù)有利于被告人原則,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為自首。
對(duì)此筆者是不同意的,筆者認(rèn)為如果沒有相關(guān)證據(jù)能證實(shí)此問題,不宜認(rèn)定犯罪嫌疑人構(gòu)成主動(dòng)投案。在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主觀方面的證據(jù)往往除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以外不會(huì)存在其他直接證據(jù),除此之外的客觀證據(jù)往往都是間接證據(jù),很難起到直接否定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作用。在此不能機(jī)械性地適應(yīng)有利于被告人原則,對(duì)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沒有其他直接反證的事實(shí)予以認(rèn)定,否則將導(dǎo)致事件中很多問題的認(rèn)定陷入困境,比如1998年5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yīng)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guī)定:經(jīng)查實(shí)確已準(zhǔn)備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機(jī)關(guān)捕獲的,應(yīng)當(dāng)視為自動(dòng)投案。
針對(duì)此情況,如果所有被抓獲的犯罪嫌疑人均辯稱自己正準(zhǔn)備去投案,很顯然在大多數(shù)案件中很難有直接的相反證據(jù)去否定犯罪嫌疑人的這一辯解,那么如果機(jī)械性地適用有利于被告人原則,這些犯罪嫌疑人都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為自首,這顯然會(huì)產(chǎn)生和實(shí)際嚴(yán)重不符的結(jié)果,因此在包括此問題在內(nèi)的很多問題上,都不能機(jī)械的適應(yīng)有利于被告人原則,唯犯罪嫌疑人供述論。
綜上,筆者認(rèn)為在上述關(guān)于自首的相關(guān)司法解釋中,之所以在司法實(shí)踐中存在分歧,主要是因?yàn)樗痉ń忉屆枋龅闹饕欠缸锵右扇丝陀^的行為方式,但我們?cè)谶\(yùn)用的過程中不能機(jī)械性地進(jìn)行直接套用,因?yàn)閷?shí)際案件千差萬別,在適用司法解釋的同時(shí),我們不能忽視認(rèn)定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需具備的主動(dòng)性、和自愿性兩個(gè)關(guān)鍵點(diǎn),即便是客觀是和司法解釋描述符合,但如果不具備主動(dòng)性、自愿性的也不能認(rèn)定為投案自首;相反即便是司法解釋沒有羅列的方式,只要能反應(yīng)出犯罪嫌疑人主動(dòng)的、自愿的將自己歸于司法機(jī)關(guān)控制并如實(shí)供述的,也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為自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