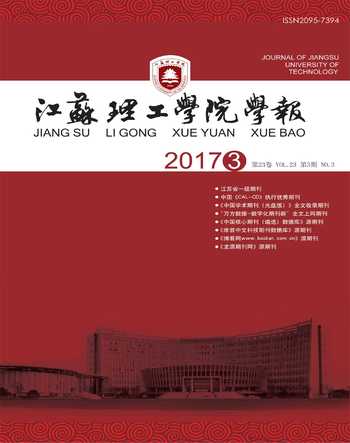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的比較研究
朱紅
摘 要:隨著社會(huì)市場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作為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的主體,合同關(guān)系在市場經(jīng)濟(jì)往來中起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而利用合同在簽訂和履行的過程中實(shí)施的詐騙行為也有愈演愈烈之勢,鑒于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的復(fù)雜性和多樣性,詐騙犯罪也在實(shí)踐活動(dòng)中變得極為復(fù)雜,因此,在認(rèn)定詐騙類犯罪過程中,其客觀上很難對詐騙類犯罪進(jìn)行此罪與彼罪的區(qū)分。通過比較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的立法意圖、法律構(gòu)成要件,可以進(jìn)一步區(qū)分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
關(guān)鍵詞:詐騙罪;合同詐騙罪;構(gòu)成要件;比較
中圖分類號(hào):D913.6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2095-7394(2017)03-0064-03
一、我國合同詐騙罪來源
在計(jì)劃經(jīng)濟(jì)時(shí)代,經(jīng)濟(jì)生產(chǎn)分配活動(dòng)更多依靠行政指令完成,合同僅在很小的范圍內(nèi)使用,因此,無論是刑事立法還是司法實(shí)踐,都沒有對利用合同進(jìn)行詐騙的行為進(jìn)行規(guī)定。
自1979年,我國實(shí)行對外經(jīng)濟(jì)政策開放以來,國家將發(fā)展的重點(diǎn)放在了經(jīng)濟(jì)制度的改革之中,隨著市場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發(fā)展形勢的不斷進(jìn)步,社會(huì)中有一部分人利用經(jīng)濟(jì)政策的不完善之處,從事不法行為,擾亂正常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建設(shè)。為此,在1985年,司法上率先對利用合同進(jìn)行詐騙的行為進(jìn)行了規(guī)定,但在此時(shí),利用合同進(jìn)行詐騙的行為被普通詐騙罪吸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fā)的《關(guān)于當(dāng)前辦理經(jīng)濟(jì)犯罪案件中具體應(yīng)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試行)》的通知》中,首次將采取欺詐手段與其他單位、經(jīng)濟(jì)組織或個(gè)人簽訂合同,騙取財(cái)物數(shù)額較大的行為,以詐騙罪定罪處罰。此通知第一次提出了個(gè)人或者經(jīng)濟(jì)組織以簽訂經(jīng)濟(jì)合同的方法騙取財(cái)物的行為,應(yīng)當(dāng)以詐騙罪追究其刑事責(zé)任。但該通知,本質(zhì)上屬于司法實(shí)踐。當(dāng)時(shí),利用簽訂或履行合同進(jìn)行詐騙的行為以詐騙罪定罪處罰,不存在合同詐騙罪這一單獨(dú)罪名。
到了1996年隨著市場經(jīng)濟(jì)的高速發(fā)展時(shí)期的到來,與財(cái)產(chǎn)相關(guān)的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也變得越來越復(fù)雜化,社會(huì)交易活動(dòng)日趨頻繁,利用經(jīng)濟(jì)手段而進(jìn)行的違法活動(dòng)的形式越來越多,包括利用合同進(jìn)行詐騙和普通的民事合同糾紛也越來越難以區(qū)分和識(shí)別,合同詐騙行為與民事欺詐行為互相交織。為應(yīng)對新時(shí)期的經(jīng)濟(jì)形勢,司法實(shí)踐對利用合同的詐騙行為進(jìn)行了細(xì)化,《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yīng)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次對于以合同形式而進(jìn)行的詐騙羅列出了六種詳細(xì)情形,為司法實(shí)踐中,細(xì)化了合同詐騙行為和普通詐騙行為的區(qū)分,該司法解釋也為了1997年《刑法》中將合同詐騙罪單獨(dú)分離出來做出了準(zhǔn)備。
1997年,我國《刑法》迎來修訂,這次修訂中,立法者認(rèn)為有必要將合同詐騙罪列入《刑法》新罪名,且列入新罪名的時(shí)機(jī)也已經(jīng)成熟。因此,立法將合同詐騙罪從詐騙罪中徹底獨(dú)立出來,形成單獨(dú)罪名,并在《刑法》第三章“破壞社會(huì)市場經(jīng)濟(jì)秩序罪”,“擾亂市場秩序罪”一節(jié)單獨(dú)闡述本罪名。根據(jù)罪刑法定原則,合同詐騙罪已經(jīng)成為獨(dú)立罪名,而利用合同進(jìn)行詐騙的行為不再以詐騙罪定罪量刑。
由此看來,合同詐騙罪是隨著市場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為了應(yīng)對新形勢下的犯罪行為,保護(hù)新形勢下的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從詐騙罪中獨(dú)立出來的新罪名。
二、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比較研究
如何區(qū)分此罪與彼罪呢?從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定義來看,雖然二者的目的都是非法占有他人財(cái)物,且都需要采用虛構(gòu)事實(shí)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但是二者之間仍然存在本質(zhì)的可以區(qū)分的特征,相比于普通詐騙罪名,構(gòu)成合同詐騙罪還要求行為人是在簽訂或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實(shí)施的詐騙犯罪行為。但是在現(xiàn)實(shí)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中,絕大部分的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的當(dāng)事人之間不存在簽訂書面合同的行為,我國《民法通則》第五十六條也規(guī)定:“民事法律行為可以采用書面形式、口頭形式或者其他形式……。”而詐騙犯罪在采取虛構(gòu)事實(shí)的過程中又常常伴隨著承諾受害人實(shí)現(xiàn)部分利益的行為,受害人也常常在基于某種可得利益的誘惑下而做出的處分自己財(cái)物的行為,因此,在實(shí)踐中,如何才能明確判斷是否是在簽訂和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實(shí)施了詐騙行為?認(rèn)定合同詐騙罪是否一定要求具有書面的合同?這給司法認(rèn)定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為了使讀者對于兩者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更好的區(qū)分,同時(shí),考慮到我國的司法實(shí)踐,筆者認(rèn)為,首先應(yīng)從犯罪的構(gòu)成要件分析。
(一)犯罪的主體區(qū)分標(biāo)準(zhǔn)
犯罪的主體是指實(shí)施危害社會(huì)的行為、依法應(yīng)當(dāng)負(fù)刑事責(zé)任的自然人和單位。達(dá)到法定刑事責(zé)任年齡、具有刑事責(zé)任能力的自然人當(dāng)然能構(gòu)成詐騙罪的犯罪主體,但是根據(jù)罪刑法定的原則,單位并不能成為詐騙罪的犯罪主體。而在合同詐騙罪中,自然人和單位都可以成為本罪的犯罪主體。這是由于在市場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中,不僅是自然人,作為法人的單位也具有民事權(quán)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可以依法獨(dú)立享有權(quán)利和承擔(dān)義務(wù),該犯罪的行為恰恰是發(fā)生在合同簽訂或者履行的過程中,因此,單位的主管人員或者責(zé)任人員利用單位資格簽訂合同對外實(shí)施詐騙,也可以構(gòu)成合同詐騙罪。
(二)犯罪的主觀方面區(qū)分標(biāo)準(zhǔn)
筆者認(rèn)為兩者都是以非法占有公私財(cái)物為目的。都具有直接故意,因此,犯罪的主觀方面不具備區(qū)分此罪與彼罪的條件。
(三)犯罪的客觀方面區(qū)分標(biāo)準(zhǔn)
兩者的表現(xiàn)形式上卻有很大的不同,詐騙罪是以虛構(gòu)事實(shí)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shù)額較大的公私財(cái)物行為。根據(jù)我國《刑法》對于詐騙罪的規(guī)定,不難看出,詐騙罪中,行為人實(shí)施詐騙行為是以虛構(gòu)事實(shí)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讓被害人陷入錯(cuò)誤的認(rèn)識(shí)之中,再利用被害人基于其錯(cuò)誤的認(rèn)識(shí),而對其財(cái)物“自愿”做出處分,使得行為人占有被害人的財(cái)物,而被害人遭受損失。詐騙罪中行為人騙取的對象往往是被害人所持有的財(cái)物,其目的較為直接客觀。例如,某甲向某乙許以高額的收購價(jià)款,欲收購其所收藏的元代青花瓷瓶,某乙信以為真將花瓶交付某甲,某甲將某乙的青花瓷瓶騙走后消失。該行為人就是以許以高價(jià)購買為誘餌,誘使某乙陷入某甲以高價(jià)購買其藏品的假象而對其所持有的瓷瓶做出交付某甲的處分,致使某甲在取得某乙的瓷瓶后消失,從而使得某乙遭受財(cái)產(chǎn)的損失。而根據(jù)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guī)定,合同詐騙罪在客觀方面,強(qiáng)調(diào)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行為人采取虛構(gòu)事實(shí)或者隱瞞真相等欺騙手段,這些手段發(fā)生在簽訂、履行合同是行為人采取詐騙的方式。因此,其行為人虛構(gòu)事實(shí)和隱瞞真相的的行為往往發(fā)生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因此,可以看到,相比于一般的詐騙罪,合同詐騙的行為往往以合同為掩護(hù),因此其更加隱蔽和多樣,而且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實(shí)施的詐騙,騙取的既有可能是被害人直接可得財(cái)物,也有可能是基于合同關(guān)系而取得的其他利益。例如:某甲向某乙許以高額的收購價(jià)款,欲收購其所收藏的元代青花瓷瓶,并與之簽訂收藏品買賣協(xié)議,但同時(shí),又以需要對藏品進(jìn)行專業(yè)檢測,確認(rèn)是否滿足收購條件為由,要求某乙對藏品進(jìn)行檢測,于是某乙信以為真將花瓶交付某甲事先串通的檢測機(jī)構(gòu)進(jìn)行檢測,檢測費(fèi)用由某乙承擔(dān),檢測機(jī)構(gòu)故意虛構(gòu)事實(shí)致使檢測結(jié)果與合同約定不符,使之達(dá)不到雙方協(xié)議收購的條件,從而使得該合同無法繼續(xù)履行。該犯罪行為中,行為人不僅僅是在簽訂和履行合同中虛構(gòu)事實(shí)使得被害人陷入錯(cuò)誤的認(rèn)識(shí),其還基于被害人錯(cuò)誤認(rèn)識(shí)下簽訂合同后所能取得的可得利益,做出的并非針對其所持有的財(cái)物進(jìn)行處分。犯罪行為人的直接目的并非被害人手中持有的財(cái)物,而是基于被害人為促成合同目的的實(shí)現(xiàn)而處分其他財(cái)產(chǎn)。由此可以看到,合同詐騙罪的表現(xiàn)形式往往比詐騙罪的表現(xiàn)形式更加的隱蔽、復(fù)雜,其非法占有的財(cái)物,范圍也更為廣大。
(四)犯罪的客體區(qū)分標(biāo)準(zhǔn)
一般經(jīng)濟(jì)犯罪的區(qū)別,主要是看侵犯的客體。[1]我國《刑法》將詐騙罪放在第五章“侵犯財(cái)產(chǎn)罪”中,而將合同詐騙罪放入了第三章“破壞社會(huì)市場經(jīng)濟(jì)秩序罪”一章中。從中也可以看出,兩者侵犯的客體不同。一般詐騙罪侵犯的是簡單客體,即公私財(cái)物的所有權(quán),而合同詐騙罪侵犯的是復(fù)雜客體,即不僅侵犯了公私財(cái)物所有權(quán),而且破壞了社會(huì)正常的市場交易秩序。因此,前者在犯罪的歸類上屬侵犯財(cái)產(chǎn)罪,而后者則屬于破壞社會(huì)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秩序罪。[2]
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所侵犯的法益以及社會(huì)危害性也有所區(qū)別;
雖然合同詐騙罪的犯罪客體為復(fù)雜的客體,相比與詐騙罪,更侵害了市場經(jīng)濟(jì)秩序,但刑罰的輕重并不是以侵犯客體的數(shù)量決定,而是由其社會(huì)危害性決定,合同詐騙罪客體的復(fù)雜性不必然導(dǎo)致其所造成的社會(huì)危害性的后果就大于詐騙罪,其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兩個(gè)方面。
1.合同詐騙罪中行為人與被害人雙方均為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的主體,在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中,被害人有著較高的風(fēng)險(xiǎn)承擔(dān)能力和認(rèn)識(shí),而詐騙罪的被害人為社會(huì)活動(dòng)中一般主體,其范圍更廣,對于風(fēng)險(xiǎn)的承擔(dān)能力和防范意識(shí)較低,收到侵犯的可能性更高,而造成的后果往往大于合同詐騙罪帶來的危害。
2.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中,涉及合同類詐騙的數(shù)額動(dòng)輒較大,為避免刑罰打擊范圍擴(kuò)大,也為了更好的適用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因此合同詐騙侵犯的法益雖多,但未必其危害性就大于普通詐騙行為。我國立法者在修訂《刑法》時(shí),將合同詐騙罪編寫入“破壞社會(huì)市場經(jīng)濟(jì)秩序罪”這一章節(jié)而非“侵犯財(cái)產(chǎn)罪”這一章中,可以看出,立法者的本意是寄希望于通過立法的目的用以規(guī)范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的秩序,從而遏制市場參與者通過簽訂和履行合同進(jìn)行詐騙活動(dòng)。因此,合同詐騙罪的功能更多的是在于維護(hù)市場經(jīng)濟(jì)秩序而非對公私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保護(hù)。
在清楚了解了立法者在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的立法目的,以及清晰兩者之間的犯罪構(gòu)成,明確兩者之間的本質(zhì)區(qū)別后,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合同詐騙罪的出現(xiàn)更好的適應(yīng)了社會(huì)的發(fā)展,規(guī)范了市場經(jīng)濟(jì)的秩序,將其從詐騙罪中徹底分離出來,并根據(jù)我國法律關(guān)于適用法條競合的處理原則,能夠?qū)υp騙罪和合同詐騙罪進(jìn)行更好的區(qū)分和把握。
參考文獻(xiàn):
[1] 芮雪春子.試論金融詐騙罪[J].新學(xué)術(shù),2007(2):192.
[2] 喻美奇,陸曉偉.利用口頭合同詐騙如何定性[J].法律適用(國家法官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2(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