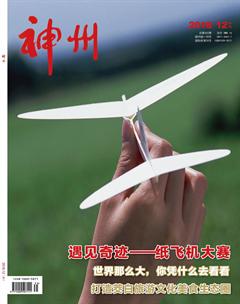讀魯迅《傷逝》有感
葉韜
摘要:文章針對魯迅先生的《傷逝》展開分析討論,從子君與涓生的生活軌跡出發,試圖以全新的視角審視二者愛情悲劇的根源。
關鍵詞:魯迅;《傷逝》;感悟
《傷逝》出自我國偉大思想家、文學家、革命家魯迅先生的筆下,著于1925年年底,屬于魯迅先生人生彷徨時期的文學作品。小說《傷逝》以特殊的筆觸描述了主人公的愛情故事,帶給讀者特殊的審美體驗,同時也為讀者帶去了無盡的深思。時至今日,盡管時代變遷、斗轉星移,依舊在人格塑造上發揮著指導意義。
在魯迅先生的心中始終倡導“寫真實”,但是也倡導文學創作的內容不等同于真實生活,文學是一種藝術形式,其必將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所以,在《傷逝》這不高度概括性的文學作品當中,我們是可以讀出特殊社會背景下普通民眾的真實生活情境與心靈困境的[1]。
通常我們否認為,小說《傷逝》當中涓生與子君之間的悲情愛情故事的根源在于當時社會背景下,封建勢力太過強大,社會是充滿黑暗與陰霾的,而社會中的民眾沒有經過最廣泛的思想啟蒙,同時在社會民眾的意識形態中,過分的將目光聚焦在小家庭的幸福與安定之上,對于社會的發展認知不夠清楚,沒有更加遠大的理想抱負去支撐民眾對于美好生活的希冀與追求,進而也就使得生活在黑暗與陰霾中的普通民眾面對強大的封建勢力無力回天,所以導致男女主人公愛情悲劇的根源是社會、是經濟、是政治。而在筆者看來,如果從文化或者哲學的角度去審視,使得男女主人公愛情沒能碩果累累的根源的確是他們缺少遠大的理想抱負,而導致理想抱負缺失的根源在于二者生活領域存在著天壤之別[2]。
在《傷逝》當中所刻畫的子君是一位經歷了新思想洗禮的時代女性,在五四運動的四朝當中,在個性解放這一思想的影響之下,子君的內心中布滿了對于自由戀愛、自主婚姻的渴望與追求,所以她勇敢的打破了封建家庭的桎梏,沖出了封建禮數的牢籠,在無數反對的聲音中與涓生確立了戀愛關系并且同居。在與涓生相處之后,子君的性格發生了改變,之前子君與涓生一同去討論雪萊、泰戈爾,一同去暢想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同去努力打破破舊習慣、家庭專制……而后來,子君由于繁瑣的家務變成了一位落于俗套的家庭婦女。而對于涓生來講,這位被繁瑣庸俗家務所左右的女人來講,精神上是具有隔閡的,同時二人的生活在經濟上是捉襟見肘的,從而使得涓生不堪物質與精神的壓力拋棄了子君,子君從新回到了封建的牢籠當中,最后在孤獨與寂寞當中,在思念與落寞當中老去、死去。
在女主人公子君的生活軌跡當中,她首先在新思想的啟蒙之下勇敢的走出了封建家庭,之后進入到了自己期待已久的、與涓生同生同樂的新家當中,而后來有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與制約再次返回那個充滿著陰霾的封建家庭,直到孤獨寂寞冷的死去,所以在她的生活領域就是家庭。在人類的生活起居當中,在人類生老病死的歷程當中,家庭生活始終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家庭生活中有飲食男女、有生老病死、有家務瑣事、有柴米油鹽,也正是這些因素才鑄造出了家庭生活的活動領域,在家庭生活當中更多的是將自然主義與經驗主義作為基礎。家庭這一領域是一個既定的、帶有濃厚經驗性特質的世界,在這一領域當中屬性及其多元化,不僅有自在,但是也有無盡的重復。在家庭生活中,可以帶給我們每一個人寧靜、溫馨、舒適的感覺,但是它也會讓惰性滋生,讓保守性成長,在家庭生活的基本構造與圖示當中會抑制我們的創造性思維,會讓理智戰勝創造性實踐。在小說《傷逝》當中的子君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之下,她已經在主觀上對于那些腐朽的封建禮教充滿了厭惡與憎恨,在她的內心當中是渴望回避那些已經失范的文化傳統,于是在她與涓生結合的時候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的聲音。但是,峰回路轉,當子君沖破了封建禮教桎梏勇敢的走出了封建大家庭之后,又回到了與涓生共同建造的小家庭,她始終是沒有抵制住在身邊無時不刻都在蔓延的生活惰性,在她的生活軌跡中,也始終都沒有抵御住滿足現狀、安于自我的文化傳統,最終使得這位曾經受過新思想影響的現代女性在自認為“自在的”文化氛圍中喪失了自我的睿智,迷失了努力的方向。可見,在小說《傷逝》當中,魯迅借用子君這一人物的生活軌跡向我們闡釋了脫離日常生活的必要性,更向我們揭示了追求與夢想的力量。
而在涓生的生活中,家庭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涓生不僅有與子君構建的家庭,他還有自己的工作,雖然只是一名小小的公務員,但是他卻可以更加清晰認清世態炎涼。在涓生的人生當中,空間是比較大的,在子君的意識里涓生是她的全部,而在涓生的世界中,子君只是一個組成部分,在他的生活中是一個豐富多彩的、是一個各種社會活動交織的環境。所以,子君與涓生最后產生矛盾的根源或許不在于社會的黑暗,或許不在于封建勢力的強大,或許也不在于那特定的歷史背景,而是他們的生活領域存在巨大差異,使得他們在思想上形成了差異,這種思想上的差異聚積起來之后,必將要找到一個宣泄口,而對于子君來說,這個宣泄口只能是生活中的矛盾以及不適應。
結語:
《傷逝》向我們展現了特定時代的愛情悲劇,或許魯迅先生寫作的過程中集中想呈現的是社會的黑暗,但是對于生活在現代社會的高中生來講,那個時代已經遠去,我們在和平的今天,在現代化的當下應該以一種全新的目光去審視《傷逝》,去解讀《傷逝》。
參考文獻:
[1]李林榮.情愛悲劇,“主義”哀歌——魯迅小說《傷逝》主題蘊含再解讀[J].東岳論叢,2012,33 (07):15-24.
[2]蔡苓,張猛.情為何物,愛又如何——讀魯迅《傷逝》有感[J].科技創新導報,2008 (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