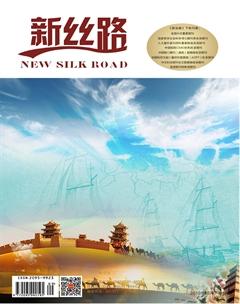狂歡與規約
盧曦
摘 要:日神精神訴諸美和適度,帶給人規范與制約,酒神精神象征人的自然本性和原始生命意志,讓人在狂歡中復歸本性。《黑皮膚的圣母》中斯托克這一人物形象既體現了日神精神的規約,又體現了酒神精神的狂歡,并且在其體內還交織著兩者的矛盾和斗爭,讓他飽受精神折磨。斯托克由自我分裂向自我整合的轉變可以看作是文明與蒙昧的搏擊,盡管啟蒙最終以失敗告終,但至少曾在他心中激起了漣漪,讓他的人性漸漸復蘇。通過斯托克作者表達了小說的主旨,即被蒙蔽的心靈需要文明的救贖,被扭曲的人性需要人文主義的療救。
關鍵詞:斯托克;日神精神;酒神精神;抗衡;啟蒙
200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1919—2013),是英國繼伍爾夫(Virginia Woolf)之后又一偉大而獨特的女作家。她一生筆耕不輟,著作頗豐,作品題材涉獵廣泛,寫作風格奇譎多變。國內對萊辛長篇小說的研究浩如煙海,而對其短篇則很少有人問津。事實上,萊辛的短篇小說匠心獨到、短小精悍,如她的長篇小說一樣體現著她在作品題材、風格、主題上的追尋與探索。以早年非洲經歷為題材的短篇小說集《非洲故事》就展現出萊辛獨有的魅力。
《黑皮膚的圣母》選自萊辛的短篇小說集《摶日記:非洲故事二集》,故事主要講述了二戰后期在非洲殖民地贊比西亞這片土地上,意大利戰俘米歇爾和英格蘭軍官斯托克上尉之間的故事,原本身份地位懸殊的兩個人在一段時間的相處中竟變成可以吐露心聲的朋友,在米歇爾的影響下,斯托克試圖拋卻束縛去追求自我、平等和幸福,但最終屈服于現實而痛苦的結束了這段友誼。現有研究大都是從小說的主題入手或分析米歇爾這一人物形象,而筆者在閱讀的過程中發現斯托克這一形象充滿張力更為飽滿,在斯托克身上融入了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并且交織著兩者的矛盾和斗爭,本文擬分析這兩種精神在斯托克身上的表現及在其體內的對抗,并試圖探尋產生分裂自我的原因及作者通過這一人物形象想要表達的思想。
一、日神精神的規約
在《悲劇的誕生》一書中,尼采給日神的含義做了一個明確的界定:“我們用日神的名字統稱美的外觀的無數幻覺,它們在每一瞬間使人生一般來說值得一過,推動人去經歷這每一瞬間。”[2]108據此,我們可以簡單地把日神定義為外觀的幻覺。日神狀態還有一個鮮明的特征即適度,這是日神本質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界限:“適度的節制,對于狂野激情的擺脫,造型之神的智慧和寧靜。”[3]周國平在其文章中分析指出:“適度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個人界限的遵守,是倫理的尺度,另一方面是對美麗外觀的界限的遵守,是美的尺度。” [3]這種訴諸美和適度的文化就像清規戒律一樣給人帶來規范與約束。
《黑皮膚的圣母》中斯托克所體現的日神精神一方面就表現在他對美麗外觀的界限的遵守。他人高馬大、金發碧眼,有著磚紅色的肌膚和布滿漂亮的黃色汗毛的雙手。他首次出場便穿著熨燙過的卡其色制服,走起路來腰板挺直、氣宇軒昂,給人留下美的印象。而相比之下,酒神精神的象征米歇爾則是隨意地躺在樹下的行軍床上,手里拿著個酒瓶子,卷著褲腿,穿著沒有領子的臟兮兮的衣服,胡子拉碴的邋遢形象。單從外形上我們就能輕易的看出二人的差別,一個注重外表、衣著講究,一個放浪形骸、不修邊幅。
作為德行之神,日神要求信奉者要適度,以及為了做到適度要有自知之明。于是,與美的審美必要性平行的提出了“認識你自己”和“勿過度”的要求。[2]15斯托克所體現的日神精神的另一方面就表現在他對個人界限的遵守,也是社會規范和社會文明對他的規約。斯托克是被派駐在贊比西亞的英格蘭軍官,作為高高在上的殖民者的代表,他身上有種天然的優越感,總是以征服者的姿態對待黑人。當上尉聽到米歇爾拒絕派給他來幫忙修建村莊的黑人時,他猶豫了,因為原則上他是不贊成讓白人干重體力活的;當看到涂成黑色的圣母像時,他感到周身不適,并且斥責米歇爾這是德國人的村子,不能有黑色的圣母像存在。在他眼中,這些都是對白人統治權威的挑戰,也是對白人自尊心的嚴重貶低,可見殖民主義和種族歧視的思想已經在他體內打上深深的烙印。即使對于淪為戰俘的白人同胞,他也表現出很強的等級觀念,嚴格遵守著上級與下級,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他第一次在樹下的行軍床上看到米歇爾的時候,即使離他還有十步遠,就深感自己位置的尷尬,他覺得米歇爾應該給他敬禮,跟米歇爾說話的時候也是昂起頭、豎起眉、翹起下巴,幾乎全是命令的口氣。當然,斯托克自己也是很有自制力的人,他多年的從軍生活讓他訓練有素,懂得節制,日常生活都遵守著軍隊的行為規范而沒有多少自主性,生活就在簡單的重復中度過。總而言之,日神精神所要求的“適度的節制”在斯托克上尉身上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
二、酒神精神的狂歡
酒神精神是尼采哲學的又一核心概念,如果說日神象征外觀的幻覺,那么酒神象征著情緒的放縱。酒神的象征來自希臘的酒神祭,在酒神崇拜儀式上,人們打破一切禁忌,群情亢奮,狂飲縱欲。尼采認為,這是為了追求一種解除個體化束縛、復歸原始自然的體驗。在《悲劇的誕生》中,尼采對酒神精神進行了解釋:“在酒神的魔力之下,不但人與人重新團結了,而且疏遠、敵對、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慶祝她同她的浪子人類和解的節日……此刻,貧困、專斷或‘無恥的時尚在人與人之間樹立的僵硬敵對的藩籬土崩瓦解了。此刻,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每個人感到自己與鄰人團結、和解、款洽,甚至融為一體了。”[2]6因此,在酒神精神的作用下,人與人之間的界限瓦解了,個體生命的束縛也得以解除,從而回到生命的原始狀態,達到一種忘我的境界。
在《黑皮膚的圣母》中,意大利戰俘米歇爾整日以酒為伴,放浪形骸,不拘小節,不受種族觀念的影響而和黑人友好相處,他身上所表現出的迷狂、自我、真性情讓我們看到了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影子,在他與斯托克相處的過程中,他身上這種強烈的“狄俄尼索斯情緒”無疑感染到了斯托克,讓一直被束縛、被禁錮著的斯托克嘗試著破除個人的界限,體驗狂歡的快感,回歸真實的自我。米歇爾用自己的真實打動了斯托克,讓斯托克一改初見時輕視、敵對的態度而和米歇爾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在這其中“酒”可以說是斯托克和米歇爾感情的催化劑。他們第一次喝酒是在分配完工作后的夜晚,兩人各有所思只是喝酒幾乎沒有交流。第二次他們并肩坐在草地上,一起喝酒消磨著時間,這一次斯托克感覺自己不一樣了,暫時從平常的行為規范中脫身出來,此時他已經在酒神精神的感染下慢慢放低高傲的姿態和米歇爾相處在一起,兩個人就像多日未見的舊友在把酒話家常一樣,在米歇爾面前他開始學著吐露自己的心聲,表達內心最真實的情感。到最后斯托克完全沉浸在醉酒帶來的快樂中,他不再有那么多的束縛,也不再注重自己的形象,穿著酒跡斑斑的襯衣,整日醉意朦朧。顯然他已經沉湎于醉酒之后的迷狂狀態,享受放縱帶來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