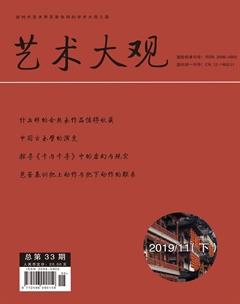讓未見看見
廖沙泥
摘要:藝術發展至當代已經具有了更多的表達的可能。隨著觀念的深入和形式、媒介的拓展,藝術對社會的關注塑造了“社會雕塑”也拓寬了藝術自身的維度。使在藝術中不同人群的平等共享成為可能。本文試圖通過對《同一雙眼睛藝術共享計劃》的分析,闡釋當代藝術展覽表達的可能性。通過與視障人群共享藝術,體現在當代語境下,藝術、展覽中的人文關懷。
關鍵詞:藝術共享;人文關懷;同一雙眼睛
一、當代語境下藝術的維度
在傳統藝術史的敘事中,對視覺的倚重是顯而易見的,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視覺藝術涵蓋了大部分的藝術的創作和敘事,人們習慣通過視覺交流對藝術的理解和體悟。而自杜尚以來,藝術自身的邊界和表達不斷地被拓寬,傳統的創作語言開始擁抱新的媒介向生活本身靠攏,達到了新的詮釋維度。人們在探討中更加關注藝術自身的可能性以及它所表達的觀點對社會景觀的塑造和影響。而博伊斯的出現,又將這樣的討論再次向前推演。“社會雕塑”的概念強調了藝術對與社會生活的介入,使其更加廣泛地參與了社會議題的討論和價值觀的塑造。在“人人都是藝術家”提出之后,藝術創作的主體延伸至具有潛在的藝術創作力的可能的每一個人中,藝術通過觀念的升華達到價值的體現。在此之后,隨著不斷地反思和視角的開拓,當今藝術的可能性和想象力也愈發寬廣。除了對自身語言及創作主體的討論之外,亦將視角投入在受眾之中,嘗試藝術實踐的另一個維度,重思人與藝術的關系。
二、《同一雙眼睛》展覽中人文關懷的表達
在《同一雙眼睛——藝術共享計劃》中,展覽嘗試打破視覺的壁壘,將關注投入到易被忽視的視障群體之中,讓視障人士和普通觀眾平等地分享藝術成為可能。這樣的實踐不僅是對藝術的維度的再次延伸,同時亦使作品與觀眾之間的互動有了深層的思考并呈現出彼此之間的關懷。展覽由十位中國藝術家的作品構成,分別在三個維度的層面上呈現了一場關于“未見”的“被看見”——他者視角(你的眼睛)、主體視角(我的眼睛)以及第三視角(新眼睛)。藝術家通過對視障群體的長期接觸和研究,將鮮為人關注到的視障群體的生活狀態展現在觀眾面前。在黃文亞《見非見》的鏡頭中,可以看到他們與普通人同樣的情感和行為,衣食住行,學習、娛樂……他們與明眼人不同的“閱讀”世界的方式,以及他們自身的局限和因此而更加敏銳的感知。這些平凡的日常,被“他者”的目光所記錄,透露出細膩的內省和對比。其中感人的一幕出現在對視障人士的一次沙漠旅行的記錄,在常人的理解中他們也許無法感知曠野的無垠,但當鏡頭在認真地撫摸手中的砂礫,并說出每一粒沙子的大小是不一樣的時候。頓時讓人感受到他們世界的無限。在隋建國作品《握手》中,藝術家所創作的雕塑作品以外在簡約的造型避開視覺上對細節的捕捉,同時在作品內部用自己的手的狀態構建了唯有觸摸才能感受的負空間。任何一次觀眾將手放入這負空間之中,便是一次與藝術家、與彼此,隔空的“握手”體驗。同時,負空間也象征的表象之下的內在——“握手”這件表達善意和尊重的行為原本就無關于外界的差異,它更是一場內在心靈的交流和體驗,不分狀態,無關身份……人人平等。共享藝術的平等在藝術之外延伸。在盧珊的作品《糧倉》中,藝術家試圖尋找一種與視覺之外的平衡點,肌理與觸感,氣味與記憶。她以個體記憶的經驗作為創作的藍本,將兒時生活在糧倉的記憶場景,片段式地縫制在帶有糧倉氣味的米袋或者面布袋上。布面上有窗臺、植物,有兒時在家周圍溜達的小狗,也有鄰居的奶奶的形象……他們分別出現在不同質感的布上,或是粗糙的粗麻布,或是輕柔的棉布,還有毛絨玩具表面的絨布……不同的肌理質感回應著它們所代表的記憶的感受。粗糲或溫柔,手上觸摸的痕跡,曾經也留在心里面。關于童年與記憶,是每個人都有的成長的痕跡。他們像氣味一樣,想肌理一樣不經意間,儲存在觸覺和嗅覺當中,當他們突然被激發,又會突然被喚醒。在作品中,它不是文學語言中常說的明確而轉瞬即逝的味道,而作為糧倉的氣味和米袋的觸感,它大概如記憶一般伴隨一生,如影隨形。在此,明眼觀眾與盲人觀眾共同可以通過觸覺和嗅覺“感同身受”的藝術家遙遠而豐富的童年時光。它也許叛逆也許柔軟,充滿了日常的氣息和溫情。藝術成了語言之外的另一種“語言”,在視覺之外,依然在熟悉的日常中,在內心里,彼此“抵達”。這樣的平等交流,不關注差異,更關注共同。
然而,差異始終存在,求同是一種尊重,而尊重差異也是一種關注和理解。在范勃的作品《世界》中,他以平面的方式展現的盲人世界中立方的形象。在對展覽的前期調研中我們了解到,先天失明人士對空間和立體概念的理解與明眼人有著很大的不同,他們的世界是被平面的曲度所構成。立方也被展開的平面所解讀。藝術家敏銳地洞察到這個差異并感性地將它表達。他用從失明人士家中收集的刻有盲文的雜志、畫刊、照片、廣告等等。將它們鋪在墻面上,構成了他們世界的立方。一是以平面解讀了明眼人眼中的立方概念,二是解構了兩者之間差異地獲取信息的體系。在明眼人眼中,色彩圖像的傳達是非常廣泛,是大家傳遞及獲取信息的一種有效的方式,然而在藝術家所收集的畫刊和照片上,圖像對盲人而言卻沒有實際意義,他們在上面刻上了盲文才讓這些充滿的圖案的紙張可以被解讀。而盲文對明眼人而言又仿佛是一種“密碼”。能夠被看見,被觸摸,卻無法被解讀。這種差異仿佛平行世界,卻在現實中重疊。當差異能被看見,被理解,又不被打擾。這大概是求同存異最好的狀態。
讓未見被看見,是此次《同一雙眼睛藝術共享計劃》展覽另一種重要的主旨和體驗。對于視障觀眾,在場的藝術作品建構了視覺之外,平等共享的基點和可能;而對于明眼觀眾而言,在藝術中認知差異,是一種尊重和走出“自我”的觀察。此次展覽的除了作品本身的呈現之外,生動而豐富的公共教育體驗,也將觀眾進一步帶入到展覽語境之中。在展廳的公共教育區域中,工作人員為觀眾準備了許多副不同功能的眼鏡,它們成了眼睛前天然的“濾鏡”,視力正常的觀眾佩戴上它們,可以模擬體驗不同視力的狀態。無論是弱視還是色弱,眼前的模糊讓觀眾再走入展廳時,變成了一種新的“觀看”。這是一種直觀于別人“眼中”的“觀看”,也是常人視覺經驗之外的“看見”。當這種互動經驗成為展覽的一部分時,作品中所表達的對視障人群的人文關懷,藝術中可能的平等共享,認知與尊重差異的價值觀念在體驗之中慢慢深入人心。如果說,約翰伯克在《觀看之道》中解析了視覺審美社會層面的要素以及圖像所內含的文化意義,那么,《同一雙眼睛》的展覽所呈現的是一種別樣的觀看之道——讓體驗本身成為觀看,又讓觀看在看見之外。也是展覽和藝術本身在今天的進步。
三、藝術中人文關懷形成與發展
在文藝復興時期,以神為中心的意識形態逐漸轉變為對人自身的思考和關注。對人的關注逐漸獨立于對神而存在。人的價值得到肯定,現世生活得到頌揚。人文關懷開始在藝術中得到書寫和體現。藝術創作中的人在不再都是神的子民的視角,而成了觀察世界的尺度。在繪畫藝術極為發達的時刻,透視法的發明亦代表了與神全知全能視角不同的人的觀察方式。它在以理性為基礎的規則中,表達了人類視角下的博愛與自由。但在當時,這樣自我關注的自覺,更多所討論的是對人類整體的現實關懷。而隨著藝術在當代的發展中,藝術敏感的觸覺所能感知到更多的是人群中的差異。人類的自我關注和人文關懷體現在深入現實的思考中,以及對差異的理解和關注。在《同一雙眼睛——藝術共享計劃》中,展覽聚焦于視障人群,在視覺所主導的世界中易被忽視的群體。它以藝術方式喚起大眾對他們的關注和了解,同時也在試圖以藝術的語言中尋找一種平等感知,相互理解的方式。差異在此,并不僅是一種缺陷,它更是一種生存方式和認知世界的角度。在此,展覽試圖打破了我們對差異可能的固有的一些偏見,以人文關懷態度照亮彼此的盲區,讓共享這件事,成全了視覺之外最大的共同。在藝術的可能性中觀照出人的可能性,而藝術的可能性,本身也就是人的可能性,未來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