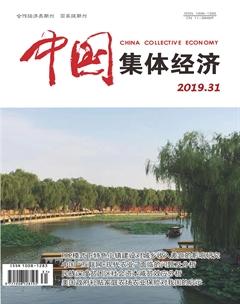民族深度貧困區社會資本減貧效應分析
祁永康 姜力瑋 吳新苗 陳強強



摘要:民族地區的精準扶貧是中國精準扶貧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資本作為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資本,在精準扶貧中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文章以甘肅省臨夏州和政縣為例,以社會資本中的社會信任維度、社會網絡維度和社會規范維度為出發點,運用問卷調查法和文獻檢索法,基于入戶調查資料,對比分析了漢族、回族和東鄉族地區社會資本投資與減貧效應的關系。研究發現,社會資本投資與農戶的年齡、民族、性別等因素有很大關系,且在農戶社會網絡、規范和信任維度均具有明顯的減貧效應。要實現農民收入結構優化、農民增收渠道拓寬,不僅需要外部相關政策以及農業結構調整的引導,還需要農戶進行社會信任、社會網絡、社會規范等社會資本的持久投入。農民自身也應該多和外界溝通,注重培育人與人之間及團體之間的良好信任,政府也應積極為當地服務組織和社團的發展提供資金及政策支持,促進各種資源及信息的流動,農戶之間更要培育一定的互惠機制,使其為農戶自身發展提供幫助。
關鍵詞:精準扶貧;農戶;社會資本;民族地區
貧困問題是許多國家長期面臨的共同問題,也是中國政府正在努力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精準扶貧是國家扶貧開發和貧困治理能力的創新,它既是傳統扶貧政策的發展,又是新貧困形勢下的創新。由于受自然條件、發展基礎、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制約,少數民族地區普遍呈現出貧困程度大、程度深、扶貧難度大等特點,這已成為精準扶貧領域
中的重點領域。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作為臨夏州扶貧工作的重點縣,總人口約19.5萬人,其中少數民族占總人口的57.4%。為了深度推進地區扶貧工作,縣委、縣政府運用建檔立卡的方法,努力摸清摸準扶貧目標和對象的準確信息,為精準扶貧的順利實施提供了可靠依據。
洛瑞提出作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資本,社會資本是嵌入到區域中的,家庭內部與社會關系中廣泛存在著社會資本。周燁欣提出,社會資本是自然資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必要補充,也是發展所不可或缺的,社會資本關注的是個體與個體間的關系,個體行為的嵌入性、個體對社會資源的擁有和動員能力以及個體在社會網絡中的位置等方面。王志剛,張璟等提出社會資本是指能夠促進合作與協調的網絡、規范和信任,它可以通過促進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經濟效率。綜上所述,社會資本在民族地區的精準扶貧中起著極其關鍵性的作用,對于改善貧困地區農戶的生產生活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在各學者研究學習和思考的基礎上,基于對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的農戶入戶調查的數據,來研究分析民族地區精準扶貧中社會資本投資的減貧效應。
一、理論基礎及指標體系
(一)社會資本投資的理論基礎
社會資本作為一種資本形式,具有社會和經濟的雙重屬性。社會屬性是關系網絡所提供的社會保障和經濟支持,信任所提供的精神支持、規范提供的社會秩序保障等;經濟屬性是指社會網絡所提供的信息、人際關系和其他資源形式來引導人力資本流動,降低交易成本,從而增加個人收入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陸遷,2012)。社會資本的這種“資本”功效使人們既可通過某種投資策略來維持和加強,也可能因負面影響而有意識地疏淡致使社會資本下降。格魯特爾特(Gro-otaert,2001)研究發現,控制其他變量后,社會資本對家庭有正面影響,可以顯著改善家庭經濟狀況,社會資本越豐富,物質資產積累越多,家庭應對風險的能力越強,與富裕家庭相比,社會資本對窮人家庭的作用更加明顯,社會資本對農戶收入的影響來自于公共服務、社區合作和對信任的利用。社會資本可劃分為三個層面,即關注社會網絡和規范的微觀層面,關注網絡結構化的中觀層面以及關注“外在”文化、政治和宏觀經濟的宏觀層面。不同層次的社會資本形式反映出社會資本的多重經濟效應,使社會資本對收農戶入有現實影響。
(二)社會資本的指標體系
近年來,社會資本已經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農戶的社會資本投資對促進貧困地區農戶的經濟增長、緩解貧困等有顯著作用。通過從文獻的綜述性概括中選取的依據,本文從社會網絡、社會規范、社會信任等維度對社會資本進行測量,其中,選用與周圍人的融洽程度、對周圍人的信任度、對村委會的熟悉度及對村委會的信任度來衡量社會信任維度;以與外界的聯系、是否使用網絡以及上網的頻率來衡量社會網絡維度;選用是否參加村委會活動、不參加村委會活動是否會受到責罰、是否有人主動借錢、遇到困難是否會找村委會或向當地政府求助和是否參加當地社會服務組織或協會等來衡量社會規范維度。
社會信任是在同一個社會群體下,人們在基于共同的價值觀體系的基礎上建立的相互信任和認可。對于和政縣農戶來說,社會信任表現為對周圍人的熟悉和信任、以及對村委會的熟悉及信任上,即農戶在同一價值觀體系下,對村委會及周圍人的相互認可。
社會網絡是在社會個體成員之間形成的相對穩定的聯系和關系。就和政縣而言,農戶的社會網絡指農戶使用網絡與外界的聯系、使用網絡的頻率等作為參考指數來綜合測量社會的網絡。
社會規范是指調整人和人之間以一定的社會關系為內容、維護一定的社會秩序行為的規范。就農戶而言,參加社會活動與不參加是否會受到責罰在其價值體系下反映農戶之間的社會秩序,有人是否愿意借錢給你反映的是農戶之間的社會關系,是否了解當地的社會服務組織或協會以及是否主動參加等可以很好的體現和政縣農戶的社會參與度,由此組成的指標體系將更好的反映社會規范。如表1所示。
二、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分析
(一)基本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重點抽樣方法,在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從卜家莊鄉和陳家集鎮各抽取150名農戶進行問卷調查,回收有效問卷分別為147份、144份,發放的300份問卷中有效問卷為291份,有效回收率為97%,其中男性174人,女性117人。少數民族為150人,占總體的51.55%,其中東鄉族90人,占總體的30.93%,回族60人,占總體的20.62%(表2)。
(二)描述性指標分析
1. 農戶年齡及知識水平分析
在此調查中,發現參與調查的農戶年齡趨于年輕化,年齡18~29歲之間的有138人,占有效參與人數的47.4%;文化程度存在一定差距,其中小學及以下的有75人,占有效參與人數的25.77%,而大專及以上的占到了38.11%,具體數據如表3和圖1。
本次接受調查的農戶受教育程度與其年齡、民族、性別等有一定的對應性,例如文化程度在小學及以下有的占總體的25.77%,其中東鄉族最多,為39人,占總體13.40%。由調查數據可知,在民族地區,少數民族接受小學教育的女性略多于男性,而接受初中、高中以及高等教育的人數中男性遠多于女性,且漢族多于少數民族,說明男性的受教育程度總體高于女性,漢族受教育程度總體高于少數民族,這也直接影響了社會資本投資向男性和漢族傾斜。具體數據如表4所示。
2. 農戶基礎數據分析
從調查數據來看,農戶家庭勞動力少,50.55%農戶家庭只有兩個勞動力,且有53.61%的農戶健康狀況一般;農戶年收入偏低,47.42%的農戶年收入在1萬元以下,只有9.28%的農戶年收入較高,在3萬元以上;且農戶收入來源絕大多數以務工和務農為主,另外也有一小部分農戶的收入來源多元,以政府補貼、個體工商戶、和其他收入為主;農戶住房結構多元,以鋼混結構、磚混結構、磚木結構和土木結構為主,其中磚木結構在接受調查的農戶中所占比重最大,為43.3%,鋼混結構所占比重最小,為8.25%(表5)。
表5數據表明在臨夏州和政縣的農村中,農戶收入不高,且勞動力以務工和務農為主,受教育程度有嚴重的傾斜趨勢,少數民族和漢族的教育不平衡,這導致很多農戶缺少自主創業的思維和能力,家庭經濟狀況一般,有的在政府補貼的幫扶下,仍處于貧困狀態。
3. 扶貧數據分析
本文主要以享受過或正在享受政府扶貧項目的農戶為主要調查對象,數據顯示農戶參加最普遍的社會保障項目是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分別占62.89%、81.44%,其次是最低生活保障和農村醫療救助,占到30.93%、19.59%,最低是農村“五保”政策補助,為6.19%;農戶表示能從根本上解決困的措施是幫助貧困地區發展旅游業、幫助貧困地區銷售滯銷農產品、培訓年輕人的電商思維、培訓農業技術給予資金支持、加大教育投資及補貼以及提供小額貸款。在問及扶貧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時,農戶表示幫扶渠道單一是主要問題,其次是農戶認為貧困地區難以實現持久富裕和幫扶資金過少等。對于更好的實現脫貧,農戶的意愿是加大農業技術培訓投資及教育投資,堅持資金投資,重視人力投資和項目投資。具體數據如表6所示。
表6中數據是根據農戶選擇某一個選項的次數與總體參與人數的比重得出,表明農戶在生產生活中仍處于貧困狀態,且需要政府及先關部門重視是給予適當幫助,合理利用社會資本。
三、社會資本投資的減貧效應分析
(一)信任維度
在社會資本的社會信任這一維度中,本文通過農戶與周圍人的融洽程度、對周圍人的信任度、對村委會的熟悉程度以及對村委會的信任度等角度來衡量信任維度,根據調查數據顯示,與周圍人相處好和較好的各占參與調查人數的41.24%、48.45%,對周圍人比較信任的占參與調查人數的71.43%,與周圍人關系融洽的農戶對周圍人的信任度較高。在對村委會的熟悉程度這一指標上,有46.39%的農戶對村委會熟悉度高的農戶表示一般,20.62%的農戶表示不熟悉,僅有12.7%和20.62%的農戶表示熟悉和比較熟悉,這一現象表明農戶對村委會的信任度相對較低在社會信任維度,男性更多的熟悉村委會,與周圍人關系融洽,在對村委會成員以及周圍人的信任的人群中,年齡在30歲以下的男性的信任度更高。通過信任維度各指標的正相關指數均值得知,對村委會的熟悉度和信任度指數低,說明農戶在平時生活中與村委會的接觸較少,對村委會缺乏信任,這從側面說明村委會工作需要進一步透明化,對農戶需求的解決力度不夠大。在調查中,與周圍人的融洽度和信任度高,說明農戶之間有較好的互惠機制,這將有利于提升農戶間的信任、情感關注和團結程度,也會影響個體的態度以及行為。同時,信任維度對農戶的減貧效應更多的表現在農戶對政府扶貧措施和相關政策的擁護與支持,減輕扶貧措施的實施難度,提高農戶和政府的配合度,有利于當地扶貧措施順利開展,為農戶的生產生活帶來實際的幫助。
(二)網絡維度
在社會資本的社會網絡維度方面,本文通過農戶與外界聯系次數、渠道以及使用網絡的頻率等指標進行衡量。其中有21.65%和46.39%的農戶與外界聯系多和較多,4.12%和27.84%的農戶與外界聯系少和較少,有86.60%的農戶與外界聯系的渠道是通過網絡與外界聯系,且上網的頻率多集中在每周或每天1~3次,其比例分別為22.68%和50.52%。近年來,隨著社會技術的發展,農戶的社會網絡投資較高,但調查發現,男性對網絡的利用度和使用頻率遠高于女性,30歲以下的農戶對網絡的使用度和頻率高于30歲以上農戶,漢族高于回族和東鄉族,這表明社會網絡維度的投資出現了性別、年齡以及民族間的不均等,網絡更多的被農戶接受并應用,也成為農戶了解外界、獲取信息的重要途徑,農戶也普遍接受利用網絡學習各種相關知識和政策,社會網絡維度的投資將更有利于農戶自身的發展,將進一步減少農戶的知識貧困、收入貧困、信息貧困等,這對和政縣的農戶減貧有積極的作用,尤其是在漢族家庭中或者在少數民族家庭男性中作用更為突出。
(三)社會規范維度
本文通過農戶參與社會活動的意愿、不參加是否受到責罰、是否愿意借錢給別人、是否會向村委會或政府求助以及對社會志愿服務組織的認知度、參與度等指標衡量社會規范維度。接受調查的農戶中有39.18%的人表示偶爾會參加村委會的各項活動,12.37%表示只要有活動就參加,與之相反的是基本不參加和不參加的占到了38.14%和10.31%,并且有71.42%表示不參加且不會受到責罰,79.38%農戶愿意借錢給別人,當被問到是否在有困難時求助村委會或當地政府,表示不會和基本自己解決的分別占到8.25%和37.11%,看困難大小決定和會的分別占46.39%和8.25%。農戶表示不了解和完全沒聽說過當地的社會服務組織或協會人數有180人,占61.86%,據了解,當地的社會服務組織和協會經常組織一些利農的活動,了解和參加過社會組織或協會的農戶表示這些利農活動有多種形式,例如種養殖業培訓、相關就業培訓、電商培訓、勞務輸出培訓以及國家惠農政策知識講座等,這些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對農戶的生產和生活有較大影響。受當地的風俗習慣等影響,漢族的社會參與度遠遠高于少數民族,男性高于女性,社會參與度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農戶的生產生活,有利于調動農戶的積極性,在就業、種植、養殖等方面給農戶為農戶提供便利,在一定程度上減輕農戶的負擔。通過分析規范維度,和政縣農戶社會規范投資指數較低,說明農戶缺乏相應的管理機制,農戶的社會參與度與規范性不夠,然而社會參與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農戶的生產生活和就業等。就和政縣而言,當地的社會服務組織或協會會經常舉辦一些利農利民的政策宣講或相關技術培訓,為農戶提供就業信息等,這些活動提高了農戶的社會資本投資同時,對減少農戶貧困有積極的作用。
具體數據如表7、表8所示,社會信任、社會網絡、社會規范的正相關指數均值為農戶所選正向選項百分比的均等,社會資本總指數為三大要素的均值,且對于各要素的比較數據為各影響因素所占人數與三大要素的均值相乘得出。表中數據意在表明各資本指數的投資程度。
社會資本三個指標的共同作用對農戶收入的影響高于單一指標對收入的影響,在新的發展形勢中,培育和豐富和政縣的社會資本,對貧困地區具有直接的減貧作用,通過對社會資本的投入能促進農戶扶貧進程,改善貧困地區農戶的生產和發展條件,增強貧困地區農戶的自主發展能力。
四、對策
(一)扶貧的精準性有待提高
和政縣作為民族地區貧困縣,在扶貧過程中易出現貧困對象信息不精確,貧困農戶的需求無法精確反饋,導致政府扶貧措施無法精準實施,若要減少和政縣農戶的貧困狀況,就必須做好精準扶貧工作,提高扶貧對象的性精準、項目安排的精準性、資金使用的精準性、扶貧措施的精準性、脫貧成效的精準性,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切實保障農戶利益,積極解決農戶需求,充分發揮村委會的作用,及時登記更新農戶信息,為精準扶貧工作打好基礎。
(二)引導農戶加大社會資本的投入
在新的貧困條件下,精準扶貧是扶貧致富的根本出路,社會資本的合理利用是一個關鍵性問題。農戶社會資本同人力資本、物質資本等資本形態一樣,對于農民家庭經濟狀況都具有一定的作用,是一種不可忽略的資本形式。也就是說,要優化農戶收入結構和促進農戶增收,不僅需要促進農村居民在糧食作物方面增收,更需要農戶對社會信任、社會網絡、社會規范等社會資本的投入。農民自身應該加強與外界的溝通,注重培養農戶之間與團體之間的良好信任,政府也應該積極的為當地社會服務組織和協會的發展提供資金和政策支持,促進發展各種資源和信息的流動和變通,同時,和政縣相關政府部門應提高貧困人口中農村居民的社會資本水平,作為提高減貧能力、建立貧困群體和其他群體的互助機制、建設包容、共享的社會組織與社會資本的重要舉措。
(三)重視農村教育與技術培訓
本研究也證實了和政縣教育、民族、年齡結構等對扶貧社會資本投資的影響,因此要合理利用社會資本投資減少貧困、增加農民收入,還需大力發展農村教育,并加強實用技術的培訓,增強農民發展能力。政府還應積極倡導本地區的少數民族農戶在參加宗教活動時,應理性管理宗教費用的支出,注重積累物質資本。
參考文獻:
[1]趙雪雁,趙海莉.漢、藏、回族地區農戶的社會資本比較——以甘肅省張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臨夏回族自治州為例[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03).
[2]李忠華,詹霞.產業集群及其社會資本競爭優勢演進[J].經濟師,2007(11).
[3]周曄馨,葉靜怡.社會資本在減輕農村貧困中的作用:文獻述評與研究展望[J].南方經濟,2014(07).
[4]王志剛,張璟,蔣亞敏.社會資本對城鎮減貧的影響——基于CGSS微觀數據城鎮樣本的實證分析[J].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2013(01).
[5]譚洪業,王澤.家庭社會資本影響下的農戶收入結構選擇[D].中國社會科學院,2017.
[6]陸遷,王昕.社會資本綜述及分析框架[J].商業研究,2012(02).
[7]王恒彥,衛龍寶,郭延安.農戶社會資本對農民家庭收入的影響分析[J].農業技術經濟,2013(10).
[8]王格玲.社會資本對農戶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響[D].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2.
[9]姜梅紅.社會資本視角下的農村減貧策略研究[D].華中師范大學,2012.
[10]羅連發.社會資本與農村減貧研究[D].武漢大學,2012.
[11]路慧玲,趙雪雁,侯彩霞,張方圓,張亮.社會資本對農戶收入的影響機理研究——以甘肅省張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與臨夏回族自治州為例[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14(10).
[12]周曄馨.社會資本是窮人的資本嗎?——基于中國農戶收入的經驗證據[J].管理世界,2012(07).
[13]周玉龍,孫久文.社會資本與農戶脫貧——基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的經驗研究[J].經濟學動態,2017(04).
[14]王春超,周先波.社會資本能影響農民工收入嗎?——基于有序響應收入模型的估計和檢驗[J].管理世界,2013(09).
[15]裴志軍.制度剛性下的村民自治參與:社會資本與政治效能感的作用[J].農業經濟問題,2013(05).
基金項目:甘肅省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資助項目(10733082);甘肅農業大學青年研究生指導教師扶持基金項目(GAU-QNDS-201705);甘肅農業大學學科建設專項基金(GAU-XKJS-2018-235)。
(作者單位:祁永康、姜力瑋,甘肅農業大學財經學院;吳新苗,甘肅農業大學 動物科學技術學院;陳強強,甘肅農業大學財經學院、甘肅省區域農業與產業組織研究中心。陳強強為通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