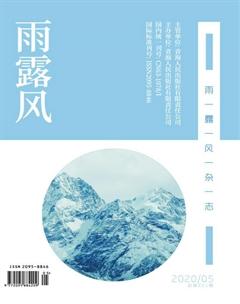《離騷》的象喻范式與文化內蘊
王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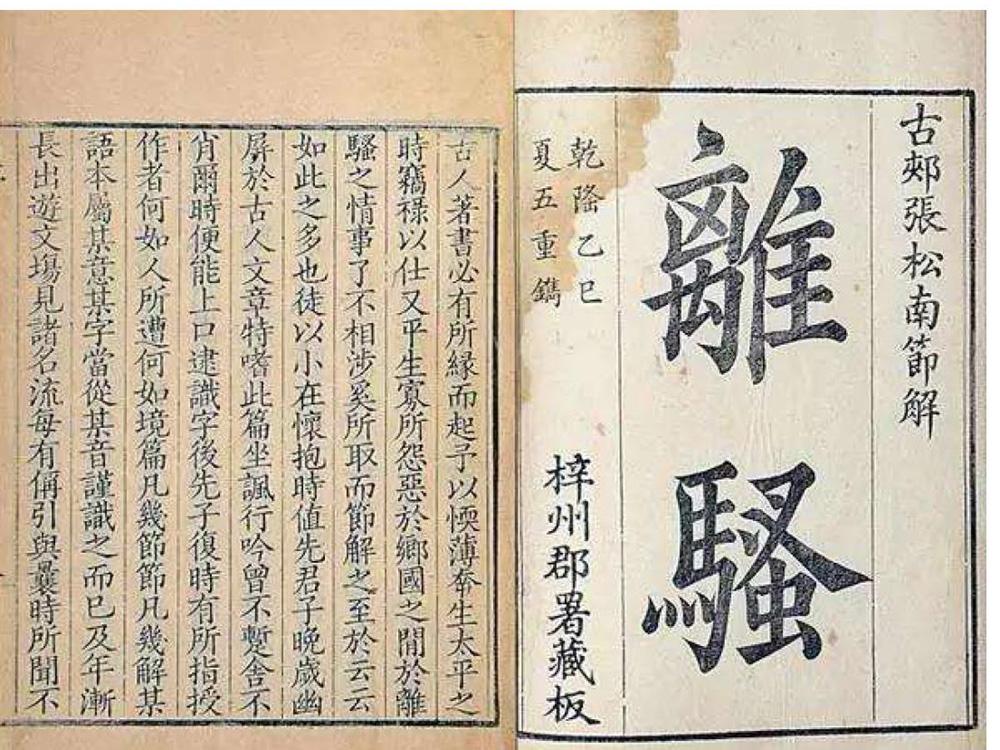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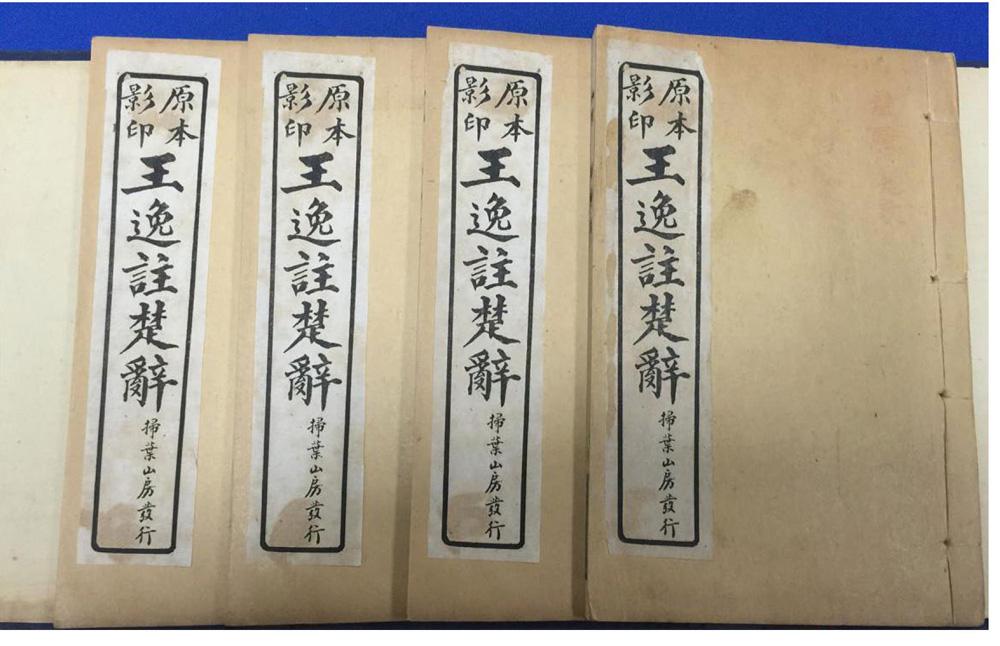
摘要:《離騷》不但借助了香草之喻和美人之喻,還借助了男女君臣之喻和求女之喻,通過整體思考和逐步遞進,構建了一條借棄婦喻逐臣、借男女喻君臣的象喻系統,該系統不但具備龐大性,還具備統一性,可以使物象世界與觀念世界的深層契合全面達成。該創作手法極具典范性,其實際的思維方式也是以象喻為主要核心,而且隱含了中國文化的陰陽以及男女等基本元素。《離騷》展示了此種象喻特點,并以此為依據,構建了相應的創作典范,即結合了其自身深厚且廣博的思想內容,形成一種極大的典范性和吸附力,從而提升棄逐文學的高度,全面提升整體的藝術表現力。
關鍵詞:離騷;象喻范式;文化內涵
《離騷》所指的象喻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層面,依次為:香草之喻,美人之喻,男女君臣之喻,求女之喻。四個層面各不相同,側重點也并不相同,實際內涵也有一定的差異性,但是又存在相互依托和層進層深的關系。所謂香草之喻,就是對外在的物象過于矚目,重點是借物比德;美人之喻就是由物而人,借助對美的張揚和護持,將自身的位置置于高處,體現棄而復求的思想;男女君臣之喻就是將家與國、倫理和政治結合在一起,重在提取和比照人物關系的相似性,借助虛實對接,進一步拓展棄逐事件的意義范圍和藝術空間;求女之喻就是以尋找媒介為實際的出發點,既是直接求臣,又是間接求君,借助被棄者的追求過程,展現出詩人本身對于理想君臣關系的渴望。根據這四個層面可以發現,美人之喻與男女君臣之喻是最為核心的兩個要項,前者主要提供了獨特的女性敘述視角,并且以性別的層面為依托,使香草之喻和求女之喻獲得了有力的支撐;后者則定格了國之君臣與家之夫婦的相似性關聯,并且映射了中華文化的深層意蘊。與《詩經》進行對比,《詩經》僅僅應用了簡單且局部的比興手法,而《離騷》實際的象喻方式,不但涵蓋了宏觀的整體性思考,還開辟了新鏡,在中國歷史上獨樹一幟。引用西方人的概念,可以認為其屬于一種范式,簡單來講,就是棄逐文學的象喻范式。
一、緣于性別變換的香草之戀和美人情節
孤立地看待香草之喻,可以發現,其只是應用了傳統的比興手法,而且延續了儒家的“以象比德”方法。在《離騷》中,涉及的名花香草非常多,如木蘭、江離、秋菊等,均屬于詩人最愛之物,詩人與這些名花香草朝夕相伴,如飲食、種植、培育等,象喻其自身的品性高潔;而椒、荃蕙等,則隱喻黨人和變易志節的朝臣。與此同時,王逸在評說《離騷》時也進行了相應的解釋,指出:“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故行清潔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塊,故孔子無所不佩也”。基于此,細微地展示了詩中對于“比德”方法的文化淵源。屈原之所以會借助“香草”之物比德,與孔子借“水”擬君子德行有極大的不同,但是在《離騷》中,屈原已經變身成為異性,即“美人”,因此,相應的愛好之物也會發生同樣的轉變,進而香草之喻融入了明顯的性別因素。
在《離騷》中僅一見“美人”,即“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這里的“美人”究竟是指屈原,還是代指君王,爭議頗多。王逸與朱熹都認為這里的美人主要代指懷王,將詩篇的上下語境全面聯系在一起,可以進一步發現,其解釋存在著一定的偏頗之處。在《離騷》中,有這樣一段話提及了“美人”,前言為“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后言為“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根據此可以發現,“余”與“吾”為所述者應用的主語,而且與君王并沒有任何的牽涉。如果對于“美人”而言,其實際指的含義為君王,整篇就會存在捍格難通的問題。此外下一段才將詩意過渡到了君王的身上,即“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作者在提及君臣時,或曰“靈修”,或曰“荃”,由此可見,其與“美人”本身有著本質性的差別,所謂“美人”代指的就是作者本身。
倘若可以確定“美人”是詩人的自喻定,則在《離騷》中,“美人”就是最為核心的形象,通過“美人”可以進一步感受到詩人愛美求美的多元旨趣。首先,美女情結與香草之戀的執著。以詩人的角度來分析,在這世間,最為高雅清潔之美是女性的內外兼修之美,因此,與之相配的只有大自然中的名貴花草,將其冰清玉潔的品格表現出來;只有真正的美女才會如此執著佩蘭戴芷,由此形成美女與香草之間穩固的關聯。其次,全面展示與護持美女之美。在《離騷》中,雖然僅一見“美人”之詞,但是透過字里行間可以感受到美女的氣息和特點。詩歌的前半部分反復出現對名花香草的酷愛,即是應用了“比德”的手法,達到以物喻人的目的;在整篇詩歌的后半段,展現了美女之美的自珍和固守。最后,結合了美女與棄婦,使其融合為一體,深化人物美而被棄、棄不失美的品性,以象喻的層面為實際的出發點,揭示了逐臣的悲劇命運以及堅剛意志。美女和棄婦是文學想像的重要產物,主要借助象喻的喻體,所謂的逐臣代表的是現實中處于流放狀態的作者,也就是象喻的本體。美女因為“美”遭受到了“眾女”的嫉妒和憤恨,最終被已與之“成言”的夫君中道拋棄;棄婦雖然對自身的淪落感到非常悲傷,但是美女的初衷并沒有發生任何的改變,仍然佩花結草。此種情形與屈原本身的被逐經歷完全貼合,也與屈原被逐之后的心態緊密相扣。由此虛實的結合,性別的轉換,不但導致香草與美人密切關聯,還構成美女到棄婦的合理過渡,進而達到棄婦向逐臣的邏輯轉換,從藝術表現的角度來分析,則深層對接了物象世界與觀念世界,與此同時,還展現了外在棄婦與內在逐臣之間的象喻主軸。
二、男女君臣之喻的文化因子及其后先傳承
以中國文化的基本形態為主要出發點,“一陰一陽之謂道”,通俗來講,決定萬事萬物發生發展的核心要素就是陰陽兩極,而且與其他領域存在相對應的關系,例如政治、家庭等。具體而言,在自然層面上,陰陽代表的就是天地和日月;在性別層面上,代表雌雄與男女;在倫理層面上,代表夫婦和父子;在政治層面上,代表君臣和上下。《離騷》展現了一套完整的宇宙、人倫以及政治秩序的發生論,不論是君臣、男女,還是父子和夫婦,其構建模式均為一陽一陰。陰代表的是服從地位的一方,具備柔弱的特性;陽代表的是統治的一方,具備陽剛的特性。因此,以陰、陽本身的性質不同為依據,則可以發現,婦與子以及臣均屬于同一個系列;同理,則夫與父以及君屬于同一個系列。而具體的系列內部,雖然人物存在極大的不同,但是整體的性質趨近相同。在一定情況下,不同身份者之間可以進行相應的置換,存在一種極為深刻的異體同構現象。
夫婦與君臣、婦道與臣道存在著一種異體同構的關系,所以,借男女比喻君臣,借棄婦比喻棄臣,早在春秋時期,就有很多政治家以及詩者對其關注和采用。例如《衛風·氓》有這樣一句“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其表面的含義是棄婦指責那位見異思遷的薄情丈夫,但實質上棄婦所指的是魯國和四方諸侯,而“氓”則為晉國。
由此可見,在中國文化中,男女君臣之間的緊密對應是存在的,在實際的文學創作以及傳授過程中,形成一種認知和詮釋系統。屈原在對前人承接的基礎上,又融入了自身的遭遇和感悟,進而重新整合了男女君臣之喻,借助篇幅的擴大,創作更為鮮明的騷體逐層詩。細細品讀《離騷》文本,可以發現,屈原對于傳統的承接和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首先,屈原應用“美人”進行自喻,以“眾女”喻眾臣,從傳統的陰陽觀念為實際出發點,進而達到落實男女君臣之間藝術性轉換的目的。《離騷》中的“美人”,主要指內美與外美集合于一身,高潔不群,得到了“靈修”與之“成言”的待遇,但是在此過程中惹來了“眾女”的嫉恨,則紛紛“謠諑”。根據此處可以明顯感受到現實與藝術之間的對應關系,其不單單存在于屈原與“美人”之中,楚王與“靈修”之中,還進一步體現了屈原與楚王的知遇經歷,將二者由忠到誹謗進而棄的悲劇命運全面表現了出來。而屈原本身處于弱勢,又不愿與強勢的一方合流,因此招來了眾多的嫉恨,導致君主聽信片面之詞,進而棄逐屈原。
其次,屈原身為逐臣,對于自身與棄婦等同的身份和命運有著超越他人的體驗,更加認識到男女君臣之間的相似性關聯,進一步強化了《離騷》中男女君臣之喻手法的自覺使用。王夫之在《詩廣傳》中解釋,“臣之于君委身焉,婦之于夫委身焉,一委而勿容自已,榮辱自彼而生死與俱”。根據此可以發現,古人已經清晰地認識到婦與臣二者的關聯性,屈原在遭到棄逐之后,則落實了這一文學創作層面。《離騷》中的夫婦關系,實質上對應的就是君臣關系。而且在《離騷》中,屈原重點反映了男女與君臣、棄婦與逐臣之間的關聯,并且應用了象喻手法,使創作層面圓滿呈現。簡單來講,從《離騷》開始,“家之棄婦”與“國之逐臣”的結合由隱晦逐步走向了明朗,由局部轉向了整體,由隨意轉向了自覺,因此,實際的典型范式意義誕生。
三、“求女”內涵及其象喻特點
在《離騷》的后半部分,“求女”情節貫穿其中,不但起到了對男女君臣之喻的延續作用,還進一步展現了中國文化中的陰陽觀念,因此,構成了這首騷體逐臣詩象喻系統的另一個關鍵。
對于“求女”這一部分的內容而言,前人論述各有差異,有人稱之為求賢君者,有人稱之為求賢臣者,不僅如此,還有人認為是為楚王求賢妃等。但是通過細讀文本可以發現,為楚王求賢妃這一論說頗為荒謬,與通篇毫無關聯,將其刨除。此外,楚國只有一君,又談何四處“求女”,因此,“求女”泛指求賢臣。這類賢臣在陰陽系統中與詩人相同,都屬于“陰”這一系列。以政治層面為實際的角度進行分析,則與詩人自身有著志同道合之意,而且可以通過自身的媒介作用,使遇合于君的目的得以達成。王逸注“哀高丘之無女”句日:“女,以喻臣”“無女,喻無與己同心也”;注“相下女之可詒”句曰:“言己既修行仁義,冀得同志,愿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而聘遺之,與俱事君也。”其意大體是準確的,“求女”最為直接的目標就是臣,而君則為間接的目標;又可以說第一階段的目的為求臣,而第二階段的目的則為求君。在品讀《離騷》的過程中,結合屈原的經歷,則可以看得更加清晰。在《離騷》文本中,詩人總結了自身早期與“靈修”的“成言”,到后面的“離別”導致自身的棄婦命運,最為關鍵的就是“眾女”的“謠諑”。逐臣要想重新獲取君主的信任,最為首要的就是打通中間的環節,找到真正了解自身且可以向君主關說的賢臣,進而揭露群小,杜絕讒言,確保君主看清真相。與此同時,文本中的棄婦要想使自己的夫君可以回心轉意,就要找到有異于“眾女”的“女”。
此外,還要指出一個問題,就是詩人在直接求女和間接求君的過程中,都借助了“媒”與“理”這樣的中介,所異之處則是在“求女”時借助了一些鳥類進行象喻;但是對于間接求君而言,“媒”與“理”并沒有直接表現出來。換言之,詩人將“女”喻指為賢臣,又以“女”對可通君側的“媒”與“理”進行喻指,使“女”本身充當兩種含義,構建了《離騷》男女君臣之象喻范式的補充和展示。
四、結語
本文主要對《離騷》的象喻范式與文化內蘊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討。《離騷》主要的中心內容就是逐臣的遭際和自我的求索,此種象喻范式和文化內涵,與以往的楚地文學有極大的不同之處,極為獨特,將香草美人作比,借助特定物象,同時應用比興、暗示等方法,委婉表達主體的情感。此外,《離騷》展示了此種象喻特點,以此為實際出發點,創作范式一經出現,就結合了深廣的思想內涵,吸附力和典范性極強,為后世帶來了極為深遠的昭示作用,不僅如此,還以承接前人為基礎,提升了棄逐文學和藝術表現的高度。
參考文獻:
〔1〕劉悅笛.“屈騷傳統”的巫本源與情本體——論中國思想與文化的“第四大傳統”[J].中原文化研究,2020,8(6):77-85.
〔2〕曾若源,劉穎.功能對等理論視角下的《離騷》德譯本分析[J].文學教育(上),2020(11):146-147.
〔3〕張曙光.草書屈原《離騷》節錄[J].大學書法,2020(5):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