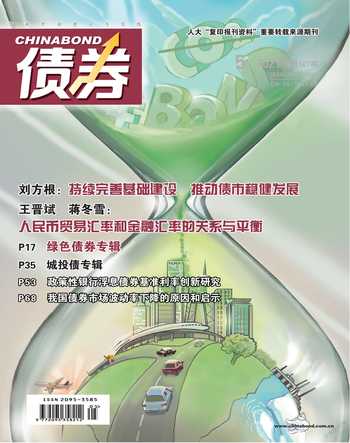從美、日債券市場發展歷程看債券市場發展的一般規律
劉芳菲
摘要:近年來,隨著我國債券市場不斷深入發展,市場的一些問題引起廣泛討論。本文從境外兩個典型債券市場(美國和日本)的發展經驗出發,通過梳理兩個典型市場的發展歷程,總結出債券市場發展的一般規律,希望對國內債券市場發展有所啟發。
關鍵詞:債券市場? 場外交易? 做市商? 注冊制
2021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穩步推進注冊制改革,完善常態化退市機制,加強債券市場建設,更好發揮多層次資本市場作用”。資本市場普遍認為,在加強債市法治化建設、防范違約風險的前提下,促進債券市場高質量發展、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是未來資本市場發展的大勢所趨。
由于歷史沿革和發展路徑等因素,近年來債券市場的一些問題開始暴露并引起廣泛討論。作為債券市場發展的參與者,筆者從海外債券市場發展經驗出發,通過梳理美、日債券市場發展歷程,總結出債券市場發展的一般規律,希望對學界和業界有所啟發。
美國債券市場發展歷程
相較中國債券市場,美國債券市場起步更早、規模更大、投資者群體更豐富,與全球市場的聯動性也更高。因此,研究美國債券市場的發展歷程,對于我們厘清債券市場的一般發展規律、看清未來發展方向有較大啟發。
美國擁有全世界規模最大、流動性最強的債券市場。根據美國證券行業和金融市場協會(SIFMA)的統計,截至2020年底,美國債券市場存量達到50.14萬億美元,在全球債券市場中的占比超過30%。同時,美國債券市場還具備如下特點:一是基礎產品和衍生產品種類豐富,包括國債、市政債券、住房抵押債券、公司債券、貨幣市場工具、資產抵押債券、利率互換、信用違約互換等;二是投資者群體多元化,有銀行、保險、共同基金、養老金、對沖基金、個人投資者等;三是基礎設施和服務機構生態豐富,涵蓋監管機構、自律組織、市場化交易平臺、做市商、托管清算后臺等,各司其職。羅馬建成非一日之功,美國債券市場的發展大體上經歷了五個主要階段。
階段一:交易所階段(1940年以前)
全球債券市場最初起源于戰爭時期的政府債務,美國債券市場形成于獨立戰爭時期,戰爭經費通過發行短期債券(如信用券、公債券和國庫券等)進行籌集,這些債券的發行催生了早期的債券交易市場。戰爭結束后,政府發債數量減少,企業發展迅速,特別是進入工業化大發展后,隨著產業升級和公司化改革,企業融資中直接融資的比例越來越高,股票與債券成為最重要的資金來源。
在最初階段,美國債券市場以交易所(紐約證券交易所)為主,當時的股票、債券均通過商業銀行發行與交易,銀行、保險是最主要的投資者群體。
階段二:場外交易興起階段(1940—1960年)
二戰時,為應對戰時的資金需求,美國國債發行量激增,戰后國債發行量有所下降,但市政債券、公司債券發行量持續穩定增長。在這一時期,美國債券市場有以下幾個特征:一是戰后重建階段,受經濟利好驅動,公司債券規模在1945年至1965年間增長了1.83倍,超過股票發行量增長幅度;二是從債券市場持有者看,商業銀行的持有比例達40%以上,仍是債券市場的主導力量;三是伴隨著債券發行規模的增加,債券市場的做市商逐漸崛起,批發——零售市場的格局初見雛形,到20世紀60年代,美國債券場外交易(OTC)市場共有17家做市機構;四是較多大型投資機構尤其是養老基金的進入增加了場外交易的需求,同時推進了做市商機制的發展。
階段三:以做市商為核心的市場格局形成(1970—1990年)
在“嬰兒潮”、石油危機、企業兼并潮和利率市場化的影響下,美國債券市場誕生了更多類型的債券品種——抵押貸款支持證券(1970年)、抵押擔保債券(1983年)、資產支持證券(1985年)及債務抵押債券(1987年),債券品種的多元化使得場內交易的模式不能滿足債券交易的需求。從投資者結構來看,這一時期,更多長尾且風格較激進的投資者進入了市場,如共同基金、養老基金和對沖基金等,需求端的增加帶動債券市場進一步增長。與此同時,多樣化的投資者結構要求更高效的交易機制,投資者對交易透明度及債券流動性的要求從根本上促進了場外市場做市商和經紀商制度的誕生與發展。這一時期的做市商和經紀商以聲訊(voice)方式服務客戶,建立了以郵件、電話、傳真等方式服務客戶的模式。
階段四:多層次資本市場生態逐漸豐富(1990—2008年)
20世紀90年代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之前,是美國債券市場發展較快的一個時期。這一時期呈現如下幾個特點:一是金融創新日益活躍,抵押貸款債券、資產支持債券和其他結構債券日益興起并逐漸成為市場新寵;二是信用債券的占比逐漸上升,“垃圾債券”的大量發行增加了企業債券的吸引力,政府債券發行量雖持續增加,所占比重卻日益下降;三是電子交易方式逐漸興起,做市商、經紀商和第三方交易平臺紛紛通過自建交易系統和交易平臺的方式服務客戶,服務效率和信息透明度大大提升;四是場外交易的地位進一步強化,場內交易的份額已經降至不到1%,大量交易圍繞做市商—經紀商完成,交易平臺百花齊放,但由于場外交易的隱秘性和分散性特征,市場的整體成交數據難以實現全口徑統計。
階段五:監管趨嚴下的多層次資本市場(2008年至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暴露出的監管缺位、市場過度自由化及場外市場信息不透明等問題對美國金融監管理念產生了重要影響。金融危機后,美國加強了對債券市場的立法、功能監管和自律管理,強化了對發行人、中介機構、交易平臺、托管結算等機構的監管和信息披露要求。
2009年之后,由于量化寬松政策的實行,公司債規模增速明顯回升。截至2020年末,美國債券和國債余額分別為50.14萬億美元和20.37萬億美元,債券余額分別是中國(全球第二大市場)和日本(全球第三大市場)的2.88倍和4.76倍,國債余額則分別是中國和日本的6.49倍和2.07倍。
當前,美國債券市場實行以立法為基礎,發行市場多頭管理,交易市場統一監管,發行和交易環節由市場機構自主選擇,托管結算集中統一的監管體制。首先,在發行監管層面,美國證券發行均采取注冊制,國債、市政債券及銀行發行的債券屬于豁免證券,無需注冊。其次,在交易監管層面,美國債券交易市場屬自由市場,但功能監管仍在該市場發揮作用——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集中監管,美國金融業監管局(FINRA)在SEC 的領導下發揮自律管理職能。再次,在基礎設施監管層面,美國全國證券清算公司(NSCC)和固定收益清算公司(FICC)負責清算,并接受SEC的監管;登記、托管、結算則是由美國證券存托與清算公司(DTCC)負責。最后,在交易服務機構層面,近年來,諸多電子交易服務平臺逐漸涌現,為強化市場規范管理,SEC將提供與交易所類似交易服務的機構統稱為另類交易系統(ATS),并建立相應管理規則,SEC和FINRA負責對ATS進行管理。
日本債券市場發展歷程
自20世紀60年代起步至今,日本債券市場已發展成為全球第三大債券市場。相較于西方金融體系,日本金融體系具有典型的東亞經濟體特征,呈現出以銀行為主體、以作為間接融資的補充為定位、以政策管制為抓手的早期特征,發展軌跡和路徑與我國債券市場的早期特征較為相似。因此,日本債券市場的發展歷程可為我國債券市場發展提供借鑒。日本債券市場大體經歷了如下幾個發展階段:
階段一:作為間接融資的一種補充(二戰結束至1973年)
二戰結束后,日本債券市場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未發展起來。1965年是標志性時間點,當年的經濟衰退使得政府啟動了國債發行,銀行和證券公司組成的承銷團開始進行債券承銷、投資,多數將債券買入并持有到期。
這一階段,日本的公司債券市場處于非常嚴格的管控中。具體來說,證券發行由銀行、證券公司共同構成的發行委員會來確定發行人、發行利率和發行金額等要素,而發行委員會成員的構成則以銀行為主體,公司債券的承銷機構和投資機構也以銀行為主。可以看出,在這一時期的日本債券市場中,銀行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公司債券更像是貸款等間接融資手段的一種補充。
階段二:利率逐步市場化和市場逐步開放(1974—1999年)
在利率市場化和金融對外開放的雙重驅動下,這一階段的日本債券市場發展較快:一是1973年日元匯率由固定匯率制變為浮動匯率制后,債券發行利率也隨之進行了市場化改革;二是1975年國債的大量發行、二級市場流通限制的放開,為債券市場的自由化、國際化奠定了基礎;三是1980年新外匯法頒布,日本債券市場向外資機構全面開放;四是1985年建立東京證券交易所國債期貨市場,完善了一系列交易機制,市場流動性得到提升;五是做市商—經紀商機制等海外實踐經驗被引入日本市場,促進了市場體制機制的完善。
在這一階段,日本公司債券市場比較顯著的變化包括:一是建立債券市場做市商制度并持續改進和完善;二是逐步解除公司債券發行標準中關于凈資產、股息率、凈資產倍率、自有資本比率等6項標準,并從事實上取消了決定統一發行條件的發行委員會;三是推出債券借貸等衍生交易方式,增強二級市場的活躍性和流動性。
應當指出,這一階段日本市場的開放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外界的推動。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日美貿易摩擦,美國憑借政治、經濟、軍事的多重優勢向日本提出了開放市場、解除管制的訴求。為應對外界壓力,也為內部發展尋找新動力,日本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如修改外匯法、提高對外投資比例、放松對資本流出的限制,促進了其債券市場的對外開放進程。
階段三:“東京金融大爆炸”下的開放和發展(2000—2011年)
在全球金融自由化的思潮下,日本從1998年啟動了名為 “東京金融大爆炸”(Tokyo Big Bang)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方案,進一步助推了日本的國際經貿發展和金融交易自由化。借助這一階段的躍升,日本金融市場最終發展成為一個自由、成熟的市場。從產品類型來看,日本債券市場種類繁多,可以分為公共債券、企業債券和外債三個大類,每一大類項下又可以細分為許多具有不同用途、采取不同交易方式的債券;從交易機制來看,日本政府通過豐富債券種類、優化國債期限結構等方式,極大地提高了其債券市場的市場化程度。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隨著日本經濟泡沫破滅,日本債券對境外機構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境外機構持有比例開始降低。形勢倒逼日本繼續進行一系列改革,不斷降低境外機構參與門檻,并從1999年到2004年先后多次推出多項針對境外投資者的稅收優惠。到2008年,境外機構持有日本債券的比例上升至11%左右,其后也一直保持在這一水平左右。
階段四:企業債改革和東京機構債券市場階段(2011年至今)
2011年,東京交易所成立東京機構債券市場(Tokyo Pro-bond Market),標志著日本企業債市場化改革進一步提速。該市場定位于服務專業機構投資者,基于相關法律框架,以信息披露主義和形式審核為主要管理手段,高度簡化債券的上市發行程序和信息披露要求,各類管制門檻極低。自建立以來,東京機構債券市場很快就吸引了來自全世界的各類發行人和投資者,市場發行主體、發行品種豐富多元,發行規模和交易規模屢創新高。
日本債券市場發展走過了一條不斷豐富發行主體、發行品種、發行方式,不斷放松管制,走向注冊發行的道路,在許多方面均能夠找到與我國債券市場發展軌跡相似的印記。略有不同的是,日本金融市場一直采用統一監管模式,1997年日本創設金融廳獨立行使統一的金融監管權。正是在金融廳設立后,監管理念才逐步向事后監管的市場化監管理念轉變,推動了日本債券市場管制的進一步解除。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日本債券市場日臻成熟,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相比于日本經濟體的體量而言,日本債券市場國債占比較高,支持企業融資的公司債券發行規模依然較小,發展存在結構性問題及深度不足問題;其次,從發行主體來看,沿襲日本經濟體以大企業、大財閥為主的特征,公司債券市場的發行人多為評級較高的企業,發行人多樣性上嚴重不足;再次,從二級市場來看,日本債券投資者投資結構單一且呈現分化交易特征,普通公司債券由銀行、保險(含養老金)、家庭等部門持有,而境外投資者、對沖基金等更多持有日本國債,對公司債券的持有率較低;最后,日本境內債券市場和離岸市場相比存在較大差距,無論是品種創新、發行規模上,還是交易活躍度上,境內市場都遠不如離岸市場。
從海外經驗看債券市場的共性特征和一般規律
雖然美、日債券市場的發展路徑不同、結構不同、投資者群體不同,但還是能從中總結出債券市場發展的共性特征和一般規律。
(一)注冊制下的市場化發行是市場擴容的前提
美國和日本債券市場的發展充分證明了注冊制在債券市場管理模式上的優勢,政府機構退出信息披露細節指導,大幅減少作為裁判的“主觀裁量權”,避免行政審核程序,對于大幅提升資本市場效率有積極意義。近年來,我國債券市場特別是銀行間債券市場也采用了以注冊制為核心的市場化發行機制,并取得突破式進展。注冊制這一國際市場通行的債券市場發行機制在我國新證券法中也被正式確立下來,并在公司信用類債券領域予以全面推行。
(二)以機構投資者為主,場外市場特征顯著
從發展歷程來看,國際主流債券市場和我國債券市場幾乎都經歷過由以交易所債券市場為主導、面向中小機構和個人投資者,向以場外債券市場為主導、面向機構投資者,且以做市、詢價等為主流交易方式的轉變。這樣的轉變并非偶然,而是由債券產品個性化、大額交易占主導、風險識別和風險承擔能力要求高等特性所決定的。因此,要進一步推動我國債券市場發展,仍應把握以場外市場為主體、面向機構投資者的發展方向,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
(三)通過承銷商、做市商、經紀商等中介機構引導市場定價和分層
與場內市場的中央對手方機制不同,國際成熟的場外市場都是通過承銷商、一級交易商、做市商、經紀商等中介機構來進行價格發現和市場分層、定價傳導的。以美國為例,場外交易市場無固定交易場所,而是一個債券交易商聯絡網,通過做市商和經紀商維持運行。場外交易市場主要由做市商通過各自的報價系統向公眾提供報價,而做市商之間的交易主要通過經紀商完成。近年來,隨著通信、網絡等技術的發展和ATS平臺的崛起,做市商之間直接進行交易的情況也逐漸增多。做市渠道的多元化、市場的分層、有效的價格傳導使得不同投資偏好、不同風險屬性的投資者可以快速找到合適的交易對手和價格,對于提升市場流動性有極大幫助。
(四)投資者群體擴大和多元化是流動性提升的基石
從全球債券市場的實踐經驗來看,在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的國家或地區(如美國、中國香港),基金、保險等非銀行金融機構在債券市場的投資比例較高。以美國為例,基金類投資者是美國債券市場的第一大投資主體,持債比例保持在30%左右,而銀行類機構持債比例在15%以下,這使得美國債券市場無論流動性還是換手率在全球都首屈一指。在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國家或地區(如日本、韓國),銀行掌握大多數金融資源,在債券市場中占據主導地位,債券更偏信貸替代的屬性,其二級市場流動性相對偏低。投資者群體的多元化程度與金融體系的歷史沿革、市場化程度、對外開放程度等有關,直接影響著市場的流動性提升。
(五)機構和平臺間的有機互聯可促進流動性提升和價格發現
在全球債券市場發展過程中,多個資產品種、不同區域、不同交易平臺之間存在市場分割現象一度較為普遍。但是在最近二十年里,隨著電子交易的興起和交易平臺的引入,傳統固定收益市場結構正在逐步被顛覆,場外市場電子交易平臺逐漸出現并快速發展。隨著美國SEC為ATS建立管理規則,各機構和平臺之間也紛紛建立接口傳輸規則,在機構和ATS之間、各ATS之間通過應用程序接口(API)等進行連接后,交易平臺和場所的界限進一步模糊,各平臺實現有機互聯互通,大大提升了市場信息傳輸效率和價格透明度,市場的流動性得到進一步提升。由此,近十年美國國債的換手率提升了1.5倍以上。
結語
與美、日債券市場相比,我國債券市場起步較晚但成長迅速,目前存量規模已位居世界前列。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伴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深化,我國債券市場逐漸與國際接軌,其發展和壯大為實體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強勁動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站在債券市場互聯互通、資本市場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筆者認為,債券市場發展有其自然規律,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一定要尊重這些內生規律,發揮市場的主觀能動性,方能有長遠的發展。
作者:上海快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騰訊QTade總裁
責任編輯:羅邦敏? 鹿寧寧
參考文獻
[1] 李虹含. 東京機構債券市場的發展與啟示[J]. 清華金融評論, 2020(9).
[2] 李松梁, 侍荻. 日本債券市場開放:歷程、特點與啟示[J]. 債券, 2018(10).
[3] 榮藝華, 朱永行. 美國債券市場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及主要作用[J]. 債券, 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