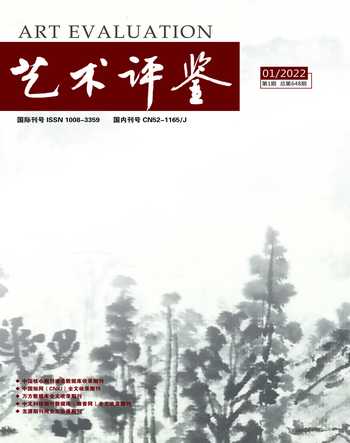人文關懷:紀錄片《好死不如賴活著》的嗓音特色
謝童
摘要:《好死不如賴活著》作為國內外享有盛名的紀錄片,對其嗓音特色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導演陳為軍從參與模式、連續性剪輯、視聽和解說詞等多方面進行敘述,并將其獨有的人文關懷注入影片,使得影片再現真實的同時也包含著導演對生命真切的同情和敬畏。
關鍵詞:《好死不如賴活著》 ?人文關懷 ?參與模式 ?真實性原則
中圖分類號:J9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3359(2022)01-0144-04
一場潛入,一個家庭,一束活著的希望。21世紀初,紀錄片導演陳為軍潛入了河南文樓村,記錄下一個被艾滋病纏擾的苦難家庭。他們是冰冷世態下蜷縮的生物;是油盡燈枯后殘留的蠟油;是夕陽西下時喊出最后一聲哀嚎。而就是這樣一個被灰藍色陰霾包裹下的家庭,在導演的參與下,也透出了一絲陰沉后的暖陽。制作者以其獨特的嗓音帶領我們一起“潛入”文樓村,在他的視角下一同與被觀察者經歷那段被還原的歷史,這也使得這部紀錄片被賦予了綿延至今的社會價值和聲譽。
一、參與模式:觀眾互動的窗口
紀錄片不僅僅是反應現實,同時也承載著制作者想表達的觀點與情感,而如何了解影片的觀點,我們需要觀察導演如何安排和處理畫面,以摸索其表達方式。在《好死不如賴活著》這部紀錄片中,社會演員通過自身生活的言行舉止直接給觀眾傳達導演想表達的內容,即艾滋病患者的生存狀態。除此之外,導演的參與也成為影片呈現的重要手段。
(一)參與模式的建立
20世紀60年代,隨著同期錄音的新技術誕生,一種全新的參與模式逐漸開始運用于紀錄片的制作中。這樣一來,制作人有機會舍棄曾經單獨地向我們敘述故事的方式,而向“我和你一起談論(交談)”的表達方式轉換。制作者也不再是“墻上的蒼蠅”,對歷史世界冷眼旁觀,而是主動參與到被拍攝者的生活,放下高高在上的姿態,與其處在同一高度交流和互動。
在參與模式發展的歷時進程中,不得不提到的一位就是邁克爾·摩爾。“許多人發現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60分鐘》采用了突襲式采訪,邁克爾·摩爾在他所有的存在道德邊界的影片中提煉成一種主要的策略,突襲式地攔截一個措手不及或者毫無準備的人進行采訪,可能意味著不夠尊重或者傲慢無禮”。而恰巧,在《好死不如賴活著》這部電影的尾聲處,導演陳為軍的發問也引來了相似爭議和質疑。他們認為其問題對于一個七八歲的孩子來說過于殘忍,甚至有人要求刪除或者改變這樣令人不適的結尾。但實際上,觀眾的視角是局限的,他們僅能作為受眾對影片進行自我式的解讀。結尾問題的真正意義其實在于導演利用采訪引導著馬寧寧講出她所懂得的東西,道出她所理解的艾滋病和家庭當下的狀況,以達到與觀眾交流的意圖。這僅僅是一個導演的私心嗎?其實不然,問題的答案顯然并不是導演所想刨根問底的,而是觀眾。但如此風格的采訪在這部影片中只是個例,總體而言,作為一部具有人文關懷的參與式紀錄片,導演在與被拍攝者關系的處理上仍然是以尊重為前提的。以采訪為主要特征的參與模式也正是在這樣的方式下被制作者一步步創建出一個觀眾和被拍攝者的共同話語環境。
(二)平民化的視角轉換
與邁克爾·摩爾不盡相同的是,導演陳為軍面對這樣一個極度悲劇性家庭時所構建的互動風格并不是挑釁性和攻擊性的,具有強烈的人文關懷。陳為軍把紀錄片看成是電影最高級別的藝術:“很多電影導演人生最大夢想就是拍攝一部紀錄片,而這是不可能的,他們永遠做不到像我們這樣和被拍攝者平起平坐,所以他們永遠進不去別人的心里。”正如陳為軍所說的,在拍攝《好死不如賴活著》時,他一直以平等的姿態面對被拍攝對象,與馬深義一家同吃、同住,真正融入到馬深義一家的生活當中。陳為軍在參與馬深義一家的生活時,對于他們來說其實更像是一位陪伴者,而非冷冰冰的拍攝者。雷妹死后導演和馬深義進行的交流,以及當小兒子馬占槽開始學會走路時二者的互動等等,毫無疑問地都向我們傳遞著導演在此時擺脫了“闖入者”的身份,換上了“傾聽者”的衣服,聆聽著這一家不幸的遭遇與寬慰。這樣的交流顯示的是建立在被拍攝者對制作者充分的信任基礎上的,敏感的艾滋病患者在拍攝中敞開內心,甚至主動面向鏡頭訴說,達到這樣效果的背后陳為軍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這的確超出了紀錄片某些概念上的意義。再來審視該片在道德上拿捏時,問題已經不再是是否揭開了他人的傷疤,而在于面對這樣一個群體,導演或是我們是否給予了應有的溫暖和關懷。在筆者看來,導演做到了。不僅如此,導演以一種與被拍攝者進行聊天的狀態融入到拍攝環境中,不僅拉近了自身與被拍攝者的關系,也使觀眾更易理解影片。這樣一種參與是超功利性的,沒有過多利益的驅使,就如同陳為軍所說,“我只是想記錄這個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
二、真實性原則:影片的內容表達
真實是紀錄片的靈魂,紀錄片與非紀錄片的最大區別就在于記錄真實。而記錄真實并非是將素材完完整整、毫無保留地呈現在觀眾面前,制作者有選擇性的將素材剪輯,并無可避免的進行有意識的加工是紀錄片之所以成為紀錄片的必然過程。因此,無論是剪輯還是視聽的建構,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都具有共時性。我們不應該探討紀錄片是否將真實純粹的“拋”給我們,作為觀眾,應把握住真實背后的無窮盡的意蘊與價值。
(一)連續性剪輯
“研究敘述的時間順序,就是對照時間或者時間段在敘述話語中的排列順序和這些時間或時間段在故事中的接續順序”。電影因為剪輯而富有強大的生命力,連接性剪輯一直都是電影剪輯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詩意模式的出現,拋棄了電影在傳統敘事上的時間節奏和空間的并置,但我們無法否認的是這樣的模式更注重的是渲染導演主觀情緒,對于《好死不如賴活著》這樣一個具有強烈悲劇色彩的紀錄片來說顯然是不合適的。在前期拍攝過程中,導演陳為軍一共拍攝到四十多個小時的素材,然而想要全部展現出來是不現實的,如何在保證真實的前提下用素材建構起導演的意志是對制作者巨大的考驗。最終,陳為軍選擇以時間為序,真實地將馬深義一家的日常生活鋪陳開來。“大暑”“秋分”“中秋”“霜降”“立冬”“冬至”“春節”,影片順著七個節氣的時間順序敘述著關于馬深義一家的陰晴圓缺。隨著時間的遷移,變化在每個人的身上悄然發生。雷妹的身體每況愈下,從大暑開始到霜降,逐漸割去了雷妹生命,而馬深義帶著三個孩子開始了艱苦的新生活。這種時間的連續性在敘事上抓住了時間對于馬深義這個家庭來說的重要性,對于他們而言,生命就像一場倒計時,永遠不知道死亡將會在何時到來。從適應模式的角度思考,作為一部參與模式的紀錄片,若拋棄了連續的時間,采用倒敘、插敘等手法,整部作品在風格上就有極大的差異。而連續性剪輯能更好的帶領觀眾與導演一起參與到被拍攝者的世界里,一起隨著時間感受馬深義一家的生活。
(二)視聽的建構
1.畫面
“有些紀錄片固然對未經加工的自然表現出一種真摯的關心,顯然是通過它們的攝影工作——它們的畫面——傳達出影片含義的。”殘破的屋檐、填不飽的肚子、嗅滿蒼蠅的臉,這就是馬深義一家真實的生活。為了強化這樣的生存狀態,導演運用了很多推鏡頭引導觀眾一起揭開、觀察這個悲劇性家庭的真實面貌。隨著鏡頭逐漸地推進,放大了馬深義臉上的悲楚、滄桑;雷妹黝黑消瘦面龐;孩子們的稚嫩且天真的眼神與諸多的近景和特寫鏡頭將他們背負的絕望展現得淋漓盡致。此外,長鏡頭的運用也使得影片的敘述更加真實。長鏡頭不間斷的連續性拍攝不僅能夠深化人物情感、烘托氣氛,而且更易激起觀眾的情感共鳴,留給觀眾深層的思考。
導演陳為軍曾在采訪中表示他在拍攝一些過于殘酷的畫面時猶豫不決。披著華麗外衣的社會表象下,隱藏多少裸露在陰暗潮濕處的螻蟻?這樣殘忍的記錄本身就是猶豫、徘徊的衍生物,更是人們不敢觸摸的真相。影片中的一些畫面確實引來了一些爭議和質疑,例如雷妹躺在拖車上時,嗅滿蒼蠅的臉和絕望的眼神以及她去世之后的畫面都引起了一些觀眾的不適,而最終他以“你記錄的是一種冤枉”來說服自己,仍然選擇將這些震撼的畫面搬上熒幕。他認為,如果為了迎合觀眾的心理而刻意舍棄一些情節,違背了紀錄片真實性的原則。真實的畫面恰好是反映和馬深義一家同樣處于社會邊緣人物的最好武器,紀錄片以此揭露真相,還原歷史,以達到對社會更大目的的意義和功能。
盡管紀錄片固然是在記錄真實,但是做到純粹、原始的真實是難以實現的,因此很多時候,紀錄片呈現的是一種被構建的真實,融入了導演極為細膩的情感表達。但這種建構并不等同于虛構,它仍然是以真實性為原則的,這里所說的建構是在沒有改變人物行為走向的前提下,寄托導演對于馬深義一家的同情和關懷。面對這樣一個被命運捉弄的家庭,導演在幾乎沒有調色的片中特意擇取一段寄托僅有的一點慰藉,這表現在導演將孩子們在中秋豐收后愉快玩耍的鏡頭刻意地渲染成金黃色,原本雪上加霜的家庭在有意識的畫面表達中被賦予了短暫的幸福感。而這,也僅僅是全片唯一一個褪去悲劇色彩的場面。作為電影制作者,畫面就是其傳達意志的方式,在馬深義一家凄苦的生活中給予一些溫暖則是導演陳為軍的意志。
2.音樂
除此之外,音樂作為在這部紀錄片中“奢侈”的部分,同樣是為傳達影片涵義所服務的。在音樂的選擇和運用上,導演極為謹慎,沒有過分用音樂進行情感渲染,而是短小精悍,點到為止卻余味深長。大雪紛飛的日子,馬深義孤身薄履地前往雷妹的墳前,這時,曲劇唱詞《張產兒》隨著畫面響了起來,“為了兒不受屈,我學會做飯又做衣,又當爹又當娘并非容易……”不得不說,導演在音樂上的選擇上可謂是別出心裁,前有視覺表達,后有聽覺效果,二者的結合完完全全使馬深義的處境展現出來,將影片的悲劇氛圍推向高潮。
(三)輔助性解說詞
作為“上帝之聲”的解說詞在這里并沒有扮演一個評論者的身份,僅僅是為影片的內容作出一些必要的解釋和補充。例如,當影片中雷妹沒有出現在鏡頭里時,觀眾會疑惑,是否雷妹此時已經不在人世?為了避免和解決觀眾的疑問,導演在此時安排了相應的解說詞,人們這才知道,原來雷妹是到診所掛吊針去了。又如馬深義給雷妹上百日墳,解說詞已經在這個行為開始之前做好解釋和補充,“這天是雷妹去世一百天的日子,按照祖上傳下來的規矩,該辦了犧牲,上一個百日墳”。之后,畫面即是馬深義孤身走在大雪中的背影。設想一下,要是沒有這段解說詞,影片在內容上就會存在傳達不明的現象。因此,這部紀錄片的解說詞看似被縮小化,其實發揮了必不可少的輔助作用。
三、人文關懷:邊緣群體的群像刻畫
《好死不如賴活著》瞄準的雖是艾滋病患者,但艾滋病并不是導演拍攝的主題。導演從簡單的日常生活出發,探求被艾滋病折磨下馬深義一家的生存狀態和人的求生本能,實則是為了引起大眾對處于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的關注和共鳴。陳為軍對于馬深義一家的記錄和刻畫影射了整個邊緣群體的生存圖景,這是作為媒介本身的紀錄片反映社會現實的基本功能,也是其應具有的社會責任。無論什么時期,以人為本的創作理念永遠是紀錄片創作的核心。
四、結語
在國內大環境的驅使下,一些制作者在追求紀錄片的路上越走越偏,生硬、強行的給影片套上華而不實的大道理,卻忽視了“大言希聲,大象無形”。距離《好死不如賴活著》的拍攝已經過去近20年,它的嗓音如潤物細無聲般滋潤著影片的風格,雖不華麗卻實實在在,飽含著對社會現狀的人文關懷,而像這樣真正有社會意義的影片價值是不會隨著時間消蝕的。
參考文獻:
[1][美]比爾·尼可爾斯.紀錄片導論[M].陳犀禾等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7:182.
[2]張瀚,陳為軍.我的攝像機就是觀眾的一雙眼睛[J].電影世界,2011(10).
[3]熱拉爾·熱奈特.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14.
[4]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電影的本性物質現實的復原[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