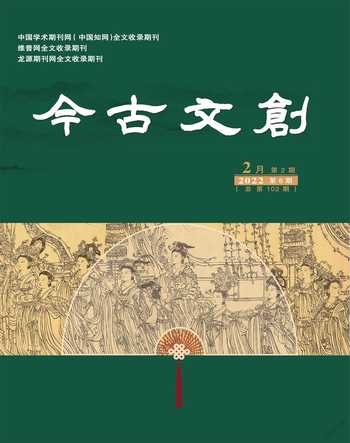阿佩爾與伽達(dá)默爾詮釋學(xué)之爭初探
黃浩雄
【摘要】本文要探究的是發(fā)生在20世紀(jì)兩位德國哲學(xué)家之間一些不甚矚目,卻依然重要的哲學(xué)爭論。爭論的經(jīng)過大致如下。伽達(dá)默爾(1900-2002年)在1960年出版了代表作《真理與方法》,宣布要建立一種哲學(xué)詮釋學(xué),它將以“理解”為立足點(diǎn),在人文科學(xué)領(lǐng)域抵制自然科學(xué)方法論的過分要求。這種獨(dú)特的理論主張和思維模式,在西方哲學(xué)界逐漸掀起了一陣?yán)顺保粫r(shí)間喝彩聲無數(shù)。但也不乏有人提出質(zhì)疑,比如同為詮釋學(xué)領(lǐng)域的阿佩爾(1922-2017年)。此后30多年,阿佩爾針對(duì)詮釋學(xué)的“理解”問題,包括理解中的意識(shí)形態(tài)疑難、理解要“不同”還是要“更好”等問題,與伽達(dá)默爾展開了一系列爭論。筆者嘗試對(duì)爭論的重點(diǎn)做扼要的闡述與分析。
【關(guān)鍵詞】伽達(dá)默爾;阿佩爾;詮釋學(xué)之爭;理解;意識(shí)形態(tài)
【中圖分類號(hào)】B089? ? ? ? ? ?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 ? ? ? 【文章編號(hào)】2096-8264(2022)06-0046-03
一、理解中的意識(shí)形態(tài)疑難
伽達(dá)默爾的哲學(xué)詮釋學(xué)思想豐富而充實(shí),阿佩爾其實(shí)和很多人一樣,對(duì)其中很多內(nèi)容贊嘆有佳。但在一些關(guān)鍵性的細(xì)節(jié),特別是關(guān)于詮釋學(xué)的“理解”問題上,阿佩爾頗有異議。須知,傳統(tǒng)(方法論)詮釋學(xué)想要提供一套解讀文本的方法來幫助人們理解文本,而伽達(dá)默爾的(本體論)哲學(xué)詮釋學(xué)關(guān)注的就是“理解”本身。傳統(tǒng)詮釋學(xué)認(rèn)為讀者先要把文本理解了再解釋給別人聽,所以理解在先、解釋在后;伽達(dá)默爾卻揭示出理解與解釋的內(nèi)在統(tǒng)一性,認(rèn)為理解與解釋本是一回事,讀者只有把文本解釋出來,自己才算達(dá)成了某種理解。
這還不夠,伽達(dá)默爾認(rèn)為詮釋學(xué)除了理解與解釋,還有個(gè)必不可少的要素,那就是應(yīng)用(application)。他指出,過去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與狄爾泰(Dilthey)的方法論詮釋學(xué)拋棄了應(yīng)用這一要素,導(dǎo)致詮釋學(xué)誤入歧途;而真正地理解只有在應(yīng)用中才能達(dá)成。伽達(dá)默爾以歷史悠久的神學(xué)詮釋學(xué)和法學(xué)詮釋學(xué)為例。他指出,牧師要將同樣的經(jīng)文在不同處境下解釋給不同的信眾聽,法官要將同樣的法律用于判決截然不同的案例;這意味著,他們每次都要針對(duì)某種情形,將自己對(duì)文本的理解加以應(yīng)用,在應(yīng)用中達(dá)成某種理解。事實(shí)上,各行各業(yè)的人們都必須在每次應(yīng)用或者說介入(engagement)中,達(dá)成自己的理解。伽達(dá)默爾相信這足以說明,應(yīng)用是詮釋學(xué)必不可少的一環(huán),理解與應(yīng)用密不可分。
但阿佩爾卻發(fā)現(xiàn)了令人不安的一面。既然理解與應(yīng)用密不可分,人們難道不會(huì)因此做出“別有用心”的理解嗎?“一旦理解內(nèi)在地與應(yīng)用相聯(lián)系,歷史機(jī)會(huì)主義的問題就不可避免。”[1]他認(rèn)為,過分地要求人們對(duì)自己的理解進(jìn)行有約束力的(binding)應(yīng)用,就會(huì)在意識(shí)形態(tài)上敗壞人文科學(xué)。[2]的確,阿佩爾贊同說,任何理解與解釋都有歷史性,都離不開某種的歷史而實(shí)踐的介入,而且伽達(dá)默爾的貢獻(xiàn)就是否定了實(shí)證主義對(duì)這種介入的否定。但這種介入會(huì)使得理解與應(yīng)用合二為一嗎?在他看來,伽達(dá)默爾錯(cuò)誤地混淆了兩種形式的應(yīng)用,比如法官和法學(xué)史家各自對(duì)法律的應(yīng)用。在伽達(dá)默爾眼中,法官和法學(xué)史家都必須理解法律怎樣應(yīng)用于每一個(gè)案,所以他們大同小異。阿佩爾卻指出,法官的職責(zé)比法學(xué)史家重大的多:法學(xué)史家只是負(fù)責(zé)把生硬難懂的法律條文解讀出來,而法官不僅要根據(jù)自己對(duì)法律的理解來判決罪行,而且必須對(duì)自己做出的理解負(fù)責(zé)。他說:“無疑,法學(xué)史家不可自夸,他能夠通過語言和歷史研究成為與法典文本(corpus iurus)同時(shí)代的人,而這一點(diǎn)——作為達(dá)到與作者的最終認(rèn)同的條件——正是施萊爾馬赫所要求的。但法學(xué)史家也不可為了有意識(shí)地現(xiàn)實(shí)化理解而否棄施萊爾馬赫的詮釋學(xué)理解。” [3]
伽達(dá)默爾真的如此愚蠢嗎?阿佩爾有沒有弄錯(cuò)什么呢?的確,伽達(dá)默爾是從“理解會(huì)被理解者的處境所制約”推出了“有必要在應(yīng)用中實(shí)現(xiàn)理解”,但他并不是說這就意味著“有意識(shí)地”對(duì)理解加以應(yīng)用。伽達(dá)默爾其實(shí)是說:“在理解中,我們總是在應(yīng)用。”法官的職責(zé)確實(shí)與法學(xué)史家大為不同,然而理解的條件卻沒有變:無論哪種情況里,如果要完全理解法律,就必須應(yīng)用法律。[4]
不過,雖然阿佩爾誤會(huì)了伽達(dá)默爾,但人們的確有必要像他那樣,對(duì)理解與應(yīng)用相結(jié)合的意識(shí)形態(tài)后果留點(diǎn)心眼。曾有批評(píng)者指出伽達(dá)默爾立場中的機(jī)會(huì)主義傾向,伽達(dá)默爾雖然試圖用理解中的“對(duì)話”結(jié)構(gòu)來回應(yīng)這種批評(píng),但如今意識(shí)形態(tài)批判卻質(zhì)疑這種解決方案。“這里的問題不只是我們關(guān)于我們社會(huì)或他人的理解可能由于我們不承認(rèn)他們主張所包含的意識(shí)形態(tài)模糊所歪曲。我們自己的理解可能包含我們對(duì)之無意識(shí)的意識(shí)形態(tài)組成成分。換言之,我們的理解可能不僅包含從我們?cè)趯?shí)踐和歷史上的介入而形成的、我們通過和對(duì)象的照面可以改變的前見;它還可能包含真理與歪曲的特別聯(lián)系,正如我們已經(jīng)說過的,這種特別聯(lián)系刻畫了意識(shí)形態(tài)和病理學(xué)的特征,并且至少按照阿佩爾的看法,是反對(duì)詮釋學(xué)深入的。”
由于歷史不只是產(chǎn)生于行為者的自覺意向,而且產(chǎn)生于因果聯(lián)系、無意識(shí)動(dòng)機(jī)、無意向后果。人們的行為與表達(dá)常常源于超出他們控制的各自因素,無法通過詮釋學(xué)式的談話加以澄清,只能在因果上加以解釋。因此阿佩爾認(rèn)為,必須用一種“準(zhǔn)客觀的說明性科學(xué)”來補(bǔ)充詮釋學(xué)式的理解,而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為此提供了一種模式。
美國學(xué)者喬治婭·沃恩克(Georgia Warnke)認(rèn)為阿佩爾的這種做法令人困惑。第一,阿佩爾錯(cuò)以為伽達(dá)默爾只把歷史當(dāng)成人們自覺意向的結(jié)果,但從《真理與方法》中對(duì)德國歷史學(xué)派的蘭克(Ranke)與德羅伊森(Droysen)的批判來看,伽達(dá)默爾與阿佩爾一樣認(rèn)為,歷史還包括人們無意向的結(jié)果和超出人們控制范圍的因果聯(lián)系的結(jié)果。理解歷史不是要把歷史人物的意圖重構(gòu)出來,因?yàn)榻忉屨呖偸菐в挟?dāng)事人不具備的“后見之明”,因此無法像當(dāng)事人那樣體驗(yàn)歷史,只能根據(jù)能感知到的因果關(guān)系和非意向的結(jié)果來重構(gòu)歷史處境。
但阿佩爾爭論說,如果我們?cè)诶斫鈿v史時(shí)超出了當(dāng)事人的實(shí)際意圖,不僅是因?yàn)槲覀兊臍v史視角與他們不同,而且正如馬克思所說,人類確實(shí)無法有“意志和意識(shí)”地創(chuàng)造他們的歷史。人類依然會(huì)作為對(duì)象,對(duì)他們控制不住乃至感知不到的因果性因素產(chǎn)生反應(yīng)。按伽達(dá)默爾的說法,傳統(tǒng)詮釋學(xué)的誤區(qū)是在存在論上誤解了意義、意圖與理解的關(guān)系;但阿佩爾認(rèn)為,他們真正的問題是誤解了歷史條件。光靠詮釋學(xué),人們既不能弄清個(gè)體會(huì)在多大程度上對(duì)因果性因素起反應(yīng),也不能明白人們表現(xiàn)出來的意圖和理由會(huì)伴隨著多少歪曲。
第二,如果這樣來闡明阿佩爾的立場,就會(huì)留下兩個(gè)問題。阿佩爾認(rèn)為,只有當(dāng)人們假設(shè)自己不只是歷史的主體也是歷史的對(duì)象時(shí),才會(huì)發(fā)現(xiàn)人們的自我理解的確在意識(shí)形態(tài)上有所歪曲。大家的行為和表達(dá)可能不是來自合乎邏輯的意圖,而是有各種原因;不斷的對(duì)話不但無法弄清它們的真實(shí)含義,反而會(huì)把含義變得更加模糊。面對(duì)這一難題,阿佩爾主張用準(zhǔn)客觀的說明性科學(xué)來解決。
但在伽達(dá)默爾看來,這樣一種科學(xué)信念本身就有問題。伽達(dá)默爾不認(rèn)為因果上推出的行為只是有著偶然的問題,并且主張阿佩爾作為理想而指出的理由和意圖之透明性完全是空想。他認(rèn)為,人們的思想總是受制于一些控制不了的前見與傳統(tǒng)因素。這意味著前見無法徹底消除,只能用新的正確前見取代舊的錯(cuò)誤前見。而且每次取代或消除都是片面而有視角的。對(duì)伽達(dá)默爾而言,每一次闡明與自我啟蒙的過程都依賴于自我理解的其他可能方式補(bǔ)充性的暗淡或模糊。按自然科學(xué)的發(fā)展模式,把人類歷史視為“從神話到啟蒙的線性進(jìn)步”就錯(cuò)了。實(shí)際上,人類文明的“顯”與“隱”之間有一種從未停止的緊張關(guān)系。即便是意識(shí)形態(tài)批判與精神分析也一樣,揭示出某種意義就意味著模糊掉其他可能的意義。
二、理解,“不同”還是“更好”
除了意識(shí)形態(tài),這場爭論的另一維度就是理解中的差異與進(jìn)步之爭。伽達(dá)默爾宣稱“理解”只是“不同的理解”,只有差異沒有高下;阿佩爾則認(rèn)為不能止步于“不同”,要追求“更好的理解”。施萊爾馬赫曾認(rèn)為,讀者可以比作者自己更好地理解作者;這在阿佩爾眼中是個(gè)反駁伽達(dá)默爾的好理據(jù)。但伽達(dá)默爾顯然無法接受。
每個(gè)誤解都要以一個(gè)基本的意見一致為前提,指出這一點(diǎn)是海德格爾對(duì)詮釋學(xué)的一大貢獻(xiàn)。阿佩爾不僅和伽達(dá)默爾一樣接受了這一洞見,還承認(rèn)詮釋學(xué)的理解是在對(duì)每個(gè)局部語境的理解之上。然而,雖然他們都要捍衛(wèi)詮釋學(xué)式“邏各斯”(logos)的普遍性,卻是出于不同的理由。阿佩爾認(rèn)為,詮釋學(xué)的理解屬于一種“調(diào)節(jié)性理念”(the regulative idea),這一理念或原則會(huì)促使“理想的交往共同體”達(dá)成“理想化的共識(shí)”。因此,他要破除詮釋學(xué)“對(duì)邏各斯的遺忘”,實(shí)現(xiàn)對(duì)理解的規(guī)范化。
阿佩爾不反對(duì)差異性的理解,但他強(qiáng)調(diào),差異中存在著進(jìn)步。與伽達(dá)默爾不同,阿佩爾深受美國哲學(xué)家皮爾士(Peirce)的影響。就像皮爾士“先驗(yàn)哲學(xué)所假定的目的性研究過程”一樣,阿佩爾也假定了一種目的性理解過程,這個(gè)理解過程的出發(fā)點(diǎn)是“一個(gè)實(shí)在的解釋共同體,它把理想化的、無限擴(kuò)大的共同體假定為終極目標(biāo)”。
伽達(dá)默爾將理解視為一種效果歷史事件,阿佩爾對(duì)此表示反對(duì),“他認(rèn)為伽達(dá)默爾的過去目的論沒有對(duì)詮釋學(xué)的經(jīng)驗(yàn)邏輯進(jìn)行恰當(dāng)?shù)拿枋觯峭ㄟ^對(duì)理論模式的挑選使它變成了傳統(tǒng)關(guān)聯(lián)性實(shí)體化的結(jié)果。”在阿佩爾看來,伽達(dá)默爾關(guān)于“應(yīng)當(dāng)加以理解的東西在任何解釋面前都具有完全的優(yōu)勢(shì)”這一觀點(diǎn)站不住腳;從先驗(yàn)詮釋學(xué)的視角看,不能從過去的視角對(duì)理解進(jìn)行考察,而必須從一種目的性理解過程出發(fā)對(duì)理解進(jìn)行描述;只有轉(zhuǎn)換成這樣的視角 ,才能完整地發(fā)現(xiàn)理解過程,并且對(duì)其進(jìn)行規(guī)范性判別。對(duì)阿佩爾而言,如果“假定應(yīng)當(dāng)被解釋的東西的實(shí)際效用要求原則上優(yōu)于(受實(shí)際傳統(tǒng)形成驅(qū)使的)解釋者的理論與判斷”,那么“對(duì)理解的規(guī)范性調(diào)控”就不再“立足于未來”,而是讓位于“過去的優(yōu)先性”。
伽達(dá)默爾并沒有徹底拒絕“更好的理解”,他和阿佩爾一樣,將理解視為一個(gè)規(guī)范性概念。但阿佩爾覺得這還不夠。他指出,皮爾士與伽達(dá)默爾一樣發(fā)現(xiàn)了“前見”在理解過程中的作用;不同之處在于,對(duì)于先驗(yàn)哲學(xué)中的奠基理論這一傾向,皮爾士沒有簡單地拋棄掉,而是在真理共識(shí)論的框架內(nèi),通過加深意義批判而予以保留。通過將這種真理共識(shí)論與“先驗(yàn)詮釋學(xué)對(duì)皮爾士符號(hào)學(xué)的闡釋”相結(jié)合,并應(yīng)用于理解過程,阿佩爾確保了“伽達(dá)默爾所缺失的批判必然性的標(biāo)準(zhǔn)尺度”。
不過,皮爾士的共識(shí)論面對(duì)不是詮釋學(xué)的理解過程,而是科學(xué)的認(rèn)識(shí)過程。為了避免這一科學(xué)主義傾向,阿佩爾援引了皮爾士的繼承者羅伊斯(Royce)。“在羅伊斯的闡釋哲學(xué)種,皮爾士的符號(hào)學(xué)在一定程度上從對(duì)康德的實(shí)用主義轉(zhuǎn)化,變成了對(duì)黑格爾的新唯心主義轉(zhuǎn)化,這無疑使美國哲學(xué)最大程度地同哲學(xué)詮釋學(xué)的德國傳統(tǒng)相接近,這種哲學(xué)詮釋學(xué)借助伽達(dá)默爾的傳統(tǒng)中介理論又繞回到了黑格爾的路線上。”[5]
但是,如果人們把“伽達(dá)默爾有關(guān)存在詮釋學(xué)的論斷同符號(hào)實(shí)用主義的闡釋理論”相比較,就會(huì)依照阿佩爾的觀點(diǎn)得出兩個(gè)結(jié)論:第一,羅伊斯明確指出“理解”與“說明”的關(guān)系不是互斥,而是互補(bǔ),從而將自然科學(xué)與精神科學(xué)的關(guān)系提上了一個(gè)臺(tái)階。第二,羅伊斯還“消除了對(duì)意見一致性問題的科學(xué)限制”并“指出了先驗(yàn)科學(xué)的詮釋學(xué)改造方向”。羅伊斯與伽達(dá)默爾一樣以“傳統(tǒng)”為詮釋學(xué)的中介;不同的是,羅伊斯允許將這一中介視為黑格爾意義上的目的性進(jìn)程。[6]
通過援引羅伊斯,阿佩爾將皮爾士的未來主義真理觀從科學(xué)研究領(lǐng)域轉(zhuǎn)化到意義理解領(lǐng)域,從而讓先驗(yàn)哲學(xué)所假定的理解過程能夠?qū)ο闰?yàn)哲學(xué)假定的目的性理解過程起支持作用,而這一理解過程經(jīng)歷“長跑”后將達(dá)到“理想化的共識(shí)”。理想化的交往共同體將取代理想化的實(shí)驗(yàn)共同體和解釋共同體,前者中形成的理想化詮釋學(xué)共識(shí)也將取代后兩者中形成的未終結(jié)的理論共識(shí)(它們都屬于調(diào)節(jié)性理念)。阿佩爾認(rèn)為,這樣一種調(diào)節(jié)性理念會(huì)促成“解釋性絕對(duì)真理的理想化極限值”,而為了達(dá)到這一目的就要同時(shí)“消除交往的一切障礙”。
但在伽達(dá)默爾眼中,這些都難以成立。他在回復(fù)阿佩爾時(shí),雖然承認(rèn)“詮釋學(xué)的意義向度是同理想的解釋共同體無盡的談話相關(guān)聯(lián)”,但他并不認(rèn)為這種談話“會(huì)達(dá)到自我認(rèn)識(shí)的理想模式”,“以致意義完全被把握并流傳下來”。[7]伽達(dá)默爾覺得“意義理解的這種理想化概念”把阿佩爾在內(nèi)的很多批評(píng)者都迷惑住了。伽達(dá)默爾承認(rèn),鑒于阿佩爾“關(guān)于詮釋學(xué)問題的討論因其援引皮爾士和羅伊斯而大為增色,他在所有的意義理解中都制定出實(shí)踐關(guān)系,因此,當(dāng)他要求提出一個(gè)不受限制的解釋共同體(Interpretationsgemeinschaft)的觀念時(shí),他是完全正確的。顯然,這樣一種解釋共同體的特征就是證明理解努力的真理要求的合法性。”但是伽達(dá)默爾懷疑的是“把這種合法性僅限于進(jìn)步觀念是否合適。”畢竟“業(yè)已被證明的解釋可能性的多樣性絕不排除這些可能性會(huì)相互取代(sich verschatten)。事實(shí)也是如此,在這種解釋實(shí)踐的進(jìn)程中出現(xiàn)的辯證反題也絕不會(huì)保證它達(dá)到真正的綜合。”[8]
伽達(dá)默爾既不反對(duì)在“完滿性前把握”意義上與事實(shí)相反的合理性假設(shè),也不反對(duì)讓語言天賦和理想天賦都匯聚到現(xiàn)實(shí)交往共同體中。因?yàn)榧词狗磳?duì)也無法達(dá)到對(duì)理想化程度的近似接近。人們?cè)诶斫膺^程中通過完滿性前把握而實(shí)現(xiàn)的東西,可能正好排斥理想的結(jié)果。伽達(dá)默爾反對(duì)的是取消對(duì)語言含義時(shí)間限制的主體間性的理想化;準(zhǔn)確地說,他反對(duì)在意義理解的極限值上對(duì)理想化理解條件的總體性前把握,因?yàn)樗鳛槔硐胝Z言的極限值,必然會(huì)拜托歷史環(huán)境和社會(huì)環(huán)境的一切限制條件,為作為理解過程的標(biāo)準(zhǔn)效力。
可見阿佩爾的思路并非無懈可擊。伽達(dá)默爾認(rèn)為理解的可能性和語言含義的透明性不該被錯(cuò)誤地理解為“最終”理解的顯現(xiàn),因?yàn)橛捎趯?duì)語言含義之存在的運(yùn)用所做的客觀主義誤讀,將使上述錯(cuò)誤直接回溯到形而上學(xué)。伽達(dá)默爾曾在不同的關(guān)聯(lián)性中指出,這種理想化會(huì)拋棄可能性的現(xiàn)實(shí)條件,而只有在這種現(xiàn)實(shí)條件下語言才是充滿意義且必需的。原因是理想化的交往只存在與交往可能性條件的外部與彼岸,這樣的交往由于拋棄了交往的現(xiàn)實(shí)條件而升級(jí)為“完全唯心論的意義透明”。
因此阿佩爾的理想交往共同體似乎自相矛盾,因?yàn)檫@一理想的實(shí)現(xiàn)就是歷史的終結(jié),而伽達(dá)默爾無疑會(huì)反對(duì)這種形而上學(xué)的觀念。伽達(dá)默爾相信,通過援引完滿性前把握就能論證“應(yīng)當(dāng)加以理解的東西在任何解釋面前都具有完全的優(yōu)勢(shì)”,因?yàn)檫@里的前把我只是對(duì)真理與合理性的假設(shè)。但不能有用“自我認(rèn)識(shí)的理想化模式”來框定詮釋學(xué)理解。
德國學(xué)者烏多·蒂茨認(rèn)為,如果說阿佩爾批判的詮釋學(xué)相對(duì)主義成長于其絕對(duì)主義的陰影,那么明確地說,“阿佩爾關(guān)于傳統(tǒng)于共識(shí)、過去的目的性與未來的目的性、調(diào)節(jié)理念與真理事件兩者比居其一的論斷是一種錯(cuò)誤的取舍。”[9]但伽達(dá)默爾亦有其不足之處。伽達(dá)默爾高估了語境的效果歷史力量,低估了理解過程的限制條件;阿佩爾則正好相反。他們的主張互成鏡像關(guān)系。不過阿佩爾足以使我們滑向相對(duì)主義,足以讓我們分清較差的理解與較好的理解。
參考文獻(xiàn):
[1][2]喬治婭·沃恩克.伽達(dá)默爾:詮釋學(xué)、傳統(tǒng)和理性[M].洪漢鼎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9:143.
[3][4]喬治婭·沃恩克.伽達(dá)默爾:詮釋學(xué)、傳統(tǒng)和理性[M].洪漢鼎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9:144,144-145.
[5]卡爾-奧托·阿佩爾.哲學(xué)的改造[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133.
[6][9]烏多·蒂茨.伽達(dá)默爾[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0:176.
[7][8]漢斯-格奧爾格·伽達(dá)默爾.詮釋學(xué)II:真理與方法——補(bǔ)充和索引(修訂譯本)[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
2011:34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