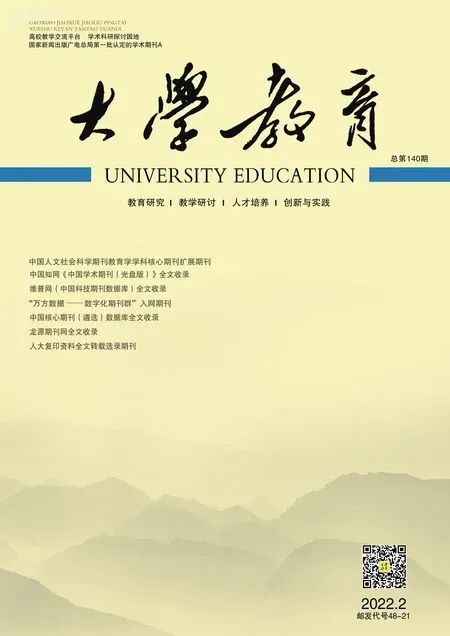課程思政語境下西方文化通識課的育人價值意蘊探索
閆建華 楊寧寧
[摘 要]在目前我國高校開設的有關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的通識課中,希羅神話課幾乎可以說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門文化基礎課。但這門課程歷來注重知識的傳播和對能力的培養,對價值引領關注不夠。近年來,隨著我國高校“課程思政”的推廣和深入,如何有效利用希羅神話課特有的育人資源成為任課教師必須要思考的一個問題。而由于希羅神話屬于異域文化,教師還要把握好如何從中提煉出契合本土現實的育人內涵來塑造學生價值觀的問題。文章擬通過對契約精神、人性尊嚴與悲憫情懷、世界公民意識等育人價值意蘊的探索來說明這一問題。
[關鍵詞]希羅神話;課程思政;契約精神;人性尊嚴;世界公民意識
[中圖分類號] G64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437(2022)02-0053-04
“課程思政”是近年來我國高校大力推廣的一種教書育人理念,其核心是要教師充分挖掘專業課程所蘊含的“思政”潛能,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實現思想政治教育與專業知識體系建構的有效統一。“課程思政”就是要培養有道德、懂專業、識大體的合格人才,其源頭可追溯到1987年5月出臺的《中共中央關于改進和加強高等學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決定》,該文件明確要求高校教師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與業務教學工作結合起來”。此后,黨中央又分別在1994年、2004年和2013年出臺的相關文件中反復強調這一點。2016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再次重申了“課堂育人”的重要性。隨后,教育部于2017年出臺了綱領性文件《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質量提升工程實施綱要》,積極推行以“課程思政”為目標的課堂教學改革。各高校以此為契機,將“課程思政”作為專業課程教學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來抓,在全員、全程、全方位、協同化育人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觀點和方法,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效。但從近兩年發表的研究論文來看,當下的“課程思政”大多存在“思政”話語單一、“思政”內涵不夠豐富等問題。譬如,論文作者大都圍繞奉獻、助人、敬業、愛國等學生所熟悉的“正能量”話題展開,可當不同專業的課程都圍繞類似的話題、運用類似的話語合力進行“課程思政”時,就有可能暴露出“課程思政”的單一性和重復性問題。這種“千書一面、千人一面的大一統”[1]做法不但有悖于“課程思政”的初衷,而且會削弱“課程思政”的成效。為此,任課教師只有根據各自的課程特色來進行“思政”融合,才有可能取得立德樹人的預期效果。我們且以異域文化特色鮮明的希羅神話課為例來說明這一點。
眾所周知,希羅神話是西方文化的一大源頭,我國許多高校也因此將其列為西方文化知識模塊中的一門基礎課程,該課程的目的是讓學生了解有關西方文化的源頭性知識,辨識希羅神話對西方國家尤其是歐美國家文學、藝術、宗教、歷史等方面的滲透和影響,在拓展學生文化知識的同時,提升學生的文化辨識能力和跨文化交際能力。鑒于此,希羅神話課向來注重知識的傳播和對能力的培養,如藝術審美能力、心理調節能力、跨文化交際能力、文學賞析能力、思辨能力等[2-3]。 這樣做固然符合英語專業大綱對文化知識模塊課程的目標要求,但在當下“課程思政”業已全面推開的語境中,任課教師除了要重視知識和能力之外,還要充分挖掘希羅神話課特有的、有別于其他課程的育人內涵,巧借他山之石來“琢”自家之“玉”,借此實現對學生的價值引領和人格塑造。
毋庸置疑,希羅神話課的育人資源就蘊涵在一個個動人的神話故事中,教師的任務就是將故事傳達出來的精神品質、思想氣度、情感體悟等“動人”之處與學生所關注的焦點問題或現實問題結合起來,藉此感化學生、育化學生,合情合理地引導學生樹立一種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實踐證明,教師只要在課堂上提出一些既可以考查學生運用神話知識的能力,又可以發揮學生想象力和“共情力”的問題,學生在討論問題、回答問題的過程中就會自然而然地表露出其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教師再適時地加以引導,就可以以一種隱性的、看似“不思政”的方式達到“課程思政”的目的。以下為筆者運用希羅神話故事來“育人”的幾點粗淺嘗試。
一、契約精神
契約精神是西方文明社會的一種守信精神,用伊恩·瓦特(Ian Watt)的話來說,“整個西方的文明就建立在個人契約關系的基礎之上”[4],可見契約精神何等重要。它是雙方或多方在平等自愿基礎上達成的一種相互制約、共同遵守的合約或條款,其精神實質也可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誠信”二字來概括。誠信也是中華民族的一種傳統美德,所謂“一言九鼎”“一諾千金”“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等就是這種傳統美德的形象再現。遺憾的是,誠信在當今社會有所缺失,一些諸如毀約、欺詐、作弊、貪污、謊言等負面新聞屢見不鮮,對學生造成了不小的困擾。而誠信之所以被視為當今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原因之一便是社會對誠信美德的強烈呼喚。因此,對學生誠信品格的培養顯得十分重要。大量的希羅神話故事告訴我們,無論是神還是人,但凡自己承諾要做的,都必須說到做到,任何欺詐帶來的后果都不堪設想。這種契約精神與我們所倡導的誠信美德十分契合,因而以“契約”之石來攻“誠信”之玉再合適不過了。
希羅神話故事中的契約精神體現在正(守約)反(毀約)兩個方面。我們先來看兩個守約的著名事例。在希臘大軍攻打特洛伊期間,阿基里斯(Achilles)出于人道宣布休戰九天,為的是方便特洛伊為其勇士赫克托耳(Hector)舉行國葬。倘若阿基里斯在這期間乘虛而入,便可以輕松打敗特洛伊,但一向視榮譽為生命的阿基里斯信守諾言,一直等到赫克托爾葬禮結束才來叫陣。太陽神赫利俄斯(Helios)對兒子法厄同(Phaethon)發誓說,兒子的任何愿望他都會滿足。可出乎意料的是,兒子竟然提出要駕著太陽神車到天上去“炫”。赫利俄斯明明知道這等于讓兒子去送死,但諾言就是諾言,無論是敵對的雙方還是親友都必須遵守,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價。在毀約的事例中,一個是克里特國王米諾斯(Minos)由于沒有遵守將白牛獻祭給波塞冬(Poseidon)的約定,致使其妻生出吃人怪物米諾牛(Minotaur)。一個是俄耳甫斯(Orpheus)違背了普魯托(Pluto)不許他回頭的約定,永遠失去了讓亡妻返回人間的機會。正反兩方面的例子都表明,契約精神是一種不容任何人褻瀆的神圣的東西,但凡毀約者,無一例外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這一點學生很容易看得出來。為了讓學生進一步領會契約精神的內涵,筆者給學生布置了一項任務:“眾所周知,特朗普打著民族利益的旗號,擅自取消了美國與國際社會或其他國家的公約。請你運用所學神話知識警告特朗普,停止毀約。”(問題為英文,文中僅給出中文譯文,下同)。為方便學生討論,筆者特意給出《今日美國報》上的一則報道,原文如下:
After 16 months as president, Trump has shown himself less talented at making new deals than at breaking existing ones. The list of broken or endangered agreements keeps growing: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trade agreement. The Iran nuclear deal.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The 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 (DACA) policy. In other words, Trump's pretty good at deal-breaking(USA Today , May 24, 2018) .
從結果來看,學生無一例外都在稱頌神話故事中的契約精神,并能夠運用契約精神來譴責特朗普的毀約行為,警告其行為可能會導致的嚴重后果,誠如神話故事所昭示的那樣。其中有學生還針對報道中提到的第一條事實指出,當特朗普擅自撕毀《巴黎氣候協定》時,其行為就跟法厄同駕駛太陽神車一樣,看似在自由奔馳,其實早已失控,整個世界都有可能被他“燒焦”。學生的意思很明了:如果每個國家都像美國那樣拒絕減排,整個世界都將承受全球變暖的嚴重后果。難能可貴的是,有個別學生還能結合《莊子·盜跖》中的“尾生之約”來闡述契約精神所昭示出來的為人處世之道,并以此來反襯特朗普作為大國總統屢屢失信于天下的行為。可以說學生的回答既體現出他們對神話知識的掌握程度和運用能力,又體現出一種正能量的價值觀,后者在教師隨后的點評中還可以著重加強。筆者給出的點評是:既然神話故事中上至眾神之王下至凡界女仆都要遵守契約精神,那么同理,當今世界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百姓,大到國家小到個人,都應該用一種契約精神來約束自己。如教師規定什么時候完成作業,學生就必須什么時候完成,因為這看似尋常的規定也是一種“契約”,一種“抱柱之信”,它其實涉及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由此觀之,就我們所熟悉的誠信美德而言,教師只要講好希羅神話故事,用故事打動學生,讓學生自行挖掘其中所蘊含的契約精神,并將其與現實問題結合起來進行思考,就可以讓學生在不知不覺間自行“思政”,自覺“誠信”,正可謂殊途而同歸,殊語而同道。
二、人性尊嚴與悲憫情懷
希羅神話對人性尊嚴的維護、對悲憫情懷的釋放俯拾皆是,這與當今核心價值觀中的“友善”,與儒家的“寬厚待人”是相通的。從大義親情的安提戈涅(Antigone)到殺死兒子的普洛克涅(Procne),從忠貞不渝的佩涅洛普(Penelope)到背叛妻子的伊阿宋(Jason),從泣求愛子尸體的普里阿摩(Priam)到獻祭愛女的阿伽門農(Agamemnon)等,這些學生所熟悉的神話故事無一不在闡釋善惡之間的取舍、人性尊嚴的神圣以及悲憫情懷的偉大。與此同時,這些故事也告訴學生:凡是踐踏善良、違背人倫的惡行幾乎都受到了懲罰,凡是堅守真愛、悲天憫人的善行幾乎都得到了回報。這一點幾乎可以說是佛教因果報應的翻版。為此,教師要充分利用這類材料,引導學生品味希羅神話中的人性尊嚴和悲憫情懷,以此來喚起、激發、強化學生心中的善(我們權且稱之為“友善思政”),并使之自覺“行善”。
“友善思政”的關鍵是要從情感上打動學生,讓學生從內心深處產生共鳴。我們不妨以普里阿摩的故事為例來說明這一點。普里阿摩是特洛伊末代國王,他的長子就是前文提到的赫克托耳。這位老國王所承受的最大打擊就是目睹自己的愛子被阿基里斯殺死。更為殘忍的是,阿基里斯還將赫克托耳的尸體拖在馬車后邊進行踐踏和侮辱。在古希臘,對亡者的尊重是一個關乎人性尊嚴的神性原則,即使交戰雙方也不能違背。更有甚者,如果戰敗的一方無力埋葬其陣亡將士,該義務則由勝利的一方來承擔,由此可見阿基里斯的所作所為到了何等程度。當然,阿基里斯也是因為悲憤過度才做出此等辱尸之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普里阿摩決定乞求阿基里斯歸還愛子尸體。二者會面的場景堪稱神話故事中最感人的一幕。筆者據此給出的思考題是:“在普里阿摩與阿基里斯會面的場景中,最打動你的是哪一點?他們的行為在你看來有無不妥之處?”
大多數學生的反應是深受感動,理由不外乎這幾點:(1)普里阿摩為了兒子竟然跪倒在仇敵面前,親吻殺死兒子的那雙手。他跪倒在地的身軀看似低矮,實則是人世間高不可攀的一座父愛之山。(2)老國王堪稱英雄,他雖然年事已高,卻敢于獨闖敵營。(3)普里阿摩有著鋼鐵般的意志和過人的膽識,因為要讓暴怒的阿基里斯歸還兒子尸體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他卻能夠以柔克剛,用父愛和真誠打動對方。(4)他的下跪不是屈辱,而是一種神圣的尊嚴。(5)阿基里斯的英雄氣概不在于他刀槍不入、戰無不勝,而在于他的“軟弱”,在于他靈魂深處的某種柔情。(6)阿基里斯雖然表現得冷酷無情、毫無人性,但當看到白發蒼蒼的老父親跪在自己面前乞求兒子尸體時,他心中的憐憫和慈悲就被喚醒了,他將老國王輕輕扶起,與之一同哭泣的瞬間最令人感動。很顯然,當學生被打動的時候,他們心中的愛和善也隨之得到了升華,而神話英雄身上那種比技藝和能力更加重要的“德行的理想、美德的理想”勢必會對學生的善良人格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5] 。但也有少部分學生并未被打動,理由有兩點:普里阿摩作為一國之君不能因為自己的兒子而對仇敵下跪,這有辱國格;阿基里斯并沒有做錯,對敵人就應該無情打擊、毫不手軟。從宏大敘事的視角來看,這樣的說法不是沒有道理的,但脫離了古希臘歷史文化語境,時空錯位明顯。在古希臘,哪怕是痛恨至極的勁敵,一旦死去,都要給予應有的尊重。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甚至認為,讓死者曝尸荒野遠比讓活人無家可歸還要邪惡[6],可見“死者為大”的觀念是何等的深入人心。故而安提戈涅毅然違反“國家禁令”埋葬兄長,奧德修斯即使在漂泊途中也要為死者補辦葬禮。教師只要有針對性地說明這一點,再佐以中國傳統文化對先祖或亡者的敬重,就能于情于理地撥動學生內心深處的柔情之弦。這種柔情其實是人性深處共有的一種悲憫情懷,是對死難者或受難者所產生的一種深切的同情心或“共情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國學界提出的學生思辨能力培養層級模型中,也納入了好奇、開放、自信、正直、堅毅等情感特質[7]。這固然是一個不小的創舉,但倘若能將人性尊嚴與悲憫情懷也納入其中,現有的、與情感相關的思辨品質或許就會顯得更加溫情、更加“柔軟”一些,尤其是在國家層面大力倡導“友善”與“和諧”的當下,對學生善良人格的塑造不可不為。
三、地球公民意識
“和諧”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旋律,它不僅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而且意味著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不僅是確保社會和諧的前提條件和重要因素,而且是一個民族生態文明的重要標志。鑒于此,希羅神話課除了要關注契約精神等關乎人際關系的“思政”內涵,還必須挖掘人與自然和諧的“思政”內涵,力求實現“學生—社會—人類—環境”的協調發展[8]。而這也是高校全人教育的核心目標。從英語專業學生的文化課程來看,針對人與環境或人與自然關系的專題討論并不多見。受其影響,授課教師對此也著力不多,這就勢必影響學生個人素質的全面發展,且從長遠來看,也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和諧。針對這一現狀,授課教師要充分發揮希羅神話課的優勢,從大量有關神祇/英雄與動物、植物等自然生命互動的神話故事中挖掘“生態思政”潛能,以培養學生眾生平等的地球公民意識。
我們先來看動物。希羅神話中的動物多數情況下是作為神祇的“寵物”或英雄人物的陪襯物出現的,許多英雄人物的英雄壯舉和功業幾乎都是通過屠殺動物來實現的。如在大英雄赫拉克勒斯(Hercules)完成的十二項任務中,就有七項是殺死、馴服或活捉各種野獸,這與卡德摩斯(Cadmus)殺死水龍、帕耳修斯(Perseus)殺死海怪、柏勒羅豐(Bellerophon)殺死卡米拉(Chimera)的故事如出一轍。在被殺死的動物中,除了個別食人怪獸之外,多數都是無辜的“地球公民”(Earthlings),它們要么生活在人跡罕至的荒野山林,要么遵照神囑充當看守,只要人不去攪擾它們,它們也不會傷害到人。
可即使這些動物很無辜,也處于荒野,僅僅由于它們是有別于人類的物種,它們就成為人類想象中的敵人和他者,成為必須要消滅的對象。這其中反映出來的物種主義思想在今天看來無疑是反動的、非生態的,教師必須要引導學生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讓他們懂得地球不僅僅是人類的地球,也是生存在這個星球上所有生命的地球。人類只有摒棄極端物種主義,將人類的悲憫情懷延伸到動物身上,學會與其他地球公民和諧相處,人類文明才有可能千秋萬代地延續下去。筆者據此提出的問題是:“英雄神話對現實中的動物會產生影響嗎?你認為這類故事對當下的動物保護有利還是有弊?倘若武松生活在當今中國或當今希臘,你認為他還會被尊為打虎英雄嗎?”在引導學生思考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教師還應該提供一些確切的依據,讓學生切實看到遠古神話與當今動物殺戮之間的關聯。納什(Roderick Nash)的《荒野與美國思想》(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2014)、《山海經》中關于獸肉的種種神奇功效、電影《地球公民》(Earthlings, 2005)中殘殺動物的紀實鏡頭等,都可以作為培養學生地球公民意識的輔助材料。
學生的地球公民意識還可以通過植物來喚起。“希羅神話中蘊涵著怎樣的植物觀念?哪些神話故事對于減緩當今的森林破壞現象有啟迪意義?”筆者提出的這個問題并不難回答,因為在此之前學生已經了解到,樹木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甚至在黑夜和白天未分之前就已經存在[9]。學生也知道,許多樹木也因此被賦予神性,如朱庇特的橡樹、雅典娜的橄欖樹等,且不說一些樹木本身就是人或精靈。因此,那些膽敢闖入圣林,或是膽敢砍伐圣樹者,其行為無異于瀆神,而瀆神的結果無疑都是毀滅性的。學生最熟悉的冒犯者是厄律西克同(Erysichthon),這位狂妄自大的國王不顧他人勸告,用蠻力砍倒了五谷女神得墨忒爾(Demeter)的圣樹,最后在饑餓女神的折磨下自噬身亡。神話往往以敘述故事的象征形式表達一個民族或一種文化的基本價值。一般學生都能從這類象征性神話中悟出這樣的道理:植物就是自然力量或自然生命的代名詞,毀壞植物無異于毀壞生命、毀壞自然,而毀壞自然無異于毀壞人類自己的家園,其苦果也只能由人類自己來吞咽,其痛苦狀一如厄律西克同吞吃自己的肉體一樣。自然,教師還可以借用孔子的話來強化學生的認知:“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禮記·祭義》)孔子提倡百善孝為先,所謂的“非孝”就是不善,或者說就是惡。可見在孔子眼里,任意毀壞樹木、殺戮動物無異于作惡,而作惡必將受到懲罰,這與希羅神話故事給我們的警示并無二致。
除了警示功能,神話植物的實用功能和精神功能也可用來進行“思政”教育。以奧德修斯為例,在他長達十年的回鄉征程中,關鍵時候不僅有神祗助力,而且還有植物助力。如果他沒有魔莉(Moly)做解藥,沒有那棵生長在錫拉和卡津布迪斯(Scylla and Charybdis)海峽上方的無花果樹做抓手,奧德修斯要么被變成動物,要么死于非命。不僅如此,奧德修斯故鄉的植物也屢屢給他一種精神上的寄托——他對妻兒和父親的思念常常化為記憶中的莊稼地、蘋果樹和葡萄架。與他生活數年的、伊甸園一般的“盤絲洞”相比,他的故鄉伊薩卡(Ithaca)并不富有,但那里卻有童年時父親給他的13棵梨樹、10棵蘋果樹、40棵無花果樹[10]。所有這些都為奧德修斯的故土之戀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精神力量。這其實與我們告別故鄉時的“楊柳依依”心態,或是用桑梓指代家鄉的傳統是一個道理。至此,學生不僅會加深對神話植物的認識,而且還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愛護現實中的花草樹木,尊重花草樹木生存的權利。這不正是我們想要的結果嗎?
四、結束語
以上僅從契約精神、人性尊嚴與悲憫情懷、世界公民意識三個方面說明希羅神話課如何育人的教學情況。我們知道,神話表達的是人類對生命、對自然的一種體驗,其豐富多樣性必然決定了育人內涵的多樣性,因而文中所述僅為其中一斑。其他如冒險精神、開拓意識、責任擔當、好客之道等,都是這門課應該不斷豐富、深入挖掘的育人意涵。實踐證明,只要教師抓住神話故事可資育人的著力點,并將其有機地融入神話知識與思辨能力的運用中,讓學生在探討問題的過程中自行甄別哪些精神品質是值得借鑒和繼承的,哪些是要警惕的,哪些是要摒棄的,然后教師再適時加以引導,就能自然而然地實現知識傳授、能力培養與價值引領的有機統一。“守好一段渠,種好責任田”業已成為當下高校教師教書育人的一個隱喻[1]。雖說“守好”并非難事,但要“種好”卻非易事,任課教師只有確保各自責任田里的鮮花“獨秀獨好”,才有可能吸引學生欣賞百花齊放的“思政”美景,并使其在學習、生活和今后的工作中自覺踐行,這樣才算是真正“種好了責任田”。
[ 參 考 文 獻 ]
[1] 習近平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 把思政工作貫穿教育教學全過程 開創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新局面[N].人民日報,2016-12-09(1).
[2] 潘桂娟.希臘羅馬神話通識教育功能教學探討[J].教學研究,2018(3):59-64.
[3] 譚靜.國內英語專業西方文化教學研究綜述:2007-2016年知網載文分析[J].湖北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17(6):111-114.
[4] Watt, Ian. The Rise of the Novel [M]. London: Chatto & Windus,1957:63.
[5] 周天.中西神話異同論[J].中國比較文學,1997(2):90-99.
[6] Graves, Frank Pierrepont. The Burial Customs of the Ancient Greeks [D]. Columbia: Columbia College, 1891:11.
[7] 王宇.“希臘羅馬神話”課程改革的核心理念[J].沈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6):164-166.
[8] 李竹.從專業訓練到全人培養: 大學教育目的的迷失與回歸[J].江蘇高教,2018(8):52-55.
[9] Guthrie, W. K. C.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The Presocratic Tradition from Parmenides to Democritu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208.
[10] Homer. The Odyssey [M]. Trans. Ian Johnston. Arlington, Virginia: Richer Resources Publications,2007:477.
[收稿時間]2020-07-24
[作者簡介]閆建華(1965—),女,甘肅人,博士,教授,碩導,研究方向:環境文學、生態批評及教學法。楊寧寧(1981—),女,湖北人,碩士,講師,研究方向:美國文學與生態文學。
sdjzdx202203231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