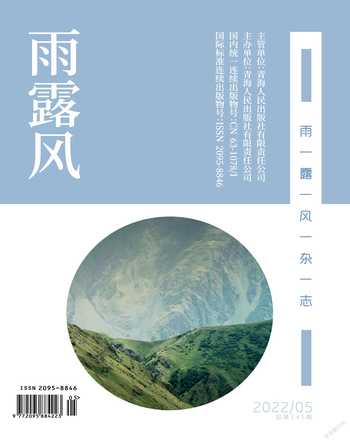無法被救的孩子
朱致遠

摘要:在魯迅的小說作品中有著眾多的孩子形象。從“救救孩子”的啟蒙角度來看,本文將這些“孩子”分為“好孩子”與“壞孩子”兩種,并闡釋了其為何都不能被救,以及在魯迅看來如何才能“救孩子”的問題。
關鍵詞:魯迅小說;孩子;啟蒙
魯迅的小說、雜文,甚至是日記中都帶有對啟蒙、教育與國民性等問題的反思。這種固化的標簽容易讓我們在解讀魯迅的文本的時候以一種慣性的思維方式去對待文本,即將魯迅作品中的復雜思想都武斷地一刀切,并將其與啟蒙思想扯上關系。
在《狂人日記》的最后,魯迅寫道:“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早些時候,學界對此的解讀還是較為統(tǒng)一的,即魯迅在此第一次以啟蒙的視角提出了“救救孩子”的觀點,并在其后多年的創(chuàng)作中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持續(xù)且深入的思考。但是近兩年來,這種似乎已經(jīng)蓋棺定論的“原點”式的觀點開始受到了人們的質(zhì)疑。本文所討論的有以下幾個問題:魯迅筆下的孩子都有哪幾種?他是否認為這些孩子是可以被救的?如果不能,那么應該如何使孩子得救?
一、“好孩子”與“壞孩子”
現(xiàn)今學界對于如何從啟蒙角度出發(fā)給魯迅作品中的孩子形象作出分類這一問題有著不同看法。有的學者以魯迅作品創(chuàng)作的時間為軸進行縱向的分類:“1918年前后的孩子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犧牲品,是需要人救的孩子,也是能救的孩子。到了1925年前后,孩子成了民眾中的一員,是不可救的,也是不需要救的。”[1]也有學者按照孩子的不同性格橫向地將孩子分為了身體孱弱的“病孩子”、頑劣不羈的“熊孩子”與孺子可教的“好孩子”,認為“‘病孩子不可救,‘熊孩子救不了,‘好孩子不用救[2]”。但以時間來給這些孩子做出分類未免武斷。因為即使是1918年前后也有像《狂人日記》中如狂人所感覺到的“也在那里議論我;眼色也同趙貴翁一樣,臉色也都鐵青”的孩子[3]445,而顯然這樣的孩子不能與《社戲》中的雙喜、阿發(fā)和《故鄉(xiāng)》中的少年閏土歸為一類。而將孩子分為“病孩子”“熊孩子”與“好孩子”的分類方式雖然在整體上更加合理,但作者本人也承認“病孩子”并不具有作品文本的現(xiàn)實意義,即在討論魯迅的啟蒙觀點的時候,“病孩子”這一分類意義并不大。
筆者認為,既然是要討論魯迅對于啟蒙問題的思考,就應該從這個角度出發(fā),進而去思考魯迅的啟蒙思想在這些孩子身上的具體體現(xiàn),而非先造出一個漂亮的分類,再用這個分類回過頭去闡釋魯迅的啟蒙思想。因此,筆者將涉及討論魯迅的啟蒙思想的孩子形象大體上分為兩類:一類是“好孩子”,另一類是“壞孩子”。
所謂“好孩子”,是指在魯迅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主要是以正面形象出現(xiàn)的自由、純真、美好的孩子形象,其典型代表是《社戲》中的雙喜、阿發(fā)和《故鄉(xiāng)》中的少年閏土。在描寫這些孩子的人物形象的時候,魯迅往往會以抒情化的筆調(diào)給我們描繪一個記憶中的,充滿詩情畫意的美好且自由的故鄉(xiāng),并將這些孩子置于這種美好的回憶中。《故鄉(xiāng)》中,“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著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而處在其中的少年閏土“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猹盡力地刺去”[3]502。這些景象都是在城市里的“我”所沒有見過的,因而“我”對少年閏土,對雙喜、阿發(fā)等孩子們充滿了新奇與敬佩。
至于所謂“壞孩子”,則是魯迅小說中愚昧、丑陋,甚至還有些可怖的孩子形象。“壞孩子”包括但不限于《孤獨者》中魏連殳所見的拿了一片蘆葉對他喊“殺!”的小孩,《長明燈》中拿著葦子對瘋子喊著“吧(殺)”的小孩。每每讀到魯迅對這些“沒學會走路,先學會殺人”的孩子的描寫,筆者總覺后脊發(fā)涼。魯迅實際上已經(jīng)將他們作為那一時期的民眾群體的一部分來加以描寫。大多數(shù)“壞孩子”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已經(jīng)被黑暗社會這個大染缸染色。其做出的驚駭?shù)膭幼鲗嶋H上只是這個社會的整體氛圍在一個個孩子身上的具體體現(xiàn)。
二、孩子可否被救?
魯迅自《狂人日記》中就開始呼喊“救救孩子”。雖然近幾年的研究使我們開始逐漸懷疑魯迅對于“孩子是否能被救”這個問題是否堅定,但筆者認為,魯迅對于“啟蒙是否有必要”這個問題是從來沒有懷疑過的——這體現(xiàn)在這他幾乎所有的創(chuàng)作中。
魯迅小說中的“壞孩子”是愚昧麻木的民眾的一員,是不可救也是不需要救的。《孤獨者》中,“我”和魏連殳關于“孩子”的一段對話鮮明地體現(xiàn)了這一點。魏連殳本認為“大人的壞脾氣,在孩子們是沒有的。后來的壞,如你平日所攻擊的壞,那是環(huán)境教壞的。原來卻并不壞,天真……我以為中國的可以希望,只在這一點”[4]。后來魏連殳卻悲哀地認為“想起來真覺得有些奇怪。我到你這里來時,街上看見一個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蘆葉指著我道:殺!他還不很能走路……”[4]。本來“我”就認為“如果孩子中沒有壞根苗,大起來怎么會有壞花果”[4],而魏連殳對于這種“壞孩子”的態(tài)度的前后轉變剛好印證了“我”的觀點。
那么,“好孩子”是否是可以“被救”的?《社戲》中,“我”在十多個鄉(xiāng)下“孩子”的陪同下到阿發(fā)和六一公公家的田里去偷羅漢豆[3]595,在作品的結尾處,魯迅感慨萬分地寫道:“真的,一直到現(xiàn)在,我實在再沒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戲了。”在魯迅對這種美好記憶表現(xiàn)出無限懷念的前提下,有學者強調(diào)說,孩子們“是魯迅心中理想兒童之化身,是其希望之所在[5]”。但魯迅只是通過回憶,去同讀者分享自己童年時代的快樂,而并非在這些“好孩子”身上寄托什么對未來的希望和期待。須知這些“好孩子”只是在魯迅的回憶中被美化了,這些孩子本質(zhì)上還是在自然環(huán)境中成長起來且未接受過文化教育的孩子。魯迅顯然沒有認為未來的中國就是由這些“好孩子”肩負的。魯迅當然明白,他們那種不讀書沒文化的自由和快樂,無非就是一種“昏天黑地的在社會上轉”。《故鄉(xiāng)》中,原來如小英雄的少年閏土最終變成了像木偶人一樣的中年閏土,恭敬地喊著童年好友“老爺”。在這里可以看到,魯迅認為,哪怕是美好如少年閏土一樣的“好孩子”,最終也只是變成一個“辛苦麻木而生活”的中年閏土。可想而知,《社戲》中的雙喜、阿發(fā)的未來也不會與閏土相差很遠。雖然這些“好孩子”的本性并不壞,但是正如“壞孩子”一樣,他們的未來已經(jīng)是可以望見且不可改變的了。“好孩子”也是無法被救的。83F82672-524C-4726-961C-C7B8E1E62CB2
三、令人絕望的自啟蒙
既然不管是“好孩子”還是“壞孩子”都無法被救,那么,怎樣才能在真正意義上“救孩子”呢?魯迅在其雜文《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中提到了“解放子女的父母,應該先有一番預備;而對于如此社會,尤應該改造”“沒有法,便只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3]138”。因此,有的學者認為,魯迅認為思想啟蒙的核心問題,不是從“救救孩子”入手,而是從“救救父親”做起。[6]但這種觀點是比較片面的。首先,孩子較之父親來說,仍然未被黑暗社會影響得那么徹底、那么絕對。如果孩子是無法被救的,那么轉而去救更愚昧麻木、更難救的父親,這種觀點豈不是自相矛盾嗎?其次,那“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的父親,至多只能是少數(shù)像魯迅一樣已經(jīng)醒來的啟蒙者,要讓作為普通民眾的父親放孩子“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這在當時的那個時代未免不太現(xiàn)實。因而,這種對魯迅的文本直接做文字表面的解讀而得出的結論是有失偏頗的。
回到應該如何“救孩子”的問題,其實在魯迅的作品中也是早已經(jīng)被回答過了。1918年5月發(fā)表的《狂人日記》中,魯迅借狂人之口說道:“你們可以改了,從真心改起!”在這里,魯迅以及其他同時代的啟蒙者是以一種高姿態(tài)的傳授的方式向世人傳輸著啟蒙者們自己的態(tài)度與理念。他們是通過給出自己的思想,讓民眾們接受,進而開化民智的方式完成啟蒙的。但是,也正是從《狂人日記》開始,魯迅意識到啟蒙者本身也像狂人一樣,“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啟蒙者本身與封建文化就有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這也是魯迅相較于其他的啟蒙者的一點更深刻的認識。既然啟蒙者本身就是有缺陷、不完美的,他們又怎能像上帝布道一樣來給民眾開化民智呢?后來在1925年的時候,魯迅在《導師》中提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什么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么烏煙瘴氣的鳥導師![7]”在這個時期,魯迅顯然不再以授人以魚的方式去教導民眾去做什么,而是想要以授人以漁的方式去讓民眾擁有思考、判斷的能力,進而以這份能力使自己去選擇要做什么。因為這時候魯迅發(fā)現(xiàn),像之前那樣的所謂啟蒙只是啟蒙者將自己的觀點加諸于被啟蒙者,對被啟蒙者而言,這絲毫無助于改變其思想的愚昧麻木的狀態(tài)。筆者認為,從“告訴民眾怎么做”到“告訴民眾怎么想”,這是魯迅的啟蒙思想的一個重要的轉變。
具體到“救孩子”的問題上,筆者認為,魯迅也并不認為孩子應該是“被救”的,而應該是“自救”的。魯迅并不認為應該由他充當一個導師的角色去告訴孩子應該去做些什么,而是應該讓孩子得到教育,進而學會自我思考與判斷,最終實現(xiàn)自我啟蒙。魯迅在教育其子周海嬰的時候總是扮演著嚴父的形象。雖然時常打罵孩子,但總也以其子周海嬰能學到新知識而欣慰。筆者認為,這也是魯迅的自啟蒙的觀點在其子身上的具體體現(xiàn)。
然而,在那個沒有義務教育的年代,能夠進私塾學習和受教育的孩子畢竟只是存在于少數(shù)富裕人家。更多的孩子只是在小時候沒頭沒腦地在街上玩,長大后“昏天黑地的在社會上轉”,庸碌一生而不知其所。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普通人家中,能夠有實現(xiàn)自啟蒙的條件的孩子可以說是極少的——少到幾乎沒有。這也就意味著,如果想要通過孩子的自啟蒙進而拯救社會,這將會是一個極其漫長而坎坷的過程。魯迅正是深刻意識到了這一點,并對這種現(xiàn)狀感到無力與絕望。明知看不到這個社會的希望所在,卻也義無反顧地面向黑暗吶喊——這也無怪魯迅的哲學被稱為絕望的哲學了。
四、結語
關于如何“救孩子”這個問題,魯迅作了極深刻的思考。他既不認為有可以“被救”的孩子,也不認為有全知到有資格去啟蒙孩子的所謂“導師”。他以誠實而嚴肅的態(tài)度告訴我們:想要真正地“救孩子”,最重要的是教孩子們懂得自啟蒙,使孩子充分認識到自己的不完善,然后自己尋路,自我拯救——即使這條路坎坷而漫長。
作者簡介:朱致遠(1997—),男,漢族,江蘇蘇州人,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現(xiàn)當代文學。
參考文獻:
〔1〕謝曉霞.魯迅小說中“孩子”形象的變化及其意義[J].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03):81-93.
〔2〕宋劍華.“悲哀”與“絕望”:一個真實魯迅的五四姿態(tài)[J].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1,64(05):29-36.
〔3〕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4〕魯迅.魯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5〕談鳳霞.再觀“人之萌芽”:論魯迅兒童觀的深刻性[J].江淮論壇,2018(01):132-140.
〔6〕宋劍華.“病孩子”、“熊孩子”與“好孩子”——也談魯迅筆下兒童形象與其啟蒙思想的內(nèi)在關聯(lián)性[J].魯迅研究月刊,2019(07):4-12.
〔7〕魯迅.魯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83F82672-524C-4726-961C-C7B8E1E62C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