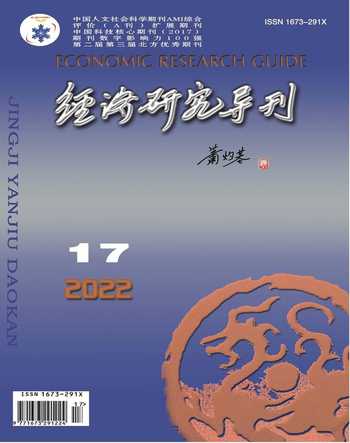新時期我國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協調研究
劉雪景
摘? ?要: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時期,“金融體系不平衡不充分,影子銀行規模過大、資金脫實向虛”的問題也隨之出現,而這些問題的迅猛發展會嚴重影響我國金融穩定。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讓各國領導者認識到傳統貨幣政策的不足,宏觀審慎監管由此成為學術界研究與探討的焦點。因此,從我國新時期宏觀經濟金融環境著手,借鑒金融危機教訓及前人研究,分析了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應如何協調配合解決中國新時期的宏觀經濟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新時期;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
中圖分類號:F822?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2)17-0109-03
引言
從當前經濟狀況和發展環境上看,中國已經進入一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新時期。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實施改革開放的決議后,中國GDP總量從0.36億萬元增長到了2008年的26.4億萬元,年均增長率達到9.82%;2003年GDP增長率更是從10%一直增長到2007年的14.2%。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后,我國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到2012年的7.9%,并且在之后也一直處于一個緩慢持續下降的過程。這表明我國經濟已從改革開放后的高速增長階段過渡到了中高速增長階段,我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下,中國成為疫情期間唯一經濟正增長的國家。雖然從表面上看我國金融風險在疫情沖擊下仍然處在可控范圍之內,但實際上,高債務、高杠桿的風險尚未根本解除,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矛盾尚未解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尚未徹底打通,金融監管體系還需進一步完善。正如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的那樣,“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中國經濟現已步入以中高速增長為基本特征的新時期,出現了趨勢性的新常態。在這樣一個新時期,中國選擇哪種貨幣政策、如何構建宏觀審慎政策、怎么完善雙支柱調控框架來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使中國經濟行穩致遠的發展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一、文獻綜述
我國當前所處的新時期是一個疊加了金融科技浪潮的經濟新常態時期,經濟的發展一方面要適應經濟新常態下的階段性特征的轉變,另一方面需迎合金融科技浪潮的來襲[1]。在這樣一個新時期,單一的貨幣政策或宏觀審慎政策并不能在穩物價的同時穩金融,只有兩者相互協調配合才能推動宏觀經濟健康發展。
現有文獻對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者之間的關系、配合方式以及有效性問題上。在關系問題上,大部分學者認為兩種政策之間既存在一定的替代性,也存在互補性[2]。宏觀審慎政策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對貨幣政策進行有益的補充[3],但是兩者在實施過程中也存在潛在沖突[2]。兩種政策的配合方式,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三種。第一種觀點認為,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的協調由經濟周期和金融周期的同步程度以及所面臨的沖擊類型決定[4];第二種認為,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的協調搭配方式主要取決于經濟狀況;第三種認為,兩種政策之間的協調搭配應注意可能存在的潛在沖突問題。
學者們也對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協調配合的有效性做了大量實證研究,發現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可以相互輔助應對金融沖擊,實現幣值和金融系統雙重穩定。比如,Akinci和Olmstead-Rumse認為,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相協調的政策組合更有助于實現金融穩定[5]。黃益平等發現,單一的貨幣政策所產生的福利效應明顯小于雙支柱宏觀調控[6];其次可以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馬理和范偉發現,當出現房價泡沫時,單一政策的使用難以在降低風險和穩定增長兩者之間找到平衡;而“雙支柱”調控不僅能夠減小金融風險和控制房價過快上漲,還能夠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7]。除此之外,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的協調配合還可以有效減小匯率沖擊給產出、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帶來的波動[8],對企業和銀行產生明顯的穩定效應[9],以推動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治理[10]。“雙支柱”調控框架把保持價格穩定與
維護金融穩定兩大目標有機結合,為新的歷史時期維護我國宏觀經濟行穩致遠和國家金融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新時期我國宏觀金融環境問題分析
(一)金融體系不平衡不充分
隨著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新時期,原有的金融供給已不能滿足人們當前的金融需求,這就導致了金融體系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我國金融體系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金融資源配置不合理,與國有企業、大型企業相比,民營企業、小微企業、獲得的金融資源支持相對較少。二是直接融資發展不平衡,企業融資仍以高成本的間接融資為主,而低成本股權債權融資發展仍不充分。三是間接融資發展不平衡,銀行體系層次發展不充分,金融機構缺乏多樣化和專業化的產品與服務。四是個人金融服務發展不平衡,普惠金融發展不充分。當前我國金融市場專門為個人定制的金融產品服務種類較少、質量也參差不齊,不能滿足人們與日俱增的多樣化金融需求。
(二)“影子銀行”整體規模過大
影子銀行是金融監管和金融創新博弈下的產物,一方面可以活躍金融市場,彌補傳統融資渠道缺陷,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但另一方面會造成金融杠桿水平上升、貨幣政策傳導有效性減小、金融風險持續積聚等問題。影子銀行可能會引發金融風險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影子銀行的高杠桿經營方式。影子銀行相比于商業銀行有著更高的杠桿率,引發金融風險和破壞金融穩定的可能性也更大。第二,風險傳染性強。我國影子銀行體系以商業銀行為核心,是金融體系中的重要金融中介,影子銀行一旦陷入危機,將具有高傳染力,極大程度上會影響到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而影子銀行的特性決定了其業務的高流動性要求,當市場受到沖擊時,相比于其他金融機構,影子銀行將更容易陷入流動性危機,進而導致整個金融體系流動性風險增加。近年來,隨著我國金融體系的不斷完善發展,影子銀行規模水平日漸增大,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增強,導致金融風險不斷累積,當經濟下行壓力增大時,其內部積累的流動性風險一旦爆發釋放出來,就可能會引起銀行業甚至整個金融體系風險加劇、金融穩定被破壞。
(三)資金持續“脫實向虛”
“實體經濟”是指能生產實實在在的商品與服務的經濟產業,包括農業、工業、服務業、教育、藝術等生產服務部門;而“虛擬經濟”是指與實體經濟相對應的其他經濟活動,通俗來說是一種錢生錢的經濟活動,主要包括金融業、房地產行業等。“脫實向虛”表現為企業金融化,實體經濟脫離主營業務,生產資金不斷流向虛擬部門進行投機獲利。在進入經濟發展新時期后,我國經濟出現了明顯的“脫實向虛”趨勢,表現在企業金融資產占總資產比例持續上升、實體經濟有效投資不足、影子銀行規模不斷擴大,使金融風險加劇。在經濟新時期,貨幣政策對資產價格的促進作用與日俱增,在經濟結構失衡和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低于利率的背景下,資金脫實向虛成為市場趨勢,進一步加劇了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發生,給金融穩定帶來了巨大的沖擊。
三、2008年金融危機帶來的啟示
(一)貨幣政策難以實現“穩物價”和“穩金融”雙目標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是美國2000年的寬松貨幣政策使得美國房地產泡沫化,貨幣政策由松到緊的極端變動是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信貸時松時緊導致房地產泡沫提前爆裂。這次危機讓各國央行將金融穩定制定為宏觀調控目標之一,各個國家也不約而同開始出臺宏觀審慎政策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我國先后實施了差別準備金動態機制、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并在2019年設立了專門的“宏觀審慎監管局”,提出建立“雙支柱”調控框架的目標。
(二)實體經濟應與虛擬經濟相匹配
危機爆發前,美國為了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將實體經濟中的制造業轉移到國外,使得國內實體經濟比重降低、虛擬經濟占比上升;同時還在國內大力推動金融衍生品創新,造成經濟虛擬化程度進一步增加。最后,美國虛擬經濟過度脫離實體經濟的結果就是泡沫爆裂,金融危機席卷全球。所以,應當大力發展實體經濟,正確看待虛擬經濟。要根據實體經濟的發展需要來規劃設計虛擬經濟的發展,從而推動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協調發展、彼此促進。
四、新時期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的應用
(一)面對“房住不炒”的雙支柱調控機制
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房價泡沫會對居民消費、實體經濟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將投資更多引向房地產,一方面帶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導致宏觀經濟杠桿率加速上升,進而引起金融風險累積。因此,需要使用恰當的宏觀政策來約束房價的過快增長。單一的盯房價貨幣政策可以有效控制房地產價格的上漲,降低信貸供給量,但卻會對家庭消費與實體經濟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11]。宏觀審慎政策通過控制房地產抵押品的貸款價值比,進而使得房地產價格上升引起的信貸擴張降低、擠出效應和金融風險減緩,但并不能有效帶動實體經濟的發展[12]。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的協調使用,可以有效弱化金融加速器效應,降低信貸擴張以及房價波動,改善房地產泡沫對居民消費和實體經濟的擠出效應,促進實體經濟發展,進而維護金融穩定和控制金融風險[7]。宏觀審慎政策對房地產及資本市場的嚴格監管可以緩解貨幣政策調控造成“顧此失彼”的困境,從而使得貨幣政策可以更好將資金引向實體經濟部門。
(二)將“影子銀行”納入監管體系的廣義宏觀審慎政策
宏觀審慎政策的實施一方面可以抑制經濟上行時期的商業銀行信貸擴張,另一方面卻會促進非銀行金融機構的信貸規模增加。現有的僅針對商業銀行的宏觀審慎政策存在許多不足。影子銀行會減弱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引起監管套利,因此應當將影子銀行納入監管體系,結合影子銀行的風險特征,有針對性地施行與之適配的宏觀審慎政策。侯成琪和黃彤彤發現,將影子銀行納入監管體系的廣義逆周期資本監管,既限制了監管套利,增強了監管指標的真實性,又緩解了宏觀經濟的波動。相比于只針對商業銀行的狹義逆周期資本監管政策,廣義宏觀審慎政策效果更好[13]。逆周期宏觀審慎政策通過平滑資產價格變動,既能增強金融監管效果,還可以降低影子銀行對經濟波動的推動作用,從而增進社會福利[14]。藍天從經濟發展狀況著手發現,在經濟上行階段,較優的政策選擇是對影子銀行施行獨立的宏觀審慎監管;而在下行階段,宏觀審慎的貨幣政策是較好的選擇[15]。影子銀行在可能帶來金融風險的同時也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所以應正確評價影子銀行的發展。監管當局應將影子銀行納入監管范疇,并對影子銀行的風險特征針對性地使用宏觀審慎工具、制定宏觀審慎政策。
五、政策建議
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指出,“金融穩,經濟穩。”這一講話深刻表明了金融與經濟之間的關系,經濟健康穩定的發展離不開金融市場的支撐,良好的金融環境有助于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基于對新時期金融環境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三點改革建議。
一是實施定向調控類的貨幣政策將資金引入實體經濟。由于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低于虛擬經濟,可能會導致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流動性流向房地產市場等高收益行業,造成房價上漲,進而擠壓實體經濟,使貨幣政策效果削弱。因此,建議中央銀行實施特定的貨幣政策將資本引入實體經濟。
二是完善金融監管體系。金融監管容易引起監管套利,導致大量金融創新活動出現,弱化貨幣政策傳導。因此,監管層應致力實現“分層”精準監管,壓縮不合理、違法違規杠桿,鼓勵推動實體經濟的正常合規杠桿。
三是應繼續完善“雙支柱”調控框架,深入分析不同經濟金融環境下貨幣政策工具和宏觀審慎政策工具之間的影響機制和政策效果,讓“雙支柱”調控政策可以在不同情形下都能發揮良好作用,促進經濟健康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1]? ?張蕊.新時期我國商業銀行的業務轉型與信用風險研究[D].南昌:江西財經大學,2020.
[2]? ?王璟怡.宏觀審慎與貨幣政策協調的研究動態綜述[J].上海金融,2012,(11):58-64,117.
[3]? ?葛志強.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管理政策協調配合研究——基于損失函數的動態一般均衡分析[J].征信,2013,31(2):73-77.
[4]? ?徐海霞,呂守軍.我國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監管的協調效應研究[J].財貿經濟,2019,40(3):53-67.
[5]? ?程方楠,孟衛東.宏觀審慎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搭配——基于貝葉斯估計的DSGE模型[J].中國管理科學,2017,25(1):11-20.
[6]? ?Akinci O,Olmstead-Rumsey J.How Effective are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2017.
[7]? ?黃益平,曹裕靜,陶坤玉,余昌華.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共同支持宏觀經濟穩定[J].金融研究,2019,(12):70-91.
[8]? ?馬理,范偉.促進“房住不炒”的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雙支柱”調控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21,(3):5-23.
[9]? ?蘆東,周梓楠,周行.開放經濟下的“雙支柱”調控穩定效應研究[J].金融研究,2019,(12):125-146.
[10]? ?黃繼承,姚馳,姜伊晴,牟天琦.“雙支柱”調控的微觀穩定效應研究[J].金融研究,2020,(7):1-20.
[11]? ?李力,溫來成,唐遙,張偲.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下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治理[J].經濟研究,2020,55(11):36-49.
[12]? ?陳利鋒,范紅忠.房價波動、貨幣政策與中國社會福利損失[J].中國管理科學,2014,(5):42-50.
[13]? ?Gelain P,Lansing K J,Mendicino C.House prices, credit growth,and excess volatility: implications for monetary and macroprudential polic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Banking,2013,9(2):219-276.
[14]? ?侯成琪,黃彤彤.影子銀行、監管套利和宏觀審慎政策[J].經濟研究,2020,55(7):58-75.
[15]? ?江振龍.融資約束、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活動與宏觀審慎政策[J].金融評論,2020,12(5):91-109,126.
[責任編輯? ?妤?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