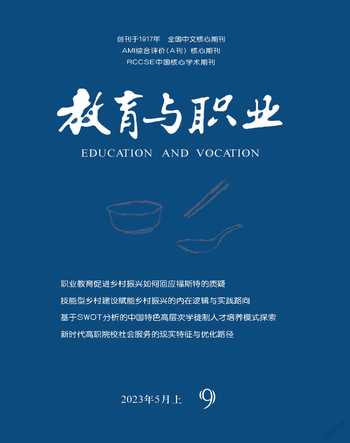基于知識變革背景的職業教育教材建設:旨歸、反思與進路
[摘要]職業教育教材建設需要以知識變革的深度反思作為實踐起點。職業教育教材建設應該堅持政治性與思維性統一、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統一、歷時性與共時性統一的理性旨歸。同時,職業教育教材依然面臨著“知識邏輯”遮蔽“能力邏輯”、“教材依賴”固化“知識邊界”、“原子賦能”限制“比特傳播”、“專家裁定”阻隔“讀者在場”等問題。對此,應以遵循“能力邏輯”為導向,重塑教材的組織結構;以突破“知識邊界”為旨向,構建教材的內容標準;數字化賦能“比特傳播”的技術藍圖,助推教材的數字化轉型;慎思“讀者在場”反身對話機制,回歸教材裁定的主體。
[關鍵詞]知識變革;職業教育;教材建設;數字化;新形態教材
[作者簡介]方緒軍(1982- ),男,黑龍江大興安嶺人,南寧職業技術學院教育政策與法規研究所,副研究員,廣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在讀博士。(廣西? 南寧? 530008)
[基金項目]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新技術時代知識變革與職業教育課程轉型研究”的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2YJC880014,項目負責人:方緒軍)
[中圖分類號]G714?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43985(2023)09-0097-09
當前,世界范圍內正掀起一場以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虛擬現實等為核心的第四次技術革命,科學知識轉化為技術知識的范圍擴大、速度加快、周期縮短、交叉并進,進而使知識的完善、淘汰與革新成為一種新常態。知識變革不僅僅催生技術知識的不斷變化與發展,引發崗位能力結構和內容的不斷調整與優化,客觀上也滋生了技術知識生長的假象,對職業教育教材知識內容的選擇造成困惑。于是,重拾與反思“什么知識進入教材”便具有時代境遇和現實訴求。同時,我國職業教育教材建設依然“存在著良莠不齊,適應性不強,難以滿足行業企業需求等問題”①,集中體現在教材舊、難、偏、同質等癥結,影響到我國職業教育教材的整體質量。2022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中明確提出:“國家鼓勵行業組織、企業等參與職業教育專業教材開發,將新技術、新工藝、新理念納入職業學校教材,并可以通過活頁式教材等多種方式進行動態更新。”這為我國職業教育教材建設提供了指導性意見。
一、應然樣態:職業教育教材建設的理性旨歸
教材是職業教育課程落地的載體、工具以及中介,職業教育教材建設必須堅守理性旨歸,解讀好教材對于“培養什么樣的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的應然樣態,為職業教育教材高質量建設提供理性保障。
(一)政治性與思維性的統一
培養什么樣的人,這是職業教育教材建設的基點問題。2017年國務院成立國家教材委員會,教育部組建成立教材局和課程教材研究所,負責對各級各類教材的統籌管理,進一步體現了黨和國家對教材工作的重視程度。
所謂政治性,就是職業教育教材建設必須扎根中國大地、服務社會大眾,必須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必須“始終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價值導向”②。具體來說,要始終堅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陣地,立足于我國社會主義國情,以社會經濟發展與變革、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為依據,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教材目標、內容、形式、評價等全過程中,切實培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需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同時,在強調教材“為國育人”的政治性基礎上,也不能忽視教材“賦智提技”的思維性功能。要通過整體設計教材的知識結構與內容、崗位能力的布點與銜接、工匠精神的融入與內化等,強化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形象思維能力和技術思維能力等,培養社會經濟發展所需要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總之,實現政治性與思維性相統一,就是要求職業教育教材建設將育人與育魂相結合,在引導學生學習知識、習得技能的同時播種家國情懷、民族情結、文化自信。
(二)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統一
為誰培養人,這是職業教育教材建設價值取向的問題。知識的客觀有效性和普遍必然性是哲學家們普遍認同的觀點,自斯賓塞提出“什么知識最有價值”的觀點后,便衍生出韋伯關于“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討論。工具理性作為一種重要工具和手段,深深地影響到當今西方社會的價值體系和理解慣習;價值理性則注重行為本身所代表的價值,強調社會價值要比行為結果更重要。
工具理性要求職業教育教材建設堅持“實用主義”原則,緊跟知識變革的發展趨勢,準確地掌握知識數量增長、技術升級、技能革新的方向和屬性,促使職業院校主動對接產業鏈發展、崗位能力要求以及新技術研發趨勢,進而將技術標準、崗位標準、員工標準等融入教材之中,以便培養更多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同時,在強化工具理性的基礎上,還需要將價值理性的基因注入教材建設精神內核之中,使人文知識、工匠精神、勞模精神等與技術知識實現融合,并且插入案例解析、創業故事、風土人情等內容,從而豐富教材內容、吸引學生注意、激發學生興趣,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知識觀、技術觀、職業觀等。
(三)歷時性與共時性統一
如何培養人,這是職業教育教材建設方法的取向問題。世界萬物都處于動態發展之中,具體到職業教育教材上體現為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特點。
就歷時性角度而言,從最開始的漁獵和農耕技術發展到如今各行各業的崗位能力,職業教育教材體現出知識在不同時代所呈現出的樣態,會根據知識變革與技術革新適時而變。這種變化并不是顛覆性的、批判性的,而是在原有教材體系的基礎上,從整體思維視角來考量教材內容的增加和減少,以使教材可以體現出最新的知識與技術要求。但是,在實踐中存在“小修小補”的思維誤區,認為教材僅僅需要增加一些新知識、新技術、新工藝、新方法,減少過時的技術與工藝,忽視了教材內容結構體系以及技能鏈條系統性的變化,呈現出碎片化的思維定式,其本質是局部性思維定式僭越整體性思維定式,客觀上導致教材知識鏈、技術鏈和技能鏈無法有機鏈接,從而影響到教材內容的整體邏輯序列。同時,職業教育教材還需要在尊重教材原有結構和體系的基礎上,注重教材內容和邏輯與崗位結構和能力相匹配,特別是既要滿足當前工作崗位對人才培養“共時性”的需求,同時也要順應數字化、智能化產業發展的趨勢實時向數智化轉型與升級,以便更好地適應知識變革時代對于人才質量和規格的要求,實現“教材育人”的目的。
二、現實審思:職業教育教材建設的理性反思
職業教育教材建設的理性反思是教材類型化發展的自覺性。教材建設問題涉及教材內容、教材受眾、教材媒介、教材編者等多個客體,呈現復雜性與關聯性并存的特點,可以從知識、受眾、媒介以及編者視角出發,對職業教育教材建設的現實進行多維反思,從而在反思中審思現實。
(一)知識視角:“知識邏輯”遮蔽“能力邏輯”,深陷“思維邏輯”
所謂“知識邏輯”,是指按照人類認識自然所遵循的知識認知序列而形成的完整知識結構,呈現出由簡入繁、由知識點到知識群的知識序列。在理性主義感召下,“知識邏輯”催生并形成了以知識邏輯為核心的學科知識體系,將清晰地認識自然的原貌作為知識使命,側重于運用嚴謹的學科知識邏輯構建起知識大廈,呈現出嚴謹的邏輯性和結構性,衍生出美國教育心理學家布魯納(Jerome Seymour Bruner)的結構主義課程論、德國教育學家瓦根舍因(Martin Wagenschein)的范例方式課程論等。但是,建立在“知識邏輯”基礎上的學科知識體系詮釋知識合理性、普適性和科學性的同時,對于具有獨特性的“訣竅”“技巧”等經驗知識或隱性知識卻表現得不盡如人意,甚至對于職業教育教材而言出現了“知識至上”的思維誤區,呈現出知識本位的教材觀。特別是深受學科課程和結構主義教學觀的影響,職業教育專業課教材的結構設計、編寫體例、內容邏輯和教學評價等基本上被禁錮在學科知識邏輯的架構中,不僅僅陷入了學科本位的“思維陷阱”,更限制了教材對學生能力養成與職業能力發展的賦能。
20世紀20年代中期,能力本位教育理念在我國職教界廣泛傳播,出現了基于職業行動邏輯的教材結構設計,價值取向由學科知識學習轉向職業行動能力培養。但是,從學科知識邏輯向職業能力邏輯轉型、從知識學習向技術學習轉向、從顯性知識養成向隱性知識內化、從專業通才向職業專才轉變的過程并不是一帆風順的,職業教育教材依然在“知識本位”與“能力本位”中間游走而難以選擇。誠然,“能力本位”主要是以“能力邏輯”為知識主線,以崗位實際需要為出發點,以能力養成作為知識學習走向,以模塊化技能點作為教材組織結構,側重于工作勝任力,具體是指成功生活或謀生所必需的工作能力、專業技能、勞動態度、價值觀以及鑒賞力等,而不是傳統能力觀所指的對知識的掌握。但是,由于以“知識邏輯”為理念的教材編寫方法發展時間長,且具有客觀性、穩定性、邏輯性等特點,更加容易被學科知識體系下的教師所接受,已經固著為教師的心理圖式,短時間內難以得到扭轉。雖然經歷過多次課程教學改革,但“知識邏輯”遮蔽“能力邏輯”的現象依然廣泛存在,教材建設中也依然將“知識邏輯”作為先驗經驗潛隱默化地影響著教師。由此,“許多本應該通過實踐過程來獲得的知識被錯誤地按照認識過程來讓學生獲得,從而使職業教育課程呈現出學問化傾向”③。
(二)受眾視角:“教材依賴”固化“知識邊界”,誤入“思維躺平”
教材以文字符碼為主要語言,記載了學生所要掌握的學科知識和技術知識。從教材發展的歷史來看,教材不僅僅是職業教育課程知識的有效載體,同時也是人類知識傳承與發展的重要陣地,對于教育公平化、平民化、規模化以及制度化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承載著課程知識的印刷教材文本并不是完美無瑕的,許多教材的文字表述質量不夠高,對課程原理與學習原理的體現不夠,具體內容與職業崗位要求脫節嚴重。為了扭轉教材內容與職業崗位要求脫節的問題,《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職業教育提質培優行動計劃(2020—2023年)》《職業院校教材管理辦法》等文件中均積極倡導使用新型活頁式、工作手冊式教材以及配套的數字化教學資源,以保持課程內容的動態更新。但是,多數職業院校還是將教材作為技術傳授的金科玉律,將教材內容作為技術知識學習來源、將教材知識組織方式作為技術技能學習序化模塊、將教材知識分布點作為技術技能學習的要點,無形之中強化了以教材為學習中心的“教材依賴”現象。
所謂“教材依賴”,就是教師習慣性地將教材內容視為開展教學的唯一來源,在認知層面上對教材產生嚴重依賴的心理圖式,表現為“以教材為中心”的教學思維。長期以來,受學科化課程的影響,職業教育教材內容的組織理念、形式等與普通教育基本一致,主要是系統地闡述專業理論知識,并形成了“以教材為中心”的刻板印象,導致“知識邊界”固化為以“教材為中心”所劃定的范圍,客觀上窄化了知識的來源,其本質就是“教材依賴”。可以說,“教材依賴”客觀上導致教材知識預設了嚴格的邊界和范圍,不僅僅使教師的教學局限于有限性的知識來源,同時也限制了學生學習課程內容的范圍,并逐步影響到學生對于世界的認知與再理解,導致學生的思想表達和技術思考也變得靜默、僵化。
同時,職業教育教材雖然具有動態性、發展性和跨界性,但如果想對教材中的技術知識進行修改、補充和更新,就必須額外承擔更多的時間、精力和經費等,而且即便實現動態更新也無法消除形式獨立性與思維對抗性的基因。特別是在知識變革背景下,知識的邊界呈現出無限擴張、學科交叉、迭代更新等發展趨勢,在“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等的沖擊下,傳統的形式僵硬的教材文本可能瞬間就被靈活性更強的新型活頁式、工作手冊式教材以及數字化形態教材所瓦解,這迫切需要職業教育擺脫“教材依賴”而走向更為寬廣的知識空間。
(三)媒介視角:“原子賦能”限制“比特傳播”,造成“數字鴻溝”
人類歷史上經歷了四次大的媒介革命,包括從口語媒介到文字媒介、從手寫媒介到印刷媒介、從印刷媒介到電子媒介、從電子媒介到網絡媒介。每一次媒介革命都引發大眾傳播工具的革新,在促進知識和技術在不同種族、階層和個體之間傳播的同時,也實現了人類文化基因和精神火種的傳承。
當前,職業教育教材正處于由“原子賦型”向“比特傳播”轉型期,紙質版教材難以適應數字化時代的技術認知方式和慣習,而電子化、數字化的教材已經逐步成為“數字移民”一代的新寵兒。依托其獨特的泛在性、便捷性、多樣性等技術特點以及“超鏈接”“數字在場”“超文本”等技術優勢,泛在學習、數字賦能等成為現實。同時,借助于多維空間的開放性和流動性的特點,知識化身為“比特”在網絡空間中跳轉、流動,打破了原有教材所劃定的知識邊界,使知識邊界彌散、知識傳播連續以及知識范圍無限拓展。但是,也應該清楚地看到,在數字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由于對數字化信息與網絡通信技術的擁有和應用程度不同,信息落差、知識隔離以及貧富差距等普遍存在,導致“數字鴻溝”和“數字依賴”等數字異化問題的產生。生活在“原子賦能”學習場域中的一代正面臨著“比特傳播”中“望梅止渴”的尷尬境地,最終造成新的“數字鴻溝”。這種新的“數字鴻溝”主要表現為信息技術的可及性差異(第一類數字鴻溝)、技術的使用差異(第二類數字鴻溝)以及互聯網獲取知識多少(第三類數字鴻溝),呈現為信息技術基本設施缺乏、信息素養能力不足以及信息檢索能力欠缺等問題。這在客觀上導致紙質版教材依然是職業教育教材的主體,“原子賦能”依舊發揮著不可取代的作用,甚至電子化、數字化的教材被貼上低效、無序等標簽,成為職業教育教師不敢踏入的“禁區”。
(四)編者視角:“專家裁定”阻隔“讀者在場”,導致“群體沉默”
教材既是編者創作和表達知識的產物,也隱含著作者的生命體驗和生命表達,具備組織系統的邏輯性。當然,教材不僅具有吸收知識的他組織特質,無論是學科知識還是技術知識都可以成為教材內容,體現出全納性的特點。同時,也秉持著自我改造與創新的自組織慣習,摻雜著過多的“他者觀點”和“一家之言”,體現出選擇性的特征。
在從知識到教材的過程中,以編者為主導的知識教材化已經成為職業教育教材編寫的習慣,但受編者能力所限和視野范圍等影響,凝聚著人類智慧的教材其實并不是完美無瑕的,甚至存在“教材開發思路不清晰、內容質量不佳、文字表述水平不高”④等問題。編者對于知識的“選擇性”僭越了知識的“全納性”,導致教材的編寫帶有濃厚的人為性色彩。雖然對于知識基數和增長速度而言,知識的選擇性有利于將專業新知識、新技術、新工藝以及新方法編入教材之中,縮短學生學習與崗位能力之間的距離,有利于學生從自然人蛻變為職業人,但是教材一旦成為出版物無形中就會被貼上權威性、依賴性的標簽,讀者容易陷入“專家裁定”的話語體系之內,以教材作為知識的來源和技能養成的圭臬,阻隔了“讀者在場”,導致“他者的消失”,甚至產生“群體沉默”現象。同時,教材出版本身就代表著作者獨立性和僵固性的自我表達。知識變革背景下,新知識、新技術、新工藝以及新方法層出不窮。但如果想對原來的教材內容進行修訂、更新和補充,必須經過來稿審稿、編輯加工、裝幀設計、排版校對、簽批付印、復制印刷、裝訂成冊等流程。即便可以縮短這一流程,也無法消除印刷文本與生俱來的形式固定性與思維排他性,最終難免陷入教材“專家裁定”的困局。
三、未來圖景:職業教育教材建設的理性進路
考察“知識的可能性”無非就是知識與行動、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映射到職業教育教材層面上無疑是如何實現“知識的可能性”,進而打通知識與行動的通道、縮短理論與實踐的距離。為此,高質量的職業教育教材建設,既要秉持復雜性、科學性、先進性為內核的研究態度,把握好教材設計、編訂、使用、評價等技術性環節的理性進路,更要立足于職業教育類型化特征的理性進路,凸顯職業教育教材的本質特色。
(一)判斷與拆解:以遵循“能力邏輯”為導向,重塑教材的組織結構
課程是教材的基石,決定著教材的定位、目標、內容、結構和評價。然而,受課程知識主導、學科影響、邏輯至上等價值取向的影響,我國職業教育教材被貼上知識化、學科化、邏輯化的標簽,其“類型化”的特點被“等級化”所掩蓋,成為“他者教育”的復制品,學生則被打造成為“知識的存儲器”和“技能機器人”,從而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問題解決的能力和自我發展的能力。對此,職業教育教材要聚焦學生能力的培育,應將“要使一個‘自然人’或是一個‘生物人’,成為一個社會所需要的職業人”⑤作為職業教育教材的價值旨向。
首先,堅持價值導向,判斷新時代我國職業教育教材的邏輯起點。知識變革背景下,新知識、新技術、新工藝以及新方法更新速度不斷加快,職業教育教材不僅面臨著對知識的選擇、加工、呈現、評價等問題的慎思,也需要遵循教材的周期更新規律,以更好地適應產業發展對于人才培養質量與規則的要求。為此,職業教育教材建設要立足于類型化本質特征,從邏輯起點找尋教材的內在價值與時代使命。一方面,教材是體現出國家意志的重要事權,是學生獲得知識和技術的重要載體,也是國家對于職業教育人才培養質量與規格的具體體現。2022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中明確提出:“為了推動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提高勞動者素質和技術技能水平……制定本法。”同時,又將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作為職業教育人才培養定位。由此可見,職業教育教材承載著為國育人與以文育人雙重價值,并將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作為編制的起點。另一方面,知識變革背景下,無論技術知識如何變革、職業教育政策如何發展,學生能力培養自始至終都是職業教育教材建設的核心所在,凸顯出人才培養的類型特色與本質屬性。而“以能力為基本單位更能發揮職業教育教材的優勢”⑥,因此其定位應主要聚焦在學生能力的養成。職業教育教材的組織不僅要呈現出是什么的學科知識點,還要使學生掌握怎么做的操作知識點,進而提升學生認識知識的內容、掌握知識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反思技術的能力,充分體現職業教育的類型定位。
其次,聚焦能力養成過程,拆解具體崗位能力,進而組織模塊化教材。能力養成既是我國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理念和目標,同時也是職業教育教材編制的組織結構和內容依據。能力養成必須以實際的崗位能力需求為導向,以真實的工作規范和崗位操作要求為依據,將一項工作或某項能力按照能力邏輯分為若干個完整的、系統的能力模塊。這既有利于學生職業能力的養成,也有助于學生的自主性學習、個別化學習以及協同化學習,進而破解“學科邏輯”教材“難、偏、繁、舊”的問題。特別是與職業教育傳統教材“章—節”體例的組織不同,職業教育教材組織的模塊化是以能力養成為組織原則,側重于模塊化的知識組織方式,一個“模塊”就是“一個單位的課程內容,它有自己的起點和終點,可以對之增加一些模塊,以完成更大的任務,或達到更為長期的目標”⑦,彰顯出模塊的相對獨立性、能力完整性、絕對靈活性等特征。正是由于這些特征,學生既可以在模塊化教材中學習到完整的、真實的、可操作的知識和技術,還可以根據新技術、新工藝和新方法對模塊化教材的模塊進行更新,而不會對教材的整體結構產生太大影響。為此,職業教育教材建設要以提升學生能力為核心要義,明確教材編寫理念、內容選擇、組織結構等,以模塊化的組織方式構建教材的能力邏輯體系,以實現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時代使命。
(二)倡導與厘定:以突破“知識邊界”為旨向,構建教材的內容標準
由于知識域迭代重疊,邊界知識交叉互補,邊界的知識粒度分布各異,導致知識邊界呈現出重疊、交叉和差異等特點。同時,知識邊界的建構是專業形成的重要機制,是以學科專業知識和學科交叉知識為基礎而形成的無形邊境,在職業教育傳統教材的設計理念中專業知識與專業知識之間存在“異質性”,是區別于專業類型的重要判斷標準。但是,“知識邊界”既在客觀上成為“教材依賴”的直接原因,同時也是知識變革背景下職業教育教材編制可能性的根源。為此,要以突破“知識邊界”為旨向,構建教材的內容標準,生成具有特色的職業教育知識觀。
首先,倡導使用新形態教材,突破職業教育專業“知識邊界”的限制。“知識邊界”在客觀上攜帶著學科化、知識化和邏輯化的思維慣習,使職業教育教材讓位于抽象化的知識概念和符號,不僅無法提高學生的技術技能水平,同時也削弱了職業教育的學科本質。為此,職業院校應該積極探索并倡導使用新型活頁式、工作手冊式教材等新形態教材,在實踐教學過程中凸顯“新”“活”“用”三方面的特征,將學科知識轉化為技術知識,將教師教學轉化為學生學習,將接受知識轉化為創造知識。其中,“新”即理念新、內容新、形式新,主要是校企在先進理念的指導下,根據知識變革適時調整內容,并以活頁式、工作手冊式等形式呈現,體現出新知識、新技術、新工藝以及新方法的融入,凸顯出教材編訂的與時俱進,進而突破現有知識數量邊界,實現學生知識數量的增長;“活”即體例活、教學活、學習活,主要是指職業院校要根據能力模塊編制模塊化章節、可拆可分的教材,同時根據能力知識點靈活地設計采用任務導向、工作過程導向等教學方法開展理實一體化教學,進而引導學生自主學習、個性學習,凸顯出教材學習的靈活多變,進而突破現有知識組織邊界,實現學生理實知識的融合;“用”即教師用、學生用、實操用,新形態教材應以學生為中心,既要滿足教師的日常教育教學活動,也要通過興趣驅動、項目導向、能力進階來引導學生從被動學習向主動學習轉變,還要配有任務目標、任務過程、學習測試、評價總結等技能操作訓練引導學生實現自主實操,進而突破現有知識學習邊界,使學生成為創造知識的主體。
其次,厘定知識變革的內在特征,構建教材的內容標準。處于第四次技術革命的前沿,知識的變革不僅僅促使知識數量增多、種類繁多,更衍生出知識學科分類細化、知識交叉性加強等現象,特別是在不同專業的知識之間、不同課程的知識之間也形成了技術邏輯上的關聯,導致教材組織在模塊的基礎上知識交叉性日益明顯,集中表現為交叉性課程知識、交叉性技術知識、交叉性專業知識等形態,在對職業教育教材建設提出挑戰的同時,也為職業教育教材建設指明了改革方向。基于此,職業院校應該重塑教材的內容標準。根據《職業院校教材管理辦法》中“教材審核應依據職業院校教材規劃以及課程標準、專業教學標準、頂崗實習標準等國家教學標準要求”的規定,職業教育教材應該在政治標準、課程標準、專業教學標準、頂崗實習標準、職業標準(規范)以及技術質量標準和規范等基礎上構建教材的內容標準。具體來看,既要在政治標準上突出立場堅定、遵紀守法,課程標準上體現技術導向、模塊設計,專業教學標準上彰顯尊重學生、豐富教學,還要在頂崗實習標準上實現任務驅動、理實一體,職業標準上反映前沿技術、緊密對接崗位,技術質量標準上科學合理、梯度明晰,進而實現教材內容的標準化。
(三)延展與優化:數字化賦能“比特傳播”的技術藍圖,助推教材的數字化轉型
當前正處在由紙媒化向數媒化轉型的時期,人類的認知圖式不再局限于天然的物理空間中選擇知識,而是游離于數字化營造的圖文聲像一體呈現的虛擬空間中獵取知識,進而突破教材所帶來的“教材依賴”的屏蔽,使職業院校學生的認知空間從“物理空間”走向“數字空間”。
首先,延展數字化工具,探索數字化賦能“比特傳播”技術藍圖。隨著知識變革日益深入,職業院校學生學習不再是“從A到Z的漫長旅程”,而是由網絡化的知識勾勒出的“一個無定形的、相互交織的、不可掌控的大網”⑧。借助教育數字化轉型,職業教育領域引入“云計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支持的‘數字畫像’、‘多模態數據支持的作業分析’、‘人機協同的個性化輔導’、‘需求導向的精準作業推送’等信息技術手段”⑨,進而延展了數字化工具的種類和功能,使知識的權利組織從“垂直分布”轉變為“平行分布”,大大縮短了知識在傳遞過程中的自然距離。同時,借助網絡技術和大數據等手段,更是開辟了一種非階級、非種族、非功利、非封閉的知識傳播渠道,使“比特傳播”的藍圖從理想圖景變為現實可能。特別是隨在知識變革引發產業結構性調整、崗位工作能力要求變化的背景下,職業教育教材承載著技術傳播、技術育人雙重任務,更應該直面數字化、智能化技術與教材深入融合對于印刷教材的挑戰,尤其是印刷教材更新必須經歷調研、編寫、審核、出版、發行等一系列程序性工作,客觀上導致“現實教材”與“理想教材”之間巨大的時間鴻溝,并呈現出固著性、滯后性等后天性不足。然而,數字化時代數字化技術化身成為課程轉型的利器,在打破紙媒知識體系中嚴格的科學邏輯與學科邊界的同時,還使知識化身為“比特”在網絡空間中靈活流動,“在客觀上促使課程內容的聯接性加強、情境性逼真、交互性更高、空間性更延展、邊界更模糊,進而實現職業教育課程動態更新,使泛在學習、具身化等概念得以實現”⑩。
其次,優化配套建設數字化教學資源,助推教材的數字化轉型。2022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指出:“開發職業教育網絡課程等學習資源,創新教學方式和學校管理方式,推動職業教育信息化建設與融合應用。”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知識增長的數量和速度均令人驚嘆,對于教材是否可以承載人類認知的欲望也產生了“促逼感”。借助于數字化教材強大的比特傳輸能力、便捷的文字處理技術等,可以自由靈活地增加新技術、新工藝以及新方法等內容,隨時在數字文本增加相關網絡拓展知識、技術等資源,從根本上打破傳統印刷教材“一家獨大”的壟斷格局,使教材學習從“實在”走向“云在”成為一種可能。為此,職業院校要抓住專業數字化轉型關鍵期,優化配套建設數字化教學資源。特別是在“數字化生存”日益成為人類生活、學習以及工作的新常態下,數字化教學資源并不是簡單的資源“數字化”過程,而是需要現有教學資源的數字化、拓展性教學資源的鏈接化、教學資源內容的多樣化以及教學資源呈現的多維化,在此基礎上才能實現教材的數字化轉型。
(四)解蔽與重拾:慎思“讀者在場”反身對話機制,回歸教材裁定的主體
職業教育教材既可以反映新知識、新技術、新工藝、新方法等產業的變化與發展,同時也遮蔽了教材應有的面貌,導致教材“固化”與讀者“躺平”并存,客觀上偏離了職業教育教材的類型化特點。為此,必須加強讀者與編者之間的平等對話,慎思“讀者在場”反身對話機制,回歸讀者作為職業教育教材的裁定主體地位。
首先,解蔽職業教育教材的學術權威禁區,構建“讀者在場”反身對話機制。《職業院校教材管理辦法》中明確提出“專業課程教材要充分反映產業發展最新進展,對接科技發展趨勢和市場需求,及時吸收比較成熟的新技術、新工藝、新規范等”的要求,無疑是在強化職業教育教材的科學性與規范性相結合、動態性與發展性相結合。但是,目前教材客觀上還是存在內容滯后、“專家裁定”等情況。為此,要解蔽職業教育教材的權威禁區,松綁讀者對于教材的絕對依賴,就必須堅持慎思“讀者在場”反身對話機制,使“讀者在場”成為現實。第一,“讀者在場”必須實現“多元到場”,破解“一家之言”。這就要求教材編寫吸納相關學科專業領域專家、教科研人員、一線教師、行業企業技術人員和能工巧匠、學生等人員參與其中,發揮多元主體的學科優勢和技術經驗。第二,“讀者在場”必須恪守“層級監督”,破解“一葉障目”。這就要求教材必須以體現黨和國家意志為前提,在國家教材委員會宏觀指導和統籌下加強分級管理。同時,強化教育行政部門牽頭負責實施中觀管理,有關部門、行業、學校和企業等多方治理主體微觀參與,特別是要強化職業院校對于教材具體的管理權限和自主權。不僅要落實學校黨委對教材工作的總負責制,進一步健全內部管理制度,嚴格地執行國家和地方關于教材管理的有關政策規定,更要強化職業院校教材編寫的靈活性,根據產業發展對于人才培養質量和規格的要求編好、選好、用好教材,以便實現教材的政治性、科學性、合理性、及時性等目的。第三,“讀者在場”必須倡導“反身對話”,破解“故步自封”。這就要求職業院校教材建設堅持“自反”與“反思”相結合,既要體現教材編者對于教材本體的理性反思,以便實現純粹理性,又要克服各種非理性因素的作祟,以便追求自知和確定性的理性。
其次,重拾職業教育教材的類型本質,回歸教材裁定的主體。類型決定著職業教育教材既具有教育普適性的一面,更需要具有職業教育特殊性的一面。知識變革使知識數量激增、迭代速度加快,導致教材無法承載如此多變、多量和多質的知識。教材編寫者憑借著知識占有的權威,通過教材加強了知識權利配置差序格局,成功地塑造了“無所不知”的教師和“一無所知”的學生,教材學習往往被視為對于知識真理明燈的朝圣,被壓抑的學生異化為知識的容器,客觀上使學生淪為了僅僅掌握一種或一門單一技術的,失去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為此,必須彰顯職業教育教材的類型本質,將專家從“一家獨大”的知識權威神壇上拉下來,重新審視并回歸教材裁定的主體——學生。從“學生成才—產業發展”之間的關系而言,職業教育教材要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和產業升級新動態及時進行修訂,以滿足學生智能與能力的生長;從“學生生長—職業適應”之間的關系而言,職業教育教材要從學生生長中選擇知識、從學生發展中建設教材;從“學生學習—教材呈現”之間的關系而言,職業教育教材要充分利用數字化技術工具,不僅借助數字化教材在文字處理、知識編輯與比特傳輸技術等方面的優勢,隨意隨需增刪、潤裁、優化內容,使學生的想法觀點、思想以及創意可以在靈動的網絡空間內率性釋放,還要創設網絡空間的職業教育技術文化環境,使知識在網絡空間內情境化、操作化、體驗化,真正實現“讀者在場”。
[注釋]
①曾天山,馬建華,劉義國.以國家規劃教材提升職業教育教材質量[J].課程·教材·教法,2021,41(5):27.
②曾天山.我國教材建設的實踐歷程和發展經驗[J].課程·教材·教法,2017,37(12):18.
③徐國慶.實踐導向職業教育課程研究:技術學范式[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17.
④徐國慶.職業教育專業課教材建設(筆談)——如何提升職業教育專業課教材質量[J].當代職業教育,2021(4):5.
⑤姜大源.職業教育要義[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10.
⑥李政.職業教育新形態教材:內涵、特征與編寫策略[J].職教論壇,2020(4):23.
⑦Warwick D.Modular Curricula[A].In Husen T,Postlethwaite T N (eds.).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Great Britain:BPC Wheatons Itd. Exeter,1994:3886.
⑧(美)戴維·溫伯格.知識的邊界[M].胡泳,高美,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147.
⑨趙健.技術時代的教師負擔:理解教育數字化轉型的一個新視角[J].教育研究,2021(11):151.
⑩方緒軍,施淵吉,梁晨.數字化時代職業教育課程轉型:理據、風險與辯證[J].職教論壇,2022,38(10):51.
[參考文獻]
[1]方緒軍.技術知識變革:職業教育課程本體遮蔽與適應性選擇[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22(14):12-20+28.
[2]宋文文,曾瑤,張廣君.走向“超越知識觀”:智能時代的知識觀變革與教學知識觀取向[N].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06-10(4).
[3]馬桂香,鄧澤民.我國職業教育教材研究40年綜述[J].職教論壇,2019(10):57-64.
[4]周慧珺,鄒文博.數字化轉型背景下數字鴻溝的現狀、影響與應對策略[J].當代經濟管理,2022(12):1-12.
[5]石偉平,徐國慶.職業教育課程開發技術[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6](美)約翰·杜威.民主與教育[M].薛絢,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
[7]周小李.媒介教育哲學引論“蘇格拉底之疑”及其傳承[J].社會科學戰線,2020(9):22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