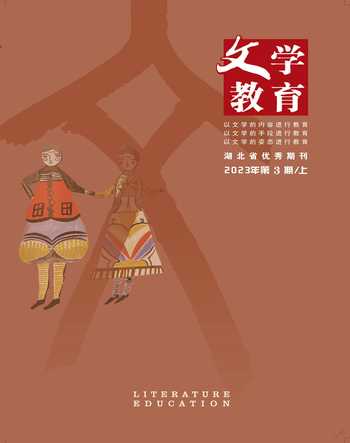于紛擾中尋求生命的暖色
內容摘要:《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和《阿長與山海經》創作的時間、創作主題、創作風格頗為相似,由于這種內容上的互文性,在教學時,亦可以著眼于其一致性和連貫性。魯迅在這兩篇散文中采用了兒童與成人的雙重敘事視角,將童年的花蕾與中年的藤蔓串聯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明暗交織的生命體驗圖。在講授這兩篇課文時,教師應該注重將文本解讀與學生的生命體驗緊密結合,引導學生在魯迅的生命歷程中感悟人生況味,從而學會發現生活中的真善美,懂得珍惜成長所必經的每個人生階段。
關鍵詞:統編教材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阿長與山海經》 生命體驗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和《阿長與<山海經>》都創作于1926年,是魯迅回憶童年生活的懷舊之作,收錄到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由于《朝花夕拾》是魯迅筆下最為溫暖的一抹亮色,因此被認為適合低年級的中學生閱讀。在統編版初中語文教材中,《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安排在七年級上冊第三單元,“單元目標”指出“了解多姿多彩的學習生活,感受他人的學習智慧,獲得人生啟示”。《阿長與山海經》安排在七年級下冊,單元目標指出“結合文體特點和作者的敘事風格,展開多種形式的誦讀,加深對作者情感態度的理解和對文本意蘊的體悟。”由此可見,兩篇課文的教學重點都是通過文本閱讀和分析,進入對作者思想情感的體悟,獲得一定的人生啟發。兩篇文章創作的時間、創作主題、創作風格頗為相似,由于這種內容上的互文性,在教學時,亦可以著眼于其一致性和連貫性,挖掘魯迅的生命體驗。兩篇文章中“我”的年紀與初中生相仿,因此在講授這兩篇課文時,尤其應該注重將文本解讀與學生的生活實際緊密結合,引導學生在魯迅的生命歷程中感悟人生況味。
一.一顆童心最珍貴
打開《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一個色彩鮮明、充滿生命力的“樂園”便呈現在我們面前。“不必說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椹……如果不怕刺,還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攢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遠。”[1]這時,人屆中年的魯迅撥開歲月的塵霧,把自己完全沉浸在孩童的世界中,沿著兒童的眼光興致勃勃地介紹著百草園。只有在孩子的眼中,石井欄才是“光滑”的,因為孩子會動手去摸,皂莢樹是“高大”的,因為“我”是矮小的。只有孩子才會注意到草里鳴叫的蟬,菜花上伏著的黃蜂,從草里竄上天的云雀。也只有孩子,會翻開磚石探究底下會有什么稀奇的東西,會用手指去按斑蝥的脊梁,看它的后竅噴出的煙霧,如此反復,不亦樂乎。孩子會聽到傳說后心心念念,執著地尋找人形的何首烏,不惜弄壞泥墻。孩子會不怕刺,摘小球狀的覆盆子,品嘗它酸酸甜甜的味道。正因為魯迅以孩童的感受力和想象力看世界,百草園之“樂”才得以靈動得再現。
當然,百草園作為“我”童年的樂園,不僅僅有趣味十足的自然事物,還有溫暖的人情味。長媽媽給“我”講了園子中赤練蛇的傳說,作為孩子的“我”對世界的認識是淺顯的,對這個傳說深信不疑,這成了“我”童年的一大心事,以至于夜晚不敢去看那墻。中國的長輩為了管教孩子,阻止兒童去危險僻遠之地,就會編出一些故事來起威懾作用。長大后的魯迅明白這不過是長媽媽杜撰的,但絲毫不怪罪她,反而感到這樣的故事為童年增加了趣味,增加了對神秘世界的神往,過后回想,也覺得饒有興味。除了長輩的厚愛,百草園里還有同齡伙伴的友情。文中提到“我”與閏土冬天捕鳥的趣事,后來這一情節也出現在《故鄉》里,可見魯迅對此印象之深。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提到的長媽媽便是《阿長與山海經》中的主角。此文采用“欲揚先抑”的手法,前半部分寫“我”對阿長的“憎惡”。這部分的語言幽默俏皮,諧趣十足,因此即使魯迅特意強調“抑”,但我們讀到的卻并非“憎惡”,雖有微諷,但不冷峻,可謂“抑中有揚”。比如魯迅描繪了阿長“切切察察”的神態,但她切切察察的后果卻有點“可笑”,那就是“我”若拔一株草,翻一塊石頭,就被她說成過于頑皮,向“我”的母親告狀。魯迅又生動形象地描繪了阿長舉止粗俗,睡姿很不講究,而“受害者”又是“我”——推不動,叫不聞,還要承受她一條臂膊壓在頸子上。阿長還教“我”許多規矩,這也令“我”頗感不耐煩,但又沒有反抗之力。不過阿長終于在講“長毛”的時候收獲了“我”的敬意。起初這個故事并沒有駭住“我”,阿長見狀更加“添油加醋”地渲染長毛如何兇殘,直到她講了自己會被擄去脫下褲子做人肉城墻,這才令“我”刮目相看。魯迅用了“偉大的神力”,“特別的敬意”這樣崇高的詞匯來形容“我”對阿長的敬意,“大詞小用”的手法含有夸張和調侃的性質,產生了濃厚的妙趣,既傳神地繪出了阿長的神采飛揚,也將“我”的童真稚氣展現得活靈活現。不過在“我”知道阿長謀害了隱鼠后,這種敬意完全消息,“我”“極嚴重地詰問”,“當面叫她阿長”,這種“鄭重其事”的畫面也令人忍俊不禁。
“隱鼠事件”之后,文本進入了“揚”的部分。“我”對《山海經》十分渴望,或許因為《山海經》并非正統科舉書籍,大人們都不肯真實地回答“我”怎樣得到它。只有阿長這個不識字的、“我”最不寄希望的人,將一個孩子的心愿放在心上,竟然買到了帶圖畫的《山海經》。盡管長大后“我”發現這是部刻印、紙張都十分粗糙的本子,但在當時,那是“我”最初得到的,最為心愛的寶書,此后回想起來依然滿懷感動。除了阿長,遠方叔祖周玉田也給魯迅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是一位胖胖的,和藹的老人,喜歡種花木,也許是為了打發時光,也許他本身喜歡孩子,他樂于與孩子們來往,稱“我”為“小友”。“我”有機會接觸他的藏書,正是通過他知道了神秘的《山海經》,打開了讀書的天地,孩子的想象力得到發展。有了這些長輩的關愛,魯迅度過了既拘束又不無美好的少兒時光。
通常在解讀《阿長與<山海經>》時,教師都將重心放在阿長身上,剖析這一人物形象的特質:她作為一個典型的底層農村婦女,具有搬口弄舌、行為粗俗、迷信無知的弱點,也有淳樸、真誠、善良的優點。事實上,“我”也是一個不容忽略的人物。童年的魯迅時常對阿長有抵觸情緒,是因為阿長總是管束他,而從成年人的角度來看,長輩管束孩子是很自然的道理,并非什么“深仇大恨”。這時的魯迅再回憶阿長,目的并非批判阿長,而是帶著更復雜的情緒,回味自己童年時的精神心理。魯迅從“我”的視角寫阿長,對阿長的態度上附著了濃厚的主觀色彩,在描寫阿長的同時,也在描寫著“我”,一個童年的小魯迅的形象便活脫脫地勾勒出來。這個“我”活潑好動,向往自由,心地單純,愛護動物,喜歡繪畫,富有想象,愛與憎的情感簡單、分明。“我”過著天真爛漫的童年生活,當然生活中也有煩惱,這煩惱無非是長輩禁止自己淘氣或不小心踩死了“我”的寵物,但這對一個孩子來說已經是莫大的打擊。“我”的快樂也很簡單,一本渴慕許久的畫書便足以讓“我”忘記曾經的不愉快,感受到天大的驚喜,萌生強烈的感恩之心。成年以后的魯迅回眸童年的自己,既羞愧于當初的幼稚,也欣賞那份珍貴的純真,揶揄中難掩洋洋自得之意,故而采用看似漫不經心的敘述,實則將對童年生活的深摯懷戀滲透在字里行間。
兩篇文章都以童趣見長,字里行間滲透著魯迅對童年的眷眷深情。在成年人眼中,百草園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菜園,比如周作人晚年時回憶道:“百草園的名稱雖雅,實在只是一個普通的菜園”[2]。阿長與童年魯迅之間的故事,也不過是極為普遍的長輩與孩子的日常。但是魯迅尊重和珍惜孩子活潑好奇的天性,懂得孩子眼中的世界和大人看到的不同,將視若平常的童年生活還原出活色生香的本色。世界著名童話《小王子》的作者埃克蘇佩里說過:“每個大人都曾是小孩,只是只有少數人記得。”魯迅自己也說過:“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處,想到昆蟲的言語;他想飛上天空,他想潛入蟻穴……然而我們是忘卻了自己曾為孩子時候的情形了……”[3]魯迅就是少數記得自己曾是孩子的成年人。他借助筆端與另一個自己相遇,小心翼翼地捧起那顆潛藏許久的童心,痛痛快快地又做了一回天真爛漫的孩子。
二.揮別童年,接受成長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的前半部分寫了“百草園”,后半部分寫了“三味書屋”。兩部分之間有個過渡段。“總而言之:我將不能常到百草園了。Ade,我的蟋蟀們!Ade,我的覆盆子們和木蓮們!……”[4]可見,魯迅在回顧自己的成長軌跡時,將入三味書屋劃作自己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入私塾意味著他從童年自由自在的形態,進入了正規的受教育階段,開啟了被社會化、被規訓的人生歷程。縱然,魯迅與自己的“樂園”告別時透露出淡淡的惆悵,但“百草園”與“三味書屋”之間并非簡單的褒貶關系。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配合對我國應試教育的反思,學界將“百草園”與“三味書屋”的關系解讀為對比或襯托關系,認為魯迅通過前后自由快樂生活和枯燥迂腐生活的比照,表現前者適合兒童的天性,后者阻礙兒童的身心發展,以批判封建教育制度對兒童的束縛和損害。近年來,研究者摒棄了先行的理念,綜合文本分析和魯迅的生平經歷,提出百草園與三味書屋是和諧統一的關系。
首先,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對于壽鏡吾先生的描寫是正向的,筆觸間不乏寬容和溫情。魯迅稱先生“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給予先生很高的評價。他主持的三味書屋傳說是全城最嚴厲的一家,雖然有著傳統私塾慣有的戒尺和罰跪的規則,但都不常用,最多是瞪幾眼令大家讀書,可以想見此“嚴厲”不是來自嚴苛,而來自先生的敬業和躬身示范。當然,魯迅也描繪了他身上迂腐的儒生氣:一是莊重嚴肅地引大家拜孔子、拜先生,二是在“我”詢問“怪哉”這蟲時,面有怒色地說“不知道”。這表明他受時代條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具有封建私塾先生的傳統性。但魯迅并不是進行辛辣的嘲諷,而是以詼諧的方式,進行善意、點到為止的展現,所以先生給人的感受整體上依然是親切的,這種親切之感也是當時作為孩子的“我”切切實實的感受。
其次,“我”在三味書屋也很快找到了樂趣。三味書屋也有一個小小的園子,可謂“百草園”的延續,孩子們可以在學習之余去折臘梅,尋蟬殼,最有興趣的是捉了蒼蠅喂螞蟻。先生并不禁止孩子入園玩耍,只要適可而止便可,但若逗留太久也不責罰,只一句“人都到那里去了”將學生們喚回來。可見,先生給孩子們留下了一定的空間,未泯的童心得到了一定的綻放。更重要的是,在先生的嚴格要求和以身作則之下,三味書屋培養了“我”對知識的興趣,養成了勤奮務實的治學態度,為將來從事文化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壽鏡吾先生最初對“我”很嚴厲,后來便好了,因為小魯迅聰明過人、品格高尚,先生對他格外器重,給他讀的書比其他同學多,這也體現了“因材施教”的原則。先生讀書時全身心地投入,這讓“我”疑心這是極好的文章,潛移默化中也啟發了“我”對讀書的興趣。在讀書的間隙,“我”迷上了畫畫,書讀得越多,繪畫成績也越來越好。考察魯迅傳記可以知道,在“三味書屋”接受的啟蒙教育是魯迅一生的寶貴財富,他離開三味書屋去南京、日本求學后,每次回紹興都要去拜訪壽鏡吾,師生之間形成了深厚的情感。
總之,進入三味書屋后,“我”并沒有產生抵觸心理,而是在適應新環境的過程中漸漸長大,進入了更加成熟的人生階段。這也是題目的意味所在,題目采用“從……到”,而不是“百草園與三味書屋”,就是為了強調“百草園”與“三味書屋”之間的承續關系,寓意著人生成長的動態過程。魯迅入三味書屋時是12歲,這篇課文安排在七年級,學生們正好也在12歲左右。七年級是學生學習生涯中的一個轉折點,告別了小學時代,進入了課程門類增多、學科內容趨向抽象化的中學階段,學習的強度和難度都有所增加。這就需要學生形成新的素質,無論心態、學習態度、學習能力都進行相應的調整,以適應新的學習生活。這篇課文選在此時可謂恰合時宜。教師可以結合魯迅的成長過程,引導學生接受成長,在目前的學校生活中找到樂趣,讓學生認識到人生的每個階段都自有其美好,中學階段雖然告別了無拘無束的童年,但也可以體會知識的美好,感受友誼的快樂。為了讓學生的認識更加深入,可以讓他們動手寫寫自己進入中學生活后的所見、所思、所想,與魯迅的寫作進行對比,從而反思當代中學生應該具備怎樣的學習智慧。
三.“在紛擾中尋出一點閑靜來”
兩篇文章在輕松、溫暖的基調之外,也時時流露出一絲沉重,這使作品不同于一般的兒童文學,而具有更豐富、更多層次的意蘊。這是因為魯迅在兒童視角之外,還采用了成人視角,他將童年的花蕾與中年的藤蔓串聯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明暗交織的生命體驗圖。談及《朝花夕拾》的創作因由,魯迅說道“我常想在紛擾中尋出一點閑靜來,然而委實不容易。”[5]魯迅于1926年3月10日創作了《阿長與<山海經>》,此時的他剛剛經歷了“女師大風潮”,又逢政治環境惡劣,心境并不明朗。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不久,北京的政治環境進一步惡化,魯迅離開生活了十年的北京南下廈門,但在廈門遭遇了與北京同樣污濁的政治空氣、人際關系危機等等,在這樣的狀態下寫就了《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朝花夕拾》是魯迅在紛擾和孤獨中的心靈之作,溫暖的回憶縱使暫時撫平了心靈的焦慮,但當下巨大而廣漠的悲哀又怎能不時時涌出。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魯迅在回憶過去的時候,現在的他也會時時站出來發出議論和抒情,為文章蒙上一層憂郁深沉的色彩。他提到百草園早已連屋子一起賣給朱文公的子孫時,言語間充滿了惋惜與留戀;他回憶起自己畫的《蕩寇志》和《西游記》的一大本繡像,后來為了要錢用賣給了一個同窗,淡然的語氣中滿是落寞和惆悵。文章就以“這東西早已沒有了吧”收尾,看似平淡實則一語雙關、余味深遠,既陳述了文化物品更新換代的事實,更是感嘆一去不返的還有自己的少年時光。當魯迅沉浸在過去的甜蜜回憶時,也會流露出現在時的焦慮感。比如,提到美女蛇的故事時,魯迅插入議論,“這故事很使我覺得做人之險”,“叫我名字的陌生聲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6],顯然這是有了豐富的戰斗經歷、背腹受敵后,魯迅對人事艱險的體驗。魯迅通過兒童視角盡顯自然之美、童年之樂,又以成人的全知視角道出了百草園后來的歸屬,客觀上抒發了成人懷念童年和故土的感懷,快樂中包含著惆悵。兩種視角之間沒有斷裂感,而是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升華了作品的精神高度,增加了作品的情感濃度。
《阿長與<山海經>》于輕松中也附著著沉重。比如魯迅一直在強調阿長“無名”。文章一開頭,魯迅就先講明阿長不姓長,“長”也不是形容詞,只因前一任女工名叫阿長,魯家的長輩們叫慣了口,于是她就默默地繼承了這個名字。在文章的結尾,成年后的魯迅懷念起長媽媽,深愧于始終不知道她真正的名字、經歷,僅知道她過繼過一個兒子,猜想她大約是青年守寡的孤孀。阿長就這樣籍籍無名地在雇主家勞動了十多年,她自己的姓名如同本人的命運一樣,淪為一片不被關注的黑暗的土地。名字不僅僅是一個稱謂,更是一種文化符號,彰顯著身份建構和身份認同。封建社會的婦女都處于“無名”的處境,她們沒有自己的名字,沒有獨立的身份和主體,在權力秩序中居于客體地位。“阿長”被命名,意味著她的存在價值首先在于作為勞動力的價值,而她自己的主體世界則無人問津。當然,這其中的沉重是兒時的魯迅無法意識到的,所以他會稚氣地在“憎惡”她時直接喚“阿長”。成年后的魯迅成為一名人道主義者,經歷家庭變故、生計艱辛等一系列曲折后,對勞動人民的生存處境產生深刻的認識,理解和親近底層勞動人民。文章全篇都未直接展現阿長的人生掙扎,但不動聲色地展示了這位底層婦女寥落的一生,傾注著魯迅深摯的同情和悲憫。
魯迅終于按捺不住內心的無限感懷,將深沉的情感都寄托到了文章的最后一句:“我的保姆,長媽媽即阿長,辭了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吧。我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懷里永安她的魂靈!”[7]魯迅在這里采用了為數不多的直抒胸臆式表達,雖保持著一貫的節制風格,但字字句句都凝結著無限深情。魯迅是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啟蒙主義戰士,肩負著破除蒙昧、開啟民智的使命,他對魂靈的有無一直持懷疑態度。不過魯迅愿意為了所愛之人“說假話”,他在雜文《我要騙人》中說過:“倘使我那八十歲的母親,問我天國是否真有,我大約是會毫不躊躕,答道真有的罷。”[8]魯迅雖不信鬼神,但他領悟了長媽媽對美好生活的祈愿,他愿意俯就她的思維,祝愿她的魂靈安息,或許這是唯一能做的對她的補償和報答。總之,魯迅以兒時的心態回憶阿長,同時以成人的眼光去反觀阿長的命運,但是第二層的意味含蓄而隱忍,滲透在文本的深處。通過兒童和成人的兩種視角,“我”與阿長的生命緊密聯系在一起。阿長偉大的母性為“我”的成長保駕護航,既帶來成長的“煩惱”,更帶來熱愛生活的溫情。與阿長相處的經歷構成了“我”日后親近底層大眾的情感基礎,隨著成年后具備了深厚的人道主義情懷,“我”進一步理解了阿長的命運,文本中便增添了理性的思索和沉重的懷念。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和《阿長與<山海經>》以兒童和成人的雙重視角敘述往事,兒童的稚氣語言和成年人的老到旁白相交織,揭示了一段重要的心路歷程。“兒童視角”為傳達魯迅“從記憶中抄出來的”內容,找到了一個最佳角度,使所述記憶取得了真實感和生動感。兒童的視野是一種“有限視野”,兒童的理解力也有限,留下了許多沒有說滿、說透的空白。于是,魯迅又設置了一個全知客觀的成人敘述者,隔著歲月的沉淀審視過去的“我”,以深沉、嚴肅、憂傷的語調,在自我對話中生發出深邃的思考。通過這兩篇課文的學習,學生可以跟隨魯迅的文章尋找其經歷過的生命痕跡,感受成長的苦樂百味中蘊含的溫馨,從而學會發現生活中的真善美,懂得珍惜成長所必經的每個人生階段。
參考文獻
[1]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87頁。
[2]周作人:《魯迅的故家》,《魯迅回憶錄·專著(中)》,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02頁。
[3]魯迅:《看圖識字》,《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7頁。
[4]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89頁。
[5]魯迅:《朝花夕拾·小引》,《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35頁。
[6]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88頁。
[7]魯迅:《阿長與山海經》,《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55頁。
[8]魯迅:《我要騙人》,《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505頁。
基金:泰山學院2021年度教師教育研究專項課題“課程思政背景下中學語文教學中的性別教育”(JY-01-202110);泰安市教育科學規劃專項研究課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視域下中小學性別教育研究”(TJK202106ZX013)。
(作者介紹:房存,文學博士,泰山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講師,主要研究中國現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