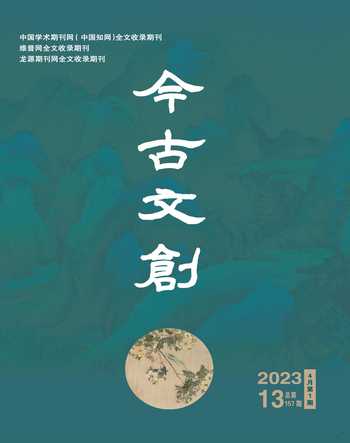余華小說的家庭書寫研究
孫雨琪
【摘要】 優(yōu)秀的文學(xué)作品脫離不了教育的深遠(yuǎn)本意。本文主要以家庭教育作為探究余華小說家庭書寫的理論立足點(diǎn)。在余華的小說中,余華將家庭教育與兒童的成長聯(lián)系起來,運(yùn)用了諸多敘事策略和寫作技巧,從家庭教育的角度書寫兒童的成長,突出體現(xiàn)了文學(xué)教育的功能。
【關(guān)鍵詞】余華;家庭書寫;成長;家庭教育
【中圖分類號】I206? ? ? ? ? ?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13-004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3.013
在閱讀余華作品的過程當(dāng)中,無論是余華的先鋒寫作時(shí)期還是后期的創(chuàng)作轉(zhuǎn)型時(shí)期,其內(nèi)容都涉及了大量的家庭書寫和對應(yīng)的人物,例如《一九八六年》中的歷史教師與妻兒;《河邊的錯(cuò)誤》中失去親人的家庭;《夏季臺(tái)風(fēng)》中受到臺(tái)風(fēng)影響的家庭生存;《十八歲出門遠(yuǎn)行》中的父親形象等。家庭書寫始終貫穿于余華作品的創(chuàng)作中,有助于我們從整體上研究其作品本質(zhì)。
一、余華小說的家庭教育
(一)兒童成長教育
教育是各類文學(xué)作品中不可避免的問題,并且在中國古代家庭教育被認(rèn)為是最為基礎(chǔ)的教育模式。在這種時(shí)代背景之下,家庭教育成了封建統(tǒng)治階級維持其統(tǒng)治的基礎(chǔ)工具.作為一種封閉的生產(chǎn)生活單位,家庭教育被抬升到了忠孝層面。實(shí)際上我國很多古典文學(xué)作品當(dāng)中就已經(jīng)涉及了家庭教育的內(nèi)容,例如,在《紅樓夢》當(dāng)中的賈政,一直希望自己的兒子賈寶玉通過科舉考試走仕途發(fā)展道路。
余華作為新時(shí)期的優(yōu)秀作家,他自然能夠意識(shí)到家庭元素對于兒童成長和發(fā)展的重要性,同理,余華在作品當(dāng)中也能意識(shí)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在其很多的小說作品當(dāng)中都包含著家庭元素,或多或少地涉及了家庭層面的敘事內(nèi)容,經(jīng)典的作品《活著》《兄弟》等都離不開家庭內(nèi)容的書寫,其中包含著豐富的關(guān)于家庭內(nèi)容。
要想了解余華小說的家庭元素,就需要了解余華對于兒童教育的看法和觀點(diǎn),從而進(jìn)一步把握其精神內(nèi)涵。在日常家庭教育當(dāng)中,他并不過分注重對孩子的苛責(zé)教育,甚至輔導(dǎo)自己的孩子時(shí),孩子的作文經(jīng)常拿低分,這并不代表他不注重兒童教育,恰恰代表了他對兒童教育有著獨(dú)特的理解和認(rèn)知。
余華的很多作品當(dāng)中都出現(xiàn)了有關(guān)孩子教育的片段,但需要注意的是,余華的這些作品并不能被稱為教育小說,只是在小說內(nèi)容中加入了家庭教育的模塊,強(qiáng)調(diào)的是長輩用言行去影響晚輩,使晚輩能夠從善如流。廣義上的家庭教育指的是父母對子女的內(nèi)部教育,而狹義上的家庭教育則指的是父母或家庭當(dāng)中的年長者對未成年兒童施加的意識(shí)影響,是一個(gè)單向輸出的過程。
各類研究的側(cè)重點(diǎn)的不同使得每個(gè)人對于家庭教育的理解和認(rèn)知存在差異,但余華的作品當(dāng)中卻涉及了很多兒童的成長經(jīng)歷,在作品當(dāng)中也有很多視角是從孩子的視角分析家庭教育的特性。在具體的作品寫作中,余華并沒有將家庭教育局限在某一個(gè)狹隘的范圍之中,而是將家庭教育和兒童的成長發(fā)展進(jìn)行有機(jī)聯(lián)系,并且塑造了一些經(jīng)典的兒童形象,包括《許三觀賣血記》中的三個(gè)兒子;《世事如煙》中被算命先生收養(yǎng)的孩子;《兄弟》中的李光頭;《死亡敘述》中被撞死的男孩和女孩等。這些兒童形象雖存在著比較大的差異,但是其具有的共同點(diǎn)都是未能接受正式的家庭教育。也正是因?yàn)榧彝ソ逃娜笔В沟眠@些兒童的經(jīng)歷都充滿著挫折,往往對應(yīng)的結(jié)果就是家庭悲劇的產(chǎn)生。
其實(shí)余華并沒有直接描寫家庭教育的方式,而是通過側(cè)面細(xì)節(jié)來呈現(xiàn)出家庭教育缺失對孩子可能產(chǎn)生的負(fù)面影響。兒童對于外在的世界并沒有正確的是非認(rèn)知觀念,他們的是非價(jià)值觀都來源于父母的耳濡目染,如果長時(shí)間受到家庭層面的畸形教育,必然會(huì)使得兒童的正常發(fā)展受到影響和阻礙。
在《一九八六年》這部作品中,女兒就忘記了自己的親生父親,也忘記了父親對自己的養(yǎng)育之恩,產(chǎn)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正是因?yàn)槟赣H錯(cuò)誤的價(jià)值引導(dǎo)和教育方式,才會(huì)使得女兒認(rèn)為父親非常陌生,又非常討厭,認(rèn)為自己的親生父親是“災(zāi)難”。
《我膽小如鼠》中的楊高家長,長期以來用自己的行為來限制楊高的行為,他的家長有極強(qiáng)的控制欲,這種畸形的成長經(jīng)歷也使得楊高開始變得柔弱內(nèi)斂和膽小怕事,面對他人的欺凌時(shí)唯唯諾諾,甚至不敢維護(hù)自己的尊嚴(yán),以至于6歲時(shí)不敢和其他人交談,8歲時(shí)無法一個(gè)人睡覺,12歲時(shí)甚至害怕鵝。
從這些悲劇形象當(dāng)中,我們不禁思考,如果這些孩子是現(xiàn)實(shí)當(dāng)中的孩子,他們的成長經(jīng)歷將多么悲慘,他們長大之后會(huì)成為一個(gè)怎樣的人呢?粗暴的教育方式,對于兒童的成長會(huì)產(chǎn)生毀滅性的影響,作為家長也應(yīng)該意識(shí)到這一點(diǎn)。
(二) 家庭教育反思
在作品當(dāng)中,余華從家庭教育的角度書寫了不同兒童的成長經(jīng)歷,說明他關(guān)注著兒童在家庭教育當(dāng)中的成長趨勢和個(gè)體的發(fā)展過程,他認(rèn)為,無論是心理還是生理層面,兒童應(yīng)該具備明確的自我意識(shí),能夠?qū)崿F(xiàn)自我價(jià)值,認(rèn)同自己的身份并順利融入社會(huì)生活當(dāng)中。
然而,余華的作品中卻有很多以悲劇收場的孩子,這些悲劇都說明家庭教育的缺失和不足,反而導(dǎo)致孩子出現(xiàn)了反成長現(xiàn)象。兒童被錯(cuò)誤價(jià)值觀所影響,他們甚至無法分辨自己的行為是對還是錯(cuò)誤。《現(xiàn)實(shí)一種》中的皮皮看到自己的堂弟倒在血泊之中,卻沒有絲毫的憐憫,甚至認(rèn)為那些從腦袋里流出來的血是一朵花。這種冷漠至極的狀態(tài)并不應(yīng)該存在于一個(gè)兒童的身上,但深究其原因正是因?yàn)槠てじ改搁L期具有暴力行為,久而久之使得皮皮自身也形成了漠視生命的心理。正因如此,他才會(huì)把堂弟視作玩具,并一手導(dǎo)致了堂弟的死亡。表面上是皮皮的個(gè)人行為引起了堂弟的死亡,但深層次原因卻是因?yàn)榧彝ソ逃笔鶎?dǎo)致,是父母的冷漠行為所產(chǎn)生的冷漠心理。
生理和心理層面的反成長傾向讓一個(gè)個(gè)兒童的成長經(jīng)歷都以悲劇收場,余華在敘述過程中,似乎在論述著家庭教育的錯(cuò)誤傾向,消極的家庭教育對于兒童成長會(huì)產(chǎn)生極其不利的影響,余華不是教育家,但他的小說卻比教育家的課程更具教育意義。
(三)家庭倫理觀念
在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家庭一直是一個(gè)非常重要的概念,談起家庭人們都會(huì)想到和睦和溫馨,在文學(xué)作品中則表現(xiàn)為夫妻和睦、兄友弟恭等,這對應(yīng)的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中國文學(xué)一直所追求的和諧統(tǒng)一。但實(shí)際上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家庭情況,卻并不一定父慈子孝和相敬如賓,傳統(tǒng)的家庭倫理觀念在文學(xué)作品當(dāng)中被抽絲剝繭也讓原有的和諧面具被徹底撕破,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夫妻倫理。家庭作為一種社會(huì)生活組織形式,以男女的婚姻關(guān)系為基礎(chǔ),并由婚姻關(guān)系為依據(jù),有夫妻之間的婚姻關(guān)系才誕生了家庭這一概念,但余華的作品中卻描述了很多夫妻不和諧的家庭悲劇。
《河邊的錯(cuò)誤》中,雖然婆婆是被瘋子毒打,但實(shí)際上瘋子的形象對應(yīng)的正是婆婆死去的丈夫的形象,讀者雖然沒有直接看到這一人物,但卻能夠從側(cè)面描寫當(dāng)中感悟到這一角色的殘忍和無情;《古典愛情》中的丈夫甚至不惜將自己的妻子賣給他人當(dāng)作“菜人”。易子而食尚且令人脊背發(fā)涼,妻子又如何甘心被他人所分食呢?但究其根本,卻是因?yàn)榛橐鏊`的家庭倫理使得所謂的倫理內(nèi)涵被無情諷刺,余華用文學(xué)描寫的方式將這些血淋淋的事實(shí)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此刻的家庭仿佛不是溫馨的港灣,而是冰冷的監(jiān)獄。
在余華的作品中,還有很多父子之間的矛盾描寫,甚至出現(xiàn)了父親殘害兒子的行為。《世事如煙》中的父親不惜以自己的子女作為延長自己壽命的工具,甚至賣出自己的子女換取錢財(cái);《南門》中的父親不分青紅皂白對自己孩子進(jìn)行毒打,在大庭廣眾之下讓自己兒子的尊嚴(yán)被踩在地上,無情踐踏,卻無法意識(shí)到自己孩子將伴隨著屈辱度過一生。我們從這些人物形象身上無法看到家庭倫理中應(yīng)有的長輩形象,這些人似乎已經(jīng)成為地痞流氓和潑皮無賴。余華的描寫雖然尖銳,卻為我們揭示了人性當(dāng)中最為丑陋的一面。
值得一提的是,余華的作品中,兄弟情分也同樣離不開家庭倫理觀念層面的破壞,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現(xiàn)實(shí)一種》當(dāng)中,皮皮和堂弟的關(guān)系就是一種畸形的兄弟倫理關(guān)系。年齡尚小的皮皮就懂得向自己的堂弟甩去一耳光,其殘忍并非這個(gè)年齡的孩子應(yīng)該有的行為。除此之外,皮皮對于堂弟的虐待由來已久,很難想象皮皮只有4歲。這個(gè)年齡的孩子應(yīng)該在生活中無憂無慮地天真玩耍,又因何成為殺害自己堂弟的兇手呢?正是因?yàn)榧彝惱淼姆磁驯浪尲彝惱硎チ似渖婧桶l(fā)展的空間,所謂的家庭倫理不過是令人哂笑的虛情假意。
二、余華小說家庭書寫的行文和敘事
(一)大量的反諷描寫
余華作品的家庭元素當(dāng)中運(yùn)用了諸多敘事策略和寫作技巧,其中反諷就是被大篇幅應(yīng)用的一種敘事策略,在講述各類故事時(shí)經(jīng)常是用一種看似正面的手法來呈現(xiàn)出反面的故事狀態(tài)。我們熟悉的魯迅先生就經(jīng)常使用反諷手法來描述小說的內(nèi)容,例如,敘述封建倫理制度對祥林嫂的迫害時(shí),以《祝福》作為小說標(biāo)題。余華也是利用反諷敘事策略的高明作家。《死亡敘述》當(dāng)中,“我”作為司機(jī)撞死了一名男孩和一名女孩,在撞死男孩還是無動(dòng)于衷,但是在撞死女孩之后,就因?yàn)閮?nèi)心的愧疚感,嘗試抱著女孩尋找他的家人,然而換來的結(jié)果就是女孩的家人用鐮刀和鋤頭來砍傷自己,最終倒在了血泊當(dāng)中。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第一次肇事逃逸沒有承擔(dān)任何責(zé)任,但第二次幡然醒悟卻換來的是生命的代價(jià),這就是一種經(jīng)典的反諷敘述,兩次相同的行為卻產(chǎn)生了強(qiáng)烈的反差,這是日常行為道德層面的一種極大諷刺,也是對生活常識(shí)的一種褻瀆。余華在小說當(dāng)中是以旁觀者的形象來描寫小說的情節(jié),并應(yīng)用反諷的手法來動(dòng)搖所謂的理性價(jià)值判斷,那些在生活當(dāng)中看似規(guī)整的秩序,在面對一些事件時(shí)卻無能為力。
(二)“生命”背后的發(fā)人深省
余華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強(qiáng)調(diào)了生命的重要性,強(qiáng)調(diào)要敬畏生命,熱愛生命,然而在描寫生命的背后,卻是一次次暴力和血腥,一次次苦難的經(jīng)歷和難以言說的委屈。余華的作品有著大量的悲劇色彩,他不厭其煩地?cái)⑹黾彝コ蓡T所遭受的苦難,實(shí)際上是為了突出整個(gè)社會(huì)的價(jià)值取向——沒有人逃得過悲劇的結(jié)果,生活的意義在于忍受苦難并克服苦難,才能對生命保持敬畏之心。
《許三觀賣血記》以一種激烈的描寫方式,表達(dá)了人在面對困境時(shí)的求生欲望。許三觀身無所長,無計(jì)可施,只能通過賣血的方式來挽救支離破碎的家庭。但屋漏偏逢連夜雨,這個(gè)家庭面對的困難一次次地折磨著許三觀,賣血的頻率也不斷增加。面對水災(zāi)需要賣血,在生日當(dāng)天為了能夠吃上一頓好飯需要賣血,兒子生病救治還是需要賣血。作為讀者,大家可能認(rèn)為文中的家庭過于悲慘,但對于文中的許三觀而言,他卻從未對生活失去希望,從未想過用死亡的方式一了百了。因?yàn)樗靼姿劳龅扔诹悖ド痛碇鴽]有走向幸福的可能。他是生活在社會(huì)底層的窮苦人民,他沒有文化,他沒有一技之長,他只有樸素的認(rèn)知,但卻能夠意識(shí)到生命的價(jià)值,始終對生命保持敬畏之心,這正是余華作品的巧妙之處。
(三)兒童主視角的敘述
在余華的小說里,他塑造的兒童形象可能跟成人世界甚至跟同齡人的世界格格不入,但他們擁有敏銳的目光、細(xì)膩的內(nèi)心、活躍的思維。余華賦予了他們洞悉一切的眼神和遠(yuǎn)遠(yuǎn)超過實(shí)際年齡的思辨意識(shí),在他們的帶領(lǐng)下與讀者一起探索一個(gè)真切的世界。
余華在作品中很喜歡用兒童的主視角來進(jìn)行內(nèi)容敘述,甚至全篇應(yīng)用兒童視角來進(jìn)行敘事,整個(gè)故事的呈現(xiàn)過程,都是以兒童的語言或口吻來講述,具有典型的兒童思維特性。與成年人相比,兒童的思維更加純潔而樸素,并不要考慮成人世界紛繁的秩序要求和利益糾葛,兒童視角觀察到的生活,往往能出淤泥而不染。在這一方面余華與魯迅先生有著異曲同工之處,魯迅先生也善于利用兒童視角來描述成人世界的丑惡和荒誕。
《在細(xì)雨中呼喊》中,“我”的絕食抗拒招致養(yǎng)父王立強(qiáng)的羞愧和憐惜,他帶“我”去吃最貴的三鮮面。小小的“我”明明馬上就吃飽了,但因?yàn)樽⒁獾脚赃呉粋€(gè)吃著廉價(jià)小面的老人正在覬覦“我”碗里的雞塊和鮑魚,于是刻意在他面前頻頻把它們夾起來又放下。膩煩這種游戲后,“我”想到了一個(gè)更“殘忍”的新游戲,假裝在他眼前威風(fēng)凜凜地離開,實(shí)際上是在發(fā)現(xiàn)他吃完剩下的面后再佯裝返回,故作詫異地看著桌上的空碗。老人的忸怩不安恰恰中了“我”的詭計(jì),得逞后的快意甚至超越了昂貴面條帶來的心理愉悅感。
《現(xiàn)實(shí)一種》看似是描寫皮皮對堂弟的虐待行為,但深入思考后,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皮皮會(huì)產(chǎn)生這樣的行為呢?答案正是他的父親經(jīng)常這樣對待他的母親,所以在潛移默化當(dāng)中,皮皮認(rèn)為自己毆打堂弟是一種理所當(dāng)然的正常行為,所以人們才會(huì)從兒童的視角了解到成人世界的不堪一面。在成人世界的壓迫之下,這些本應(yīng)該天真無邪的兒童不得不面臨社會(huì)染缸的漂染,成人世界的麻木和冷漠使兒童也變得渾身帶刺,這是一種黑色幽默,但幽默的背后卻是殘忍,是令人深思。
當(dāng)然在余華的后期作品當(dāng)中卻出現(xiàn)了一些溫和的家庭描寫,大概也是作者本身認(rèn)為,這才是兒童和家庭應(yīng)該呈現(xiàn)出的樣子,這才應(yīng)該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背景下的人際關(guān)系模式。
三、結(jié)語
余華的作品大量選取家庭作為寫作對象,以家庭作為切入點(diǎn)來描述家庭背后的深層次內(nèi)容。在他的筆下,家庭倫理仿佛是隨風(fēng)而散的蒲公英,患難與共的真情不過是令人唾棄的虛情假意。難能可貴的是余華并沒有局限于家庭教育,而是以家庭教育作為切入點(diǎn),分析了家庭教育和兒童成長之間的關(guān)系,分析了家庭教育和生命價(jià)值之間的關(guān)系等。我們需要正確認(rèn)識(shí)到家庭的價(jià)值,也應(yīng)該在面對苦難時(shí)敬畏生命,這是對文學(xué)教育功能的一種認(rèn)可,也是對文學(xué)作品的尊重。
參考文獻(xiàn):
[1]戴圣云.論余華小說的家庭書寫[D].浙江師范大學(xué),2019.
[2]郭志勇.余華小說《許三觀賣血記》的小人物形象分析[J].中國民族博覽,2021,(18).
[3]樸燕淑.試論余華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形式[J].遼寧師專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9,(06).
[4]李婷.論余華小說的兒童視角[J].吉林廣播電視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