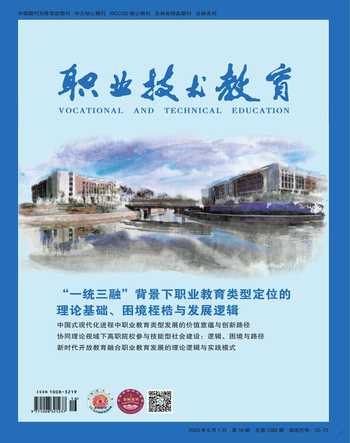社會學視角下我國職業教育類型定位分析
摘 要 職業教育是教育系統的子成分,是與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類型,其類型定位確立和強化的關鍵在于職業教育子系統與社會系統協調發展。立足于社會學視角,職業教育類型定位確立的必要性在于,社會系統功能穩定需整合協調職業教育子系統,社會權力爭奪沖突引發職普教育分流焦慮,社會運轉下職業教育交換權日益式微,社會大眾固有的職業教育刻板印象阻礙社會變遷發展。其類型定位確立的依據在于,職業教育承擔社會分工下各層次技術技能人才培養功能,在社會地位、權力與資源分配的沖突疏解中發揮“社會安全閥”部分職能,可促進社會個體通過人際互動獲取價值資源,并通過重構職業教育社會形象推動其賦能增值。為進一步優化職業教育類型定位,需協調好職業教育內外系統,構建與普通教育協調發展的職業教育體系,提高技術技能人才社會地位和政策待遇,提升職業教育社會認可度。
關鍵詞 職業教育;類型地位;社會學;結構功能論;沖突論;社會交換理論;印象管理理論
中圖分類號 G71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23)16-0020-07
作者簡介
黃曉鈿(1998- ),女,華東師范大學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職業教育(上海,200062)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重大招標課題“職業教育類型特征及其與普通教育‘雙軌制‘雙通制體系構建研究”(VJA200003),主持人:匡瑛
我國國家層面一直高度重視職業教育發展,但長期以來,職業教育被視為普通教育層次下的“次等教育”,其教育定位模糊。直到2019年國務院印發《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第一次在政策文件上明確“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教育類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022年在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中首次以法律明確了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隨后黨的二十大報告也提出要“優化職業教育類型定位”,進一步確立了職業教育在國民教育體系中類型教育的戰略定位。職業教育類型定位確立是否有其必要性?其教育類型特征體現在何處?如何促進職業教育類型化發展?職業教育作為與社會聯系緊密的教育類型,其類型屬性可以從社會學的視角進行解釋。
首先,從結構功能主義視角出發,社會是具有一定結構或組織化形式的系統,構成社會系統的職業教育系統與其他社會子系統保持相對穩定的關系,其中職業教育面對社會分工下各層次技術技能人才發展的需要,通過師資結構優化、專業設置緊密對接產業更新等結構性調整強化職業教育的社會功能。其次,從沖突論視角看,社會各部門在社會系統運作時不可避免產生沖突,人們對社會地位、權力、價值和資源的爭奪體現在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上,可通過提高技術技能人才地位、增強職業教育適應性強化職業教育“社會安全閥”職能。再次,從社會交換理論視角看,社會系統內部各子系統的交互協調能有效促進能量和資源的流動,職業教育子系統與其他系統通過提供個體相應的政治、經濟、社會機會和保障等交換權利,推動系統內部個體獲取所需的價值資源,滿足其社會需求。最后,從印象管理理論視角看,社會大眾通常會對某一社會角色產生特定的主體印象和價值期望,積極的印象管理可轉化為可持續的正面價值期待,并潛移默化地影響他人的后續態度和行為,職業教育現有負面印象可通過印象管理進行轉化重構,增強其社會認同度。本研究立足于社會學視角,探析社會系統運作下職業教育功能發揮、權力運行、系統間互動交換及印象建構,明確其類型特征,進而提出推進職業教育類型化的發展路徑。
一、社會學視角下職業教育類型定位確立的應然之意
職業教育是一個由諸多要素構成、具有開放性的復雜系統。從內涵上看,職業教育具有多層次的體系架構,包括各層次教育組成、內部學科專業構成、教育資源分布、人才培養層次和組織辦學體制;從外延上看,職業教育與社會經濟系統、普通教育系統、社會互動系統等子系統聯系緊密,尤其在教育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職業教育類型定位的確立必然受到多方牽引。
(一)社會系統功能穩定需整合協調職業教育子系統
結構功能論是社會學的經典研究理論,其典型觀點是帕森斯提出的社會行動系統AGIL四大功能模型,分別是適應、目標達成、整合和潛在模式維持四大功能[1]。人類社會系統是由多個子系統組成,這些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共同促進了人類社會的協同發展。職業教育系統是社會技術技能人才培養與相應人力資本輸出的主要陣地,作為社會系統中相對獨立的子系統,其教育結構、系統內部各層次教育目標、相應教育資源整合及文化價值觀念持續穩定影響其功能的正常發揮,同樣也影響和制約著社會整體的穩定發展[2]。第一,從系統適應功能上看,當下我國已然建立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職業教育體系,但反映在社會勞動力市場上,一方面存在大量學生“結構性失業”,另一方面大量企業“招工難”“用工難”,其根源在于職業教育層次和專業結構與社會需求結構脫節,同時職業教育與社會人才需求信息不對等現象突出,職業教育發展缺少靈活性,遠遠滯后于時代發展,培養人才的規模、質量、規格等難以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第二,從系統目標達成功能上看,當下我國職業教育正在探索建設從中等職業教育、高等職業教育到本科層次職業教育全覆蓋的完整教育體系,但在具體確定怎樣的知識和技能水平是初級、高級亦或是高層次上,各層次教育界定和相應培養規格表述模糊,難以制訂相應培養目標,進而導致人才培養適應性不足。第三,從教育系統整合功能上看,我國職業教育體系受政府管控,教育資源調配上分屬教育或人社部門管理,多方利益驅動下職業教育管理容易出現政出多門、職能交叉乃至混亂等現象,系統內部資源難以形成合力,同時職業教育本身與社會發展聯系密切,亟需全面、客觀且更新速度快的行業發展趨勢等信息資源,系統內部與外部社會環境資源缺乏暢通的溝通合作機制,校企合作也缺乏長效機制,難以實現資源充分整合。第四,從教育系統的潛在模式維持功能上看,職業教育具有職業性,為社會培養了大量高層次技術技能型人才,其在各個行業上發揮著重大作用,但受功利主義的影響,教育過程中更關注個體技術技能的培養,忽視精神文化方面的建設[3],缺乏人文素養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使學生價值取向偏向功利性,進而導致職業教育系統共同的價值理念偏移,使得其潛在模式維持功能日益衰弱。
(二)社會權力爭奪沖突引發職普教育分流焦慮
社會沖突是社會發展中不可避免的現象,源于社會各部門在社會系統運作時不可避免存在功能失調積累而成的社會矛盾或是不平等。達倫多夫從辯證的角度分析社會沖突本身是社會的普遍存在,這是由于社會始終處于變遷之中,沖突是變遷的根本動力[4]。科賽認為,有關社會地位、權力、價值和資源的斗爭,表現為不同的利益群體互相競爭進行資源爭奪,目的在于社會權力爭奪,具有強烈的動蕩性和破壞性[5]。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對社會個體科學文化知識和技術技能水平的要求也在不斷提高,推動現代社會教育更加制度化、正規化發展,加上人們對教育的追求向高學歷發展,促進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也形成了以人的受教育程度或受教育質量衡量其能力和作為人才選撥標準的傾向,即追求高學歷的文憑社會。教育資源的有限性和個體的差異性決定了教育承擔著社會人才選撥功能,一方面通過教育“提取”“篩選”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另一方面也通過教育重新進行社會“分層”,即學歷教育文憑是個體實現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重要憑證,而職業教育作為培養技術技能人才的教育面對的爭議不斷加劇,其在促進個體社會流動方面的功能減弱。職業教育培養人才的社會地位和職業聲望相比學歷教育較低,在社會權力、地位和資源等爭奪中逐步被邊緣化。職業教育似乎與文憑社會產生了互相割裂、不可調和的矛盾沖突,即進入職業教育似乎未來就業框定在體力勞動,意味著失去階層躍升至更高社會通道的機會,職業教育的社會吸引力大大下降[6],也使得許多關于社會權力、地位、經濟、勞動就業、福利制度保障的矛盾轉嫁到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上,即職普教育分流產生的社會焦慮實質上是社會權力爭奪沖突的體現。
(三)社會運轉下職業教育交換權日益式微
社會運作需要各個子系統進行相應的能力、資源等社會交換行為。在社會交換中,職業教育具有重要的社會價值和功能,是社會整體教育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但在具體政策規劃或落地實施中,職業教育應有的社會地位總會因各種現實因素或規則制約而不斷下降,使得職業教育被框定在一種低層次、低水平的辦學格局中,被人為地或制度化地剝奪或限制了職業教育的所有權和交換權利[7]。首先,在社會經濟交換功能上,職業教育在市場中的資源交換與行業企業發展具有直接的利益相關關系,即職業教育培養人才對接行業企業的輸送率、技術迭代更新頻率和產教融合的深度關系到其與市場的資源交換價值,我國職業教育在這方面傾向學習普通教育辦學和管理模式,加之受功利主義影響,追求短期快速適應就業的職業培訓,忽視個體隱性職業能力和文化素養的發展,難以適應日新月異的行業和企業發展需求,在就業市場中缺乏足夠的交換資本。其次,在社會交換保障上,我國職業教育相比普通教育“淪為”低層次教育,缺乏足夠吸引力的一大原因在于其對個體未來就業發展上缺乏交換價值,個體通過接受職業教育所獲得的能力和身份表征并未給予其足夠的權益保障和交換權利,盡管從就業規模上職業教育已然是支撐我國勞動力市場的支柱,但職業教育相關人群在就業過程中的人事招聘、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方面缺少對其權益的保護。最后,在職業教育自身資源交換權利上,許多職業院校存在辦學條件和水平較弱,接收生源質量低等問題,內部學習氛圍不足,缺乏發展動力,許多職業院校師生對未來缺乏信心,甚至在內部默認職業教育天然低于普通教育的觀念,而“自我貶低”下的職業教育“消極認知”不可避免影響到人們“主動選擇”和利益相關者“主動投資”的意愿[8],使得職業教育自身所有權和交換權益日益式微。
(四)社會大眾固有的職業教育刻板印象阻礙社會變遷發展
隨著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和新一輪科技革命進行,生產力的發展推動著社會不斷進步,傳統產業結構快速變化引起勞動力與經濟結構重新配置,推動著現代職業結構分化、職業內涵精細化、職業層次上移、職業技術性增強,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在勞動力市場供不應求。教育作為社會系統的重要組織部分,在社會快速變遷發展中要跟得上時代發展,職業教育的本質在于對接行業企業,以培養其所需的技術技能型人才,其發展已然成為社會關注的重點。但社會大眾對職業教育的認知存有偏見和傳統刻板印象,這是由于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往往會受信息傳播和解釋過程中歷史與傳統各種經驗觀念的影響。刻板印象是指對一個群體特征進行過度抽象時產生的,我國傳統便有“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價值取向,職業教育面向職業,盡管職業無貴賤之分,但社會大眾“學而優則仕”的觀念早已根深蒂固,加上當下中考教育分流機制和高考梯次錄取機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外界為職業教育貼上“差生教育”的負面標簽,這個標簽隨著社會交流互動的深入,在職業教育畢業生后續就業質量水平較低的情況下進一步固化,使得“職業教育”隱含的社會符號化意義被“污名化”[9],其社會印象管理效益較差。印象管理是基于社會符號學發展而來,社會學家戈夫曼基于社會互動情境和人際背景等要素,提出公眾往往會自發地對某一社會角色生成特定的價值期望和價值義務,印象管理者通過利用此規律可進行自我形象調適,以期對方形成自身期待的印象預期和印象狀態,并在相應價值交換規律影響下,采取符合印象管理者期待的行動[10]。積極的印象管理能轉化為可持續的正面價值期待,并潛移默化地影響他人的后續態度和行為。社會大眾對職業教育的消極認知嚴重影響了個體的教育抉擇和教育滿意度,職業教育吸引力不足不僅導致生源質量不佳,還會影響職業教育自身發展,形成職業教育消極形象不斷惡性循環的現象,阻礙社會變遷發展。
二、社會學視角下職業教育類型定位確立的邏輯依據
從社會學視角對職業教育類型定位進行分析,更能把握職業教育在社會運轉下如何實現其結構功能、如何在社會沖突下找到發展平衡點、如何與各個子系統進行權力交換、如何塑造進而改善其社會形象,本研究基于此分析職業教育社會化的類型特征。
(一)結構功能主義視域下,職業教育承擔社會分工下各層次技術技能人才培養的功能
社會系統運行的核心在人類的社會實踐,社會實踐由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構成,基于結構功能論分析社會秩序和社會各系統間結構、功能間的聯結可知,社會系統要維持自身的運行、保持社會秩序和社會團結就需要對社會成員和其崗位工作進行合理配置,即進行社會分工以便最大程度發揮社會功能。社會分工產生了以科學知識理論為核心的腦力勞動和以技術技能操作為核心的體力勞動,催生了不同的工作崗位,由此產生了對于技能類型人才的不同需求。教育作為社會發展的產物,本質功能是培養人才,社會需要什么人才,教育系統相應地就培養什么人才參與社會實踐,隨著社會工業化程度的提高,科技發展和進步需要堅實的產業基礎,社會對技術技能人才的要求不斷提升,職業教育能夠滿足社會系統對技術技能人才的功能需要。可以說,社會實踐中認識世界需要教育系統以科學的知識理論培養學術性人才,改造世界需要教育系統以技術體系培養技術應用型技能人才,這是兩種不同的教育,其人才培養目標、職能和培養方式各有不同,由此形成了當下以學科知識為核心的普通教育和以技術技能為核心的職業教育[11]。職業教育系統在社會系統中承擔著對社會人群“職業化”的功能,其通過對技術技能人才的培養會直接或間接影響社會經濟發展并整合獲取相應的資源,與社會經濟環境相互適應,實現其結構在系統中的目標功能。同時,職業教育本身具有職業性和教育性,職業性體現在其具有較強的職業針對性,教育性體現在以文化知識傳遞塑造人的價值觀,通過職業教育進行社會職業精神的生產,發揮其促進社會協調整合的功能,以共同的價值觀凝聚力量,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12]。因此,在結構功能主義視域下,職業教育系統承擔著社會系統中培養各層次技術技能人才的重要功能,其與普通教育系統同樣承擔著對人才教育的社會化功能,兩種教育有類型定位而無地位高低之分,在社會人才培養中具有自身獨特的類型定位。
(二)沖突論視域下,職業教育在社會地位、權力與資源分配的沖突疏解中發揮“社會安全閥”部分職能
職業教育是與社會和產業經濟聯系密切的教育類型,其涉及的利益群體層級類型復雜多樣,不同利益群體針對社會地位、權力、價值和資源進行斗爭是產生社會沖突的根源,占據有利地位的階層為長期持有更多社會資源與機會,試圖運用權力壟斷其他階層上升機會和通道[13]。教育本質上是培養人的活動,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普通教育培養學術性人才,職業教育培養技術性人才,兩者通過對人才的分流也可以視作一種社會階層再生產的工具[14],使得社會不同階層代表下不同職業群體間的地位、職業聲望差異和不平等的沖突轉移至職普教育。疏解社會沖突的關鍵在于“社會安全閥”。“社會安全閥”源于鍋爐里的過量蒸汽通過安全閥適時排出而不會導致爆炸,這是在不毀壞社會結構的前提下釋放對立情緒以維持社會整合的安全機制。職業教育系統與普通教育系統間的沖突本身應該得到社會正式承認,通過專門的機構來調節和管理沖突,使其制度化。沖突本身是兩個同等單位力量間的沖突,力量均衡的沖突可以相互調節促進各自關系,允許沖突不滿的存在和表現,能讓社會大眾各種焦慮情緒得到釋放,獲得某種心理上的安慰[15]。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作為兩種不同類型的教育,通過對知識和技術的提取進而分層所實現的社會流動的確是合理且合法的形式,這也是教育“社會安全閥”功能的體現和表征。而從權力、資源分配上看,職業教育通過向勞動力市場提供具有市場需求的技能和專業知識,為個體獲取優質資源提供途徑,改善社會資源分配效率和公平性,減少資源分配沖突。同時,從個體教育需求上看,職業教育可以促進個體技能的形成和社會流動,也就是說個體通過職業教育積累人力資本,為個體進入特定職業領域提供通道,尤其是針對在社會競爭中本身處于劣勢地位的個體,通過技術技能培養可提升個體的社會參與能力[16],一定程度上促進個體社會流動,緩解社會地位沖突。盡管相比同級教育,職業教育對個人社會權力地位的提升并不具有明顯優勢,但從經濟社會發展角度來看,產業轉型升級下對人才技能素養提出了新要求,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缺口不斷擴大,推動著各國政府紛紛開啟各項產業振興計劃,提高技術技能人才社會地位,促進職業教育自身定位、人才培養向著科學化方向不斷發展。因此,對于職業教育而言,需要發揮其教育優勢,主動增強教育適應性,使職業教育端人群能在平等條件下獲得相應社會資源,擁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和可能性,發揮其“社會安全閥”職能,以疏解社會沖突。
(三)社會交換理論視域下,職業教育促進社會個體通過人際互動獲取價值資源
布勞、霍曼斯從微觀層面個體日常往來和人際互動推導出支配著整個社會復雜結構的社會過程,結合與現代行為學派和經濟學派理論分析,認為人類的社會活動都可歸結為一種交換行為,其在社會交換中形成的社會關系本質上也是一種交換關系,個體往往傾向于以較小代價或者付出交換更多的利益和回報[17]。個體間的交往關系奠定了集體關系的基礎,社會系統與其絕大多數成員并沒有直接的社會互動,主要是通過其他機制性的間接交換以協調成員間的社會關系結構,個體在社會交換所處地位的不同會導致資源壟斷的不平等交換,相應交換利益的不平等導致了社會權利差異和社會分層現象[18]。基于社會交換理論視域,職業教育被視為社會交換的場域之一,通過為個體提供相應的政治、經濟、社會機會和保障等權利,推動個體參與社會交換、獲取價值資源[19]。關于其政治層面的交換權利,我國已從法律層面確定了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同等的類型地位,并在2021年出臺的《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中強調職業教育是“國民教育體系和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提高職業教育參與決策的程度,穩固其政治地位。關于其經濟層面的交換權利,接受職業教育個體的專業對口程度、知識技能儲備以及個人綜合能力直接影響著其在市場環境中行業企業的資源交換,行業企業通過職業教育培養人才提供的生產力獲取更高的經濟資源。關于其社會機會層面的交換權利,這里更多的是指職業教育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認可度,外界對職業教育的積極認知推動個體或組織團體主動參與社會交換,職業教育自身正確的認知會激發其內驅力影響其對外交換動力。關于其社會保障層面的交換權利,職業教育作為面向職業和就業的教育類型,通過參與職業教育并取得相應水平的職業技能和資格,個體能獲得與之相應的能夠滿足其生存甚至更高層次需求的資源。基于此,國家應對職業教育提供并貫徹落實制度性保障機制,為其社會交換提供堅實支撐。
(四)印象管理視域下,重構職業教育社會形象以推動其賦能增值
職業教育社會形象是社會大眾對職業教育本身存在、內部教育和運行表現的總體印象和綜合評價,反映了職業教育與社會公眾間的關系。社會對職業教育的印象體現了職業教育的實施效果,職業教育基于社會評價獲得的反饋可進一步改進和優化教育實施[20]。職業教育是使受教育者具備從事某種職業或者實現職業發展所需的技術技能、科學文化與專業知識、職業道德等職業綜合素質和行動能力而實施的教育[21],其本質是對技術技能人才就業發展的教育,與職業教育實踐教育相適應的“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校企合作產教融合辦學機制、學歷教育和職業培訓并舉的辦學格局等,是社會公眾對職業教育社會角色的價值期待和印象體驗。只有提高職業教育辦學質量,切實提高技術技能人才的就業競爭力和社會待遇,發揮其應有的社會角色效應,打好品牌形象地基,才能推動職業教育社會價值得到普遍認可。除了關注職業教育內部形象外,外界對職業教育形象的認知關系與社會需求能否得到滿足緊密相關。新中國成立初期,對技工等技術人才的需求和重視提高了職業教育的社會認可度,而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職業教育在學歷文憑上的象征意義并不具備競爭力,卻并不影響個體為追求“一技之長”選擇職業教育,可見職業教育社會形象本身是可重塑的,評價主體先前經驗和社會觀念因素是一部分,職業教育招生就業宣傳和公眾輿論媒體報道是一部分,其認知偏見是基于功能特征而來,同樣也是可轉變可優化的。因此,明確職業教育的結構功能定位,應緊跟時代步伐、社會需要和公眾教育期待,增強職業教育適應性,推動職業教育賦能增值。
三、社會學視角下優化職業教育類型定位的路徑
(一)完善職業教育內部層次結構,協調職業教育內外系統
根據結構功能理論,結構是功能的基礎,功能發揮依賴于結構,兩者具有緊密的關系,正如職業教育系統,其功能的發揮取決于結構的組成。當前,我國職業教育層次結構存在設計缺位、銜接錯位、定位不清等問題,影響其人才培養目標實現、各項資源整合和模式維持等功能的發揮,需進行系統整體功能調適,即一方面要相互協調內部各結構要素,另一方面要與外部各個系統協同發展。第一,要調整職業教育結構以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在專業、層次和規模上必須積極主動與社會環境保持密切聯系,引導鼓勵職業教育機構根據區域社會經濟發展、行業發展和自身優勢自主確立辦學定位和專業設置,同時加強職業教育與社會供需信息反饋機制,增強信息互通。第二,要適應社會系統發展,明確各層次職業教育的定位,中職教育定位于培養實操型技能人才,高職教育定位于培養應用型技術性人才,本科層次職業教育定位于培養管理型、工程型和應用型高級專門人才,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定位于培養高層次應用研究型專業人才。第三,要加強職業教育各項資源的整合,當下職業教育管理部門混亂,可從政令規范性和統一性出發,由教育部門統一管理職業院校,人力資源保障部門負責管理職業技術資格認定、相應資格證書的頒發事宜,并指導行業、企業參與職業資格標準的制定,加強校企合作長效機制構建,使企業成為職業教育的主體之一, 提高職業教育資源的利用率。第四,要加強職業教育精神文化建設,涉及到職業教育在長期教育過程中形成的辦學理念、校園文化、職業文化、企業文化等軟性因素,也包括相應職業規范、校園規章制度等硬性因素,在加強校園文化建設并與企業文化對接的同時,強化“以人為本”“以生為本”的價值理念,充分尊重個體成長,引導職業教育實現可持續發展。
(二)促進職普融通,構建與普通教育協調發展的職業教育體系
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是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下我國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是從過去被視為教育層次向作為教育類型轉變,但物極必反,若過分強調職業教育作為獨特的類型化教育體系,完全割裂職普教育,由于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在提供升學、就業機會以及薪酬待遇方面差距甚遠,自然導致優質生源向普通教育單向流動,進一步激化社會沖突。因此,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并非將其獨立于教育大系統內,而是在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同等地位下擁有同等的發展機會和平臺,以制度化的手段化解職業教育在社會系統中的矛盾和沖突。現代職業教育體系作為國家層面對職業教育發展的基本架構設計,實際上包含了職業教育類型、層次、發展形態、縱橫向及教育系統內外間等關系。通過發展多種層次和形式的職業教育,促進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相互融通,暢通職業教育內外部銜接通道,形成橫縱貫通的人才培養體系,實現職普從起點、過程到終點的系統融通,即從職普招生上同等對待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學生學籍,實現兩類考生的學籍或資格互認,并完善教育過程中兩種不同類型學生的雙向流動,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通過聯合制訂人才培養目標、設計課程體系、互派師資、共享資源等途徑,實現課程互選、學分互認、學籍互轉、學生互動,構建其合作發展機制,充分給予學生多元教育選擇機會。同時完善具有職業教育類型特征的考試招生制度,創新縱向貫通機制,推進“職教高考”制度,并建構與生源數量和質量相適應的高等學校招生計劃分配機制,積極探索從“中職—高職—職業本科—研究生教育”的完整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滿足學生掌握更高技能、獲得更高學位的教育需求,破解學歷社會下職業教育向上發展瓶頸,化解職業教育在社會系統中的矛盾和沖突。
(三)保障職業教育交換權利,提高技術技能人才社會地位和政策待遇
保障職業教育交換權利,提高技術技能人才的社會地位和政策待遇,是促進職業教育發展和滿足勞動力市場需求的重要舉措,關鍵在通過政策層面的調整,實現職業教育權利平等、機會平等和人格平等。首先,在于職業教育政治權利的保障上,一方面,通過國家政策干預,合理分配社會財富,保障各崗位勞動者的權利,激勵更多人選擇職業教育;另一方面,在政策層面確保職業教育同等的教育類型地位,即職業教育應享有平等的人才選拔權利、辦學自主權利,注重教育資源科學合理的配置,通過建立科學合理的人才選拔機制和標準,尊重個體的教育自由和天賦,同時職業院校應該明確自身的辦學目標和定位,發展多元化的辦學模式和格局,提高辦學質量水平,并完善人才評價標準體系。其次,在職業教育經濟權利的保障上,加強職業教育與行業企業各項資源的交換,借助行業企業的力量,共同建設新的專業、開發新的課程,實現職業院校育人模式的革新,同時緊跟我國產業鏈發展的趨勢,為建設技能型社會奠定基礎。再次,在職業教育社會機會層面的交換權利保障上,營造崇尚技能的社會文化,擴大對職業教育發展、大國工匠、勞動模范等主題的正面輿論宣傳,樹立“崇尚技能、人人皆可成才”的多樣化人才觀。最后,在職業教育社會保障交換權利上,改革傳統的人事管理制度,優化技能人才的職業發展通道,并完善工資結構和激勵機制,尊重技能人才的技術技能價值,真正實現其價值的體現和社會地位的提升。
(四)重構職業教育社會形象,提升其社會認可度
職業教育社會形象是基于自身實踐和社會發展,由社會大眾主觀感知、評價和情感構建而成,是一個不斷演化和調整的過程,反映社會大眾對職業教育的認知和期望,并對職業教育發展和社會認可起重要作用。當下職業教育存在社會形象與其對經濟社會的貢獻不相匹配、自我認同與社會大眾認知差異巨大、相關從業者與非從業者感知差異較大等問題。為促進職業教育功能發揮和目標實現,職業教育需進行補償性自我呈現來重構其社會形象,重點在于突出職業教育的“職業性”和“教育性”本質特征,盡可能脫離大眾偏見所形成的狹隘情景認知,加強自身積極印象管理,消解職業教育原有的消極教育標簽,進一步引導社會大眾建立對職業教育的價值期待。一方面,職業教育要真正提高社會認可度和社會地位,關鍵要有切實的育人成效,應加強內涵建設,明確自身與普通教育類型區別的基礎上,立足于經濟社會發展現實需要,堅持技術技能人才培養的辦學定位,服務于產業結構轉型和產業鏈現代化,突出自身品牌特色,正確把握受教育群體、行業企業、教育舉辦方等利益群體的不同需求,即滿足職業教育學生對未來前途發展的期待,改善人才培養供給側與產業需求側匹配度,以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推動時代發展。另一方面,社會文化價值理念是職業教育自身形象構建的重要資源,其滲透于社會大眾心理、思維模式和日常行為中,新時代呼喚“勞動光榮、技能寶貴、創造偉大”的時代強音和價值認同,需要關注職業教育文化中的核心價值觀念,強調技能的重要性和勞動的尊嚴,傳承工匠精神,弘揚工匠精神中堅韌、專注和追求卓越的品質,構建支撐工匠精神的社會文化體系,同時在經濟和政治方面采取相應的政策以切實提升廣大技術技能勞動者的社會地位和勞動回報,打好職業教育發展認同的社會基礎。
參 考 文 獻
[1]帕森斯,斯梅爾瑟.經濟與社會[M].劉進,林午,李新,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16.
[2]宮麗麗,張安強.基于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的中國特色現代學徒制探析[J].教育與職業,2018(1):25-29.
[3]肖鳳翔,董顯輝.基于AGIL模型的職業教育發展分析[J].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4)339-343.
[4]拉爾夫·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著.現代社會沖突[M].林榮遠,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16-17.
[5]科塞(Coser,A.),著.社會沖突的功能[M].孫立平,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24-33.
[7]劉云波,張葉,楊釙.職業教育與個人的社會地位獲得——基于年齡與世代效應的分析[J].教育研究,2023(1):128-143.
[7][8][20]李興洲,趙陶然,王魯藝.論職業教育的交換權利——兼論職業教育“同等地位”及其實現路徑[J].教育發展研究,2022(9):38-44.
[9]李洪榮.高等職業教育身份歧視現象論析[J].江蘇高教,2021(10):57-60.
[10]歐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M].黃愛華,馮鋼,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9-13.
[11]孟景舟.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關系的歷史演進[J].職教論壇,2011(31):4-8.
[12]胡德海.論教育的功能問題[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2):8-14+107.
[13]張翼.中國城市社會階層沖突意識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05(4):115-129+207-208.
[14]皮埃爾·布爾迪厄,J.-C.帕斯隆.再生產——一種教育系統理論的要點[M].邢克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49-97
[15]PHILLP BROWN.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igh skills[J].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 1999(3):235.
[16]沈兵虎,王興,顧佳濱.增強職業教育適應性的若干關鍵問題[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22(1):60-66.
[17]EMERSON R.Social exchange theory[M]//in ROSENBERG and R.TURER (eds) . 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Basic, 1981:31-34.
[18]布勞.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M].孫非,張黎勤,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70-135.
[19]王劍.社會交換理論視角下職業院校教師企業實踐困境與對策分析[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16(7):73-77.
[21]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EB/OL].(2022-04-21)[2023-05-10].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jyfl/202204/t20220421_620064.html?eqid=eb0926c80009b67000000006642ea00b.
Analysis on the Type Orient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Huang Xiaotian
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 sub-component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which is as important as general education. The key to establish and strengthen its type position lies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ubsystem and social system. Based on th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makes clear the necessity of establishing the type orient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stability of social system functions requires the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ubsystems, the conflict of social power struggle causes the anxie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iversion, the exchange righ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declining under the social operation, and the inherent stereotyp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the public hinders the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By analyzing its type orient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takes the function of cultivating technical and skills talents at all levels under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plays a part of the function of “social safety valve” in resolv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social status, power and resource distribution, which can promote social individuals to obtain value resources through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promote their empowerment and appreciation by reconstructing the social imag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type orient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ystem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uild a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hat is coordinated with general education, improve the social status and policy treatment of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and enhance the social recogni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type status; sociology; structural function theory; conflict theory; social exchange theory; impression management theory
Author? Huang Xiaotian, master candidate of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dult Education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