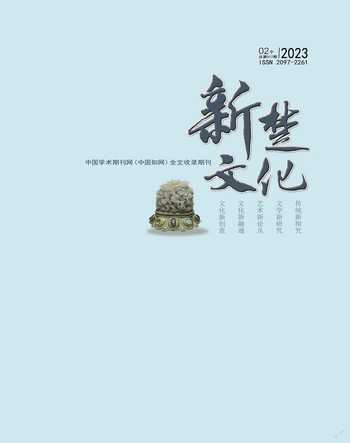文學作品中食物與華裔文化身份認同探究
熊芷璐
【摘要】長期以來,華裔群體一直面臨著文化身份認同的難題,因此文學作品中,人們常常將“食物”視為一種重要的象征和意象,以此來尋求對自身文化身份的認同,使得文學作品中的食物既有一種物質特征,又具有一定文化意義,自然具備了二元屬性,能生動展現華裔群體在雙重文化中受到沖擊、尋求文化歸屬、重塑自我的過程,從而成為一種獨特的“食物符號”。本文通過對華裔作家在文學作品中對食物的描繪和思考,深入探究他們如何將出身和自我認同相結合,從而建立起多元文化身份,實現個體的超越。
【關鍵詞】文化認同;身份建構;食物;華裔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4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3)05-0020-04
一、食物與文化身份認同
文化身份認同是一種深刻而牢固的自我身份認同過程,其內核在個體確認、自我反思和尋找群體中逐漸穩固。一個人往往在扮演好個人角色的同時又屬于一個集體,因此其個人身份與社會身份緊密相連、不易分離,共同受情感、行為、社會文化等影響。身份認同——不管是對其社會范疇角色的認同還是對其個人身份的認同,皆出于提高自我價值的需要。在這一過程中,食物可以扮演重要角色,甚至成為影響人們建構其文化身份的核心元素之一。人們主動選擇自己所享用的食物,體現的不僅是生理選擇,更是一種文化上的決策。食物作為一種有機系統,既可以作為現實物質被接受,又可以作為符號載體進行傳播,在其生產和消費的全過程中,充分展現了它所蘊含的營養價值、經濟水平和象征意義,從而與其所屬的某種類型的文明相互融合,因而食物既可以看作是一種物質形態的存在,又可視為一種精神層面的符號。
隨著人們更加重視食物背后的文化內涵,它已逐漸成為塑造人類身份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也是一種最為有效地表達和傳遞自我身份的方式。正如蘇珊·凱爾斯克在對于食物與文化身份認同的關系上曾有過這樣的表述:“身份認同問題在飲食方式中得以完整地展現出來——包括如何準備食物、吃飯、上菜、食物禁忌以及如何談論食物。”人們作出食物消費的選擇通常依賴于他們所處的人群,而投射在該食物消費過程中的,則是某個群體的文化身份認同。因此,不同群體的食物選擇將人類與其他物種、與不同地區的其他人群、與神明的觀念聯系了起來,使得食物成為“生物和文化方面世界史中一個必不可少的部分”。
正因食物與文化身份認同之間存在著的緊密聯系,所以對此進行深入研究是至關重要的。透過對食物中的二元屬性進行探究,可以更深入地看見華裔群體在雙重文化背景下如何應對文化沖擊、尋找文化認同,并最終建立起多元文化身份的過程。
二、華裔文學作品中的食物與文化身份認同
在華裔文學作品中,食物作為一種文化符號,與個體的文化認同密不可分。其關注重點往往是華裔群體在脫離原有文化環境后進入西方社會和文化環境,并在此過程中所經歷的一系列生存狀態。不僅包括他們如何在異國他鄉拼搏以獲得更牢固的生存權和話語權來實現個人價值,還包括在雙重文化沖擊中自我迷失和重建,以及對華裔身份的追尋和建構,最終確立多元文化身份的過程。
我們發現這類華裔文學作品往往離不開對食物的刻畫。透過作品主人公的飲食態度與烹飪過程可以窺見不同角色或同一位角色不同成長階段的自我文化認同變化。食物作為寄托鄉思和眷戀故鄉的媒介,更是華裔群體對寄居地認同重構的一種期待。隨著社會發展達到不同階段,華裔在西方社會的身份追求與話語權有所變化,食物與身份認同間的關系也隨之動態變化。
本文以《裸體吃中餐》《骨》和《蝦醬之戀》這三部文學作品為例,剖析文學作品中的食物描寫是怎樣表現華裔群體追尋自我文化身份,最終實現其文化身份再構建。
(一)《裸體吃中餐》中食物的文化內涵
《裸體吃中餐》(Eating Chinese Food Naked,1998)是1998年華裔作家伍鄺琴發表的一部關于新一代華裔尋求身份認同的代表作。這篇小說以瑣碎的日常生活為主線,真實地再現華裔女孩魯比(Ruby Lee)從大學畢業回到皇后區后在家庭、愛情和就業等方面發生的點滴故事。主人公是第二代華裔魯比,她出生在紐約皇后區,盡管受美國主流社會教育、吃美式食物、向美國人的生活觀念靠攏,卻仍然被美國主流社會視為文化上的“他者”而不能真正地融入美國主流文化。正是在這一邊緣化危機之中,體現出作家對華裔美國人家庭關系、社會身份等問題的反思,以及身處兩種文化夾縫中的華裔群體如何面對生活困境和身份危機。
小說中對于食物的描寫貫穿全文,并被賦予了深刻的文化意蘊。在對食材挑選、制作過程、用餐禮節與習慣及享用食物的不同選擇等各個環節,均可窺見不同人物對自身文化身份的思考。本文將該小說中對食物描寫所代表的文化含義歸納為以下幾點:
1.華裔自身文化身份認同的矛盾
這一層文化含義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小說女主角魯比。作為第二代華裔移民,她出生于紐約皇后區的唐人街,從小接受美國主流教育,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魯比在所有公開場合完全是一副“正統”美國做派,吃西餐、喝咖啡,喜歡吃甜點,工作之余會去酒吧放松,并交往不同的白人男友,企圖以此來強調她與白人“完全一致”;而每當她處在位于唐人街的傳統小家中,她又吃著母親做的中國傳統食物,對于美國主流群體所不能接受的爪子、尾巴、內臟類的食物也能自然接受,甚至內心有著不愿承認的隱秘歡喜。這樣割裂的二分做法使得魯比時常困惑與痛苦,她既想成為一個真正的“白人”,完成由不被接受的華裔群體向主流社會過渡的過程,又會為該過程必定切斷自己與祖輩文化之間的聯系而倍感焦慮,這會讓她有一種“不安的漂泊感”。被迫游移于兩種做法中的魯比甚至得了一種奇怪的“中餐烹飪癥”,即便在學校,她也會大半夜烹飪中餐并叫醒室友一起吃,以此來緩解內心對于自身文化身份未得到認同的不安。
2.家庭文化身份認同沖突
作為第一代移民的魯比父母直到結婚那天才見到彼此第一面,我們可以預見到如此一對“恪守傳統”的中國夫婦,在與故土完全不同的語言文化的國家顯得多么格格不入。書中的媽媽‘貝爾自從到了美國這一天開始,幾乎都被困在廚房這類狹小的空間里無法脫身,她融入不了當地太太的生活,面對著不肯溝通交流的老公和推崇美式文化的女兒,她在家的存在感恐怕就是從小廚房里端出各式中國美食。魯比一方面抗拒母親這樣不辭辛勞永不掙扎的懦弱,另一方面卻也渴望從具備中國傳統特質的母親那里得到無盡的溫暖與認同。
家庭間的文化沖突在魯比帶白人男友尼克回家的時候表現得更為突出。魯比對尼克在飯桌上不知“長者先動筷”這一點很不高興,當她父親還未用餐時,尼克就已經開始自顧自地吃飯,就連用餐途中也不顧形象地吃著遠離他的雞肉,把面條撒得到處都是。明明是中式的傳統用餐禮儀,魯比卻發現自己對此竟然十分在意,甚至令她產生了“沒有任何理由,會有終止這種愛情的想法”的沖動。由此,魯比也逐漸意識到她在骨子里仍然很在意中國傳統的用餐禮節,而這一點便已經與尼克所處的社會文化不匹配。
在魯比家庭中,一方面她不愿意像母親這樣的中國傳統女性們那樣,為了家庭傾盡一切而失去自我,她更愿意像美國主流社會崇尚的精英女性一樣。但同時,她又希望自己身上能有被母親認可的女性特征。尼克到她家和父母吃飯后,盡管魯比之前一直因為華裔家庭身份而有種自卑感,但她發覺自己會自然而然地按照中餐禮儀標準來評價尼克。如此矛盾的思想其實是魯比對其社會地位和餐桌禮儀的一種無意識文化身份選擇。
3.主流美國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刻板印象
小說中關于食物的描述也與當時的時代背景相結合,如當時美國各媒體中出現了嚴重歪曲中國飲食習慣、夸大乃至妖魔化中國飲食文化的現象。他們把中國人渲染成無所不吃的模樣,把中國的烹飪技巧和佐料與不健康、“致癌”等標簽畫上等號,為中國食物走進西方飲食文化豎起了一堵看不見的墻,并通過誹謗中國食物來進一步拉遠中美文化之間的距離。因此,“吃”字對華裔而言,成為一個十分敏感,極具民族特征的字眼,在一定意義上還可稱為“種族的象征符號”。表面上看似乎涉及食物選擇問題,卻代表著某種文化身份認同問題,這無形中讓華裔群體更為彷徨和困惑,很難肯定自己的文化身份,不管到哪里都難以拜托所處社會的,明顯的族裔性和區域性特征。
在《裸體吃中餐》中,食物和烹飪一直貫穿始終,連結著主人公魯比的內心世界。她經歷了對自身文化身份的困惑,但最終在還是選擇回到中餐中找到自我認同和肯定,這讓她深刻認識到華人血統是她內在的文化基因,她無法否認和逃避,而最佳的解決辦法就是客觀看待她華裔的身份,結合出身和自我認同,構建一種多元化的自我認同身份。
(二)《骨》中食物與身份認同的代際變化
《骨》(Bone,1993)是新生代華裔女作家伍慧明(Fae Myenne Ng)的代表作。這部作品將時間線拉長至三代華裔群體,與以往同類型作品不同,該小說塑造了一個善于跨文化對話的正面華裔形象萊拉,并以她的視角重新思考老一代華裔與年輕一代華裔在面對身份認同時不同的處理方式與代際差異。與《裸體吃中餐》類似的是,該部作品同樣有很多食物描寫的內容,并能透過三代華裔對祖國食物的不同態度窺見華裔群體文化身份認同隨代際變化的規律。
小說中對第一代華裔的描寫并不多,以梁爺爺為代表,書中提到他在世時喜歡喝泡著一條蛇的藥酒,也喜歡吃草藥燉的牛尾,這些都是不被大部分美國人接受的食物。在他去世后依照著中國祭祀傳統為他準備祭品,比如堆起來的橘子、干魚、雞和中式糕點等。從食物可以看出以爺爺為代表的第一代華裔的身份認同完全沒有因為身處國外而進行調整,相應的,他們這類群體也一直生活在唐人街中,與主流的西方社會完全隔絕開來。
第二代華裔則以利昂和萊拉三姐妹的母親為主,書中形容她們的母親身上總是帶有“金銀花梗和苦澀的人參的味道”,在家庭里一直堅持做傳統的中餐;父親也偏向堅持傳統,過年要求家人團圓,過清明也要遵守祭祀禮儀。在他們的觀念里,中式食物是他們與故土連接的紐帶,是他們的根基所在。
第三代華裔則是個性分明,尼娜尤其抗拒,對中式食物深惡痛絕,認為那是每天為生活奔波填飽肚子的“下等人”的象征,而西餐則是令人愉悅且體面的。因為尼娜的這種認知,她時刻想逃離家庭,擺脫華裔身份,但她在美國社會依舊無法融入,內心倍感孤獨與煎熬,她的身份認同和困惑最終也未能得到接納與解決。最終因游走在兩種文化中無法自洽而倍感痛苦,內心始終存在一種漂泊感。另一個女兒萊拉則是選擇了寬容和平和。在唐人街的家中,她能很好地接受蝦醬燉肥豬肉,她不喜歡母親每次煮的又黑又苦的人參湯,但她所愛的母親身上經年帶有人參湯味道,這又能體現出華裔家庭里的代際沖突。萊拉和自己的丈夫梅森在一起時,也慢慢習慣了享受西餐與香檳,漸漸找到了屬于自己在兩種文化間的節奏,并通過尼娜重新審視了自身的文化身份。當她回憶起“唐人街”,她能記起“被刷上蜂蜜的叉燒包的味道”,記起“最肥的鴿子”,在她的回憶里成為一種平靜而溫暖的存在。對于萊拉來說,正確認識自我文化身份,反而給她構建了一個充滿溫情的世界。
通過伍慧明的《骨》,我們既能看到不同代際的華裔群體在西方社會中文化身份認同程度的差異,也能根據他們對待中國飲食的截然不同的態度,深入到華裔們在異國尋求身份認同的內心世界。
(三)《蝦醬、蝦頭醬與兒時的蝦醬菜》中強化文化身份認同
上文提到的兩部作品很好地通過食物符號反映了華裔群體在海外生活的身份認同歷程,同時華裔群體在海外的生活現狀與構建身份認同的途徑也與當下所處的時代與社會環境息息相關。在散文集《生活的古早味——澳門作家的味蕾》中,收錄了30位澳門本土作家對家鄉美食的記憶。其中一篇《蝦醬、蝦頭醬與兒時的蝦醬菜》是作者移居海外后透過故鄉的蝦醬來構建身份認同。
作者喜歡家鄉特產蝦醬,移居海外后也對蝦醬做的菜念念不忘,甚至希望蝦醬能進口,并打上“澳門制造”的標簽,由此體現作者對身份認同的堅定執著。文中還提到某次作者在國外工作時需要自帶盒飯進行加熱,國外同事們大多選擇三明治、意大利面之類的食物,而作者則帶了蝦醬蒸牛肉配白米飯。由于蝦醬加熱后會帶有一股特殊的味道,被同事評價他吃的是“臭死人的垃圾”,當即讓作者感到不滿并進行了激烈反駁。雖然生活在同一個國度,但依舊代表的是兩種不同的飲食文化與文化身份背景。作者對自己國家美食的維護也體現了當今華裔身份認同更為強烈,不僅是食物差異,更是強勢話語與弱勢話語的聯系和碰撞,是華裔群體對自身文化身份的構建與認同。
從作者的經歷可以看到,雖然不可避免地面對一些誤解與爭議,但家鄉的美食將家園建立在記憶之中,同時也賦予兩種文化彼此流動,向對方開放的積極意義。
三、結語
不僅是華裔群體,各個生活在他國的少數族群皆會存在文化身份的追尋與認同問題。他們對于當地主流文化來說是“他者”,這時食物不再僅僅是維持生命所需的基本物質,而是作為一種符號,承載了文化的內涵與價值。當前,各類文化互相碰撞,使得原本單一的文化身份正在被新的、更多元的身份認同所取代,在這個多樣性和多元性的身份認同體系內,既有自身與故鄉文化的緊密聯結,加強認同與歸屬,更是兩種文化的交流與碰撞。
從各文學作品來看,可以看到這類群體在雙重文化中身份認同的過程,有的主角選擇完全放棄傳統文化,甚至想通過不使用母語以此加入西方社會主流文化,但這類文化身份選擇往往會導致主角既失去文化根基,也無法在西方文化中立足;有的主角選擇與西方文化完全隔絕開,只堅守最初的文化身份,最后的結果是過于封閉自我,無法真正構建多元文化身份。最適合的方式應是意識到自身血統與傳統文化是不可逃避的,通過兼收并蓄不同文化的力量,在多元文化環境中重新構建個人文化身份,在全球化多元融合時代實現對個體身份的超越。
參考文獻:
[1]Ng,M.Eating Chinese food naked[M].New York:Washington Square Press,1998.
[2]伍惠明.骨[M].陸薇,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
[3]余思亮.激發文字里的味蕾:澳門美食散文的身份認同與鄉土情結[J].新閱讀,2020(11):72-74.
[4]祁和平,袁洪庚.食物與文化身份認同——《裸體吃中餐》中華裔美國人的文化焦慮[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49(02):136-143.
[5]唐林飛.從華裔美國人對中國飲食的態度看其身份認同的困境——以伍慧明的《骨》為例[J].名作欣賞,2016(12):85-88.
[6]許雙如.從文化性到文學性——符號學對華裔美國文學研究的啟示[J].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21(05):106-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