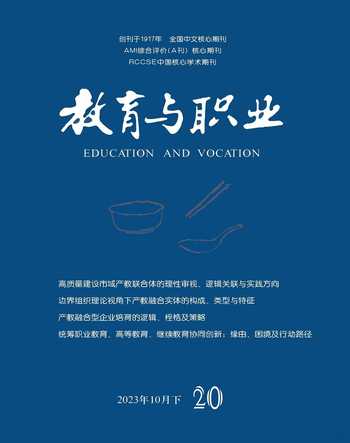智能時代高職教學生態系統的解構、審思與進路
廖思敏 蔣貴友
[摘要]高職教學生態系統是內部各要素之間及其與外部環境共同作用形成的復雜整體。在智能時代,高職教學生態系統從二維主體轉向三維主體、從生態介體單一走向知識跨界,塑造了聯通產業和社會的生態環體。然而,智能技術介入高職教學生態系統也隱含包括教學主體和智能主體的生態位重疊、教學內容和模式滯后于智能社會環境以及虛擬化的教學環境消解師生情感關系的現實挑戰。面對智能時代的技術風險,高職教學生態系統的構建與推進必須發揮育人屬性,展現生態主體的獨特價值;把握職業特性,促進生態介體與時代相適;走出虛擬空間,重視生態環體中情感交流,才能基于整體主義推動教學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智能時代;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變革;教學生態系統
[中圖分類號]G717?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4-3985(2023)20-0092-06
人工智能、云計算、數字孿生、機器學習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正在以不可逆轉之勢進入人類生產、新聞傳播和教育學習等領域,加速了各領域數字化轉型的步伐。2021年元宇宙概念得到廣泛應用,元宇宙的相關技術也應用到高等職業教育教學和技能訓練中,為眾多教學場景的實現提供技術支撐。2022年,新修訂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明確規定,“支持運用信息技術和其他現代化教學方式……推動職業教育信息化建設與融合應用”。可見,國家正積極推進將信息技術應用于職業教育,鼓勵運用人工智能加快推動高等職業教育教學方式的優化,實現高職教學生態系統的智能化變革。學界既有研究或是基于技術變革視角,提出職業教育教學變革需充分汲取人工智能的發展動能;或是從職業教育的崗位與技能特性出發,對高等職業教育現代化的路徑進行探析;或是從人才培養模式角度提出,人工智能時代需對高職人才培養理念、專業設置和教學方法等進行更新。這些研究僅從單一維度剖析智能時代高職教育教學問題,缺乏從動態聯系的整體視角對內部的教學生態系統展開剖析。因此,本研究以教育生態學理論為支撐,在對智能時代高職教學生態系統進行解構的基礎上,審思智能技術介入高職教學生態系統帶來的風險,進而探討高職教學生態系統抵御技術風險的實踐策略,以期為高職教育教學數字化轉型和促進高職教學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助力。
一、解構:智能時代高職教學生態系統的構成及轉向
(一)智能時代高職教學生態系統的構成
“生態系統指的是在特定空間內的所有生物和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具有能量轉換、物質循環和信息傳遞功能的綜合體”①。其作為一種分析框架被廣泛借鑒到多變復雜的人類社會進行解析。作為一種人工生態系統,高職教學領域同樣是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及其與外部環境共同作用形成的復雜整體系統。
1.高職教學生態系統內部各要素相互聯系。高職教學生態系統內部各要素間存在信息輸入和輸出的功能轉換。教師群體和學生群體是高職教學生態系統的生態主體,二者通過教學活動開展交流互動,完成知識講解、技能傳授和情感交流;教學環境是高職教學生態系統的生態環體,是物理環境和虛擬環境等綜合的產物,為高職教師和學生提供基于生產與崗位場景的虛擬學習空間;教學內容和教學模式構成了教學生態系統的生態介體,對生態主體之間的互動有巨大影響。可見,教師、學生、教學內容、教學模式和教學環境之間相互影響、相互聯系,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高職教學生態系統。
2.外部環境與高職教學生態系統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智能時代高職教學生態系統的外部技術環境和產業環境等與生態系統內部各要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之間存在諸多信息流。智能時代,產業面臨技術更新、結構升級,急需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這一外部變化必然帶來高職生態系統內部人才培養規格的調整、課程教學內容的更新。而高職教學生態系統內部的教學內容和人才培養等要素的優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會促進技術的革新、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可見,外部環境促使高職教學生態系統內部各要素發生適應性變革,而內部各要素與外部環境相互作用重塑了新的高職教學系統。
(二)智能時代高職教學生態系統變革的目標導向
人工智能技術成為引領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外驅力,正在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生產、生活和學習方式。智能技術介入高職教學生態系統,一方面,能夠為學生創設基于崗位場景的虛擬學習空間,有助于教學效率和質量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對高等職業教育教學主體、教學內容和教學環境帶來嚴峻挑戰。因此,如何充分發揮人工智能對高職教學的賦能作用,成為智能時代高職教學生態系統變革的主要動力。同時,系統各要素的轉向可充分體現智能時代高職教學生態系統變革的目標導向。
1.生態主體:二維主體轉向三維主體。人工智能技術的使用對傳統的教學過程、教學模式和學習方式等產生了顛覆式影響,深刻變革了高職教育教學生態系統。在傳統高等職業教育教學活動過程中,教師能夠形象生動或示范性地向學生傳授技能性知識,而學生同樣能夠體悟到實踐性知識以及教師無形中傳遞的緘默知識。具體而言,教學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具有兩種類型:一是教師和學生之間單向度傳授知識的關系;二是在教師的引導下,學生發揮學習主體的主動性、能動性,實現知識和情感雙向互動。智能時代,整個高職教育教學過程受到人工智能技術顛覆性的改造與重塑,逐漸形成了智慧學習、人機協同學習等新型教育教學體系。即當機器也躍升為高職教育教學系統中的要素主體時,不僅會協助教師完成教學任務,還促使教師、學生和機器之間形成了交互關系。此外,在人工智能深入發展的過程中,傳統行業的產業鏈與工作流水線將被重構,進而對制造業領域從業人員的資質與能力素養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所以高等職業教育需要擁抱新興的智能教學主體,進而在教學中提高師生人機協同的能力與素養。
2.生態介體:知識內容從單一到跨界。高等職業教育作為一種類型教育,具有鮮明的跨界性和整合性,與外部的產業環境、社會環境存在著密切的聯動性和相互依存性。一方面,高等職業教育的高質量發展需要產業和社會的支持,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社會對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為高職教育教學內容調整更新、專業布局以及課程開發等提供了真實導向。另一方面,智能時代,產業和社會不再滿足于掌握單一知識結構的勞動者,而是需要既掌握高階技術技能又具備創新、跨界思維等關鍵素養的現代化職業人。從高職教學生態系統的教學內容角度來看,傳統的教學內容僅僅是講授書本上的內容和滯后的生產崗位要求的技能,而智能時代知識的更新速度呈現指數增長,不再憑借傳統的知識生產方式便可獲得;同時,產業發展愈加顯現出跨界融合的趨勢,加速了不同崗位之間分工壁壘的破除,需要不同崗位之間的知識技能交叉協作。這樣的社會環境和產業環境傳導到高職教學生態系統中就表現為,教學內容應該將學校書本上的知識擴展至產業端和崗位端,由滿足單一崗位能力的知識內容轉向適應多元綜合崗位群能力的知識內容。
3.生態環體:面向聯通的產業與社會。教學環境是高職教學生態系統的生態環體,也是師生進行教學活動和情感交流的空間場所。在AR和VR及數字孿生等技術還未進入高等職業教育領域前,傳統的高職教育教學環境一般指教學活動和教育實踐發生的特定物理空間,如教室、實驗室、實訓基地等,理論知識的傳授和實踐技能的教學只能在有限且封閉的固定空間展開,教師和學生很難與外部的產業環境、社會環境溝通與聯系。而隨著人工智能和元宇宙的廣泛應用,有效銜接了虛擬空間和現實空間,淡化了高等職業教育與外界產業和社會的“圍墻”和邊界,打通了高職教育教學環境與社會環境、產業環境,促使教學能夠走出課堂或者將社會和產業中先進的設備及各類應用場景引入課堂,讓師生得以在更接近產業、崗位場景的真實場域中生成知識和培養技能。
二、審思:智能時代高職教學生態系統的風險挑戰
(一)主體重疊:教學主體和智能主體面臨生態位重疊
生態位是指生態系統中一個生態個體在時空上所占有的區間位置及與相關物種和種群之間的關系。由于教學主體和智能主體皆占據智能時代高職教學生態系統內獨特的生態位,當二者在高職教學生態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愈加相近,便會出現生態位的高度重疊現象。也就是說,隨著智能技術與高職教學領域的廣泛融合,機器這一智能教學主體在高職教學領域所承擔的教學任務越來越多,教師越來越依賴智能技術完成知識講授環節,從而導致教學主體和智能主體生態位逐漸重疊。長此以往,一方面,會弱化教師掌握專業知識技能的主體地位。在知識快速迭代更新的智能時代,教師作為教學主體極有可能失去他所擁有的知識和技能,因為既有經驗在知識高速創新之下變得越來越沒有價值,而智能教學主體憑借其技術的高位優勢,能夠快速整合優質教學資源,致使教師的主體地位岌岌可危。另一方面,會造成高職教學課堂陷入只見技術不見人的窘境。智能時代,高職院校廣泛借助智能教學主體,無形中弱化了教師主體在課堂教學中的作用,將原來鮮活的師生、生生之間的情感交流變成了簡單的人機協作,減弱了高職教育課堂教學的靈活性和生成性。
(二)介體脫節:教學內容和模式滯后于智能社會環境
智能時代,高職教育的教學內容設計既要遵循崗位或職業需求的技術性邏輯,以體現其培養現代職業人為目的的職業性;又要遵循高職教育的人文性關照邏輯,以體現其充盈的人文意蘊。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為高等職業教育領域帶來契合社會需求、產業發展的前沿技術和知識的同時,不斷地沖擊著傳統高職教育教學的知識內容體系和技術技能傳授方法。目前,高職教學生態系統并未及時跟上外部環境的變革,教學內容和教學模式呈現出與智能社會相脫節的困境。一方面,教學內容滯后。現有的教學內容還固守著傳統的知識講授和技能訓練方式,并未及時更新有關人工智能的概念性知識和方法論知識,難以達成智能社會的發展要求以及智能產業系統“德智技一體化”的用人標準。同時,技術運用還忽略了職業倫理道德規范、人格品質培養等內容,致使高職教學內容陷入技術泛濫而缺失人文性的窘境。另一方面,教學模式設計滯后。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層出不窮對高職教育教學也提出了更新更高的標準,而受校企雙方合作訴求不匹配、實踐教學條件有限等影響,導致現有的教學模式無法滿足多樣化的學習需求。例如,實踐教學依然是以校內實訓為主,較少能夠模擬真實的產業生產場景或與企業深度合作,無法為學生提供高質量的理實一體化教學環境。
(三)環體沖擊:虛擬化的教學環境消解師生情感關系
智能技術或元宇宙賦能高職教育教學可以顛覆以往困于固定的教室和實訓場所,代之以數字孿生、腦機接口、可穿戴設備等技術在虛擬空間中的模擬實訓和工作場景,并在此空間中開展教學活動的新型教學模式。虛擬化的教學環境在突破高職教學場景的物理壁壘的同時,也在無形中使高職教學生態系統中教師和學生的交流被機器阻隔,造成師生關系逐漸疏離。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使教師和學生的交流互動中心產生非理性化轉移,由此導致二者的交流隱含著“技術化”風險。因為,即便機器具備即時性和智能化,也無法模擬出真實場景下的課堂教學互動,也無法像教師一樣傳遞具身性的緘默知識。所以,智能技術驅動下的師生交流互動必然會缺失社會性、情感性和真實性,從而促使師生逐漸走向疏離,甚至產生對立和沖突。另一方面,長期沉浸在虛擬化的空間環境中,會導致教師角色被技術裹挾走向虛無化,消解教師的主導作用。在智能技術虛化的教學環境中,教師和學生越來越依賴運用數字技術認識世界與習得技能,但如果高職教師過度借助智能技術解決教育教學中的問題,便會逐漸失去解決問題的能力,消解自身在教學過程中的主體角色與權威地位。
三、進路:智能時代高職教學生態系統的優化策略
(一)獨特性進路:發揮育人屬性,展現生態主體的獨特價值
高職教師和學生要明確自身在高職教學生態系統中的主體地位與功能,積極發揮作為教學主體的獨特性價值,通過生態位特色發展實現與智能主體的生態位分離,從而促進智能時代高職教學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一方面,凸顯人類教師的育人角色,展現區別于機器的獨特價值。智能技術可以根據學生的學習需要提供精準評價,也能夠協助職業教師完成資料收集與重復性工作,但技術和機器卻無法做到與學生共情、發現學生內心的困惑與挫折。基于此,高職教師在智能教學過程中需重視因材施教和人性情感關懷兩個方面,發揮教師獨特的育人屬性。具體而言,一是高職教師在既有智能教學的基礎上尊重學生個體的發展需求,根據其成長規律、性格等因材施教,盡可能讓每個個體都得到充分的發展;二是除知識和技能的傳授者角色外,高職教師應積極關注學生的情感狀態和學習體驗感,關注其精神成長。另一方面,高職教師要提升數字化素養和人機協同合作能力。新理念、新技術嵌入高職教育教學過程衍生了微課、翻轉課堂等新型數字資源載體,這就促使高職教師需盡快提升數字化素養,以實現人機高度協同合作。高職教師不僅要在教學設計、教學方法、教學評價等全過程合理使用智能技術,還要增強自身在使用智能技術和設備時的創造性與能動性,根據課程類型、學生特點漸進式進行人機協同教學,從而達到技術賦能高職教育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的目的。
(二)適應性進路:把握職業特性,促進生態介體與時代相適
智能時代,隨著技術知識更新、專業技能改進不斷加速,陳舊的技術知識和滯后的專業技能已無法適應外部社會環境、產業環境和技術環境對人才培養的要求,凸顯出高職教學生態系統中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模式與智能時代相適應的必要性與迫切性。高職教學的數字化轉型務必盡快根據未來發展需求進行適應性調整,同時與職業教育特性充分融合。首先,高職院校要革新教學內容,增加人工智能元知識的傳授,以提高學生在人工智能時代的社會適應性。高職院校要將人工智能的演進歷史和在職業教育領域的應用場景,以及人工智能的基本算法、技術倫理道德等知識融入教學內容,不斷重構與革新既有的課程教學體系。其次,高職教學內容要堅守職業本質,與智能時代工作世界相適應。高等職業教育的職業性決定了與工作世界相聯系是其區別于普通教育的本質特征,因而教學內容需要將工作任務與職業能力分析結果轉化為相應的課程和教學內容,從而符合智能時代對高職人才培養的能力要求。除基本理論學習和技能訓練外,智能時代高職教學更應該關注數字素養和創新能力等通用品質的培養,從而培養出復合型、創新型技術技能人才。最后,構建以數字化、智能化為特征的智慧教學模式,深化產教融合的改革進程。高職院校探索構建以數字化和智能化為特征的智慧教學模式應該重視學生的主體地位,引導自主探究與合作,利用智能技術突破產教融合中的桎梏,優化智慧課堂中的教與學的體驗。同時,實現職業性和跨界性目標還需要產業、企業、高職院校共建智能教學場景,為學生的實習實訓提供真實的場所、設備和環境,切實開展理實一體化的教學,讓學生在“做中學”。
(三)情感性進路:走出虛擬空間,重視生態環體中情感交流
智能時代,智能化的虛擬教學空間成為開展高職教育教學的主要場所。數字化的教學媒介為師生之間的教學互動構筑了虛擬和現實相結合的空間和環境,教師和學生深層次的內在交互和情感交流逐漸被智能技術所遮蔽。因此,為有效規避虛擬教學環境中出現的師生情感淡漠問題,必須在教學環境中加強師生的情感聯結,引導師生走出虛擬空間以及強化二者在智能教學中的生命互融。一方面,合理規范智能化教學的邊界與標準,重視教學場景中師生的情感交流。情感是良好師生關系的核心及重要維系紐帶,在制定智能化教學的行為標準與實踐指南時,務必注意強化師生之間人文與情感的體驗,規避教師被智能技術裹挾而陷入不同程度的技術風險中。此外,智能時代更應強調現實與虛擬相結合,注重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言傳身教與情感聯結,強化學生在技能學習與知識獲得中的體驗感與互動性。唯有如此,智能時代高職教學生態系統才能告別純粹的技術知識獲得,使學生在與教師的交流互動中獲得更多的情感體驗和職業體驗。另一方面,加強引導學生多與現實空間中的人交流,完善學生的社會化進程。當前高職院校學生大多是數字“原住民”,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或多或少會伴隨著虛擬空間和現實世界的沖突與迷失,當虛擬空間和現實場景切換時,容易混淆兩個空間的時間和規則。這就需要教師加強對學生在現實空間中人與人交流的引導,完善學生的社會化進程,將學生培養成有著健全人格并且情感充沛的人。
(四)協同性進路:遵從整體主義,促進教學生態系統平衡發展
智能時代,高職教學生態系統是由生態主體、生態介體和生態環體構成的復雜整體,各要素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一個要素的變化會牽動或影響整個高職教學生態系統。因此,智能時代高職教學生態系統要遵從整體主義,注重各要素之間的協同共進,確保生態系統處在動態平衡狀態。一方面,智能時代高職教學生態系統的構建需要圍繞師生主體、教學內容、教學環境各核心要素而展開,共同促進智能技術影響下的高職教育教學領域變革。另一方面,從整個高職教學生態系統來看,若要維系教學生態系統各要素的協同共進以及系統的動態平衡發展,必然離不開政府部門的頂層設計和統籌規劃。一是政府應該積極鼓勵各產業、企業與高職院校開展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將行業前沿的技術、設備等資源整合為教學資源,促進高職教學生態系統內人才培養結構、課程教學內容等要素的優化。二是政府應積極倡導形成高職院校教學系統聯盟,并制定相應的指導意見,為智能時代高職院校教學生態系統規劃發展方向,推動整個高職院校教學的變革和教學系統的平衡發展。
[注釋]
①郭麗君,陳中,劉劍群,等.高等教育生態學引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139.
[參考文獻]
[1]蔣貴友.數字時代文科知識生產的運行機制——基于全球26個高校計算社會科學實驗室的分析[J].比較教育研究,2023(1):44-53.
[2]沙玉娥,丁鋼.人工智能時代職業教育的人文遷進[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20(18):93-96.
[3]辛繼湘.當教學遇上人工智能:機遇、挑戰與應對[J].課程·教材·教法,2018,38(9):62-67.
[4]方緒軍.智能化時代:職業教育學習論的路向[J].成人教育,2019(6):69-74.
[5]郭麗君,廖思敏.智能時代大學教學生態系統:演化邏輯、現實隱憂與發展向度[J].現代大學教育,2023(4):93-100+113.
[6]張燁,蔡翔華.元宇宙+職業教育:未來虛實融生的職業教育發展新趨勢[J].教育與職業,2023(2):5-11.
[7]郭麗君,周建力.困頓與突破:高等職業教育的生態位辨析[J].現代教育管理,2022(4):93-101.
[8]方緒軍,王屹,陳業淼.人工智能時代職業教育課堂教學改革的邏輯分析、現實挑戰與時代進路[J].教育與職業,2022(12):80-86.
[9]肖鳳翔,陳鳳英.技術工具論視角下職業教育教學生態系統的困境與重構[J].現代教育技術,2021(5):52-58.
[10]周馳亮,方緒軍.人工智能背景下職業教育教學改革的三重邏輯:起點、挑戰與路徑[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22(20):33-39.
[11]樊明成,陳小娟.面向人工智能時代的高職院校專業建設:現狀、問題與應對[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23(5):34-39.
[12]趙書琪.元宇宙賦能職業教育:價值意蘊、應用機理與實踐路徑[J].職業技術教育,2023,44(1):34-39.
[13]譚維智.不教的教育學:“互聯網+”時代教育學的顛覆性創新[J].教育研究,2016(2):37-49.
[14]劉偉,譚維智.人工智能時代的師生交互:困頓與突破[J].開放教育研究,2022,28(2):54-63.
[15]于家杰,劉偉,毛迎新.人工智能時代教師存在的價值[J].現代教育技術,2020(7):21-27.
[16]石偉平,林玥茹.新技術時代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模式變革[J].中國電化教育,2021(1):34-40.
[17]董文娟,黃堯.人工智能背景下職業教育變革及模式建構[J].中國電化教育,2019(7):1-7+45.
[18]夏雪芹,袁忠霞.虛擬交互場景中高校師生關系的構建路徑研究[J].黑龍江高教研究,2020,38(3):148-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