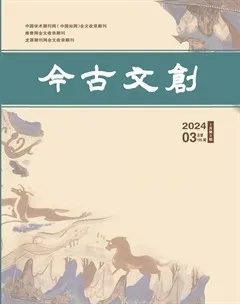《史記》與《聊齋志異》中的酷吏形象對比
【摘要】司馬遷在《史記·酷吏列傳》中第一次為古代官場中作風與傳統儒家道德理念稍顯背離的官吏群體立傳、命名,稱其為“酷吏”。此后這一稱呼為后代各種文學作品所沿用。《史記》中的“酷吏”形象,苛刻狠厲,卻又為漢初社會穩定做出不可忽略的貢獻。《聊齋志異》中的“酷吏”形象,殘酷暴虐,貪腐昏聵。從《史記》到《聊齋志異》,全面多元的“酷吏”形象,逐漸演變為僅余殘暴個性的“反派”,深究其中原因,與文本體裁特點、作者所處時代、作者主觀意愿等因素息息相關。本文將依次分析《史記》與《聊齋志異》的酷吏形象,再將二者對比分析,探究造成其變化的根本原因。
【關鍵詞】酷吏形象;《史記》;《聊齋志異》;對比;演變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03-0043-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3.014
“酷吏”一詞的來源隨著后世的不斷研究,有了較為統一的說法:“酷”字偏旁從酒,原意指酒味濃烈。此字較早與法律、法吏等產生聯系源于《荀子·議兵》“其使民也酷烈”,而“酷吏”一詞最早見于《史記·酷吏列傳》。司馬遷說:“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太史公自序》)“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當是這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酷吏列傳》)此處的“嚴削”“武健殘酷”與現代漢語里的“殘酷”,感情色彩略有不同。這種差異于《酷吏列傳》的贊語中更為明顯:“雖慘酷,斯稱其位”,表明司馬遷心里對酷吏整體的認知是“刻薄少恩”,但司馬遷也公正地認定大多數酷吏在特定的時代環境里,在公務的處理上動用的手段、刑罰屬合理范疇,因此,司馬遷的“酷”雖包含殘酷之意,也有著合理的酷烈、冷酷之內涵。《聊齋志異》作為文學性作品,將酷吏的負面性格無限放大,提煉出個性鮮明的,能夠深刻反映時代現實的,用于諷刺批判的“殘酷暴虐”的“反派”酷吏形象。到了近代,在近人編寫的《辭源》《辭海》中,“酷吏”一詞擁有了現代漢語固定的詞義,專指“以嚴刑峻法殘虐百姓的官吏”“濫用刑罰,殘害人民的官吏”。“酷吏”的詞義由寬變窄,由客觀描述變為一個具有固定負面情感色彩的詞匯,凡此種種均源于《史記·酷吏列傳》,卻也與司馬遷的本意有了很大的不同。
下面將對《史記》與《聊齋志異》酷吏形象進行分別表述,在此基礎上對其相同點分類整合,以及對酷吏形象發展變化的原因進行探究分析。
一、《史記》中的酷吏形象
《酷吏列傳》中司馬遷系統地介紹了十三位酷吏:侯封、晁錯、郅都、寧成、張湯、周陽由、趙禹、王溫舒、尹齊、楊仆、義縱、減宣、杜周。作者對他們的介紹有詳有略,或將其個人事跡完全流暢敘述,或將幾個人的事跡用同一事件穿插在一起,互為補充。共同構成了一個大體相似又獨具個性的酷吏“團體”。
其中侯封“刻鑠宗室”,晁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郅都“獨先嚴酷”,張湯、趙禹“以深刻為九卿”,杜周“內深刺骨” ①。文中多次出現“刻”“深”等字眼,意為苛刻、刻薄,可以看出司馬遷對于酷吏的整體評價是“刻薄少恩”,這是“酷”的含義的一方面。
“酷”的另一方面含義,多為酷烈暴虐,各有缺點。如寧城、義縱的驕橫:寧城“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濕薪。滑賊任威”,義縱在寧城送自己出關時,任性使氣,不行禮;周陽由、王溫舒任用惡吏,且總依自己的喜惡“撓法活之”或“曲法誅滅之”;張湯的巧詐,他憑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以及優越的思辨思維,在堂中與他人分庭抗禮,義氣相爭,偶有曲解誣陷他人之所為,樹敵眾多;杜周的阿諛主上,不顧法律的公正,處處揣摩上意,帝喜則活之,帝不喜則曲法殺之。這些酷吏大都結局慘烈,不得善終,造成這些酷吏結局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當時宗室貴族的勢力強大,改革不易,處處受阻,他們最終成為中央與豪強爭斗的犧牲品;另一方面便是司馬遷心聲的曲折反映,他并不認同酷吏的刻薄少恩,以及他們性格中完全違于儒家思想的法家個性,他堅信善惡到頭終有報,酷吏這樣的結局是符合司馬遷的觀念的。
但通讀文章又不難發現,作者司馬遷對于酷吏群體呈現出的矛盾心理。首先,由于他的個人身世遭遇,因受李陵事件牽連,慘遭宮刑,酷烈的刑法定斷,刑訊過程的慘痛、屈辱,均讓他對酷吏怨憤至深。但司馬遷作《史記》一直秉承務實求真,秉筆直書的實錄精神,他不能也不愿脫離歷史真實,將過分主觀的個人想法混入其中,破壞作品真實性。于是司馬遷結合特殊的時代,對人物作了公正的評述,在揭露他們“冷酷無情”的同時,也不否認他們身上的閃光點。如郅都能在推行法制時不避貴戚,廉潔奉公;張湯對弱小有同情心,并且業務能力極強,在處理淮南王、衡山王、江朝王反叛案件時,“皆窮根本”。當他與皇帝意見相左時,也不是一味媚上,而是堅持己見,為君為國。不僅如此,張湯還是位廉潔之官,他雖然官職顯赫,位列三公,但死后“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趙禹“為人廉倨”“據法守正”;義縱“治敢行,少蘊藉”;尹齊廉潔武勇;楊仆執事效法尹齊;減宣“官事辨”“敢決疑”“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等等,司馬遷對他們的正當行為給予了充分肯定,并稱贊其“方略教導,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文武焉”。因此,李景星在《史記評議》中說:“贊語與傳意義各別,傳言酷吏之短,贊取酷吏之長,褒貶互見,最為公允。”
司馬遷秉承良史原則,筆下塑造的人物有優有缺,客觀真實地描繪了當時的酷吏人物形象與他們的生平,塑造出后世酷吏內涵中所沒能涵蓋的更廣闊豐滿的人物,使人們于厭惡恐懼中又能體味到一絲獨屬于那個黑暗時代的光亮與溫情。
二、《聊齋志異》中的酷吏形象
蒲松齡《聊齋志異》是部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神鬼怪異小說。其中有大量篇章影射批判黑暗的社會,用充滿浪漫色彩的夸張筆法,揭露整個封建吏治的腐敗與罪惡,矛頭直指封建統治者。篇章中有大量情節涉及官吏,無論是貪官污吏還是愛民的仁臣均在故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他們的形象鮮明突出,曲直分明。
依據劉小潔的《〈聊齋志異〉官吏形象分類研究》的分類方法,將其中的官吏分為陰間官吏、人間官吏和仙界官吏三類:陰間官吏可對一個人進行一生的審判,蓋棺定論;人間的官吏是對現實中黑暗官場的真實影射;仙界官吏是作者對現實生活的幻想。無論是處在哪種界域的官吏,總是惡者居多,明顯是良官的幾倍。
陰間的暴虐貪腐之官。如《席方平》中的冥王,他接受羊某的行賄,顛倒是非,整個陰間吏治系統在他的掌控下渾濁不堪,無一點清明跡象。冥王更是對質疑者席方平大肆施展酷刑,火床揉捺,鋸解其體,殘酷可怖。《考弊司》中的鬼王,大膽行賄賂之事,見錢眼開,視錢如命,對于行賄者可免刑,而對于貧窮無財的新鬼就施以割髀肉之刑,在陰界為非作歹,無法無天,貪婪卑鄙。《伍秋月》中的皂隸,雖是小職,卻依然可以因為手頭用度不足,濫抓民女,以此要挾其家人,以錢贖之,與強盜無異。在押的囚犯遭受到許多難以想象的非人待遇。
人間的昏聵虐民之官。如《夢狼》中白翁之子白甲,魚肉百姓,為害一方。走無常者丁某借夢將白甲的惡行告知白翁,白翁寄書信于白甲規勸他為官愛民,可白甲竟以“黜陟之權在臺上,不在百姓。上臺喜便是好官;愛百姓,何術復令上臺喜也?”將討好上官視作為官之本。《潞令》中的宋國英,以杖殺百姓為榮,對百姓沒有絲毫體恤之情,視百姓的性命存亡為玩樂之事。他的種種惡行在人間之時,竟無人敢檢舉揭發,讓惡貫滿盈之人逍遙法外。《紅玉》中的宋御史,因行賄罷免后依然毫無悔改,強搶民女,致使一個原本完整和美的家庭驟然崩潰,家破人亡。
仙界的仗勢欺民之官。此處仙界的概念與佛、道體系關系密切,道教的飛升和佛教的成佛觀念,使得這些飛升者和成佛者的容身之所“仙界”應運而生。人們生來就可生活在人間,死后不可避免地“存在”于陰間,而仙界概念與之大不相同,需要人們經過一生的努力才有可能實現,甚至是一生都永遠無法到達的境界。因此,仙界的官吏讓人們更加神往和尊重,但即使是這樣一個仙界官吏系統,在蒲松齡筆下依然有自私自利,愛慕虛榮,毫無憐憫之心的惡徒。如《靈官》中的靈官,因某翁為狐妖,且孤身一人,不顧妖的本性是否良善,只一味以其妖身為原罪,追殺鞭打,力圖除之而后快,沒有絲毫善惡憐憫之心。該狐翁卻能在大劫當前,因不忍坐視凡人喪命,幫助他人逃生。將妖、仙二者的所作所為相比較,是何等的諷刺與悲哀。《夏雪》中的龍王只因蘇州人民稱之為“小老爺”,不滿意“小”字當前,就懲罰當地人民夏天降雪,不顧人民生死,莊稼生長,為一己私心而使天下蒙難。龍王貪慕虛名,傲慢自恃,仗勢欺小,為人所不恥。《土地夫人》中的土地夫人,不顧村民王炳已是有妻之人,橫入其家,妄圖破壞其家庭,即使是被王炳百般拒絕后仍不肯離開。土地夫人毫無羞恥心,不憐憫百姓生命,為神界敗類。
這些酷吏人物在蒲松齡的筆下不再是多面的矛盾復雜的形象,而是變成了單一特定的負面形象,人物性格中不再有矛盾、掙扎、成長的光芒,而是惡劣至極的臉譜化人物。
三、酷吏形象的演變及其原因
(一)酷吏形象的變化
通過前述的舉例對比,不難看出從《史記》到《聊齋志異》的酷吏形象的變化。酷吏由復雜多面的現實人物,變成了性格內涵相對狹小的故事反派;由有能力有頭腦的嚴厲之吏,變成了一味作惡,思想空虛的殘酷之吏。還有《史記》中司馬遷為酷吏專門作傳,詳略得當,寫盡了主人公的一生,而《聊齋志異》中的酷吏僅是作為推動情節發展,襯托主人公的小配角。
(二)酷吏形象變化的原因
1.文本類型不同
人物形象的復雜與否,臉譜化與否與文本自身的特質密切相關。《史記》是紀傳體史書,司馬遷采用專題形式真實而深刻地記述了武帝時期嚴法誅殺,官吏嚴酷的歷史現實。人本就是多面的,人性是復雜的,想要真實反映一個人,必定要于他的生平事跡中探尋他的特質。閱讀史書通常會以具體的歷史的眼光解讀,必定會更加寬容理性,會設身處地想當事人之所想,思當時人之所思,這份寬容是面向那個特定時代下的人物,更是將心比心,易地而處地體味那個時代背景下古人生存的不易。所以,《史記》中的酷吏形象既有刻薄寡恩的一面,也有卓越的治理才能以及肯定這個群體在穩定國家局面時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而《聊齋志異》的文本體裁是小說,蒲松齡運用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結合的創作方法“說鬼說怪”,通過擬人化的鬼怪形象,曲折委婉地影射殘酷黑暗的現實。小說塑造人物需在有限的篇幅中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抓取人物的某一顯著特征,既有利于推動故事的發展,又能讓寫作者于思想高度不自由的封建社會中,宣泄對丑惡現實的不滿,于惡吏貪官受到懲罰,惡有惡報、大快人心的結局中得到片刻解脫。
因此文本體裁的差異,讓酷吏形象從紀實文學進入文學性作品視域后變得越來越固定,越來越單一。經過長期的積累,讀者的閱讀反饋,使人對此有了相對固定的判斷認知。
2.創作理念不同
《史記》的創作理想宏大,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為太史令時,就曾遺憾于春秋戰國因戰事紛繁,記錄歷史者懈怠,讓許多名人偉業埋沒于歷史的洪流中,自漢朝穩定興盛之后,賢明君主、死諫忠臣、俠義之士輩出,作為太史官員,司馬談認為自己責任重大且義不容辭,堅定地要將史書修繕。然天不假年,他時日無多,于彌留之際將自己的宏愿囑托給司馬遷。司馬遷子承父志,確立其修史的宗旨:“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秉承其旨,不難理解他對于當時社會重要群體——酷吏,專列一章,讓他們作為本章主人公,于歷史長河中大放異彩。
《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他生活在社會劇烈動蕩的明清交替之際,政治腐敗黑暗,作者在書中說:“花面逢迎,世人如鬼”“官虎而吏狼者,比比皆是也”。作者不滿于黑暗現實卻也無力改變現實,但他依然想要揭露批判現實,完成作為儒家思想實踐者的文人使命。在廣闊的現實面前,酷吏只是作為一分子,是社會生活的參與者,他們僅能作為事件線索,才能讓作者的創作具有更深的批判意義。
3.作者經歷不同
這種變化還與作者的自身經歷和所處時代有關。司馬遷繼承父親司馬談的遺志,在史學著書方面殫精竭慮,卻因正義直言,受李陵敗降之事牽連,慘遭宮刑,在牢獄中深刻認識到酷吏的殘暴與不公,他怎能不怨不怒,卻在創作《史記》抒發憂憤的過程中依然謹遵史家教誨,謹守史家原則,秉筆直書,客觀公正,只為讓后代能擁有接觸最真實歷史的機會。并且司馬遷所處的漢朝,異性諸侯、貴戚宗室以及地方豪強勢力強大,嚴重威脅著剛剛建立的漢朝封建帝國的穩定統一。面對這樣的客觀現實只有酷吏政治的以暴制暴,以暴鋤奸,嚴刑痛殺,這些舉措往往立竿見影,循吏政治能從根本上快速穩定局面。太平盛世的建立需要儒法并用,酷吏們精強能干,“酷能稱職”,在維護社會穩定和封建統治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作者經歷和時代背景決定了“酷吏”一詞的最初創建包含的是褒貶相間,有功有過的群體。
而蒲松齡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他成長于科舉制下,以考取功名做官為人生的終極目標,但終究差點運氣,屢試不中。一生貧困交迫,懷才不遇,不時受到蠹吏的催逼和侮辱,他將科舉受挫的苦悶與對社會制度、社會現實的不滿,移志入書,所謂“集腋成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 ②。蒲松齡所處的時代,是整個中國中央集權政治最鼎盛的時代,八股取士思想控制嚴密,大興“文字獄”,作者不得不在恐怖的形勢之下將眼光投向神仙狐鬼的世界。作者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將時代、人物身份定位移至前朝,才能避免因文章之言受到當地官員的苛責與懲罰。很多的時代局限,讓蒲松齡無法于小說的真實性中任意揮毫筆墨,臉譜化的表達反而是一種保護自己的方式。
(三)酷吏形象的繼承
《史記》與《聊齋志異》在對比中也顯現出明顯的繼承性:《聊齋志異》中極為殘暴的酷吏形象實際是對《史記·酷吏列傳》中性格復雜真實的酷吏形象的殘忍冷酷的一面,做了文學性的提取與夸張放大。還有,兩部書中的酷吏結局幾乎都十分悲慘,躲不過報應輪回。
(四)酷吏形象延續的原因
1.文本因素
小說與史傳文學本就一脈相承,司馬遷首創了以人物生平事跡為中心的紀傳體后,“傳”與“記”幾乎成為小說的特殊標志,敘述人物生平,描寫人物形象,以人物為中心組織材料、表現社會生活,是史傳文學與小說的相通之處。蒲松齡在《題吳木欣〈斑馬論〉》中提道:“余少時,最愛《游俠傳》,五夜挑燈,恒以一斗酒佐讀”,足見蒲松齡對《史記》的熱愛,他在創作《聊齋志異》中的酷吏形象時,必定會在黑暗現實的真實人物原型基礎上,也借鑒了《酷吏列傳》。
2.儒家思想的影響
司馬遷與蒲松齡都深受儒家思想文化影響。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的治世觀念以及“仁愛”觀,深刻影響著每一個想要入仕為官的青年才俊。司馬遷雖然對于酷吏的所作所為有認同與贊揚,但依然不能倚仗儒家信奉的“禮治”去全盤接納法家的“法治”思想。法家思想在動蕩的歷史時期發揮著強大的作用,但隨著社會逐漸穩定,武帝依舊利用酷吏加強皇權,酷吏政治下聚斂財富,外伐四夷,內興功作,使得全國人民都生活在高壓政治環境下,百姓苦不堪言。真實的酷吏終于消磨掉最后的一點價值,淪落到“盜賊欲加多,上下相為匿”的混亂境地,殘酷暴虐的酷吏形象逐漸完全取代了雖冷酷殘暴,但在事業上偶有建樹,或剛正不阿、或執法不避權貴的復雜的酷吏形象,并由此綿延千年,形成了日后的酷吏文化。
注釋:
①司馬遷著,陳曦、周旻注:《史記》,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717-2736頁。
②蒲松齡著,于天池注,孫通海、于天池譯:《聊齋志異(第一冊)》,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6頁。
參考文獻:
[1]蒲松齡著,于天池注,孫通海,于天池譯.聊齋志異(第一冊)[M].北京:中華書局,2015.
[2]司馬遷著,陳曦,周旻注.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
2011.
[3]劉小潔.《聊齋志異》官吏形象分類研究[D].河北大學,2019.
[4]張鈞濤.《史記》法家人物與酷吏之異同剖析[D].渭南師范學院人文學院,2017.
[5]陳潔.淺論《聊齋志異》對黑暗社會的批判[J].小說評論,2012,(S1).
[6]王保健.《聊齋志異》中的胥吏“群丑圖”[J].河南社會科學,2011,19(3).
[7]王緒霞.《史記》中“酷吏”詞義的文化解讀[J].鄭州大學學報,2006,(2).
[8]何春環,何尊沛.《史記·酷吏列傳》之我見[J].貴州社會科學,2003,(1).
[9]張新科.《史記》文學經典的建構過程及其意義[J].文學遺產,2012,(5).
[10]張慧禾.《聊齋志異》對《史記》的繼承與發展[J].語文學刊,2004,(5).
[11]李莎,羅月.《聊齋志異》社會批判之吏治批判[J].赤子(上中旬),2014,(4).
[12]王緒霞.“酷吏”之“酷”辯——兼及傳統法律文化批判[A]//陜西省司馬遷研究會.司馬遷與《史記》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0.
作者簡介:
牛璐瑩,女,山西師范大學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