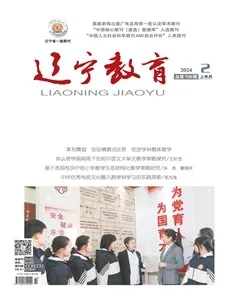優化小學數學作業設計 促進高階思維活動發生
吳秋香 黃畢年


作者簡介:吳秋香,福建省上杭縣第二實驗小學一級教師。黃畢年,福建省上杭縣教師進修學校特級教師,正高級教師。
課題項目:本文系福建省教育科學“十四五”規劃2023年度“協同創新”專項課題“核心素養導向下小學數學大單元作業設計實踐研究”階段研究成果。課題編號:Fjxczx23-126。
摘要:發展高階思維能力是小學數學作業的重要目標。教師應基于布盧姆提出的高階思維能力的內涵特性,變良構為劣構、變碎片為結構、變說教為思辨、變求解為設計,以促進應用、分析、評價與創造等高階思維活動的發生,培養學生數學核心素養。
關鍵詞:高階思維;數學作業;核心素養
高階思維是發生在較強的認知能力和較高的思維水平之上的一種心智活動。美國教育學家布盧姆基于教育目標分類提出了思維水平六層次框架,指出了“識記”和“理解”屬低階思維,而“應用”“分析”“評價”“創造”等層面的認知活動屬高階思維。這種高階思維能力對于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辯證否定的批判性思維、獨立創造和求異創新等認知活動都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有益于學生認知能力的提升和思維的發展。從高階思維的視角探索小學數學作業優化路徑,實質是引導學生以“三會”的眼光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過程,是優化數學作業設計、助力“雙減”落地的重要途徑。
一、變良構為劣構,促進學生“應用”認知活動的發展
布盧姆認為高階思維“應用”層面認知水平是指利用模型或基本概念、原理在不同的情境中進行轉換的能力。“情境”有著良構與劣構之分,美國學者瑞斯尼克深刻地指出:高階思維具有不規則性、復雜性,能夠形成多樣化的問題解決方法,能夠自我調節,具有不確定性等特質。由此可以看出,高階思維孕育于復雜的劣構情境中。為此,數學作業的應用要適時打破封閉的、標準的、定勢的良構情境,置于設有不易操作確定性條件,呈現方式多樣,蘊含多種解決問題方法、途徑的劣構情境中。數學作業的“應用”情境指的是從簡單熟悉情境轉向復雜陌生情境,有利于提升情境的挑戰性、真實性,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首先,教師應變常規為開放,使數學作業中的情境豐富化。數學作業中的“應用”情境不能囿于條件恰好、路徑明確、答案唯一的規范化、標準式的良構設計,也要基于現實生活的特點,注重信息冗余、思考路徑不明、解答方式多樣的劣構設計,使學生的作答從機械模仿的近遷移水平拓展到理性決策的遠遷移水平。
例如,在教學人教版數學教材六年級上冊“用百分數解決問題”時,教師設計了如下兩類作業。
【作業A】往100克水中加入10克糖,求糖水的含糖率。
【作業B】下面的兩杯糖水,哪杯比較甜?你是怎樣思考的?甲杯:往100克水中加入10克糖; 乙杯:將18克糖加到160克水中。
相對于常規、標準、模式化的作業A而言,作業B具有閱讀信息量增大、呈現方式多樣、解題路徑不明、思考空間寬泛等作業情境豐富化的特點,有利于學生深度參與信息的提取、整理、組合、推理等復雜思考過程,多角度、有個性地思考并解決問題。作業B體現了多樣化的解決實際問題策略,讓數學作業的“應用”呈高階思維特性,具有新課標倡導的“學科實踐”特性。
其次,教師應變結果為過程,使學生在數學作業中的思考更深入。數學作業應立足于學生生活實踐,再現復雜的生活情境,使學生的思維起點從“怎么算”的分析問題層面,前置到“先思考怎么辦,再思考怎么算”的提出問題和分析問題層面,經歷生活問題的轉換、抽象、推理等長程式數學化過程。
例如,在教學人教版數學教材六年級下冊“用比例解決問題”時,教師設計了如下劣構性實踐作業。
天安門前的國旗桿有多高?1949 年開國大典升旗時是用的高為22米的旗桿,而現在的國旗旗桿是1991年5月1日重新修建的,高度達32.6米。那么,你知道我們學校的國旗旗桿有多高嗎?請你完成如下任務。
【任務一】小組討論,提出解決問題的設計方案。
【任務二】戶外實踐,記錄解決問題數據,并思考:什么天氣、什么時間測量收集數據最合適?
【任務三】交流展示,共享解決問題成果。
【任務四】思考提升,遷移解決問題方法。
【拓展】如果是陰天,無法利用影長來計算物體高度,還有其他方法嗎?除了用比例的知識解決測量旗桿的問題,還有其他辦法嗎?可以上網、翻閱書籍查找資料,試著用你找到的方法測量旗桿或生活中某一物體的高度,并用圖片與日記的形式記錄下來。
這里,將學生置于“如何求解學校國旗桿有多高”的復雜生活化應用情境中,使學生經歷通過創造性運用比例知識、科學知識等跨學科知識去發現、提出、實踐、解決問題的過程。學生從中學會用數學的眼光觀察現實世界,讓數學作業的“應用”呈現長程式特點,更富有挑戰性、曲折性與多樣性,進而具有培養高階思維的價值。
二、變碎片為結構,促進學生“分析”認知活動的發展
布盧姆指出,高階思維的“分析”層面認識水平是指厘清各部分之間的關聯程度和因果關系,尋找規律。數學是研究“關系”的一門科學,正如認知心理學家布魯納所說,數學學習就是學習數學結構的組織與重新組織,學習結構,就是研究數學結構關系。完成數學作業就是數學學習再發生的過程。作業設計只滿足于學生“會做”碎片化習題是不夠的,教師應引導學生從“發現關系,長出經驗”入手,改變靜態、碎片、零散的單一作業模式,注重動態、結構、關聯的整體設計。教師要樹立數學作業結構化的整體意識,探索“強關聯”的作業群,讓作業目標從“正確解答”提升到“揭示關聯”“尋找規律”,引發高階思維“分析”認知活動的發生。
首先,教師應由表及里,優化單題的設計。數學作業中的單題,不僅要關注顯性的數學知識技能,還要重視數學經驗、數學思想方法等隱性知識的感悟與內化,將學生思維引向“分析”層面,使其生長出數學經驗與智慧。這就要求教師從建構數學關系入手,深入挖掘數學作業題潛在的“分析”價值,引導學生展開多樣化的數學推理,找出關系,發現經驗,揭示規律。
例如,在教學人教版數學教材三年級下冊“兩位數乘兩位數”筆算24 × 13時,教師先設計了習題(如圖1),引導學生思考:(1)A與B相比,誰大?大多少?(2)A、B與C之間有什么關系?從而使學生厘清部分積與部分積、部分積與算式積之間的關系,再筆算。這樣就能使學生跳出筆算的技能訓練,由表及里,強化數量關系的推理,將作業取向從“知道”層面提升到“分析”層面,學生對筆算的算理更清晰、對筆算法則就更熟練,數學運算能力也得到培養。
其次,教師應串點成線,優化作業群的設計。就由多個習題組成的作業群而言,教師不能只關注碎片化作業量的多少,而應關注結構化作業間的關聯。也就是說,作業群要立足整體,重視結構化設計,讓題與題之間蘊含一定的內在邏輯關系。
例如,在教學人教版數學教材一年級上冊“9加幾”時,可設計如下作業。
(1)計算9 + 5,9 + 6,9 + 9,9 + 3,9 + 4……
(2)誰能將上述算式排排隊?你發現了9加幾的“和”與“幾”有關系嗎?
學生在口算題組(1)后, 通過“將上述算式排排隊”,觀察并揭示出9加幾的和“十幾”與“幾”之間關系:十幾的“幾”比加數“幾”少1,因為1和9湊成了“十”,深刻領悟了“湊十法”背后的算理,形成更為抽象、本質的數量關系。此題將學生的思維引向了高階思維的“分析”水平,體現了結構化作業群的力量。
三、變說教為思辨,促進學生“評價”認知活動的發展
布盧姆指出,高階思維的“評價”層面認識水平是根據具體的標準或特定的目的對觀點、方法、資料等作出判斷。可以看出,“評價”是學生對思維活動進行再反省與再思考的過程。在數學教學中,“評價”的意義可以使學生通過追問、補充、表征、遷移,讓數學思維更加深刻、全面、清晰、靈活,為后續的創造性思維奠定基礎。從數學作業中汲取經驗與智慧,不能僅囿于教師的簡單說教,更不能止步于學生的“會做”,而應借助學生典型性作業的思辨資源,使學生駐足回首思一思,議一議,說一說,將數學交流引向“評價”層面,形成批判性思維能力和決策力,提升數學作業的啟思價值。
首先,教師應善于捕捉資源,促進深度學習。教師要基于學生的眼光收集體現學情的典型作業,利用作業中反饋的創新點、獨特點、易錯點、疑問點、盲區等具有批判思辨價值的資源,引導學生有理有據地展開數學交流與對話,引發其思維的碰撞與交鋒。
例如,在教學人教版數學教材三年級上冊“商中間有0的除法”時,教師收集學生的典型錯題后,形成結構性錯題對話資源(見圖2),并引導學生展開思辨。
(1)改一改,這兩道題分別錯在哪?請改正過來。
(2)問一問,觀察改正后兩個豎式,被除數的個位數都是“4”,為什么商的中間卻都有“0”?而商的個位數卻不相同?
(3)想一想,8□4 ÷ 4,商中間為0,想想□里可能是什么數字?
這里,教師根據學生作業中反饋的典型錯題進行辨析、糾錯、追問與思辨,使學生獲得了豐富的活動經驗:商中間有0與被除數中間有0沒有直接關系,而與被除數十位數是否夠除有關系;盡管商中間為0,但由于筆算除法需要第二層十位上落下的數與個位數組合后再除,所以商的個位數可能不相同;商中間有0,被除數的十位數字可能不同;等等。這樣,有利于使學生思考得更全面、更深刻、更辯證,實現議一題,理一組,建一類,呈現深度學習的“價值與判斷”特征,更富有高階思維的“評價”價值。
其次,教師應善于點撥跟進,彰顯學科本質。在數學作業的思辨交流中,教師要發揮主導者角色,以教助學,把學生的思辨引向學科本質、核心概念、思維方式及基本觀念等“大概念”層面,讓數學作業的“評價”活動彰顯學科本質。
例如,在教學人教版數學教材四年級下冊“小數的性質”時,對于“小數點的后面添上0或者去掉0,小數的大小不變”這一結論,教師只使學生舉例(0.3≠0.03)來認識到錯誤是不夠的,還應適時跟進,從計數單位的核心概念入手,引導學生說理:0.3小數點的后面添上0得0.03,為什么小數的大小變了?你能結合計數單位來說理嗎?從而讓學生認識到0.3變成0.03,計數單位縮小到原來的十分之一,而計數單位的個數不變,所以這個小數變小了。這樣,從數的概念本質入手展開“評價”活動,圍繞著計數單位的“大概念”進行思辨與說理,數學“評價”活動就能直抵小數基本性質的概念本質,更顯批判性與思辨性。
四、變求解為設計,促進學生“創造”認知活動的發展
布盧姆指出,高階思維的“創造”層面認識水平是指將要素組合成連貫的整體,完成新模型或新結構,設計完成任務的方法或創作一個新產品。這里,強調學生根據新模型或新結構,完成相應“設計”與“創作”的作業,指向教育目標最高認知水平——“創造”。評價學生對數學學習的建構水平,不能只看學生是否會正確地解答一般性常規問題,而是應看學生基于數學理解與推理的表現性活動。因此,數學作業的認知取向,應在“評價”基礎上,變“求解”為“設計”,即創設學科實踐運用情境,引導學生將數學學以致用,靈活遷移,參與“設計”或“創作”等表現性活動, 指向數學的“創造”層面,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能力,提升學生的元認知水平。
首先,教師應注重在真實情境中實踐。數學教學要引導學生在探索真實情境所蘊含的關系中發現問題和提出問題,運用數學和其他學科的知識與方法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這就要求教師基于真實情境設計數學實踐性作業,使學生在實踐中進行數學表達與創造。
例如,在教學人教版數學教材五年級上冊“平行四邊形的面積”時,教師可跳出“根據給定的平行四邊形的底和高有關數據求面積”的一般性作業框框,呈現如下真實情境的作業:請設計一個面積為18平方米平行四邊形車位,并說說你的設計理由。學生根據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公式和對小車車型、尺寸的了解,設計出了不同的小車車位:有的是a = 3 m,h =6 m;有的是a = 5 m,h = 3.6 m……。這里,教師引導學生變正向求解為逆向設計,從表現性實踐運用角度評價學生對數學公式的運用水平,讓數學作業從“解答”走向了“創造”,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其次,教師應重視在開放情境中構題。數學概念不僅可以用于數學問題的求解,也可以用于數學問題的重構。相對于前者的正向思維而言,后者的逆向思考,更趨挑戰性、開放性,更具創造性思維的價值。教師要創設開放情境,使學生主動探索,利用已有的數學經驗學會逆向設計與構題。
例如,在教學人教版數學教材五年級下冊“分數的意義”時,關于單位“1”的作業,僅使學生識記“‘一個物體’‘一個計量單位’‘許多物體組成的一個整體’都可以看成一個整體,用單位‘1’表示”是不夠的,教師還可以設計以大問題為驅動的作業,促使學生重構單位“1”的概念。
師:這些圓片可以用哪些數來表示?你是把什么看成一個整體的?○○○○○○
這樣,學生在開放的大問題情境中,多樣化完成作業,重構單位“1”概念,進一步強化單位“1”可以是1個,可以是多個,還可以不足1個,在親歷創造中豐富對單位“1”的理解,發展了數感,培養了創造性思維能力。
總之,教師要基于高階思維的“應用”“分析”“評價”“創造”等思維層次的特定內涵,優化數學作業設計,培養學生的數學學科核心素養。
參考文獻:
[1]布盧姆. 教育目標分類[M]. 羅黎輝,譯.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
[2]姚小琴. 高階思維“核心素養”導向的數學教學[J]. 數學教學通訊, 2018(10).
(責任編輯:楊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