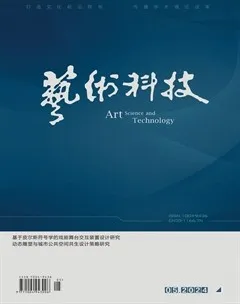徽州人物木雕的文化內涵探究
摘要:目的:位于安徽省黃山市黟縣盧村的志誠堂廣泛運用了木雕裝飾,紋樣類型題材眾多,在同時期的徽派建筑中十分突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它集中體現了徽派木雕的文化內涵和藝術特點。文章聚焦志誠堂的人物木雕裝飾圖像,挖掘徽州人物木雕的文化內涵,旨在加強大眾及相關研究者對盧村志誠堂木雕藝術價值和文化價值的認知。方法:采用田野調查法,搜集志誠堂相關資料,深入了解徽州木雕的發展脈絡以及志誠堂木雕樓中人物木雕的藝術特色。梳理志誠堂中的人物木雕題材、裝飾部位以及功能,比較研究志誠堂木雕人物背后的文化內涵。結果:志誠堂人物木雕作為徽派建筑中的構件,既具有藝術美感,又兼顧實用功能。志誠堂人物木雕的主題和形象充分體現了徽州特有的文化,成為儒家文化和民俗文化的重要載體。結論:徽州人物木雕并不是獨立的雕塑藝術作品,而是建筑裝飾構件的一部分,實用性與審美性兼具;徽州人物木雕體現著傳統儒家文化與徽州民俗文化,內涵豐富;徽州人物木雕在形式上具有民間性,在內容具有世俗性,儒家思想的滲透使其產生雅俗共賞、亦精亦樸的文化特質,具有極高的審美價值。
關鍵詞:志誠堂;人物木雕;文化內涵
中圖分類號:J31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4)05-000-03
0 引言
位于安徽省黟縣盧村的著名徽派建筑——志誠堂,有著“徽州木雕第一樓”的美譽,內部結構和木雕狀態保存相當完整,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其建筑物上的精美木雕更是蜚聲中外。志誠堂的木雕裝飾與其他同時期的徽派建筑一樣,雕刻技藝成熟,風格協調統一。在志誠堂繁多的木雕裝飾中,制作最為精美且引人矚目的莫過于琳瑯滿目的人物木雕,這些人物木雕中蘊含著豐富的民族文化和傳統的審美觀念。
1 徽州木雕與志誠堂人物木雕概述
元末明初,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皖南徽商崛起,一些富有的徽商回鄉后置地造宅。為了提升建筑物的精美程度,他們多以木雕、磚雕、石雕等民間手工藝來裝飾,形成獨具特色的徽派建筑,木雕技藝初具規模。早期的徽州木雕以淺雕和浮雕為主,造型圓實古樸。徽州木雕發展到明朝中期至清朝初期,逐漸過渡到精雕細刻和多層透雕的風格,裝飾手法日益復雜。清朝是徽州木雕的鼎盛期,注重視覺美感和實用功能的統一。在清晚期的一段時間里,徽州木雕則以精雕為主。
盧村是以盧姓為主聚居的古村落,清道光年間,盧氏三十三代傳人盧邦燮建造,由“七家里民居”組成的木雕樓群,包括志誠堂、思濟堂、思成堂等宅院。盧邦燮早年經商,家富百萬,人稱盧百萬,后轉入仕途做官,官至奉政大夫、朝政大夫。在盧村的建筑群中,以志誠堂木雕最為豐富精美,很好地體現出清中晚期徽州木雕鼎盛時期的藝術風格。踏入志誠堂室內,就會被其琳瑯滿目的木雕所吸引和震撼。門窗、欄桿、雀替、梁枋、斜撐等建筑構件的木雕形象變化萬千,繁簡交替,令人驚嘆。
總體來看,志誠堂的木雕題材可以分為人物、動植物、圖案紋樣三種類型。其中人物紋樣木雕最多,題材廣泛。人物形象多以寫實為主,外形樸拙生動,表情天真爛漫,多做喜樂之態,動作具有戲曲舞臺風格,具有獨特的民間藝術趣味。
2 人物木雕的種類及裝飾部位
志誠堂的人物主題木雕從題材上可以分五類:一是如群童鬧春、漁樵耕讀等世俗生活場景;二是刻畫如陶公醉酒、羲之戲鵝、伯樂相馬等歷史故事;三是如桃園三結義、三英戰呂布等著名故事;四是如二十四孝圖、蘇武牧羊等忠孝節義題材;五是如八仙過海、太公釣魚、洞賓升天等神話傳說故事。
志誠堂的人物木雕主要裝飾部位主要有:隔扇上的中心盤、腰板和裙板,檻窗的腰板和裙墻,花窗的裝飾性花板,以及斜撐的大部分。
2.1 隔扇
隔扇是徽派建筑中常見的建筑構件,又稱蓮花門。隔扇既有窗的作用,又有墻、門的作用,可以對外進行圍護,對內進行分隔,也可以發揮采光、通風等基礎作用。這種高而長的隔扇左右相連,一扇接一扇,一般多為雙數,以保證房屋的中央是可以開啟的兩扇隔扇門[1]。志誠堂的隔扇是人物木雕的主要載體,主要分布在前廳東西兩廂房和天井東西兩側的過廂,以及后廳天井東西兩側過廂和東書房。
隔扇可以分為眉板、胸板、中心盤、腰板和裙板五個部分,人物主題集中在中心盤、腰板和裙板上。中心盤面積較小,雕刻較為簡略,前殿東西兩側的中間圓盤上刻有二十四孝的故事,以告誡子孫后代要對長輩盡孝,體現以孝道為核心的傳統禮制文化。腰板與人的視線平齊,因此須以深浮雕的形式精細雕刻,可供觀者細細品味。下方的裙板面積較大,為淺浮雕,工匠發揮空間較大,多雕刻有歷史典故,附以大面積植物、建筑、山川為背景,與人物共同組成畫面。
前廳西側裙板上的典故依次為:買臣負薪、東坡賞菊、管仲夜讀、蘇武牧羊、韓愈招親、李白醉酒、陶公歸隱、羲之戲鵝。東側裙板上的歷史故事依次是:學富五車、陶公醉酒、伯樂相馬、洞賓升天、對弈手談、進京趕考、太公釣魚和高山流水。這16幅作品濃縮了中國的歷史文化、中華民族的思想與品格,彰顯著主人的文化品位。
2.2 檻窗
檻窗,又稱半窗。與隔扇部門結構相似,檻窗由眉板、胸板、中心盤、小腰板、大腰板、木墻裙組成,缺少裙板,取而代之的是木制的板壁或短墻,因此檻窗僅具備窗的功能。
志誠堂正廳檻窗東西兩側的小腰板上雕刻著“群童鬧春圖”,共計12塊,為多層深浮雕。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百子圖寄托著“多子多福”的期望。據記載,主人盧邦燮一生共娶了六房妻妾,育有16個女兒和8個兒子,正是“多子多福”的完美演繹,而志誠堂就是盧邦燮大房和二房以及父母的居所。每塊腰板上的兒童活動各不相同,淋漓盡致地反映了徽州地區的兒童生活、民俗活動等。
小腰板下方為大腰板,為了與下方的木墻裙和上方的小腰板協調,長度增加,東西兩邊各三片,以深浮雕為主,東西兩側的左右四片是名著《三國演義》中的經典故事三英戰呂布,畫面中人物形態各不相同,將傳神的人物動態與激烈的戰斗場面很好地展現了出來。與戰爭的激烈不同,剩余的中間兩片是“漁樵耕讀”等閑逸恬靜的內容,徽州傳統的風土人情得到了生動再現。大腰板下為木制墻裙,東側為九老圖,采用淺浮雕手法雕刻,以蝙蝠、鹿、九老仙人、喜鵲圖象征“福祿壽喜”。西側雕刻著竹林七賢圖,以淺浮雕和陰雕走線,高雅傳神,左右各有喜鵲兩只,合在一起即有“四喜登門”的吉祥寓意。
2.3 花窗
花窗是徽州民居的特色門窗,又稱遮羞窗或小姐窗,其作用是為了避免客人從外面直接看到室內。志誠堂的花窗分上下兩部分,上面部分是鏤空裝飾,下面部分為實心裝飾的花板。人物雕刻主要集中在花板的上半部分,著重表現征戰的場景,與小姐閨房的寧靜安逸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2.4 斜撐
“斜撐是在檐柱外側用以支撐挑檐枋的建筑構件,其上部是由柱子伸出的挑枋承托挑檐枋。主要起到支撐建筑外挑木、檐與檁之間的承受力作用,使外挑的屋檐達到遮風避雨的效果,又能將其重力傳到檐柱,使其更加穩固。”[2]志誠堂正堂上四個方向有八個斜撐,刻有不同的八仙故事,人物都略微前傾,姿態生動,但其臉部被毀壞,破壞了木雕的完整性。將八仙置于斜撐上,象征著人們對天降祥瑞的美好愿望。
3 功能價值與文化內涵
儒家思想傳遞出“文質彬彬”的裝飾意向,強調裝飾對禮儀教化的作用。裝飾藝術發展到明清時代,吉祥寓意的裝飾題材被廣泛運用在各類民間藝術品上,成為民間裝飾活動的主流紋樣。“徽州人物木雕也離不開祥瑞題材的體系,對趨吉納福的內容幾乎無所不包,凡人間求福祈壽,預卜夫妻百年好合、生子主貴、考試中取、升官晉級、經商發財、金玉滿堂、五福臨門等人間福善吉祥之事,可謂一應俱全。”[3]具象的圖像成為徽商寄托人生理想價值和審美趣味的重要載體。志誠堂的人物木雕裝飾注重寫實風格和實用功能,是體現徽州文化的獨特場域。
3.1 傳播儒家思想的重要渠道
志誠堂內的建筑構件,從其表現手法、風格和題材來看,突出了儒家思想中禮制倫理的傳統美學觀念。徽州人崇尚新安理學和徽派樸學,在淳厚的儒家思想影響下,徽商們多“賈而好儒”,重文教。徽州人的禮制思想,源自程朱理學。為了適應“禮”的需求,徽州人物木雕作為一種建筑裝飾,跟整體建筑一同發揮著傳播儒家思想的作用。如在禮制文化的引導下,廳堂是最尊貴顯赫的地方,尤其是正廳的布局,寬敞明亮,多人物木雕,精巧繁密,營造出莊重富貴的氣勢,用于主人待客和議事,實現了功能性與觀賞性的高度統一。
作為儒商的典型代表人物,志誠堂的主人盧邦燮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嚴格遵守傳統的儒家禮儀。因此,在志誠堂的人物木雕藝術形象中,有大量體現儒家思想的故事題材,如表現“忠孝義節”的儒家倫理。漢代提倡“舉孝廉”,以孝治國;到了程朱理學時代,孝悌觀念更是根深蒂固,人們通常將孝悌倫理作為禮儀道德的核心,不可僭越。志誠堂正廳左右兩側隔扇的中心盤上的“二十四孝圖”,集中體現了儒家孝悌思想,用孝子孝女的故事發揮教化作用。另外,儒家思想也很注重忠孝兩全,這一點也體現在志誠堂的人物木雕上。如裙板上的“蘇武牧羊”,蘇武身上的民族大義精神即為“忠”,同樣具有重要的教化作用。“陶公醉酒”“東坡賞菊”等經典文人故事,均展現出儒家的思想境界,內涵深刻。值得一提的是,志誠堂中關于讀書的人物木雕是最多的,如“五子登科”“漁樵耕讀”等。儒家自孔子辦學以來就尤為重視讀書,盧邦燮受讀書之益,成為一位成功的商人,后又出仕為官,自身經歷使得他認可讀書的重要性,并且希望自己的子孫后代能夠通過勤奮讀書,最終成就一番事業,光宗耀祖。因此,盧邦燮用大量的讀書題材人物木雕裝飾,意在教化子孫后代,同眾多徽派建筑特色一起建立起徽州人以“耕讀傳家”為特色的傳統文化底蘊。
3.2 民俗文化的重要載體
志誠堂建于徽商文化發展最鼎盛的時期,受到民間“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的說法影響,盧邦燮同很多徽商一樣,將自己的財富轉化到徽派建筑的一磚一瓦上,因此徽州木雕裝飾內容具有非常顯著的世俗化特征,形式上也頗具民間性,避免了低俗和庸俗。制作木雕的工匠通常會采用諧音、象征手法表達人們對富貴、吉祥、平安、長壽的美好愿望,并起到一定的教育意義,使代表吉祥的民俗文化成為徽州人物木雕藝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民間藝術中,最常用諧音方式將人們的愿望或理想表達出來,也常用象征手法,傳達一個物品或一組畫面背后的意義。志誠堂木雕經常有多種形象的組合,如松樹和仙鶴放在一起象征“松鶴延年”,喜鵲、梅花寓意“喜上眉梢”,空中飛舞的蝙蝠則寓意“福自天申”。在志誠堂的人物木雕中,象征的表達方式使用較多,盡管前文提到志誠堂處處滲透著主人盧邦燮的儒生品位,但志誠堂的木雕作品仍然離不開民俗文化的影響。盧邦燮并不滿足于傳統吉祥圖案裝飾,他會利用不同物象的象征寓意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和追求,展現自己豐富的精神世界,抒發內心的情感。因此,志誠堂的木雕也有一些雅俗共賞的人物題材,內容較之吉祥圖案顯得更加含蓄委婉,如“高山流水”高雅氣質,“買臣負薪”刻苦攻讀,還有牧童放牧的勞作之趣等等。這是眾多徽商的普遍性心理,與徽派建筑的其他藝術門類以及徽州民間信仰相互交融,都是其生活環境的真實寫照。
4 結語
本文從追溯徽州木雕技藝的歷史發展出發,結合志誠堂主人盧邦燮的生平,探尋志誠堂人物木雕的時代背景,依據人物木雕的題材種類和裝飾部位分析解讀徽州木雕的文化信息。志誠堂每一件精美的木雕作品,都展現了主人盧邦燮生動的精神世界,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
參考文獻:
[1] 徐華鐺.中國傳統門窗木雕[M].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10:27.
[2] 宋博.安徽盧村志誠堂木雕裝飾藝術研究[D].蘇州:蘇州大學,2012.
[3] 王樹林.中國民間美術史[M].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4:541.
作者簡介:張紹洋(1994—),女,安徽六安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藝術品鑒藏與市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