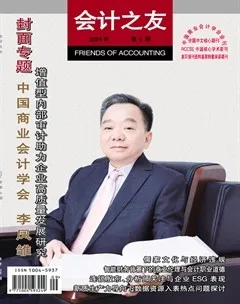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的演進與展望
候丹丹 丁瑩
【摘 要】 為確保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的規范運行和高質量發展,2023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規范實施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新機制的指導意見》。該文件明確了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新機制的總體要求、實施規范、運營監管和政策保障,開啟了新形勢下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高質量規范化發展的新篇章。文章在梳理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發展歷程和現狀的基礎上,對該文件進行詳細解讀,系統分析了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新舊機制之間的差異,提出了未來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發展的方向和建議,為政府部門推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高質量發展和公共治理體系改革提供一定的參考。
【關鍵詞】 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 PPP新機制;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 F23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24)09-0148-08
一、引言
伴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推進,以基礎設施為代表的公共產品需求呈持續增長趨勢。然而,傳統由政府主導的公共產品供給模式受到了財政資金有限、投資渠道單一、風險控制不足等多種因素的制約,導致供需缺口持續擴大。因此,探索一種更加高效和可持續的投融資模式成為政府和社會各界的迫切需求。
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是指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為滿足公眾對基礎設施或公共服務的需求而建立的長期合作關系[1]。PPP模式秉承“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合作共贏”原則,對于充分發揮政府職能、合理激發社會資本積極性與創造性、打造新經濟增長點具有重要意義。因此,PPP模式被視為基建投融資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截至2022年11月底,財政部PPP在庫項目總數已達10 363個,涉及投資額高達16.8萬億元①,覆蓋交通運輸、市政工程和環境保護等19個行業。在未來的較長時期內,以PPP模式為基礎的公共項目建設和服務提供仍將是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主要推動力之一。
PPP模式在我國實施以來,一定程度上發揮了優化公共項目投資效率、改善基礎設施建設、提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2],但在實踐中也出現了社會資本結構失衡、地方政府財政風險攀升等亟待解決的問題。2022年,《國務院關于2022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中指出,我國PPP項目存在入庫環節審核不嚴、履約環節不盡誠信、建設運營環節不當推責攬責等問題②。截至2022年6月底,151個PPP項目進展緩慢、停工甚至爛尾,造成國有資產損失高達17.22億元③。2023年2月,根據審計部門對PPP項目審計的結果,全面暫停了PPP項目的相關管理流程。2023年11月,《關于規范實施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新機制的指導意見》(國辦函〔2023〕115號,以下簡稱《新機制》)正式對外發布,標志著PPP模式在歷經九個月的停擺后,正式拉開了重啟的序幕。《新機制》在吸取以往PPP模式實踐經驗基礎上,重新確定了PPP模式的實施原則、總體要求等,對后續PPP模式規范實施提出了新的指導意見。
在現有研究中,學者們針對PPP模式的理論內涵、風險管理、影響效應等進行了深入研究[3-5],并提出了諸多有益的建議,為PPP模式在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指導。然而,盡管PPP模式在多個方面已經得到了廣泛探討,但在新的歷史時期,特別是在《新機制》發布后,PPP模式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如何更好地把握新機制的核心要義和實踐要求,如何在新的政策環境下優化PPP模式的實施策略,尚需進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討。基于此,本文在總結我國PPP模式發展歷程和發展現狀的基礎上,對《新機制》的內涵、新舊模式之間的差異以及PPP模式的未來發展趨勢進行了探討。研究旨在更全面地理解PPP新機制,繼續完善PPP模式頂層制度設計,推動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可持續發展。
二、《新機制》提出的背景
(一)我國PPP模式的發展歷程
PPP模式最初在英國誕生。為了更好地適應國內環境和需求,我國在引進PPP模式時對其頂層制度進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和優化。以不同時期的政策導向作為劃分依據,國內PPP模式發展大致經歷了初步探索、快速推進、規范調整、深化優化四個階段。
1.初步探索階段(1984—2013年)
1984年,深圳沙角B廠項目的建立標志著中國開始探索并推動PPP項目,以促進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發展。在1984—2002年間,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政策的深入實施,我國吸引了部分外資嘗試性地進入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外商參與和國際化運作模式促進了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引進,為PPP項目的發展和改革奠定了基礎。隨后,在2003—2008年間,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上升周期,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的需求日益增長,進一步推動了PPP模式的發展。然而,與早期相比,PPP投資中的外資企業比重有所下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6]。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為刺激有效需求,中央政府推出了4萬億刺激計劃,其中1.5萬億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巨額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經濟下行壓力,但也對PPP項目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導致許多PPP項目轉為政府投資,PPP市場陷入低谷。直至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允許社會資本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基礎設施建設后,PPP市場逐漸回暖,并衍生出上市、企業債、信托等多元化融資渠道。總體而言,這一階段的PPP項目運營主要以“建設-經營-轉讓”模式為主,回報機制以可行性缺口補助和使用者付費為主導,并集中在市政工程、交通運輸、能源、醫療衛生等領域。
2.快速推進階段(2014—2017年)
2014年,《財政部關于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有關問題的通知》正式提出了PPP概念。同年,財政部和發改委印發了相關文件,指導PPP模式的實施和運用,標志著PPP進入了快速推進階段。伴隨著前期PPP項目的陸續落地和新型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政府對PPP模式的支持愈發顯著。僅在2014年和2015年,政府就相繼出臺了28部和58部與PPP相關的政策文件[7],并建立了全國PPP綜合信息平臺。這一系列政策的出臺旨在為PPP項目提供更為清晰的政策框架和更具操作性的指導,從而鼓勵社會資本更加積極地參與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各地政府也積極響應中央政策,推動了一大批PPP項目的啟動和實施,使得2014—2017年間的PPP項目數量持續增長。在這一階段,除傳統的BOT模式外,ROT、TOT、BOO等多元化的實施模式也逐漸被采用④,主要涉及市政、交通、生態、環境、城鎮開發、水利建設、教育、旅游等領域。然而,在PPP規模迅速擴張的同時,也暴露出了模式泛化、落地困難、政府隱性債務增加等一系列問題。
3.規范調整階段(2018—2022年)
在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和嚴防新增政府隱性債務的大背景下,2017年11月,《關于規范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綜合信息平臺項目庫管理的通知》的發布,標志著PPP正式進入了規范調整階段。各部委對PPP項目的入庫標準、前期論證、陽光運行等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規范性要求,提高了PPP項目合規門檻,遏制了PPP模式泛化濫用現象,確保其回歸優化公共服務的本源。財政部對PPP項目也進行了大規模清理,2018年共清退PPP管理庫項目2 557個,涉及投資額3萬億元⑤。同時,對新增PPP項目持審慎態度,PPP項目新增數量和落地速度整體放緩。總體而言,在這一階段,政府逐漸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現有規則的修正和已有項目的盤整之上。
4.深化優化階段(2023年至今)
2023年2月,我國運營數十年的PPP模式首次進入“停擺”狀態。2023年11月初,《新機制》的出臺重新定義了PPP模式的運作框架。《新機制》通過整合各部門的職責,減少繁瑣的審批程序,精確調節民營資本的參與度等措施,以有效提升項目決策效率,實現效率與公共利益的平衡。這標志著PPP模式邁入了一個更加注重規范化、透明化和可持續發展的深化優化階段。
(二)PPP模式發展隱患
1.PPP模式中的公私失衡:民企邊緣化與結構沖突
在公私合作(PPP)的本意中,私營部門的核心構成應是民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實體[8]。這些經濟實體以其靈活性、創新力和效率,可為PPP項目注入活力和動力。然而,在實踐中,PPP模式存在一種公私失衡的現象,即國有企業逐漸成為PPP項目中私營部門的主導力量(如圖1所示)⑥。在中國的經濟體系中,公有制經濟占據主體地位,基礎設施一般遵循公建公營的傳統做法,這對PPP模式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盡管民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在資金實力、融資能力和風險承受能力等方面,常常面臨諸多挑戰。這些挑戰導致地方政府在選擇PPP項目合作伙伴時,更傾向于同資金實力雄厚、融資渠道廣泛的地方國有企業合作。這種“公公合作”的現象不僅對PPP項目中的民營企業產生了擠出效應,加劇了PPP項目中社會資本結構的不均衡性,還可能會增加國有企業在獲取項目機會時的腐敗行為[9],進而引發資源分配不公平、信息不對稱、資金不透明和監管不力等一系列連鎖問題[10-12]。這不僅不利于提高公共服務效率和緩解地方財政約束,而且會進一步加劇經濟結構的失衡,阻礙整體經濟可持續發展。
2.PPP模式中的治理困境:制度不健全與監管執行不力
在PPP模式中,制度不完善和監管執行不力會導致PPP陷入治理困境。在制度體系層面,我國尚未對PPP進行專門立法,PPP項目的推進主要依賴于政策性文件,而非具有強制法律效力的法律法規。這種情況帶來了一系列潛在的問題和挑戰。首先,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框架,項目的合作方可能面臨法律關系不明晰、權責不清的情況,增加了合同履行的不確定性,降低了合作方的法律保障。其次,政策性文件的可操作性和執行力相對較弱,可能導致PPP項目的推進易受到政策變動的影響。在缺乏法律約束的情況下,政策的不穩定性使得私營部門在項目中面臨更大的風險,影響其投資積極性。在項目監管方面,PPP項目存在監管內容單一、監管權力分散和社會監督不足的問題。其中,監管內容的單一主要表現在現有PPP監管內容相對于項目生命周期而言較為狹窄。我國PPP項目監管可分為準入監管和績效監管兩個階段[13]。準入監管關注項目的選擇和審核,但仍主要局限于行政審批程序和社會資本方的資質評審,而未充分涵蓋項目建設和運營中的實際執行情況。績效監管側重于對項目實施效果的評估,但由于評估標準和指標的單一性,可能無法全面評估項目在經濟、社會和環境等方面的影響。相對狹隘的監管范圍難以全面覆蓋PPP項目中的各個環節和領域,使得監管部門難以及時發現和糾正項目風險。監管權力的分散性是指我國PPP項目的監管權力分散在財政部、發改委、行業主管部門等多個部門和機構之間[14]。不同監管主體具有獨特的監管職責和重點,監管要求的不一致性和沖突給社會資本方帶來額外的合規負擔,如發改委注重PPP投資監管,力圖通過PPP推動經濟發展,而財政部注重PPP預算,強調對PPP資金的風險管控[14]。分散的監管結構容易導致監管職能重疊、溝通不暢和監管空白,增加項目合規風險。社會監督不足體現在監督渠道不暢、意識不強和機制不完善等方面。監督渠道不暢使得公眾難以獲取項目信息并提出疑慮,限制了社會監督的廣度和深度;監督意識不強導致公眾對項目的關注程度不足,使得社會監督缺乏足夠的動力和影響力;監督機制不完善嚴重制約了社會監督的有效性,缺乏健全的投訴處理和問責機制,使得公眾的監督意見無法得到及時、有效的回應和處理。
3.PPP模式中的債務隱憂:項目盈利能力較弱和地方財政風險攀升
PPP項目雖然為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開辟了一條創新途徑,但其中存在的債務隱憂仍不容忽視。首先,PPP項目通常具有資金需求量大、項目周期長、投資風險大等特點。因此,項目收益的穩定性至關重要。然而,我國PPP項目中,使用者付費占比不足10%(如圖2所示)。這意味著項目收益主要依賴于政府補貼,項目自身的市場化盈利能力相對較弱。因此,項目對政府政策變動極為敏感。無論是政府財政狀況的波動還是政策的調整,都可能對項目的長期資金保障產生不利影響,進而增加項目運營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其次,雖然PPP模式為地方政府提供了多元化的融資渠道,但不恰當的融資操作,如過度依賴政府信用背書、融資結構不透明、風險評估不足等,均可能使PPP項目轉化為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風險,進而威脅財政的穩健性和可持續性[15]。由于我國PPP項目的擔保體系、融資渠道、風險分擔機制等市場化融資體系尚未健全,各地區PPP項目的實際執行中出現了政府兜底、固定回報、明股實債等變相舉債和違規擔保操作行為[16-18],極易透支財政未來支出責任,引發隱性債務風險增長[19]。
三、《新機制》內涵分析
(一)新機制的核心要義
《新機制》系統全面地提出了未來PPP項目合作的新規則,具體體現在聚焦使用者付費、調動民間資本積極性以及重構特許經營全周期管理流程等關鍵方面:
1.市場化改革新路徑:聚焦使用者付費PPP項目
《新機制》指出未來增量PPP項目應聚焦于使用者付費機制。使用者付費機制的核心在于通過向最終用戶提供服務并收取費用來實現項目的自我維持和盈利。對于政府而言,使用者付費機制有助于推動政府從主導者轉變為監管者和支持者,進而轉移項目風險,釋放財政資源,實現公共服務領域的有效管理。對于社會資本方而言,使用者付費機制有助于激勵其更加關注市場需求,通過創新和提升服務水平來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進而吸引更多用戶,實現良性競爭和可持續盈利。在實踐中,使用者付費項目能否順利實施極易受到市場需求、定價和收費機制的合理性、使用者的支付意愿、政策環境不確定性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因此,為推動《新機制》的順利落地,政府不僅需要提升政策制定和監管能力,如明確監管標準、規范項目管理流程、加強信息透明度等,還應當制定相應的激勵措施,以鼓勵社會資本方更好地履行其監管和服務提供職責。社會資本方則需要在項目設計階段更加深入地了解市場需求和用戶支付意愿,靈活調整項目定價和收費機制,以確保使用者付費機制的順利實施。
2.公私合作新生態:優先支持民營企業
《新機制》不僅倡導民營企業積極參與到公共項目的建設和運營中來,而且在充分考量行業屬性、項目類型和民營企業專業能力的基礎上,首次編制了《支持民營企業參與的特許經營新建(含改擴建)項目清單(2023年版)》,為民營企業參與不同領域的PPP項目提供了具有針對性的參與規則和參與指引。清單的動態調整機制也體現了政府對于市場變化的靈活應對,以確保民營企業參與PPP項目的適應性和可持續性。通過鼓勵并規范民營企業的參與,政府可以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推動PPP項目向更加市場化、高效率的方向發展,同時也為民營企業創造了更多的商機和發展空間。總體而言,《新機制》不僅是2017年《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鼓勵民間資本參與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的指導意見》(發改投資〔2017〕2059號)的升級和細化,更是落實202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的重大舉措,為打破市場壁壘、促進PPP項目的健康發展奠定了基礎,營造了更加有利于公私合作的新生態。
3.特許經營新篇章:職責分工和流程重構
《新機制》明確未來PPP項目全部使用特許經營模式,這一決策標志著我國在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融資模式邁出了新的步伐。通過明確發改委、財政部、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等部門在特許經營項目中的管理職責分工,《新機制》確保了項目從規劃到實施的各個階段都能得到高效有序推進。同時,《新機制》對特許經營管理流程進行了重構,將特許經營項目周期管理分為建設實施和運營監管兩大階段。項目建設實施階段應重點關注特許經營方案審核、資金籌措、建設實施等環節,確保項目能夠按照既定的標準和質量要求高效推進。在項目運營監管階段,則應更加注重通過建立健全的監管機制和項目運營評價機制,確保項目在運營過程中能夠持續、穩定地為公眾提供優質服務。
(二)新舊機制的核心差異
相較于以往的PPP模式,《新機制》在管理主體、職責分工、信息披露、實施機構、實施模式、實施期限、實施流程及社會資本方選擇等方面展現出顯著的不同。為了推進新機制的順利實施和確保政策的一致性,《新機制》廢止了以往發布的11個與PPP相關的文件。這些變革不僅體現了政府在公共項目管理上的創新思路,也為社會資本方提供了更為明確和規范的參與路徑,有助于推動PPP模式的持續健康發展。具體如下:
1.項目管理主體、職責分工和信息披露平臺
2016年7月,國務院常務會議確認了發改委和財政部在PPP領域的主管職能分工,即發改委負責基礎設施領域,財政部負責公共服務領域[6]。隨后,兩部委相繼出臺了一系列重要文件⑦,進一步推動和規范PPP項目的實施。從已發布的文件來看,財政部基于債務控制和預算管理,從政策制定、操作指引和示范項目三個層次依次推進PPP相關工作,對PPP項目的前期論證、風險管理、績效評估,以及政策紅線的劃定給予了相對明確的指導意見。發改委則主要著眼于政府投融資體制改革,推動項目落地,優化管理,提高審批效率。為此,財政部成立了PPP綜合信息平臺(以下簡稱“財政部PPP平臺”),其主要職能是提供全面的PPP項目信息服務。發改委則是依托全國投資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臺,上線了PPP項目信息監測服務平臺(以下簡稱“發改委PPP平臺”),借助一項目一代碼的管理原則,實現項目前期手續辦理情況實時更新,側重于對項目信息的監測和監管。截至2022年底,財政部PPP在庫項目總計14 038個,總投資額20.92萬億元;發改委PPP項目共8 057項,總投資11.60萬億元⑧。兩部委共同管理PPP項目的模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發揮各自的專業優勢,推動PPP項目的發展,但也在實踐中暴露出政策不協調、立場不一致等弊端[20-21],如兩部委的PPP信息管理工作呈現信息孤島、數據標準不統一的局面[21],未就各自所管理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領域進行詳細界定等問題⑨。
《新機制》指明發改委成為PPP主要牽頭部門,地方政府承擔項目主體責任,財政部門負責預算、債務管理及財會監督等相關職能,并明確未來PPP項目相關信息將在發改委PPP平臺上一體化公開。同時,《新機制》取消了財政部PPP信息平臺,終止了長達數十年的財政部PPP項目示范工作,并廢止了財政部PPP信息平臺中項目庫、專家庫、咨詢機構庫相關管理文件和財政部PPP項目示范工作相關政策文件。在《新機制》中,組織架構的調整捋順了PPP模式中的權責關系,有望通過更為明確的職責分工和專業化管理,提升項目推進的效率和質量。信息平臺的統一也使得相關部門可以更加便捷地獲取項目的實時數據和信息,對PPP項目進行更加及時和有效的監管,這有助于預防和糾正PPP項目中的潛在問題,保障項目的順利實施。
2.項目實施機構、實施期限、實施模式和實施流程
(1)在項目實施機構的選擇方面,原PPP模式中各部委發布的相關文件存在一定的差異性。財政部相關文件中指出政府、有關職能部門、事業單位可作為項目實施機構⑩。而發改委指定行業管理部門、事業單位、行業運營公司或其他相關機構作為實施機構?輥?輯?訛。在實踐中,行業運營公司和其他相關機構能否成為實施機構一直存在爭議。部分國有企業、政府平臺公司在不能以社會資本的身份參與PPP項目時,仍在尋求以實施機構的身份參與PPP項目[22-24]。《新機制》明確了行業主管部門和事業單位作為項目實施機構的地位,統一了實施機構的認定標準,這體現了政府對項目實施專業性和有效性的高度重視。這一規定有助于通過構建更為合理和規范的實施體制,降低實施過程中的不確定性,進一步推動PPP項目的規范執行。
(2)在項目實施期限方面,原PPP相關文件中指出PPP合作期限原則上不低于10年,不超過30年?輥?輰?訛。《新機制》將項目期限延長至40年,突破了原特許經營期限最長30年的規定。期限的延長一方面可以減輕社會資本方面臨的短期風險,增加項目的預期收入額度,保障特許經營者的投資回報;另一方面也會導致項目運營、維護等資金成本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對社會資本方項目運營能力的要求。
(3)在項目實施模式方面,在原PPP模式中,按照付費機制,PPP項目可分為基于使用者付費的特許經營模式和基于政府付費的私人融資計劃模式。這兩種模式有其各自獨特的優勢。特許經營模式通過將設計、建設、運營和維護風險轉移給私營部門,降低了政府的財務負擔,同時激勵私營部門提高項目效率和創新性。而私人融資計劃模式則使政府更具項目控制權,有助于滿足社會責任和公共利益需求,但易在實踐中出現過度依賴政府財政補貼、項目運營效率低下和擾亂市場競爭機制等問題。在防范隱性債務風險的大背景下,政府開始審視和調整PPP模式的實施策略。財政部《關于規范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綜合信息平臺項目庫管理的通知》(財辦金〔2017〕92號)指出審慎開展政府付費類項目。財政部《關于推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規范發展的實施意見》(財金〔2019〕10號)進一步明確財政支出責任占比超過5%的地區不得新上政府付費項目。《新機制》的出臺則是對這一系列政策的延續和深化。《新機制》明確指出未來所有PPP項目均需采用基于使用者付費的特許經營模式。這一決策旨在推動PPP項目更加市場化、高效化和可持續化,以更好地應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挑戰。
(4)在項目實施流程方面,在原PPP模式中,財政部提出并倡導的“兩評一案”成為大多數PPP項目前期審批的標配。《新機制》框架下的特許經營項目聚焦于使用者付費項目,擺脫了對政府財政的依賴。因此,以往基于財政支出責任進行的物有所值評價和財政承受能力論證便也失去了存在的現實必要性。《新機制》顛覆了長期沿用的“兩評一案”PPP項目監管與審批的模式,轉而采用特許經營方案對項目的建設、運營、投融資等核心環節進行全面而深入的論證。這一變革不僅簡化了審批流程,還提高了項目論證的針對性和實效性,為特許經營項目的順利推進奠定了基礎。
3.社會資本方選擇
在原PPP實踐中,社會資本方以國有企業為主體。《新機制》明確提出未來選擇社會資本時要優先考慮民營企業,并制定了民營企業參與清單。這一舉措不僅為解決原PPP模式中社會資本選擇結構失衡提供了明確的指導,同時也為民營企業參與PPP項目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支持。這將有助于推動PPP模式的健康發展,促進公共服務的提升和經濟的持續增長。
四、《新機制》未來展望
(一)PPP模式潛在發展方向
1.PPP模式與高質量發展
高質量發展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繁榮的關鍵,其核心在于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協同可持續。通過PPP模式,政府和社會資本能夠實現資源的有效整合和優勢互補,使發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體人民,從而加速高質量發展目標的實現。PPP模式的運行理念可分為基礎、中級、高級三個層次[25]。其中,基礎層次將PPP視為政府采購公共服務的工具,體現的是PPP的工具屬性。通過與私營部門合作,公共服務的提供由傳統的單一政府采購模式轉變為公私合作模式,以達到減輕財政壓力、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滿足人民群眾基本需求的目的。中級層次是將PPP視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引擎,反映的是PPP的經濟屬性。通過整合政府和私營部門的資源、經驗和創新力量,政府能夠創新融資方式,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從而提高區域經濟活力。高層次是將PPP作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性合作平臺,映射的是PPP的社會屬性。在這一層次,PPP不僅是項目實施的手段,更是政府和社會資本方深度合作,共同探討和解決社會、經濟和環境方面的重大挑戰,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目標的關鍵平臺。因此,將PPP提升至高級層次,不僅有助于解決具體項目層面的問題,更能夠在宏觀層面上引領和推動整個社會向高質量發展的方向邁進。目前,我國PPP模式的基礎層次已經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而PPP模式的中級層次和高級層次仍處于不斷探索和完善中。在中級層次,政府應當鼓勵和引導私營部門參與基礎設施建設、科技創新等更多領域的項目,確保資源整合的全面性和深度性。同時,政府還需提供更加靈活和有吸引力的融資機制,以激勵私營企業積極參與,推動區域經濟更快速、更可持續地發展。在高級層次,政府需要制定長期的PPP模式高質量發展戰略,并與社會資本方建立更為緊密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以共同應對環境問題、科技發展和社會不平等等重大挑戰。將PPP提升至高層次需要政府在制度建設、政策引導和合作機制方面持續努力。只有通過更深度、更戰略性的合作,政府和私營部門才能共同推動中國經濟向著高質量發展的目標邁進。
2.PPP模式與“一帶一路”
共建“一帶一路”是中國構建高水平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重點舉措,也是完善全球發展模式和治理體系的重要載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急需通過改善交通、醫療、教育、能源、水利等方面的基礎設施,刺激建筑業和相關產業發展,為經濟發展創造條件。在這一背景下,PPP模式為各方參與基礎設施項目提供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廣闊空間,有助于解決“一帶一路”建設中資金需求龐大的問題。但同時,PPP模式也可能面臨著各參與國政治不穩定、合作意愿不確定、法律體系多樣、合同法規存在差異、市場體系建設完善度不同,以及金融機制健全性不足等方面的諸多挑戰[26]。為了更有效地推動“一帶一路”建設,PPP模式未來可以通過更進一步加強國際合作、提升可持續性和透明度、推動數字化技術、發展多元化融資渠道等方式不斷提升其效力。首先,各參與國家可以加強政府間的溝通和協調,共同制定更為一致的政策框架,以促進跨國基礎設施項目的無縫合作。建立共同的標準和規范,推動PPP項目在不同國家間的一體化發展,降低跨境項目實施中的政治、法律等風險。其次,加強對PPP項目的監管和評估機制,確保項目的可持續發展,并保障各方權益。透明的項目信息和決策流程有助于提高投資者和公眾對項目的信任度,吸引更多的資金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再次,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先進的科技手段提高PPP項目管理的效率和準確性,降低運營成本。數字化技術有助于解決信息不對稱、監管難度大等問題,為PPP項目的成功實施提供更為可行的保障。最后,在PPP項目融資方面,可以探索跨國聯合融資、發展債券市場等多元化的金融手段,以吸引更廣泛的投資者參與,“一帶一路”倡議中各國金融機制的協同將為PPP項目提供更為穩健的融資支持。通過這些發展方向的綜合推動,PPP模式將更為有效地發揮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作用,為沿線國家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和全球可持續發展貢獻更大力量。
(二)未來發展建議
1.利益協調:激發PPP參與主體的主觀能動性
在PPP項目中,政府部門作為項目發起者,面臨著公共利益最大化和財政可持續性之間的矛盾。私營部門作為項目建設方和運營方,面臨著經濟效益最大化和社會責任之間的矛盾。公眾作為PPP項目的終端用戶,關注的是服務質量和服務價格之間的矛盾。金融機構作為資金提供者,重點關注的是投資回報和風險控制之間的矛盾。能否成功協調政府部門、私營部門、公眾和金融部門之間的利益關系,不僅關系到《新機制》的順利落地,還影響到各參與主體之間的長期合作關系。因此,PPP模式利益關系的調和應包括以下三個關鍵方面:(1)透明溝通。在項目的各個階段,保持透明的溝通是調和利益關系的基礎。政府、私營部門、公眾和金融部門之間應建立有效的信息傳遞機制,確保各方了解項目的目標、計劃和進展情況,減少信息不對稱的風險。(2)明確責任和權益。在項目合同和協議中不僅要明確各方的責任和權益,還要引入明確的績效指標和獎懲機制、信息披露機制和退出機制,降低政府和私營部門的潛在分歧和糾紛、保障公眾和金融部門權益。(3)風險共擔。在項目前期各參與方應共同進行項目風險評估,了解項目建設和運營階段可能存在的技術、市場、法律等方面的風險。在特許經營協議中明確各方的風險責任,并制定詳細的應急預案,明確各方在應對緊急情況時的責任和行動步驟。在項目建設和運營的過程中,定期進行風險審查,根據項目進展情況調整風險共擔方案,提高各方共同應對風險的效率。
2.融資拓展:優化PPP項目融資路徑
當前PPP項目的融資途徑主要包括政府撥款、商業貸款、債券發行以及私人投資等方式。盡管這些傳統的融資方式有助于滿足PPP項目的資金需求,但仍存在一些弊端。首先,過度依賴政府撥款可能會限制項目規模和推進速度,加重地方政府的財政負擔。其次,商業貸款和債券發行可能面臨高利息和復雜的融資結構,增加項目的財務負擔。此外,私人投資極易受到投資者風險偏好和不確定性的影響,導致融資難度增加。因此,為了拓展PPP項目的融資途徑,提出可采取的建議方案:(1)引入新的金融工具,如基礎設施債券和綠色金融工具,在吸引更廣泛的投資者參與的同時,進一步支持環保和可持續發展目標;(2)鼓勵項目采用多元化融資渠道,包括天使投資、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以降低融資的依賴性;(3)設立專門的PPP基金,由政府、私人投資者和金融機構參與,提供靈活的融資方案,降低項目融資難度;(4)推動跨境融資合作,吸引國際金融機構和投資者參與項目融資;(5)鼓勵社會投資者,如慈善機構和社會企業參與PPP項目融資,注入社會責任和可持續性元素;(6)政府可以設立獎勵機制,激勵私人機構開展PPP項目可行性研究,并有機會參與融資;(7)探索創新的融資模式,如收費權出讓和資產證券化,以提供更靈活的融資解決方案。通過這些方案,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資,提高項目的可行性,推動PPP項目的成功實施。同時,這也有助于推動金融領域的創新和可持續發展。
3.存量優化:提升現有PPP項目運營效能
《新機制》主要針對增量PPP項目進行了規范,但如何妥善處理存量PPP項目暫未明確說明。根據《新機制》的規定,對于存量PPP項目的處理可以著重考慮以下三個方面:(1)建立存量項目管理平臺,通過數字化手段,貫徹落實財政監管標準,全面監管存量項目支出管理情況;(2)綜合考慮項目的建設質量、運行狀況、服務水平等因素,建立PPP項目全生命周期績效考核機制,塑造全生命周期可用性付費理念,確保項目在整個生命周期內都能夠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3)建立明確的監管和審計機制,將項目回報與當地財政稅收增量掛鉤,促使項目公司與政府形成緊密的合作關系,共同致力于項目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 GRIMSEY D,LEWIS M.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the worldwide revolution in infrastructure provision and project finance[M].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7.
[2] 王克強,路江林,李岳存.PPP模式提升了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質量嗎?[J].統計研究,2020,37(4):101-113.
[3] 陸天慧.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及其審計研究:回顧與展望[J].審計研究,2022(4):41-51.
[4] 葉蘇東.PPP模式中社會資本方的風險管理框架[J].北京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21(3):102-109.
[5] 唐祥來,謝雨軒.PPP模式與地方財政壓力:來自中國地級市的經驗證據[J].財貿研究,2023,34(9):58-68.
[6] 王天義,韓志峰,楊永恒,等.中國PPP年度發展報告2017[M].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7] 陳■,李丹.PPP政策變遷與政策學習模式:1980至2015年PPP中央政策文本分析[J].中國行政管理,2017(2):102-107.
[8] 徐玖玖.公私合作制PPP項目法律激勵機制的制度重估及其優化[J].商業研究,2019(6):139-152.
[9] TAKANO G.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as rent-seeking opportunities:a case study on an unsolicited proposal in Lima,Peru[J].Utilities Policy,2017,48:184-194.
[10] 姜迪,湯玉剛.PPP如何影響地方財政風險——來自債券市場反應的證據[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20(10):50-64.
[11] 韓軍,呂雁琴,徐勇.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研究[J].上海經濟研究,2017(2):106-110.
[12] 呂煒,王偉同.黨的十八大以來財政領域改革成就、內在邏輯與未來展望[J].財政研究,2022(9):16-34.
[13] 張靜.論PPP項目監管的國外經驗及啟示[J].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9(6):19-28,206.
[14] 王天義,韓志峰,楊永恒,等.中國PPP年度發展報告2021[M].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
[15] CEBOTARI A.Contingent liabilities:issues and practice[D].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2008.
[16] 李鳳,武晉,吳遠洪.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為何簽約容易落地難——基于西南地區的分析[J].財經科學,2021(6):118-132.
[17] 魏蓉蓉,李天德,鄒曉勇.我國地方政府PPP隱性債務估算及風險評估——基于空間計量和KMV模型的實證分析[J].社會科學研究,2020(2):66-74.
[18] 聶卓,劉松瑞,玄威.從“主動負債”到“被動負債”:中央監管轉變下的隱性債務擴張變化[J].經濟學(季刊),2023,23(6):2136-2155.
[19] 陳婉玲,胡瑩瑩.我國PPP模式的功能異化、根源與解決方案[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20,22(3):111-123.
[20] 仇保興.推進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的有關問題和對策建議[J].城市發展研究,2016(5):1-3.
[21] 王盈盈,甘甜,王守清.走向協同:中國PPP管理體制改革研究[J].經濟體制改革,2021(3):18-24.
[22] 李冠新.PPP項目政府特許經營爭議的解決機制研究[J].財政科學,2022(11):146-154.
[23] 馬洪,車弈■.社會資本參與生態環境損害修復的實踐困境與路徑優化[J].學術界,2024(1):197-209.
[24] 何壽奎,陳璨.PPP項目合作風險形成機理與協同治理機制[J].當代經濟管理,2018,40(7):48-53.
[25] 李開孟,伍迪.PPP的層次劃分、基本特征及中國實踐[J].北京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6(3):1-12.
[26] 趙蜀蓉,楊科科,龍林岸.“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中PPP模式面臨的風險與對策研究[J].中國行政管理,2018(11):7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