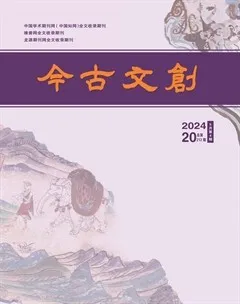語言 、 言說 、 修辭
【摘要】“語言學轉向”對當代的人文學科影響深遠。形式主義者普遍持認識論立場,視文學語言為對象,努力為文學語言與其他語言的區(qū)別營造一條界線。羅蘭巴特對文學語言的思考獨具一格,他對文學語言的思考已經不僅僅局限于認識論立場,而是走向存在論,這在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文學語言觀中具有典型性。從時間維度看,文學語言是寫作現(xiàn)象學中的語言,言說是已完成的語言。從空間維度看,作為動賓結構的“修——辭”喻示著文學語言必須關注語言與身體、主體間性等問題,這又暗合了后結構主義時代“修辭學轉向”的趨勢。
【關鍵詞】文學語言;寫作;言說;修辭學轉向
【中圖分類號】H0?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20-003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0.012
自20世紀初,哲學界開啟“語言轉向”以來,關于對語言的問題的思考就一直是哲學界的核心命題之一。同樣在其他人文學科領域,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也在人文學科領域泛起一陣波瀾。文學作為語言的藝術,自然要比別的學科對語言問題要更加的敏感。許多形式主義者認識語言主要從認識論的角度入手。如雅各布森則在此基礎上概括了語言的六大功能,即情緒功能、指稱功能、詩學功能、交際功能、元語言功能、意動功能。在這六組功能中,他尤其重視詩學功能和元語言功能,并且視二者為一組二元對立來進行研究。①可以發(fā)現(xiàn),在形式主義者那里,他們對文學語言的看法是持有認識論立場的,二元對立的方法是其基本研究思路。盡管羅蘭·巴特的文學理論思想深受索緒爾、雅各布森等人的影響,但羅蘭·巴特的對于文學語言的思考又有其獨特性,他不是從認識論,而是從存在論上進行的。他將自己對于文學語言的思考,融進自己的寫作當中。
一、作為寫作中存在的文學語言
語言的本質是什么?以索緒爾為代表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卻沒有增進多少我們對于語言是什么這一本體論問題的思考。不過或許語言是什么這一問題本身就是錯的。我們不應該從本體論或者認識論的角度認識語言,而應該從存在論的角度來認識語言。語言是怎樣存在的?在海德格爾看來,語言就是語言本身,乍一看有點同義反復,但仔細思考卻別有深味。他主張拋棄語言本質這類看法,因為無論如何解釋語言,我們始終不過是在語言內解釋語言。而語言就是語言,提醒我們注意,語言說(存在)這一事實。那么怎么觀察語言的狀態(tài)呢?答案是“在所說”中,海德格爾認為,“因為在所說中,說已經達乎完成了。在所說中,說并沒有終止。在所說中,說總是蔽而不顯。在所說中,說聚集著它的持存方式和由之而持存的東西,即它的持存(Wahren),它的本質。但我們所發(fā)現(xiàn)的所說往往只是作為某種說之消失的所說。②只有在“在所說”中,語言才得以彰顯。于是我們觀察語言就變成了觀察語言的存在狀態(tài),即關照“在所說”。海德格爾更新了人與語言是對象性、工具性的關系這樣的觀念,轉而從語言的存在狀態(tài)本身去思考語言。而這一點,與羅蘭·巴特的文學語言觀直接相通。
羅蘭·巴特思考寫作中的語言存在狀態(tài),用寫作現(xiàn)象學一詞稱呼,并無多少不妥。羅蘭·巴特說:“我并不把文學理解為一組或一套作品,甚至也不把它理解為交往或教學的一個部分;而是理解為有關一種實踐的蹤跡的復雜字形記錄,我指的是寫作的實踐。” ③在寫作當中,主語不斷搜尋著謂語,形容詞要尋找物體給它裝飾,一個詞語冒出另一個詞語借助聚合關系又跑出來,將前一個單詞取代。一個詞迫切尋找著另一個詞渴望與它結合,可這種凝固的關系并不持久,往往片刻就散了。寫作實踐就結構主義提供的聚合關系和組合關系這兩個根軸或者雅各布森所言的詩學隱喻關系和換喻關系不斷生發(fā)的。那么當一個詞找到了另一個詞構成句子,句子與句子結合形成文章,寫作實踐就結束了嗎?羅蘭·巴特認為并沒有,因為閱讀也可以算作是一種寫作。羅蘭·巴特說道:“閱讀是一種工作(以此,稱之為閱讀功能學léxéologique行為,乃至閱讀書寫功能學léxéographique行為,會更好些。因為我寫作我的閱讀)。” ④于是無論是寫作還是閱讀,都是一種詞語的碰撞、命名與消除命名行為的生成過程。我們便可從寫作現(xiàn)象學或寫作存在論的角度來理解文學語言。事實上,巴特一直抗拒著認識論,他說:“由于文學要使語言自行表演,而不只是利用語言,它就使只是編入了具有無窮自反性的齒輪機制之中。通過寫作,知識不斷地反映著知識,所根據(jù)的話語不再是認識性的,而是戲劇性的了。” ⑤文學當然有認識世界的功能,但在這功能實現(xiàn)之前,請先得欣賞字詞的表演。
在巴特看來,真正的文本,應該是不斷寫作生成著的,主語不斷尋找著謂語、詞不斷尋找著事物來命名,詞與詞之間不斷的追逐嬉戲打鬧,體會那文本的愉悅。巴特的寫作現(xiàn)象學昭示著他語言烏托邦的期望。然而,烏托邦之為幻想就是因為它不知道事物終有完結之時,當主語找到了謂語形成句子,寫作便中止了。語言則降格成言說。
二、言說——語言的降格
語言一經完成就成了言說。言說在羅蘭·巴特看來就是凝固化的表達方式。言說與福柯所謂話語的概念相近,就是帶有意識形態(tài)性質的語言。其實,按照阿爾都塞的看法,意識形態(tài)是一種無意識的東西。它通過法律、宗教、教育、語言等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每個人。在羅蘭·巴特看來,句子是語言學的核心。句子一經完成語言也就是完成了。句子有等級體系,它包括主句、從句和內在的反作用力。雖然理論上(喬姆斯基)說句子可以無限生成,然而實踐上句子總會停止的。朱麗婭·克里斯特娃曾說過:“每一意識形態(tài)活動均呈現(xiàn)于綜合地完成了的語句形式中。”巴特則從相反方向理解克里斯特娃的命題,他說:“凡業(yè)已完成了的語句均要冒著成為意識形態(tài)之物的風險。” ⑥羅蘭·巴特的擔憂是有道理的。意識形態(tài)的幽靈借助語言以形成言說。于是巴特采用符號學的方法去探究各種神話體系和流行體系的言說,剖析出其中所蘊含的意識形態(tài)。
《神話學》(又譯《神話修辭術》)是巴特所著的一部意識形態(tài)批評文集。在巴特看來,今日之種種時事都可歸入神話當中。而神話,是一種言說方式。雖然表面上,巴特探討的都是和文學不大相關的現(xiàn)象如:蘭開夏式摔角比賽、烹調好的菜肴、造型藝術展覽。⑦但實際上,它們在結構上都和文學一樣,都在言說著什么,或者說意指著什么。“神話不可能是一個客體,一種概念,或一種想象;它是一種意指樣式,一種形式。”“神話是一種交流體系,它是一種信息。” ⑧神話是一種意指樣式,就表明它可以用符號學進行分析,它是一種交流體系,就說明它可以用修辭學進行分析。關于修辭學下文再談,我們首先關注符號學。羅蘭·巴特的符號學根源自索緒爾,直接繼承自葉爾姆斯列夫。能指和所指來自索緒爾,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來自葉爾姆斯列夫。巴特認為神話是一個雙重系統(tǒng),第一層是直接意指系統(tǒng),能指指向所指,用公式來表示的話就是ERC。第二層是含蓄意指系統(tǒng),由第一層的符號成為一個能指,指向所指,用公式表示的話就是(ERC)RC,其中的所指就是意識形態(tài)。有了這個分析工具之后,巴特發(fā)現(xiàn)當今資產階級神話的功能就是將歷史變成自然。由于神話是一個雙重系統(tǒng),最值得玩味的是第一系統(tǒng)和第二系統(tǒng)的交界處,即第二系統(tǒng)的能指,或者稱之為神話能指。神話能指具有含混性,“神話的能指以含混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它既是意義又是形式,就意義而言,它是充實的,就形式而言,它是空洞的。” ⑨意識形態(tài)從本質而言就是一種社會形式,它是社會集團共有的觀念,自然不會是豐富的。這也恰好表明神話是一種言說方式,神話雖然不消除意義,但會使得意義空洞化,或者使之處于可掌控、可安排的境地。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雖然羅蘭·巴特不是分析文學,但明顯它在用分析文學的眼光來分析其他社會事物。文學本就是一個意指系統(tǒng),由直接意指系統(tǒng)和含蓄意指系統(tǒng)構成。文學語言尤其容易變成神話言說,特別是古典的文學。第一系統(tǒng)的直接意指極容易成為神話能指,服務于意識形態(tài)。或許神話作為一種言說方式,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不可反抗的。語言的命運注定它會由存在狀態(tài)降格成言說。而言說,自然就是神話了。后期巴特似乎意識到了這個語言陷阱,他放棄了采用符號學分析意識形態(tài)并且反抗意識形態(tài)的做法。他稱采用語言學——符號學分析神話言說的時期稱為科學性的時期,如今,他不再相信了。⑩即便如此我們依舊不能否認語言學——符號學方法對巴特的文學語言思考貢獻頗大。后期的巴特始終也沒有放棄對語言的思考,他回到了寫作,回到了文本,也回到了貫穿其一生都在思考的修辭學當中。
三、“修辭學轉向”
由于結構主義的諸多問題,在后結構主義,許多學者紛紛轉向修辭學研究,試圖跳出純粹語言形式的研究的窠臼當中。國內外學者稱此次潮流為“修辭學轉向”,或者“廣義修辭學轉向”。?之所以產生“修辭學轉向”與后現(xiàn)代的邏各斯中心主義被消解有很大的關系。知識源自話語,而話語需要修辭。那么什么是修辭學?亞里士多德認為修辭學是“一種能在任何一個問題上找出可能的說服方式的功能。” ?總的來說,修辭學并非關注純粹的語言形式的學問,而是關注如何調整、轉換、改寫語言以達到作者想要效果的一門學問。所以修辭學視域下的語言,不能離開語境、具體使用、聽眾這幾個因素。事實上這也是語言實際運用中離不開的幾個要素。
羅蘭·巴特恰恰是認識到了這一點,才轉向修辭學研究的。他發(fā)現(xiàn)符號學研究(他所認為的符號學)就是用語言去解釋言說,無論如何解釋語言最終命運都是降格為言說。這是無可逃避的語言陷阱。相較于所謂的“釋言之言”,采用修辭學的方法更能揭示出語言運用的實際情況。巴特與1970年出版了《舊修辭學》一書,他發(fā)現(xiàn)所有語言實踐都驗證了修辭學現(xiàn)象的廣泛性,在西方,修辭學至少流行了2500年。“修辭學(在語言禁忌之外)是在一個在其幅員和時延上比任何政治帝國都更廣袤、更持久的真正帝國,它嘲笑著科學和歷史思考之框架,并進而對歷史本身提問,至少相對于我們習慣于想象、運用并不得不思考的那種在別處可能稱作宏觀性的歷史。” ?的確,修辭學迫使我們重新思考知識生產的方式,語言是經過怎樣的生產工序最后成為言說的。此外修辭學還涉及語言與身體,以及語言主體間性的問題。在《舊修辭學》中巴特回顧了修辭學的發(fā)展歷程,并對具體的修辭技巧和修辭格進行了的分析。它認為舊修辭學并未消亡,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修辭學和我們的大眾文化之間,存在有一種牢固的一致性。由修辭學和人本主義所形成的我們的全部文學,都是從一種政治——司法實踐中產生的。?這樣文學語言經由修辭學這一中介外化成為文化研究的對象中的一員了。巴特強調當今書寫一門修辭學史的重要性,認為它可以以“文本、寫作的名義,勇于承擔一種全新語言實踐,并且永遠不與此革命性的科學分離。” ?當然除了宏觀的對修辭學作歷時的描述,在巴特自己的文學理論建構中,他也大量地采用修辭學的方法。比如古典修辭學中的一個概念:論題,一般認為論題是空間、場所,是話題的展開和論證之地,也是真理的“棲居之所”。巴特認為論題是一種方法、一種格架、一種儲藏形式的倉庫。?他將文本視作是一種論題,西方的“文本”最初的本義是編織物,文本就是編織分配安置語言的地方,文本聚集著作者及讀者于某些區(qū)域。文本中的語言被分為闡釋符碼、象征符碼、情節(jié)符碼、文化符碼和語義符碼。五種符碼在文本這一場所交織,變化,不斷生成意義。巴特就是如此將修辭學的方法用于自己的文本和文學語言的理論建構中的。
總而言之,語言、言說和修辭是巴特對文學語言思考的三個維度。從時態(tài)來講,語言和言說分屬現(xiàn)在時和過去時。作為現(xiàn)在時的語言是在寫作中存在的語言,因而可以構成一門寫作現(xiàn)象學。然而句子完成之時,就是語言降格成言說之時,身為言說的文學語言必然會受到意識形態(tài)所侵入。當然我們除了時間維度,也不可忽視空間維度。修辭學就是從空間維度來研究文學語言的。在一個場所中,主體間性、書桌、書本、文學語言、身體都是交疊錯落在一起的,共同構成文本的意義空間。所以我們必須借助修辭學來幫助我們理解文本空間、理解文學語言。語言、言說、修辭這三個經由羅蘭·巴特的思考而變得豐滿的概念,或許就是巴特留給我們的關于語言詩學思考的貢獻。羅蘭·巴特的文學語言觀擺脫了形式主義者研究文學語言時經常陷入的二元對立的窠臼。
注釋:
①趙毅衡編選:《符號學文學論文集》,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183頁。
②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6年版,第986頁。
③⑤羅蘭·巴特:《符號學原理——結構主義文學理論文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8年版,第6頁,第8頁。
④羅蘭·巴特:《S/Z——羅蘭·巴特文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4頁。
⑥羅蘭·巴特:《文之悅——羅蘭·巴特文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8頁。
⑦⑧⑨羅蘭·巴特:《神話修辭術——羅蘭·巴特文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50頁,第644頁,第651頁。
⑩羅蘭·巴特:《符號學歷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6頁。
?譚學純:《新世紀文學理論與批評:廣義修辭學轉向及其能量與屏障》,《文藝研究》2015年第5期,第50- 57頁。
?亞里士多德著,羅念生譯:《修辭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頁。
???羅蘭·巴特:《符號學歷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頁,第98頁,第99頁。
?殷振文、魏琛琳:《修辭學論題與詩性論題學:古典與當代之間》,《中國文學研究》2019年第2期。
參考文獻:
[1]趙毅衡編選.符號學文學論文集[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179-183.
[2]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上[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6:986.
[3]羅蘭·巴特.符號學原理——結構主義文學理論文選[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8.
[4]羅蘭·巴特.S/Z——羅蘭·巴特文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64.
[5]羅蘭·巴特.符號學原理——結構主義文學理論文選[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8.
[6]羅蘭·巴特.文之悅——羅蘭·巴特文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008.
[7]羅蘭·巴特.神話修辭術——羅蘭·巴特文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550-651.
[8]羅蘭·巴特.符號學歷險[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9]譚學純.新世紀文學理論與批評:廣義修辭學轉向及其能量與屏障[J].文藝研究,2015,(5):50-57.
[10]亞里士多德著.修辭學[M].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1]殷振文,魏琛琳.修辭學論題與詩性論題學:古典與當代之間[J].中國文學研究,2019,(02).
作者簡介:
鐘宇,男,漢族,廣東珠海人,暨南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藝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