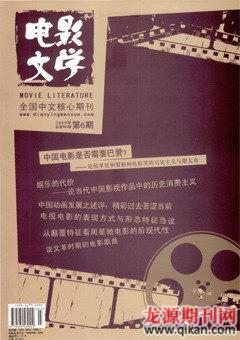靈魂的掙扎與跋涉
胡曉文
[摘要]史鐵生,是一位用生命去書(shū)寫(xiě)文章的思想者,他為自己、為人類的困境不懈地求解,從對(duì)生命個(gè)體的追問(wèn),到“幸”與“不幸”的理解,從苦難人生的自救,到神性的超越和精神的皈依,在這個(gè)漫長(zhǎng)的掙扎與跋涉中,逐漸體會(huì)到一種“過(guò)程”的幸福。人們閱讀史鐵生作品,不僅僅是同情他肢體的殘疾,更多的是理療自己心理上的缺憾,站在堅(jiān)強(qiáng)的而“健全”的史鐵生面前,我們學(xué)會(huì)了反觀自我、思索人生。
[關(guān)鍵詞]散文;過(guò)程;生命;命運(yùn);寫(xiě)作
20世紀(jì)90年代,散文熱再次興起,相比較60、70年代散文而言,新時(shí)期的散文更具理性的哲思,以“悟”為基本美學(xué)特質(zhì),直抵心靈深處,對(duì)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出現(xiàn)的困惑、痛楚等做出深入的思索和探討。史鐵生,是一位用生命去書(shū)寫(xiě)文章的思想者,他不懈地求解:人為什么活著?人為什么寫(xiě)作?……很多人認(rèn)為像他這樣“活到最狂妄的年齡忽然地殘廢了雙腿”,并且這種不幸接二連三地降臨于他,三十歲的時(shí)候“二腎一死一傷”,對(duì)于一般人來(lái)講,這種打擊必然會(huì)給一個(gè)充滿“好奇心”的志愿青年造成思想上和肉體上的大患,活著的感覺(jué)可能就是“了無(wú)生趣”,但是,我們發(fā)覺(jué)事實(shí)并非如此,我們可以用靈魂的掙扎與跋涉來(lái)形容這位作家:從對(duì)生命個(gè)體的追問(wèn),到“幸”與“不幸”的理解,從苦難人生的自救,到神性的超越和精神的皈依,在這個(gè)漫長(zhǎng)的掙扎與跋涉中,逐漸體會(huì)到一種“過(guò)程”的幸福。
一、個(gè)體生命的追問(wèn)——詩(shī)意地活著
雖然人們可能會(huì)相信佛教的涅和道家的化仙,或者相信此生的彼岸還有個(gè)天國(guó),但是現(xiàn)實(shí)生命最終存在著大限,這是一個(gè)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古往今來(lái),多少哲人對(duì)生命及其價(jià)值進(jìn)行著不懈的思索。孔子云:“不知命,無(wú)以為君子也”“志士仁人,無(wú)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莊子說(shuō)“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形全精復(fù),與天為一”。而西方文明的起源基督教“原罪”“贖罪”說(shuō)則認(rèn)為人生來(lái)有罪,要用一生去懺悔、贖罪、行善,死后才能進(jìn)入天堂。近現(xiàn)代西方哲學(xué)則主張生之虛無(wú)“事實(shí)上,人在自然中到底是什么?與無(wú)限比較起來(lái)是虛無(wú),與虛無(wú)比較起來(lái)是無(wú)限,人是虛無(wú)與一切之間的中值。由于人無(wú)限遠(yuǎn)離了理解極端的能力,事物的終止和開(kāi)始就在無(wú)法穿透的秘密中隱藏在人所不知的地方,一點(diǎn)希望都沒(méi)有。他同樣無(wú)法看到自己所誕生的虛無(wú),也看不到自己被吞沒(méi)其中的無(wú)限。”唯意志論者叔本華更是認(rèn)為:“一切都是轉(zhuǎn)瞬即逝的,如同一場(chǎng)無(wú)需任何努力的夢(mèng)幻。我們生命賴以存在的全部基礎(chǔ)便是現(xiàn)存——轉(zhuǎn)瞬即逝的現(xiàn)存。它以永恒運(yùn)動(dòng)的形式存在于人類生命。”尼采的一聲高喊,驚醒了世人。繼而存在主義哲學(xué)消解了生命存在的終極意義,一切存在都是偶然的,薩特說(shuō):“人是什么只是指他過(guò)去是什么,將來(lái)并未存在,現(xiàn)在是一個(gè)聯(lián)系著過(guò)去和將來(lái)的否定,實(shí)際上是一個(gè)虛無(wú)。因此,人注定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宿命,人必須自由的為自己作出一系列的選擇,正是在自由須選擇過(guò)程中,人賦予對(duì)象以意義,但人必須對(duì)自己的所有選擇承擔(dān)全部責(zé)任。”隨社會(huì)時(shí)代的發(fā)展,人類在一步步向前的進(jìn)程中,對(duì)于人生的終極思索,越來(lái)越推陳出新,顯示出其復(fù)雜性和多元性。而相對(duì)于這些形而上的思索,史鐵生關(guān)注生與死的問(wèn)題,更具有內(nèi)在的真實(shí)意義,或者說(shuō)更真實(shí)可感。
在他的作品中,對(duì)死亡有著審美意義上的接受。在他看來(lái),死亡極具詩(shī)意的內(nèi)涵,“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個(gè)必然會(huì)降臨的節(jié)日”。“人需要欣賞,生命需要被欣賞”。他把生命放置于一個(gè)審美欣賞的維度,坦然面對(duì)死亡與疾病,“不必過(guò)分地整理他,一衣一褲一鞋一襪足矣,不非是純棉的不可,物質(zhì)原本都出于一次爆炸。”,他又熱情地追求生存,他認(rèn)為人活著是需要目的和意義的,“讓它處在那個(gè)望眼欲穿的位置,這樣才永遠(yuǎn)有個(gè)奔頭,創(chuàng)造著、欣賞著、樂(lè)此不疲”“以方便生命的完成”,他在輾轉(zhuǎn)于輪椅和透析之隙,更有著一份勃勃的激情和不屈的壯美。
二、“幸”與“不幸”的理解——命運(yùn)之或然
突如其來(lái)的病痛,曾讓史鐵生為之感到無(wú)限痛苦,有好心人曾勸他算卦,他寧可相信命運(yùn)的偶然,而不愿相信命運(yùn)可以預(yù)測(cè),“命運(yùn),要是不單可以預(yù)測(cè),還可以預(yù)防,因而可以避禍,那當(dāng)然好不過(guò)。可是我想,預(yù)測(cè)僅僅是旁觀因而不影響世界原有的結(jié)果預(yù)防卻是干預(yù),預(yù)防之舉必定會(huì)改變?cè)械氖澜纾蛑械膭t也就不再準(zhǔn)確。”他在這種“偶然性”的“神思”中逐漸地走了出來(lái),獲得了理智,他在《好運(yùn)設(shè)計(jì)》中有這么一段話:“所謂好運(yùn),所謂幸福,顯然不是一種客觀的程度,而完全是心靈的感受,是強(qiáng)烈的幸福感罷了。”。他接受了心理學(xué)家的觀點(diǎn):幸福感的主觀性,但是他又認(rèn)為,幸福往往與痛苦是相伴相生的,沒(méi)有痛苦,哪來(lái)幸福,我們能做到的只能是減少痛苦,“在此設(shè)計(jì)中不要痛苦是不大可能了。現(xiàn)在就只剩下一條路:使痛苦盡量小些,小到什么程度并沒(méi)有客觀的尺度,總歸小到你能不斷地把它消滅就行了。”在與痛苦的抗衡與掙扎的過(guò)程中,才能夠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幸福。
只有坐在輪椅上與死亡抗衡的史鐵生,才能真正體會(huì)到命運(yùn)的偶然與必然,或者說(shuō)命運(yùn)是兩者的統(tǒng)一——或然。因?yàn)槿魏问挛锏陌l(fā)展都有其確定的和不確定的因素,偏執(zhí)于一方,在兩極間跳躍都是片面的,所以,逐漸成熟的史鐵生在經(jīng)過(guò)一段時(shí)間的思考之后,鉆出了“命運(yùn)”是“上帝”安排的絕望。他承認(rèn)苦難,他承認(rèn)命運(yùn)是有差別的,他承認(rèn)他必須接受這樣的“偶然”,同時(shí)他又承認(rèn)著自我?jiàn)^斗、懷抱悲憫情懷,以形成生命圓弧過(guò)程的必然。作為一名輪椅里的人,他用更廣博的愛(ài)來(lái)詮釋所謂的幸與不幸, “老盯著自己那點(diǎn)困苦,那不行,要理解人們都處在一個(gè)永恒的困境中,別人的困境你就也能理解,在這樣的情況下寬容才是可能的,否則寬容倒像施舍了,理解之后才能有真正的寬容。”他說(shuō):“佛的偉大,恰在于他面對(duì)這差別與矛盾以及由之而生的人間苦難,苦心孤詣沉思默想:在于他了悟之后并不放棄這個(gè)人間,依然心系眾生,執(zhí)著而艱難地行愿;在于有一人未度他便不能安枕的博愛(ài)胸懷。”,他表面是在說(shuō)佛,又何嘗不是在說(shuō)自己呢?他把“佛”“博愛(ài)”看成是動(dòng)詞,是一種歷程而不是目標(biāo),也不是終點(diǎn),“‘愛(ài)也是一個(gè)動(dòng)詞,處于永動(dòng)之中,永遠(yuǎn)都在理想的位置,不可能有徹底圓滿的一天。愛(ài),永遠(yuǎn)是一種召喚,是一個(gè)問(wèn)題。愛(ài),是立于此岸的精神彼岸,從來(lái)不是以完成的狀態(tài)消解此岸,而是以問(wèn)題的方式駕臨此岸。愛(ài)的問(wèn)題存在與否,對(duì)于一個(gè)人、一個(gè)族、一個(gè)類,都是生死攸關(guān),尤其是精神之生死的攸關(guān)。”有了這樣的境界,那么,面對(duì)人生的種種境遇和“偶然”都會(huì)釋然了。
三、苦難人生的自救——“業(yè)余”的寫(xiě)作
通過(guò)文學(xué)作品的表達(dá),對(duì)于人生,很多人認(rèn)為“死生亦大矣。”(孔子語(yǔ))“朝聞道,夕死可矣”;也有一些人通過(guò)縱情山水,感悟物我兩忘、宇宙永恒,“人生代代無(wú)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張若虛《春江花月夜》)
“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wú)盡也,而又何羨乎?”(蘇軾《前赤壁賦》);一些人感受到了某種彷徨,如莎士比亞借哈姆雷特之口,喊出:“活下去還是不活,這是問(wèn)題。”(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場(chǎng)》);另一些人則認(rèn)為人生本身是荒誕的,其終極將達(dá)成“真正的自由”,如“西西弗斯的神話”中的西西弗斯,為了追求自由,情愿重復(fù)的推動(dòng)那塊無(wú)望的石頭;更有一些人……一定的價(jià)值觀構(gòu)成了一定的行為方式,不同的人或用積極的、或用消極的方式對(duì)待人生,并且,每個(gè)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其感悟也會(huì)有所不同。
生老病死,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每個(gè)人都會(huì)耳聞目睹過(guò),人們往往對(duì)其感到永恒的敬畏、恐懼和不安,故而諱莫如深,史鐵生卻笑對(duì)身體的疾病,“職業(yè)是生病,業(yè)余寫(xiě)一點(diǎn)東西”,他毫不諱言地說(shuō)曾經(jīng)因感到絕望,“非常渴望過(guò)”“乞求過(guò)”死,但是最終失敗了,在艱難的掙扎中,他逐步產(chǎn)生了藝術(shù)家的審美情緒,把死亡當(dāng)作一種審美體驗(yàn)和內(nèi)在驅(qū)力,而寫(xiě)作則成為他精神對(duì)抗死亡最重要的方式,他極為坦率地說(shuō)出“寫(xiě)作就是為了不至于自殺”,他不止一次地表達(dá)“我其實(shí)未必適合當(dāng)作家,只不過(guò)命運(yùn)把我弄到這一條(近似的)路上來(lái)了。左右蒼茫時(shí),總也得有條路走,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筆去找。而這樣的找,后來(lái)發(fā)現(xiàn)利于此一鐵生,利于世間一顆最為躁動(dòng)的心走向?qū)庫(kù)o。”“至于寫(xiě)作是什么,我先以為那是一種職業(yè),又以為它是一種光榮,再以為是一種信仰,現(xiàn)在則更相信寫(xiě)作是一種命運(yùn)。”。我們都可以看出,或許史鐵生此生將被迫困居于輪椅,肉體沒(méi)有了自由行動(dòng)的能力,卻不能阻止他思維的“神游”。文學(xué)作品之所以多姿多彩,來(lái)自思維暢游路線的不同,更源于生活經(jīng)歷的不同。他每時(shí)每刻都在嘗試著回答對(duì)命運(yùn)的追問(wèn)、對(duì)生命的追問(wèn),梳理他的作品,幾個(gè)高頻出現(xiàn)的詞語(yǔ)是“人生”“命運(yùn)”“人間”,他的喃喃自語(yǔ),似乎在與神交流,他是在替自己,也是在替全人類不斷地叩問(wèn),“人類是要消亡的,地球是要?dú)绲模钪嬖谧呦驘峒拧N覀兊囊磺新斆骱筒胖恰^斗和努力、好運(yùn)和成功到底有什么價(jià)值?有什么意義?我們?cè)谧呦蚰膬?我們?cè)俪膬鹤?我們的目的何在?我們的歡樂(lè)何在?我們的幸福何在?我們的救贖之路何在?我們真的已經(jīng)無(wú)路可走真的已入絕境了嗎?”
他把寫(xiě)作當(dāng)成了自我療救的方式,他把事業(yè)當(dāng)作“一條能夠載度精神的船”,雖然“船不是目的,船只有在航程中才給人提供創(chuàng)造的快樂(lè)和享受這快樂(lè)的機(jī)會(huì)。”而“寫(xiě)作,在我的希望中只是懷疑者的懷疑,尋覓者的尋覓,雖然也要借助種種技巧、語(yǔ)言和形式。……寫(xiě)作不過(guò)是為心魂尋一條活路,要在汪洋中找到一條船。”對(duì)于寫(xiě)作,史鐵生謙虛地說(shuō)為了完成“渡人生”這項(xiàng)使命,而不至于迷途沉沒(méi),但是無(wú)疑,他的文字給我們帶來(lái)的心靈的震撼,已經(jīng)不完全是一種功利價(jià)值,更多是審美的超越和藝術(shù)的旨?xì)w。他視創(chuàng)作如勝境,“到了那兒就像到了故土,倍覺(jué)親切。到了那兒就像到了異地,倍覺(jué)驚奇,到了那兒就像脫離了這個(gè)殘損又堅(jiān)固的軀殼,輕松自由。到了那兒就像漫游于死中,回身看時(shí),一切都有了另外的昭示。”他用“筆”記錄著他思索人生的全過(guò)程,在此期間獲得了“另外的昭示”,豈不正是體現(xiàn)了其生命的力度與厚度?
四、神性的超越和精神的皈依——“過(guò)程。對(duì),過(guò)程!”
《法華經(jīng)》上說(shuō):“三界無(wú)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世間自有無(wú)量諸苦,而彼岸有佛在拈花微笑,面對(duì)世事,人們或祈求神佛的庇佑或?qū)捤。驅(qū)で蠹耐校虺缴溃瑢庫(kù)o而虔誠(chéng)。也有很多人認(rèn)為史鐵生作品中體現(xiàn)了宗教意識(shí),瓊州大學(xué)邢孔輝教授說(shuō):“新時(shí)期作家中,史鐵生是受宗教影響較深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也較早地體現(xiàn)了濃厚的宗教情緒和宗教意識(shí)。”嘉應(yīng)學(xué)院曾令存教授則認(rèn)為:“他從沉重的殘疾肉身開(kāi)始,在宗教神性光芒的照耀下,勘悟人生真相,追問(wèn)生命終極意義,尋找靈魂救贖之路,視‘過(guò)程為‘圓滿。”河南大學(xué)胡山林教授則說(shuō)史鐵生作品體現(xiàn)的是一種“類宗教意識(shí)”:“敬畏自然、參悟命運(yùn)、理解苦難、悲憫情懷、‘宗教精神”。無(wú)論是哪種說(shuō)法,筆者認(rèn)為,他的這種不依附于任何純意義的形式上的宗教,沒(méi)有具體的圖騰崇拜,卻堅(jiān)守著某一種生活態(tài)度、價(jià)值取向,是體現(xiàn)了他對(duì)于神性的一種超越。
關(guān)于“神佛”史鐵生說(shuō)“佛僅僅是信心,是理想,是困境中的一種思悟,是苦難里心魂的一條救路……燒香和禮拜,其實(shí)都并不錯(cuò),以一種形式來(lái)寄托和堅(jiān)定自己面對(duì)困難的信心,但若期待現(xiàn)實(shí)的酬報(bào),便總讓人想起提著煙酒去叩長(zhǎng)官家門(mén)的景象”…“我不相信佛能滅一切苦難,佛因苦難而產(chǎn)生,佛因苦難而成立,佛是苦難不盡中的一種信心,抽去苦難佛便不在了。”所以說(shuō),相信神佛,其實(shí)就是相信自我是否具有堅(jiān)強(qiáng)的內(nèi)心。
那個(gè)躲在園子深處獨(dú)語(yǔ)的人,在即將觸摸絕望之墻時(shí),他突然探尋到了“其他的辦法”——“過(guò)程。對(duì),過(guò)程,只剩了過(guò)程。”,在對(duì)自身和人類困境的不懈求解過(guò)程中,他獲得了精神超越的密匙。他在《對(duì)話四則》當(dāng)中,史鐵生以思辨的形式侃侃而談,他認(rèn)為對(duì)于活著的人來(lái)講“你惟一具有的就是過(guò)程。一個(gè)只想使過(guò)程精彩的人是無(wú)法被剝奪的……因?yàn)閴倪\(yùn)也無(wú)法阻擋你去創(chuàng)造一個(gè)精彩的過(guò)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變成一個(gè)精彩的過(guò)程。……你立于目的的絕境卻實(shí)現(xiàn)著、欣賞著、飽嘗著過(guò)程的精彩,你便把絕境送上了絕境。……當(dāng)生命以美的形式證明其價(jià)值的時(shí)候,幸福是享受,痛苦也是享受。”他從自身體驗(yàn)出發(fā),宣揚(yáng)了一種類似“過(guò)程哲學(xué)”的精神信念,沖淡了人們內(nèi)心的急功近利,消解了主觀的痛苦帶來(lái)的種種不和諧,從這個(gè)視角來(lái)審視我們的社會(huì)和人生,將會(huì)變得更為從容和豁達(dá)。
可以說(shuō),史鐵生的人生歷程,經(jīng)過(guò)了一個(gè)艱難的跋涉,從他剛開(kāi)始的經(jīng)常“發(fā)了瘋一樣地離開(kāi)家”,又覺(jué)得“沒(méi)處可去”,“中了魔似的什么話都不說(shuō)”地回來(lái),到現(xiàn)在的用思想做“船槳”,以寫(xiě)作為“渡船”,引領(lǐng)我們的靈魂走向深邃,這期間涵蓋了多少“掙扎”。當(dāng)人們?cè)谧x史鐵生作品的時(shí)候,不僅僅是同情他肢體的殘疾,更多的是理療自己心理上的缺憾,站在堅(jiān)強(qiáng)的而“健全”的史鐵生面前,我們學(xué)會(huì)了反觀自我、思索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