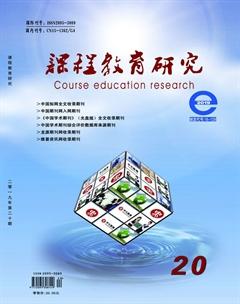高中數(shù)學(xué)學(xué)習(xí)心理障礙的成因及解決對策探究
祝禮琴
【摘要】本文從現(xiàn)階段高中數(shù)學(xué)學(xué)習(xí)存在的心理障礙的主要問題出發(fā),給出具體切實可行的對策,以此來達成推動我國高中教學(xué)質(zhì)量水平整體提升的目標。
【關(guān)鍵詞】高中數(shù)學(xué)? 心理障礙? 成因及對策
【中圖分類號】G63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9)20-0247-02
1.現(xiàn)階段,高中學(xué)生學(xué)習(xí)數(shù)學(xué)科目存在的心理障礙的原因
1,1自身因素
與初中階段的學(xué)習(xí)內(nèi)容相比,高中階段的學(xué)生不論是在學(xué)習(xí)的層面上,還是在學(xué)習(xí)的內(nèi)容上都變得相對復(fù)雜,尤其是在數(shù)學(xué)知識的學(xué)習(xí)方面更是承載著很大的壓力。與此同時,受到傳統(tǒng)中國式體制教育的影響,使得大多數(shù)的高中家長對于孩子學(xué)習(xí)成績好壞的評價,往往停留在考試成績上,如果再一次沒有考好,學(xué)生不僅要承受家長的指責(zé),而且還要面臨老師的質(zhì)問,久而久之,就容易給學(xué)生造成很大的心理學(xué)習(xí)壓力,使得他們數(shù)學(xué)科目的學(xué)習(xí)自信心大大下降,并逐漸失去學(xué)習(xí)數(shù)學(xué)的動力,從而出現(xiàn)數(shù)學(xué)學(xué)習(xí)心理障礙。例如,山東上某高中學(xué)生在學(xué)習(xí)函數(shù)的時候,由于停留在初中階段的學(xué)習(xí)模式,這就造成了他在函數(shù)部分學(xué)習(xí)過程中堆積了很多的問題,再加上長時間沒有解決,進而給后面學(xué)習(xí)更為復(fù)雜函數(shù)的學(xué)習(xí)帶來很大的困難,最終導(dǎo)致該學(xué)生對數(shù)學(xué)函數(shù)部分產(chǎn)生學(xué)習(xí)上心理障礙和壓力。
1.2計算能力差
高中階段的數(shù)學(xué)學(xué)習(xí),在運算量上相較于初中階段對學(xué)生的計算能力方面提出了相對較高的水平要求,再加上教育部取消了應(yīng)試考試中的允許使用計算機的規(guī)定,這就給許多高中生的數(shù)學(xué)計算帶來一定的難度,從而在心理上對高中數(shù)學(xué)產(chǎn)生一定的心理障礙壓力。
1.3課程因素
與其他高中學(xué)習(xí)科目相對,高中數(shù)學(xué)的思維性和實踐性要求相對較高的學(xué)科,在學(xué)習(xí)的過程中需要學(xué)生能夠通過對簡短的定義和含義的理解中找出一定的數(shù)學(xué)規(guī)律性,并應(yīng)用到實際的生活和學(xué)習(xí)中去,這對于一些數(shù)學(xué)科目學(xué)習(xí)相對較差的學(xué)生而言具有很大的壓力和難度。除此之外,數(shù)學(xué)科目的答案相對固定,如果學(xué)生在計算的過程中某一步驟或者數(shù)字出現(xiàn)錯誤,很有可能導(dǎo)致后面的計算出的結(jié)果也是錯誤的,這就造成許多學(xué)生產(chǎn)生對數(shù)學(xué)學(xué)習(xí)心理障礙和壓力,進而導(dǎo)致數(shù)學(xué)科目的學(xué)習(xí)效果和質(zhì)量明顯低于其他科目。
2.解決高中階段學(xué)生學(xué)習(xí)數(shù)學(xué)心理障礙的有效對策
2.1培養(yǎng)學(xué)生在數(shù)學(xué)科目學(xué)習(xí)中的自信心
在高中數(shù)學(xué)科目的實際的教學(xué)中,對于數(shù)學(xué)基礎(chǔ)相對較差的學(xué)生,教師可以從簡單易懂的數(shù)學(xué)知識入手,幫助學(xué)生建立高中數(shù)學(xué)科目學(xué)習(xí)的自信心,從而逐步解除他們對于數(shù)學(xué)上的學(xué)習(xí)壓力和心理障礙。
2.2幫助學(xué)生構(gòu)建科學(xué)的數(shù)學(xué)思維學(xué)習(xí)方法
高中階段的數(shù)學(xué)科目在學(xué)習(xí)的過程中對于學(xué)生的抽象性思維和邏輯性思維具有相對較高的要求,因此,這就需要高中的數(shù)學(xué)教師在進行數(shù)學(xué)科目的教學(xué)中要不斷通過合理的數(shù)學(xué)課程安排同時,幫助學(xué)生培養(yǎng)和構(gòu)建科學(xué)的數(shù)學(xué)思維學(xué)習(xí)辦法,以此來消除學(xué)生對數(shù)學(xué)科目的恐懼心理,從而喜歡上數(shù)學(xué)科目。
2.3做好學(xué)生數(shù)學(xué)計算能力的培養(yǎng)工作
高中數(shù)學(xué)題目在解答的過程中不論是在運算量上,還是在計算的復(fù)雜程度上都相對較大,所以這就要求學(xué)生相比初中階段,應(yīng)當具備較高的數(shù)學(xué)計算能力,并逐步從依賴計算機計算的誤區(qū)中走出來。因此,為了解決高中學(xué)生相對較差的數(shù)學(xué)運算能力問題就需要廣大的高中教師在實際的教學(xué)過程中要善于通過訓(xùn)練,幫助學(xué)生提高自身的計算能力,并在數(shù)學(xué)科目的學(xué)習(xí)過程中總結(jié)出屬于自己的數(shù)學(xué)計算相對簡單和巧妙的辦法,從而幫助他們走出數(shù)學(xué)科目難的心理障礙。例如,河北上衡水中學(xué)某高中教師在實際的教學(xué)中,就根據(jù)本班學(xué)生計算能力差的問題,開展數(shù)學(xué)計算巧辦法游戲總結(jié)大賽,幫助學(xué)生在游戲的過程中找到關(guān)于數(shù)學(xué)計算方面好的學(xué)習(xí)辦法,并通過讓學(xué)生將這些總結(jié)的方法應(yīng)用到實際問題的解決中去,進而真正意義上達到提高學(xué)生數(shù)學(xué)計算能力的目的。
2.4開展多元化的數(shù)學(xué)科目教學(xué)
為了解決高中學(xué)生的數(shù)學(xué)心理障礙問題,數(shù)學(xué)教師可以在實際的教學(xué)中通過開展多元化的數(shù)學(xué)教學(xué)模式,幫助學(xué)生培養(yǎng)和養(yǎng)成良好的高中數(shù)學(xué)科目學(xué)習(xí)習(xí)慣,進而逐步消除對數(shù)學(xué)科目的學(xué)習(xí)心理障礙。
3.結(jié)束語
綜上所述,基于高中數(shù)學(xué)科目的學(xué)習(xí)特點,現(xiàn)階段在高中數(shù)學(xué)的學(xué)習(xí)過程中普遍存在一定的數(shù)學(xué)學(xué)習(xí)心理障礙和壓力,針對這種情況,就需要我們在實際的教學(xué)中幫助學(xué)生培養(yǎng)數(shù)學(xué)科目的學(xué)習(xí)自信心,并最終消除心理陰影,并最終達成綜合素養(yǎng)全面發(fā)展的目標。
參考文獻:
[1]姜紅霞.尋找源頭,逐個擊破——淺析高中數(shù)學(xué)學(xué)習(xí)中的心理障礙點及解決對策[J].數(shù)學(xué)大世界旬刊,2017(12).
[2]孔凡哲,曾崢編著.21世紀教師教育系列教材——數(shù)學(xué)學(xué)習(xí)心理學(xué)[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