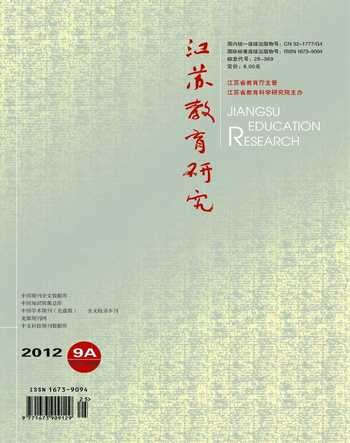特級(jí)教師是怎樣煉成的
李亮 周彥
摘要:江蘇小學(xué)語(yǔ)文的天空從來(lái)都是星光燦爛、名師薈萃。斯霞、李吉林、于永正等是江蘇小學(xué)語(yǔ)文教師的杰出代表。縱觀小學(xué)語(yǔ)文教壇的著名特級(jí)教師,他們身上有什么?作為特級(jí)教師,他們有怎樣的特質(zhì)?這些特質(zhì)是怎樣煉成的的?高尚的師德、深刻的教育思想、鮮明的教學(xué)風(fēng)格是他們區(qū)別于普通教師的職業(yè)素養(yǎng),而勤于讀書、躬于實(shí)踐、善于思考與積累則是特級(jí)教師們成長(zhǎng)的內(nèi)在成因和基本條件。
關(guān)鍵詞:特級(jí)教師;成長(zhǎng);啟示
中圖分類號(hào):G451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hào):1673—9094(2012)09—0056—04
“傳道、授業(yè)、解惑”(韓愈)大抵是我國(guó)古代對(duì)教師職業(yè)角色的最經(jīng)典論斷。而經(jīng)典之為經(jīng)典就在于它對(duì)未來(lái)的開(kāi)放性與生成性,型塑它的就是時(shí)代的發(fā)展。語(yǔ)文教育雖說(shuō)古老,但作為一門獨(dú)立學(xué)科才走過(guò)了100多年。上世紀(jì)的曲曲折折,直至改革開(kāi)放以后,語(yǔ)文教育終于迎來(lái)了春天。在小學(xué)語(yǔ)文教育蹣跚前進(jìn)的過(guò)程中,我們看到了時(shí)代型塑出了一個(gè)個(gè)溫暖的身影,其中有一批就扎根在江蘇這片土地上。
一
江蘇小學(xué)語(yǔ)文的天空從來(lái)都是星光燦爛、名師薈萃的,而且在這些名師中間,總有幾位傲立群芳,站在全國(guó)小語(yǔ)的制高點(diǎn)上。“蘇派教學(xué)”某種意義上更像是小語(yǔ)的“蘇派”。新中國(guó)成立后全國(guó)小學(xué)語(yǔ)文名師譜系大致可劃分為四代:“文革”前十多年是第一代,代表人物當(dāng)推斯霞、霍懋征、王蘭老師等。其中斯霞老師以她的“隨課文識(shí)字”,更以她的“童心母愛(ài)”,在全國(guó)小語(yǔ)界,也在全體教育者心中樹起了一座豐碑。上世紀(jì)80年代——改革開(kāi)放的頭十年是第二代,代表人物首推李吉林老師。李老師的“情境教育詩(shī)篇”不光是對(duì)母語(yǔ)教學(xué)的卓越創(chuàng)造,而且在當(dāng)代教育理論園地也堪為“教科書”。李吉林老師的成就再次證實(shí),一個(gè)小學(xué)語(yǔ)文教師也可以鍛鑄成教育家!上世紀(jì)90年代是第三代,這是全國(guó)小學(xué)語(yǔ)文教學(xué)務(wù)實(shí)精進(jìn)的十年,教壇上可謂群星璀璨,于永正、賈志敏、支玉恒等一大批名師成為小學(xué)語(yǔ)文教師的新標(biāo)桿。除了于永正在全國(guó)廣受擁戴、占盡風(fēng)流之外,張慶、朱家瓏、袁浩等一批江蘇小語(yǔ)教壇的領(lǐng)袖,在教材、教研等領(lǐng)域也是異軍突起。21世紀(jì)的頭十年自然就是第四代了。這是語(yǔ)文教學(xué)的黃金年代,課程改革的春風(fēng)把小學(xué)語(yǔ)文教壇熏得如火如荼,一批中青年名師走到了臺(tái)前,孫雙金、竇桂梅、王崧舟、薛法根等名字開(kāi)始為大家所熟知,而江蘇的孫雙金、薛法根分別以其深沉雄渾、睿智灑脫的教學(xué)風(fēng)格,成為新一代名師的翹楚。這樣的劃分當(dāng)然不可能絕對(duì),事實(shí)上,一位真正的名師,其影響力往往超越時(shí)空,深深感召和激勵(lì)著他們身后一代又一代教育新人的成長(zhǎng)。
“江山代有才人出”。江蘇小語(yǔ)未來(lái)的10年、20年誰(shuí)領(lǐng)風(fēng)騷?心里的疑問(wèn)還沒(méi)說(shuō)出口,代表“新生代名師”的祝禧、管建剛、魏星、潘文彬、王笑梅等等便已經(jīng)悄然而至。
二
歷數(shù)幾代特級(jí)教師,不禁心生一問(wèn),究竟是些什么獨(dú)特的品質(zhì)讓他們?cè)诮處熑后w中脫穎而出,在不同時(shí)代的小語(yǔ)園地中綻放異彩?面前這本《特級(jí)教師思想錄·小學(xué)語(yǔ)文卷》中也許隱藏著一些答案。“特級(jí)教師”是一個(gè)怎樣的群體?教育部《特級(jí)教師評(píng)選規(guī)定》的“定義”是:“國(guó)家為了表彰特別優(yōu)秀的中小學(xué)教師而特設(shè)的一種既具先進(jìn)性、又有專業(yè)性的稱號(hào)。特級(jí)教師應(yīng)是師德的表率、育人的模范、教學(xué)的專家。”由此看來(lái),這樣一個(gè)群體,恐怕至少具備以下一些條件——
師德的豐碑。道德、品格的崇高不僅是我們衡量一位教師,更是衡量一個(gè)人的精神標(biāo)準(zhǔn)。這一點(diǎn)從古而今已有太多的原創(chuàng)性闡述和衍生性表達(dá),但這里可能還有一個(gè)價(jià)值排序的問(wèn)題仍然值得一提。即“師德”對(duì)教師是一個(gè)必要含義,對(duì)于啟人育人之師,道德、德行就應(yīng)是教師資格準(zhǔn)入的必要條件,因?yàn)橐匀藶榻煌鶎?duì)象的事業(yè)如果道德出了問(wèn)題最終禍害的是人是社會(huì)是國(guó)家是民族。所以對(duì)于教師而言,德行具有一票否決權(quán)。當(dāng)然,這是一種理想的狀態(tài),是人們對(duì)于教師職業(yè)的美好向往,而且教師群體也仍然有道德水平差異,但德行其實(shí)更應(yīng)該是教師自己心中的“道德律令”(康德)。這一點(diǎn),諸位前輩堪為楷模。
斯霞是一座豐碑。她是一座大寫的“人”的豐碑。作為一個(gè)人,斯霞一生坎坷,但從來(lái)沒(méi)有向黑暗、向困難和挫折低頭。她堅(jiān)守自己的信仰,堅(jiān)守自己的理想,堅(jiān)守自己的學(xué)校,堅(jiān)守自己的課堂。用94年的時(shí)間長(zhǎng)度,用堪稱“偉大”的高度和寬度,書寫了一個(gè)大大的“人”字。她是一座人民教師杰出代表的豐碑。作為一名人民教師,她鐘愛(ài)教育,關(guān)愛(ài)孩子,酷愛(ài)語(yǔ)文,熱愛(ài)教學(xué),語(yǔ)文教學(xué)成為她基本的生活方式和深刻而美好的生命體驗(yàn)。作為一名人民教師,她從未停止過(guò)探索和實(shí)踐,在識(shí)字教學(xué)領(lǐng)域,她成為分散識(shí)字教學(xué)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非常了不起的[2]。
李吉林老師從上世紀(jì)60年代起就不知疲倦地奮力前行,從情景教學(xué)法到情境教學(xué)論,再到情境教育論,她超越了學(xué)科教學(xué)的藩籬,發(fā)展出了一套旨在促進(jìn)兒童生命整體發(fā)展的教育理論體系,其理念中流淌著中華民族“贊天地之化育”的血脈。
張慶老師淳樸寬厚,他與蘇教版教材編寫團(tuán)隊(duì)一同打造了一套高質(zhì)量的小學(xué)語(yǔ)文教材,讓“蘇教版”融入全國(guó)小語(yǔ)教材的主流。于漪老師認(rèn)為這套教材“特色鮮明,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經(jīng)驗(yàn)與現(xiàn)代意識(shí)的完美結(jié)合”。在《張慶文集》首發(fā)式上,柳斌先生說(shuō),張慶先生為母語(yǔ)教育研究獻(xiàn)上了一個(gè)完整的樣本,為教育工作者樹立了一座師德師范的豐碑。
王蘭老師的和諧教育思想道出了語(yǔ)文教育的本真:語(yǔ)文是一種幸福的生活,是師生共同的生活。她帶著這樣的理想,虛心學(xué)習(xí)、與時(shí)俱進(jìn)。她探索出的漢語(yǔ)拼音教學(xué)經(jīng)驗(yàn)具有廣泛的影響。更為可貴的是,王蘭老師將這些經(jīng)驗(yàn)毫無(wú)保留地給予后學(xué),近二十多年來(lái),她大力培養(yǎng)教學(xué)新秀,門下弟子已逾四代,并且在她的指導(dǎo)下快速成長(zhǎng)起來(lái),使蘭之幽香在小語(yǔ)界愈發(fā)香遠(yuǎn)。
……
這些高尚的品德與他們的教育事業(yè)密不可分,不僅讓他們?nèi)〉昧肆钊瞬毮康某煽?jī),也給后輩同仁樹立起了精神的標(biāo)桿。
思想的高地。這些特級(jí)教師關(guān)心教育現(xiàn)實(shí)且不安于現(xiàn)狀,期望通過(guò)努力去改變。有教育理想才有可能去追求理想的教育。理想的意義不在于實(shí)現(xiàn),而在于讓人明了現(xiàn)實(shí)的困境,知道現(xiàn)實(shí)距離理想有多遠(yuǎn),發(fā)現(xiàn)改進(jìn)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的可能空間,就好像柏拉圖的完美政治雖說(shuō)從未存在過(guò),也幾乎不可能存在,但它仍然是對(duì)任何真實(shí)的政治制度的一個(gè)嚴(yán)重的理論挑戰(zhàn)[5]。因此,若想看到前方的道路,就必須“用心地抬起頭”來(lái)。
對(duì)教育的深入思考使他們樹立了可貴的教育信念。可以說(shuō),這也是一個(gè)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群體。一名懷揣理想的教師必須同時(shí)勇于面對(duì)現(xiàn)實(shí)才具有的社會(huì)價(jià)值。所以僅僅提出教育理想還遠(yuǎn)遠(yuǎn)不夠,不去實(shí)踐或遇到挫折就放棄,理想就成了幻想。這其中起關(guān)鍵作用的可能就是對(duì)教育的信念。
薄俊生老師堅(jiān)信,語(yǔ)文教育的價(jià)值追求在于人的發(fā)展(于是他實(shí)踐著他的發(fā)展性教學(xué));管建剛老師堅(jiān)信,作文教學(xué)中生活富于生成,文心重于文字,講評(píng)重于指導(dǎo),多改重于多寫,真實(shí)重于虛構(gòu),發(fā)現(xiàn)重于觀察(于是他開(kāi)始他的“作文教學(xué)革命”);戚韻東老師堅(jiān)信,應(yīng)當(dāng)讓兒童以喜歡的心情來(lái)學(xué)語(yǔ)文,以語(yǔ)文的視界來(lái)學(xué)語(yǔ)文,以個(gè)性的呼喚來(lái)學(xué)語(yǔ)文,以陪伴的溫度來(lái)學(xué)語(yǔ)文(于是她總是不停地問(wèn)自己:“孩子們學(xué)語(yǔ)文快樂(lè)嗎?”);潘文彬老師堅(jiān)信,語(yǔ)文教學(xué)應(yīng)當(dāng)切實(shí)地讓每一位學(xué)生都能夠通過(guò)語(yǔ)文的學(xué)習(xí)幸福地成長(zhǎng)為具有良好語(yǔ)文素養(yǎng)的“語(yǔ)文人”(于是他要求自己從教學(xué)的目標(biāo)、內(nèi)容、手段、組織形式到教學(xué)評(píng)價(jià)都要扎扎實(shí)實(shí))……
教育信念在長(zhǎng)期的實(shí)踐中有助于建構(gòu)起各自的教育教學(xué)思想,形成一個(gè)個(gè)相對(duì)完善的體系,這種思想體系有幾個(gè)特點(diǎn):第一,靠近規(guī)律。規(guī)律是馬克思所謂從“必然王國(guó)”向“自由王國(guó)”邁進(jìn)的階梯,也是實(shí)現(xiàn)教育理想的依憑。《著名特級(jí)教師教學(xué)思想錄·小學(xué)語(yǔ)文卷》給我的整體感覺(jué)是,它所容納的思想可謂占領(lǐng)了語(yǔ)文教育教學(xué)領(lǐng)域的高地,抓住了語(yǔ)文教育中的諸多重要規(guī)律。第二,由于堅(jiān)信這些思想貼近規(guī)律,這些思想者雖然也隨著認(rèn)識(shí)的深入不斷調(diào)整和豐富完善,但核心思想被堅(jiān)守了下來(lái),不隨風(fēng)擺動(dòng),由教育信念凝固為學(xué)術(shù)定力。第三,對(duì)于這些思想的把握并非完全源自理論的論證,邏輯的推演,其中有很多是教學(xué)的直觀把握。這體現(xiàn)的可能就是一種教育智慧。只有智慧才能讓他們?cè)谌绱藦?fù)雜、割裂、無(wú)奈而又萬(wàn)分美好的教育現(xiàn)實(shí)中趟出一條路來(lái)。
風(fēng)格的境界。通常情況下,一位教師從新手到專家需要經(jīng)歷若干發(fā)展階段。往往從模仿開(kāi)始,甚至一舉手一投足都向心中的“燈塔”靠攏,這其實(shí)是一種“見(jiàn)賢思齊”的意識(shí),在模仿與思考中會(huì)逐步找到自己,過(guò)濾掉一些徒具形式的機(jī)械模仿,發(fā)現(xiàn)屬于自己一片天空,并在不斷的實(shí)踐中沉淀下一些東西,這些東西越積越厚,最終成為核心的、主要的理念與意識(shí),進(jìn)而形成他們自己的特色,步入風(fēng)格之境界。這時(shí)候自己也成了被后生模仿的對(duì)象。這種“教師在長(zhǎng)期教學(xué)實(shí)踐中逐步形成的、富有成效的一貫的教學(xué)觀點(diǎn)、教學(xué)技巧和教學(xué)作風(fēng)的獨(dú)特結(jié)合和表現(xiàn)”就是教學(xué)風(fēng)格。它是“教學(xué)藝術(shù)個(gè)性化的穩(wěn)定狀態(tài)之標(biāo)志”。風(fēng)格即是境界,“有境界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孫雙金的深沉雄渾,薛法根的清簡(jiǎn)灑脫,祝禧的文化氣質(zhì)……這些教學(xué)風(fēng)格的形成大致經(jīng)歷了幾個(gè)轉(zhuǎn)變:由局部向整體轉(zhuǎn)變,具有教育教學(xué)的全局眼光是形成風(fēng)格的必須,零敲碎打很難形成合力,搭好了觀念的大框架,各個(gè)部分就會(huì)找到自己的位置,格局才能形成;由技術(shù)向藝術(shù)轉(zhuǎn)變,如果對(duì)教學(xué)的感覺(jué)還停留在工藝加工的層面,教學(xué)就成了標(biāo)準(zhǔn)化的生產(chǎn)線,就不會(huì)用個(gè)性化的教學(xué)培養(yǎng)出個(gè)性化的學(xué)生;由自發(fā)向自覺(jué)轉(zhuǎn)變,風(fēng)格的形成往往不是預(yù)設(shè)的結(jié)果,而是在混沌中前行時(shí)的自然積累,懵懂的教學(xué)往往是一種自發(fā)的感覺(jué)使然,但由于思想框架以及個(gè)人氣質(zhì)精神的整體影響,會(huì)產(chǎn)生一種聚攏之效,而風(fēng)格一旦顯山露水,又會(huì)在不經(jīng)意間得到強(qiáng)化,成為一種自覺(jué)的行為。這樣,風(fēng)格就日趨成熟與穩(wěn)定。
三
其實(shí),無(wú)論師德、思想還是風(fēng)格,所有的一切不僅需要想出來(lái)、說(shuō)出來(lái),更需要做出來(lái),這個(gè)教師群體之所以能有今天讓人敬佩的成績(jī),說(shuō)到底還是“用思維反思現(xiàn)狀,用行動(dòng)改變現(xiàn)狀”的過(guò)程與結(jié)果,“先做起來(lái),并堅(jiān)持做下去”非常重要。于是,認(rèn)識(shí)到他們“有什么”以后,自然就該追問(wèn)他們是如何獲得這些品性與素質(zhì)的。捧讀書稿,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他們——
勤于讀書。書是人類進(jìn)步的階梯,這是一個(gè)常新的命題,它在邏輯上似乎已是不證自明了。在這里需要引起關(guān)注的是,我們常常將學(xué)習(xí)的眼光聚焦于特級(jí)教師的課堂,最多也就延伸到他們的備課(如文本的解讀等),而忽視了他們潛心涵養(yǎng)的“詩(shī)外功夫”。其實(shí),文本解讀與課堂教學(xué)更像是這些優(yōu)秀教師“學(xué)習(xí)成果的展示與交流”,而在此之前的熟讀精思博覽歷練等才更具借鑒效仿的價(jià)值。
李吉林老師每天讀書不少于3小時(shí);72歲的張慶老師至今對(duì)《論語(yǔ)》《老子》《易經(jīng)》等國(guó)學(xué)經(jīng)典保持著濃厚的興趣,每天潛心閱讀、筆耕不輟;薛法根老師即使在學(xué)校處理事務(wù)到半夜,回去后仍要再看兩小時(shí)的書;孫雙金老師則更有一種“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執(zhí)著:結(jié)識(shí)蘇霍姆林斯基,拜訪巴班斯基,和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對(duì)話,與語(yǔ)文教育大師葉圣陶交流,從而煉出自己的“十年功”……
學(xué)習(xí)名師不妨從讀書開(kāi)始。當(dāng)下,正如一些學(xué)者坦言,教師群體的讀書可能成了問(wèn)題,教師拒絕讀書有一些主客觀原因,比如缺少環(huán)境,缺少閑暇,缺少需要,所以或疲于事務(wù),或迷于題海,或干脆游戲人生。需要明白,教師的認(rèn)知結(jié)構(gòu)必須是開(kāi)放而不能是閉合的,保持開(kāi)放的姿態(tài)才能避免教學(xué)工作的低水平重復(fù),才能培養(yǎng)出符合時(shí)代發(fā)展需要的兒童,這一切都繞不過(guò)讀書。如果說(shuō)現(xiàn)實(shí)確實(shí)存在著諸多阻礙,那么這些特級(jí)教師似乎已經(jīng)找到了回旋的夾縫空間。也許我們可以說(shuō):能夠找到多大的生存夾縫,你的教育理想就有多大的現(xiàn)實(shí)空間。
躬于實(shí)踐。如果教育理想需要仰望星空,那么腳踏實(shí)地就必須躬親實(shí)踐。《著名特級(jí)教師教學(xué)思想錄·小學(xué)語(yǔ)文卷》中沒(méi)有空想家,只有實(shí)踐者。他們其中的很多人都在教壇上躬耕了十幾年、幾十年,斯霞、李吉林、王蘭、袁浩、于永正老師等老一輩特級(jí)教師,更是付出了四五十載的歲月。八十多歲的王蘭老師至今仍然堅(jiān)持每天去學(xué)校“上班”,辛勤指導(dǎo)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教師;于永正老師七十多歲仍然在課堂上為全國(guó)各地的老師垂范;新生代的青年才俊們更不必說(shuō),他們當(dāng)中的每一個(gè)人,都在做著一件事情——用實(shí)踐去實(shí)現(xiàn)理想。
情智語(yǔ)文、文化語(yǔ)文、簡(jiǎn)單語(yǔ)文、詩(shī)化語(yǔ)文、生命語(yǔ)文……他們拋出了很多這樣的主張與理想。對(duì)此一些有識(shí)之士持審慎的批評(píng)態(tài)度,但我想,對(duì)那些改革者,特別是那些青年改革者的教育主張我們更應(yīng)當(dāng)投注的是關(guān)心與幫助。畢竟發(fā)現(xiàn)問(wèn)題、提出主張對(duì)于教育研究是何等難得!畢竟勇于思想、躬于實(shí)踐對(duì)于教師的專業(yè)成長(zhǎng)何等珍貴!
善于反思。談到教師專業(yè)發(fā)展似乎已經(jīng)繞不開(kāi)“反思”的問(wèn)題。這個(gè)優(yōu)秀的教師群體之所以能夠在小語(yǔ)教學(xué)中體現(xiàn)出某種優(yōu)勢(shì),就在于他們借助反思看到了“可以做得更好”的空間,這是反思的最大價(jià)值。
我們提倡日常的教學(xué)反思,即一篇課文或一堂課教學(xué)結(jié)束后反思自己在教學(xué)過(guò)程中的利弊得失,從而讓下一次變得更好。這樣的反思當(dāng)然需要,但是還不夠。二十世紀(jì)的史學(xué)大師湯因比因其著作《歷史研究》獲得了至高的榮譽(yù),其重要的價(jià)值之一就在于他拓展了史學(xué)研究最普遍的基本單位:“(空間上)從單個(gè)的民族國(guó)家擴(kuò)展到文化或文明的范圍”,“(時(shí)間上)從一國(guó)一邦的盛衰興亡到整個(gè)文明體系的發(fā)生、發(fā)展和消亡”,打破了“國(guó)別史”和“斷代史”的研究方法。教師的反思似乎也有一個(gè)“反思單位”的問(wèn)題。一是在反思的時(shí)間上,需要有一種“長(zhǎng)時(shí)段”(借用布羅代爾的歷史學(xué)概念的喻意的反思。也就是像于永正老師那樣,反思自己走過(guò)的所有時(shí)光,甚至包括在歷史長(zhǎng)河中審視這段屬于自己也屬于語(yǔ)文教學(xué)的時(shí)間段的價(jià)值與意蘊(yùn),它的好處在于看到時(shí)代的優(yōu)越與局限,給身在其中的自己以定位;二是在反思的空間上,包括課堂的教學(xué)行為、教學(xué)方法乃至自己的整個(gè)教育理念。從教育教學(xué)到人生的成長(zhǎng)與發(fā)展,都應(yīng)當(dāng)進(jìn)入反思的視野,因?yàn)橐粋€(gè)教師對(duì)人生的認(rèn)識(shí)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他對(duì)教育的認(rèn)識(shí)。書中這些特級(jí)教師無(wú)論持什么樣的教育教學(xué)觀,他們往往隱含著一個(gè)共同的人本預(yù)設(shè),那就是將師生關(guān)系視為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我們的反思不僅需要對(duì)象,還需要能夠提供豐富意義的“反思背景”。因?yàn)楸尘暗恼w性可以讓部分顯現(xiàn)出更為全面的意義與價(jià)值。維特根斯坦說(shuō):“告訴我你怎樣在尋找,我就告訴你,你尋找的其實(shí)是什么。”[12]反思方式往往決定著你的反思所得。
課程產(chǎn)生于人類代際的更迭,它可以將前人業(yè)已熟悉的路徑以經(jīng)濟(jì)高效的方式授予后人,從而讓累進(jìn)式的社會(huì)發(fā)展成為可能。于是,使每一代人的知識(shí)可以向后無(wú)限傳承,形成可以讓后繼開(kāi)拓者拾級(jí)而上的知識(shí)的階梯,便成了課程的本然意義。
課程如是,這本“思想錄”大抵也如是。
參考文獻(xiàn):
[1]教育部.特級(jí)教師評(píng)選規(guī)定[J].人民教育,1993(Z1).
[2]楊九俊.斯霞的意義[J].江蘇教育研究,2011(1).
[3]周一貫.名師文化:小語(yǔ)界不落的彩虹——獻(xiàn)給“全國(guó)小學(xué)語(yǔ)文名師研究中心”[J].語(yǔ)文教學(xué)通訊·小學(xué)刊,2006(9).
[4]根據(jù)于漪老師在《張慶文集》首發(fā)式上的發(fā)言整理.
[5]趙汀陽(yáng).壞世界研究:作為第一哲學(xué)的政治哲學(xué)[M].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9.
[6]李如密.教學(xué)風(fēng)格的內(nèi)涵及載體[J].上海教育科研,2002(4).
[7]蔡海鵬.學(xué)“名師”與學(xué)書法[J].人民教育,2005(3—4).
[8]呂赟.我們應(yīng)該向名師學(xué)“內(nèi)功”[J].教學(xué)與管理,2006(9).
[9]朱永新.教師們?yōu)槭裁淳芙^讀書[J].天津教育,2007(9).
[10]陳納.地理與時(shí)間的碎片[J].讀書,2011(7).
[11]晁福林.論中國(guó)古史的氏族時(shí)代——應(yīng)用長(zhǎng)時(shí)段理論的一個(gè)考察[J].歷史研究,2001(1).
[12]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Remarks[M].Blackwell:1975.27,轉(zhuǎn)引自趙汀陽(yáng).身與身外:儒家的一個(gè)未決問(wèn)題[J].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