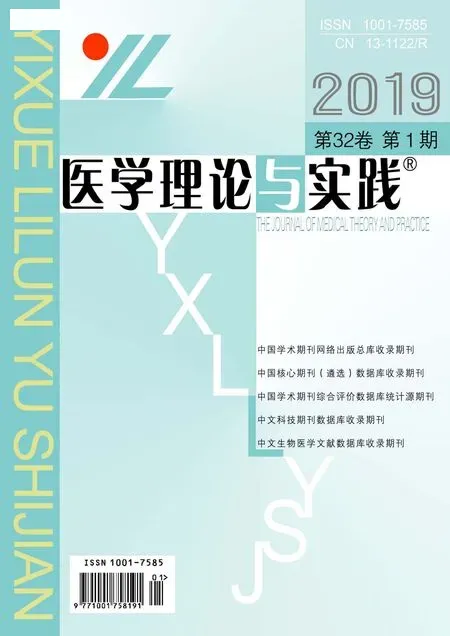連續(xù)護(hù)理和常規(guī)護(hù)理應(yīng)用于陣發(fā)性房顫射頻消融術(shù)后患者中的效果對比
周琪鈺 李 昌
湖北省中山醫(yī)院心內(nèi)科,湖北省武漢市 430033
心房顫動(dòng)(Atrial fibrillatafion,AF)按持續(xù)時(shí)間可以分為陣發(fā)性房顫、持續(xù)性房顫和永久性房顫,其中陣發(fā)性房顫是最嚴(yán)重的心房電活動(dòng)紊亂,也是最常見的快速性心律失常之一[1]。目前,對于陣發(fā)性房顫最有效的治療方法就是射頻消融術(shù),而術(shù)后應(yīng)用的抗凝、抗心律失常藥物又給術(shù)后護(hù)理工作帶來難度。目前,護(hù)理通常有常規(guī)護(hù)理和連續(xù)護(hù)理,常規(guī)護(hù)理因只在院內(nèi)實(shí)施,無法跟蹤了解術(shù)后患者院外服用抗凝藥物、康復(fù)及并發(fā)癥發(fā)生等情況,而連續(xù)護(hù)理通過定期隨訪可解決此問題。本次主要對比連續(xù)護(hù)理與常規(guī)護(hù)理在陣法性房顫患者射頻消融術(shù)后護(hù)理的效果。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6年11月—2017年11月于我院心內(nèi)科行射頻消融術(shù)治療的陣發(fā)性房顫患者60例,按照數(shù)表法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各30例。對照組男19例,女11例;年齡41~65歲,平均年齡(54.23±6.14)歲;病程1.5~9年,平均病程(4.88±2.18)年。觀察組男21例,女9例;年齡40~67歲,平均年齡(54.56±6.23)歲;病程1~10年,平均病程(5.12±2.4)年。兩組患者在年齡、病程等一般資料方面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
1.2 方法 由科室主任、護(hù)士長作為組長、副組長,小組單位配置2名責(zé)任護(hù)士,1名主管醫(yī)生,成立研究小組。
1.2.1 對照組采用常規(guī)護(hù)理模式。責(zé)任護(hù)士負(fù)責(zé)指導(dǎo)患者合理用藥、養(yǎng)成健康生活習(xí)慣、緩解患者緊張情緒及術(shù)后的生命體征監(jiān)護(hù),體溫、尿量的測量,異常情況的報(bào)告。主管醫(yī)生負(fù)責(zé)病史采集、詳細(xì)查體、制定術(shù)前術(shù)后治療方案、病情溝通等工作。
1.2.2 觀察組在對照組基礎(chǔ)上進(jìn)行連續(xù)護(hù)理。入院時(shí)對患者及家屬進(jìn)行2次房顫知識(shí)培訓(xùn),將射頻消融術(shù)治療陣發(fā)性房顫的優(yōu)勢告知患者,積極與患者溝通,消除或緩解患者緊張、恐懼情緒;出院時(shí)詳細(xì)講解INR知識(shí)及復(fù)查重要性,告知服藥時(shí)間、藥物副作用、并發(fā)癥等注意事項(xiàng),尤以各種出血并發(fā)癥為重點(diǎn),囑患者一旦在家中發(fā)現(xiàn)各種黏膜、皮下出血,消化道出血導(dǎo)致的黑便、嘔血,腦出血導(dǎo)致的意識(shí)模糊、嘔吐等癥狀,需及時(shí)通知主管醫(yī)生;出院后的第1、2、4、8周由護(hù)理人員對患者進(jìn)行電話隨訪,對患者的用藥依從性、術(shù)后并發(fā)癥、INR 達(dá)標(biāo)、護(hù)理滿意度等情況進(jìn)行了解,及時(shí)解答患者疑問,給予患者康復(fù)指導(dǎo)。
1.3 觀察指標(biāo) 統(tǒng)計(jì)患者術(shù)后并發(fā)癥發(fā)生例數(shù)、復(fù)查 INR 結(jié)果及用藥依從性情況;采用自制調(diào)查問卷對患者進(jìn)行護(hù)理滿意度調(diào)查,比較兩組護(hù)理滿意度。
1.4 統(tǒng)計(jì)學(xué)方法 采用SPSS19.0統(tǒng)計(jì)軟件分析處理所得數(shù)據(jù)。計(jì)量資料用均數(shù)±標(biāo)準(zhǔn)差表示,組間采用t檢驗(yàn),計(jì)數(shù)資料用百分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yàn)或Fisher確切概率法,P<0.05為差異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
2 結(jié)果
2.1 用藥依從性、INR達(dá)標(biāo)、并發(fā)癥情況 觀察組患者用藥依從性顯著高于對照組(P<0.05);INR 達(dá)標(biāo)、術(shù)后并發(fā)癥發(fā)生率雖優(yōu)于對照組,但差異無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用藥依從性、INR達(dá)標(biāo)、并發(fā)癥情況比較〔n(%)〕
2.1 護(hù)理滿意度 觀察組護(hù)理滿意度顯著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2。

表2 兩組護(hù)理滿意度比較〔n(%)〕
注:*與對照組比較,P<0.05。
3 討論
陣發(fā)性房顫是房顫最為常見的類型,據(jù)統(tǒng)計(jì)[2],國內(nèi)房顫發(fā)生率為0.61%,隨著年齡的增長發(fā)病率明顯增加, 射頻消融術(shù)作為有效的治療方法,術(shù)后需要較長期的應(yīng)用抗凝藥物,術(shù)后的出血風(fēng)險(xiǎn)高,房顫的復(fù)發(fā)率較高,且隨著手術(shù)后時(shí)間的延長,復(fù)發(fā)率呈上升趨勢[3],因此患者康復(fù)是一個(gè)漫長的過程。連續(xù)護(hù)理是指在不同的醫(yī)療服務(wù)機(jī)構(gòu)間實(shí)現(xiàn)無縫隙銜接,為患者提供連貫的健康照顧,形成患者與專業(yè)醫(yī)療機(jī)構(gòu)的持續(xù)聯(lián)系[4],其可以突破常規(guī)護(hù)理局限,持續(xù)地對患者提供并發(fā)癥預(yù)防、康復(fù)建議、心理輔導(dǎo)等,切實(shí)提高患者生活質(zhì)量。本文結(jié)果顯示,觀察組用藥依從性、護(hù)理滿意度明顯優(yōu)于對照組(P<0.05),在INR 達(dá)標(biāo)、術(shù)后并發(fā)癥方面,雖優(yōu)于對照組,但差異無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
近年來,連續(xù)護(hù)理的概念在我國越來越受到從業(yè)人員的重視,越來越普遍地應(yīng)用在臨床護(hù)理工作中,通過連續(xù)護(hù)理的宣教培訓(xùn)以及院外的電話或門診隨訪,對于緩解患者焦慮、恐懼的不良情緒也有幫助。深入發(fā)展很可能會(huì)降低再住院率以及合并癥的發(fā)生率,甚至是降低死亡率。已經(jīng)有部分研究證實(shí)了連續(xù)護(hù)理降低慢性病再住院率的效果[5]。
綜上所述,對患有陣發(fā)性房顫患者的射頻消融術(shù)后護(hù)理環(huán)節(jié)中,積極應(yīng)用連續(xù)護(hù)理模式, 可以顯著改善患者用藥依從性及護(hù)理滿意度,對于術(shù)后并發(fā)癥及INR指標(biāo)上也有所改善,值得臨床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