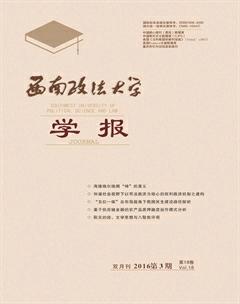平政院審理廟產糾紛評析
袁春蘭 陳紹鵬
摘要:清末民初興起了一股“廟產興學”之風,大批寺廟財產被政府提充作辦學之用,極大地損害了寺廟權益,因未有專門的審判機關審理此類案件,以救濟寺廟的權益,致使此類糾紛累積下來并逐漸多樣化和復雜化。民國成立之初,設立平政院作為處理行政處分糾紛案件的審理機關。平政院在存續的十幾年內審理了19起有關寺廟的行政處分案件,主要包括廟產管理糾紛、廟產辦學糾紛和寺庵人事糾紛三類,這些糾紛產生的原因主要有民初法治思潮的興起、法律制度的不完備和清末以來持續施行廟產興學政策的刺激。同時,這些糾紛的產生和審理也反映了近代中國法治現代化發展的狀況。
關鍵詞:廟產興學;平政院;近代化;行政訴訟
中圖分類號:DF092 文獻標志碼: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3.02
一、廟產興學——廟產糾紛的緣起考察
傳統中國社會里寺廟普遍存在,一般寺廟均有一定廟產,所謂廟產是指屬于寺廟的一切財產,包括寺田、寺塔房舍及附屬的法物等。但傳統中國社會的法律對于廟產問題卻未有完備的法律規制,尤其是對廟產歸屬于公還是歸屬于私的問題始終未能解決,加之佛教思想與傳統儒家文化之間的價值沖突,一旦出現社會危機和政局動蕩,寺廟便會首當其沖遭受類似于“三武滅佛”式的災難。
受甲午戰爭戰敗的刺激,晚清洋務重臣、湖廣總督張之洞認識到,必須要興辦教育事業以富國強兵,然而數目龐大的辦學經費是當時極度匱乏的晚清財政所無法承受的,1898年4月他作《勸學篇》上書清廷,在《設學第三》中他建議把佛道寺觀改為辦學之處,利用廟產解決教育經費不足的問題,以發展教育事業,他建議“一縣可以善堂之地、賽會演戲之款改為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費改為之。然數亦有限,奈何?日:可以佛道寺觀改為之。今天下寺觀何止數萬,都會百余區,大縣數十,小縣十余,皆有田產,其物業皆由布施而來,若改作學堂,則屋宇、田產悉具,此亦權宜而簡易之策也。……大率每一縣之寺觀取什之七以改學堂,留什之三以處僧道,其改為學堂之田產,學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計其田產所值,奏明朝廷旌獎,僧道不愿獎者,移獎其親族以官職。如此則萬學可一朝而起也。以此為基,然后勸紳富捐貲以增廣之”。在此之前,晚清著名學者、維新派代表人物陳熾在其所著《庸書》中更直白的論述道“各省叢林、道院,藏污納垢,坐擁厚資,徒為濟惡之具。有犯案者,宜將田宅一律查封,改為學校。僧道還俗,愿人學者亦聽之。一轉移問,而正學興,異端絀,宏治化,毓賢才”。然而,因并未引起重視,他的觀點少有人贊同。
維新變法期間,康有為為實施變法,改革教育事業,于1898年6月上書給光緒帝《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為學堂折》,認為“查中國民俗惑于鬼神,淫祠遍于天下。以臣廣東論之,鄉必有數廟,廟必有公產。若改諸廟為學堂,以公產為公費……則人人知學、學堂遍地”。他建議將廟產改作學堂,光緒帝采納了他的建議并發布上諭要求“各省府廳州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其地方自行捐辦之義學社學等,亦一律中西兼習,以廣造就,至于民間祠廟,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由地方官曉諭居民,一律改為學堂,以節靡費而隆教育”。在上諭中,改用“不在祭祀典者”的稱呼取代“淫祠”這種帶有歧視性的詞語,使該政策更具有可行性。戊戌變法僅僅維持103天,便因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而告終,康有為的廟產興學建議未能得以有效實施。
戊戌政變以后,清廷宣布戊戌變法期間的政策,包括廟產興學政策全數廢除,并下令保護佛教產業。1900年庚子事變以后,為挽救統治危機,清廷宣布施行“新政”,興辦教育事業,此時教育經費仍是極大難題,戊戌變法期間的廟產興學政策不得不恢復執行,清廷宣布為開學校“可借公所寺觀等處為之”。大批寺廟被政府提充作辦學之用,地方劣紳也借此機會侵占廟產,由于清政府并沒有建立相應的救濟制度,各寺廟對所受損害無法通過法律途徑維權,因此出現了不少寺廟暴力反抗廟產辦學的現象,廟產問題演化為嚴重的社會事件。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華民國成立,隨后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明確指出“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人民有陳訴于行政官署之權”、“人民對于官吏違法損害權利之行為,有陳訴于平政院之權”,依據這一精神,平政院于1914年在北京成立,開始受理行政訴訟案件,內設行政審判庭和肅政廳,分別審理行政訴訟案件和糾彈官員不法行為。這“對清末以來持續激化的廟產問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一方面使得廟產問題迅速復雜化,另一方面又使政府解決曠日持久的廟產問題成為可能”。廟產糾紛呈現多樣化的趨勢,各寺廟不僅將因廟產辦學產生的糾紛,甚至將廟產管理和寺廟人事變動產生的糾紛也訴訟于平政院。筆者依據黃源盛先生收集整理的《平政院裁決錄存》統計,發現在平政院存續的1914年至1928年間,平政院共計審理19件廟產糾紛案件,下文將通過對這些廟產糾紛案件的分析,探究平政院如何審理這些廟產糾紛,并藉此考察這些廟產糾紛產生的原因。
二、平政院審理廟產糾紛的類型
根據《平政院裁決錄存》統計,1914至1928年,平政院共計審理有關廟產的糾紛案件合計19件。這些案件主要包括廟產管理糾紛、廟產辦學糾紛和寺庵人事糾紛三類,其中廟產管理糾紛6件,廟產辦學糾紛8件,寺庵人事糾紛5件。從判決的結果來看,維持原處分者的11個,約占所有案件的58%,取消原處分者4個,約占21%,變更原處分者4個,約占21%,維持原處分者與改變原處分者(包括取消和更改)大致相當,從這一層面看,其判決“似乎難以推斷平政院有明顯偏詢行政官署立場之一方,大總統亦尚能尊重裁決的結果,謂其毫無績效,并不公允”。
廟產糾紛具有復雜性,在審理廟產糾紛案件中為了查明案件事實,正確適用法律,保障審判的有序高效,整理當事人雙方的爭點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通過對平政院審理的19件關于廟產糾紛案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平政院在審理時針對不同類型的案件,運用了不同的審判技術,集中解決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的問題,這些關鍵問題的解決為平政院裁決提供了直接依據。
(一)廟產管理糾紛
佛教的寺廟化促使寺廟以團體形式進行各項“出世”活動,1912年中華佛教總會的成立更是直接導致了大批現代宗教社團的出現,由此也產生了許多了關于廟產管理的爭端,根據《修正寺廟管理條例》第十條載:“寺廟財產由住持管理之”“寺廟財產不得抵押或處分之,但為充公益事項必要之需用,稟經該管地方官核準者,不在此限。”第二十條載:“凡寺廟住持違背管理之義務者,由該管地方官申誡或撤退之”,對于寺廟主持未能盡合理管理義務的,行政官署可以作出行政處分,由于公權力介入廟產的管理活動,使得關于廟產管理的爭端被納入到行政訴訟的范圍。如何判斷寺廟住持盡到合理的管理義務,則是審理關于寺廟管理糾紛的關鍵。
平政院判定寺廟是否盡到合理管理義務,主要是通過考察寺僧有無違背清規情形及通過違法管理行為來獲取個人私利。例如“山東福山縣尼僧正慧因紳民劉子琇逐尼霸產訴山東省公署案”,平政院認為該案之關鍵不在于廟產之屬尼屬廟,而當以原告之行為是否觸犯《修正管理寺廟條例》第二十一條之“違背第二十一條規定抵押或處分寺廟財產時,由該管地方官署收回原有財產,或追取原價給還該寺廟,并準照第十九條規定辦理”,認為該條立法之意是管理寺廟但以廟產不受損害為前提,原告“將舊房五處破料售價還債,所有基地淮人借蓋新房,收取租金十年,是舊料雖經售出,而廟地所有權仍繼續存在并未移轉。該原告以售料之價清償廟中欠債,開支尚屬正當,與盜賣情形不同,自不得謂該原告為任意處置,茲行加以撤退。即謂該原告售料租地認為一種處分,有違本條例第十一條之規定,可以準照第十九條之規定辦理。第查地方官于各寺廟僧道住持之申誡或撤退,應以不守教規情節較重為標準,該原告售賣房料還債,系屬善意經營,并非不守教規情節較重。”基于以上理由平政院裁決認為原告盡到了合理的管理義務,不得因此取消原告住持的職務,因此判決取消被告官署之處分。
類似案件還有“湖南三官殿僧愿成因寺田被烈士祠提充經費陳訴湖南前行政公署案”、“江蘇上海縣西方庵僧人因庵產被住持等假捐串賣訴江蘇巡按使公署案”、“京兆宛平縣天寧寺僧性海等因撤退住持及廟產爭執訴內務部案”等,針對上述案件,平政院在審理中援引法律規定的同時,也注重考察寺僧有無違背清規情形及通過違法管理行為來獲取個人私利,并以此判斷被告官署處分的合法性。
(二)廟產辦學糾紛
廟產興學政策使得寺廟財產受到極大損失,各地僧人為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而提起關于廟產辦學的訴訟。平政院在審理該類行政訴訟中,必須要解決的問題便是行政官署的行政處分是否違背保護人民私有財產的憲法基本原則。而哪些屬于寺廟私產,哪些是公產則難以判斷,這里必須提到民國初年在寺廟私產問題上民國北京政府的態度和中華佛教總會爭取佛教寺廟財產權益的努力。
清末以來的廟產興學使得各地寺廟面臨嚴重的生存危機,這也促成佛教的改革,各寺廟認識到必須將全國寺廟聯合起來,以團體力量保護寺廟權益,1912年2月,中華佛教總會成立,它是聯合全國80多個寺院共同發起的,總部設在上海的靜安寺,在其章程第一條即指出“凡會中各寺庵所有財產,無論檀越施助、寺僧苦積,外界如有藉端攘奪,本會得據法律實力保護,以固教權”,在它的推動下,中華佛教總會最多時發展到22個省級支會,600多個縣級分會,這極大地促進了對于廟產的保護。中華佛教總會努力說服民國政府,最終促使民國政府頒布大總統令強調:“約法頒布以后而當各教會未成立之先,凡未經查明確系宗教所私有者,其廟產仍無獨立形式,斯時國家或團體仍得適用習慣視該廟為公有而隨意處分之。”隨著之后《管理寺廟條例》的頒布,寺廟私有的財產權屬于寺廟的原則最終確立下來。
在平政院的司法實踐中,如何區分寺廟私產問題成了案件審理中的關鍵問題。例如在審理“浙江溫嶺縣崇善寺僧人雪山等因案被縣知事將寺產充公改辦學校訴浙江巡按使公署案”時,被告浙江省公署援引內務部在民國二年(1913年)四月內務部電令“中國廟宇向均視為公有財產,得由國家或團體隨意處分,已成習慣。各廟產未經各該教會查明確系私有以前收歸公用者,只得謂為適用習慣,不得謂為違背約法”。但原告認為該縣佛教分會在1911年9月就已經成立,根據大總統令該廟產當屬于寺廟,不得提充辦學。平政院查核認為該縣佛教分會于1913年9月成立,是在大總統令頒布之后成立的,原告聲明為虛,因此不認可原告主張該廟產屬于寺廟的訴請,依據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則,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請。本案中,平政院首先即確定適用《寺院管理暫行規則》關于廟產問題的規定,進而確定了行政官署將該廟產提充辦學決定的合法性,以此為依據作出裁判。
此類案件還有“江蘇宿遷縣僧人慧門等因請將原認地方興學捐款改辦慈善事業訴江蘇前巡按使公署案”、“直隸懷來縣關帝廟僧本慧因縣知事將廟產提撥學校訴直隸省公署案”等,這些案件亦是需要先解決廟產屬公屬私的問題,進而考察被告官署作出行政行為的合法性。
(三)寺庵人事糾紛
寺廟管理條例的頒布,規范了寺廟的管理模式,該條例第十條規定:“寺廟財產由住持管理之”,第二十條規定:“凡寺廟住持違背管理之義務者,由該管地方官申誡或撤退之”,條例賦予了地方政府和管理寺廟事務中央機關——內務部對于寺廟的人事管理權。主管官署有權對寺廟人事作出處分,僧尼對處分不服的可以向平政院提起行政訴訟。從本質上看,寺廟屬于宗教事務,因此宗教習慣對寺廟人事的影響作用往往比較大,因此平政院在審理時要首先解決的問題是法律與宗教習慣的沖突問題。
如在“京兆大興縣僧福海因京師警察廳令行各寺院公舉廣善寺住持訴內務部案”中,該案起因于京師廣善寺前住持達遠于民國元年因病退院,其法徒寶山承繼為住持,寶山因不守清規被人控告,被內務部撤退住持,隨即該院推選該寺監院岫明為住持,該寺僧人福海訴經京師警察廳任命普濟寺住持寬祥等公舉驚峰為住持,僧人性海等不服,訴至平政院反對任命寬祥,平政院查明后認為,普濟寺與廣善寺寺院性質不同,分屬于佛教性相二宗,當時寺廟住持繼任習慣是由退院佳持選賢承繼。本案被告認為寶山乃因不守清規被控離寺,即與經官撤退之住持不能自行傳座者無異,自應依據該條例第二十六條之規定辦理,平政院認為“京師警察廳酌令各寺公舉,雖因事實上之關系量為變通,惟叢林性質不同、宗派各異,既依條例適用公舉而該寺詢系性相二宗,京內尚多同宗之寺,則公舉方法只應于廣善寺本寺以外推及于該寺同宗之寺院,責令參與選舉方與法意相符。若不分同宗與否,泛及二十五家,未免漫無限制”,根據該理由,平政院裁決變更京師警察廳的決定,判決由內務部令行京師警察廳飭傳廣善寺退院住持達遠等,重行召集與該寺同宗之寺僧男行公舉住持。總體上看,平政院在依法裁判的同時也尊重了佛教習慣,從而較為妥善地解決了法律規定與宗教習慣的沖突。
此類案件還有“武清縣慈航寺住持僧海秋因案被內務部撤退住持訴內務部案”、“京兆宛平縣天寧寺僧性海等因撤退住持及廟產爭執訴內務部案”等案。由此可以看出,平政院在民國初年新舊交替的歷史時期,在踐行法治精神的同時,也承擔了調和社會矛盾的作用。
三、平政院審理廟產糾紛的特色
(一)廟產糾紛審理的法律依據
審理廟產糾紛的依據為何,這是平政院審理行政訴訟案件的先決問題,總體來看,民初北京政府制定頒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建立了一套較為完善的法律體系,為平政院開展訴訟活動提供了支持,主要包括以下幾種:
1.憲法
南京臨時政府頒布的《臨時約法》第十條明確了人民對于官吏違法損害權利之行為,有陳訴于平政院之權,這為平政院審理廟產糾紛案件提供了根本法的支持。北京民國政府頒布的《中華民國約法》進一步確認了平政院有權審理官吏侵害人民權利的行為。
2.法律法規
《平政院編制令》頒布以后,北京民國政府相繼制定頒布了《行政訴訟條例》、《訴愿條例》、《糾彈條例》、《行政訴訟法》、《訴愿法》及《糾彈法》等法律,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訴愿、行政訴訟及官吏監察制度。這是在部門法層面上為平政院審理廟產糾紛案件提供了依據,各部門亦依據這些法律制訂了一系列單行法規和規章,構建起一套調整廟產法律關系的法律體系。
1913年6月,內務部為加強寺廟管理,頒布《寺廟管理暫行規則》共計7條,規定“不論何人不得強取寺院財產”、“應歸國有之財產者,因辦理地方公益事業時,得由該省行政長官,呈請內務總長、財務總長許可撥用”。同年10月,內務部議定祠廟調查表,將寺廟公私財產權分開,規定“如該祠廟歷屬于國家祀典者為官產,其有年代碑記無考,非公非私者亦屬官產,由地方鳩資或布施建設者為公產,由該寺廟住守人募化以及私財建設者為私產”對于屬于公產的部分政府可以為社會公益的目的提充辦學。1915年民國北京政府以大總統名義頒布了單行法規《管理寺廟條例》三十一條,規范了寺廟界限、寺廟注冊、處罰等相關規定,但是內容龐雜,適用較為困難,故1921年5月民國北京政府廢止了《管理寺廟條例》,另以大總統命令頒布《修正管理寺廟條例》共計二十四條,單獨列一章細化規定了寺廟之財產,規定寺廟財產由住持管理。至此有關規范廟產的法律體系最終構建完成。
3.習慣法
民國初建,各項法律制度并未完備,尤其對于廟產糾紛案件,與傳統相連甚密,平政院在審理這一類型的行政訴訟案件時,也會尊重習慣,依據相應習慣來裁決,例如在“京兆大興縣僧福海因京師警察廳令行各寺院公舉廣善寺住持訴內務部案”中,平政院對于寺廟主持的傳座制度予以尊重,在調查到爭端雙方分屬于法性宗與法相宗時,認為住持的選擇“公舉方法祗應于廣善寺本寺以外推及于該寺同宗之寺院,責令參與選舉方與法意相符。”
4.行政命令
所謂行政命令是由總統及行政官署依法頒布的命令,原告如認為行政處分違反行政命令也可以提起行政訴訟。如在“湖南三官殿僧愿成因寺田被烈士祠提充經費陳訴湖南前行政公署案”中,僧人愿成因被告違反了民國元年五月十一日臨時大總統所發布的保護人民財產命令而提起訴訟請求發還寺田,平政院對大總統命令進行了解釋,作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的裁決。
(二)司法審查機制的建立
民初法制未備,不遺余力地移植西方國家的法律制度,引進西方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政治架構。通過日本介紹而來的司法審查機制,為司法體制的完善提供了重要途徑。平政院建立后,在司法實踐中,也充分利用司法審查機制,審查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如在“安徽蒙城縣僧人空華等因蒙城縣公署違法處分廟產一案訴安徽省公署案”中,平政院依據上位法優于下位法的原則,審查認為蒙城縣頒布的“抽提不在祀典廟產辦法”中對于廟產處置的規定與“新、舊管理寺廟條例”多有未合,該縣公署依據該辦法作出的行政處分自無法律依據,因此作出變更被告官署之處分的裁決。平政院在該案審理中,通過審查抽象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并進而考察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可以看出司法審查機制已經初步運用到司法實踐中。又如在“湖南三官殿僧愿成因寺田被烈士祠提充經費陳訴湖南前行政公署案”中,針對原告錯誤引用大總統公布保護人民財產命令的情形,平政院解釋道:“至原告引大總統公布保護人民財產命令,請求發還原產,詳繹令文,系指迫脅立約、尚未履行者而言。與該僧之稟請捐助并將田契遣人送交收管,而事經履行者不同。”因此平政院認為被告官署對于廟產的處分是適當的,并不支持原告的訴求,由此可見當時平政院司法審查的范圍,不僅包括法律法規,還包括大總統頒布的命令,總體來說司法審查的范圍是較為廣泛的。
司法審查的深度和廣度一直被作為衡量一國行政法治發展水平的標尺。以上兩個案件中,平政院司法審查的對象不僅包括對抽象行政行為的審查,甚至還包括對大總統作出的行政命令的審查,平政院的司法審查范圍由單純的形式審查擴展到行政行為的依據——抽象行政行為——的審查,其力度之大,范圍之廣,即使在當今的司法語境下也是難能可貴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在民國初年,平政院的司法審查機制已經開始建立。
(三)平政院審理廟產糾紛的特點
平政院在審理廟產糾紛時,依據一般法律規定進行裁判的同時,還考慮到廟產糾紛涉及宗教信仰,部分糾紛前清時期便已經產生,還有部分是與清末民初的廟產興學政策有關的社會現實,因此在審理這類案件時,其審理顯現出一些獨有的特點。
廟產糾紛案件以書面審理為原則,言辭審理為例外。1914年頒布的《行政訴訟法》第23條規定:“被告提出答辯狀后,應指定日期,傳原被告及參加人出庭參加庭審,但平政院認為便利,或依原被告之請求時,得就書狀裁決之”,確立了行政訴訟案件以言辭審理為原則,書面審理為例外的規則,然而廟產糾紛案件的審理卻依據該條的“但書”,以書面審理為原則,言辭審理為例外。平政院受理廟產糾紛案件后,先“調集卷宗證據,咨行被告官署依法答辯”,如果案件有第三人,則通知第三人參加訴訟,如在“京兆宛平縣民任德明等因不服京兆尹公署維持宛平縣署認私產為廟產之決定訴京兆尹公署案”中,僧人樂然因與該案有關,狀請參加訴訟,平政院準許其參加訴訟。平政院查明案件事實后,“并就書狀裁決如左”,說明在審理廟產糾紛時平政院一般堅持書面審理的原則。
平政院一般采取職權調查的方式查明案件事實,作出的裁決結果分為維持,變更和取消三種。值得注意的是,平政院裁決內容有時會超出當事人訴請范圍,如在“江蘇江寧縣棲霞寺住持僧人宗仰因請求發還原產未準訴江蘇行政公署案”中原告請求被告官署發還田畝,平政院裁決確定此項被提寺田準許該寺永遠承佃,在駁回原告訴求的同時,裁決由被告官署令江甯縣知事分別勘明該田肥瘠等則,比照鄰近田畝之租價,于二百元以上,四百元以下之范圍內妥為訂定年租,按數撥交勸學所支用,自此次定案之后,原告不得托故短繳,被告亦不得任意奪佃。為求定紛止爭,平政院的裁決大大超過了原告的訴求范圍,在某種程度上并不符合訴狀一本主義,但就當時來看,這一裁決無疑是為當事人雙方的爭議畫上了句號。
平政院在對證據的審查上,注重證據的真實性和關聯性。平政院在當事人提供證據的同時,也積極尋求證據作為裁判案件的基礎,如“浙江省紹興縣大善寺僧朗誦為寺基建屋被縣勒拆一案訴浙江省公署案”中,原告認為“寺內基地泄系僧善悍、僧景彪等戶完納,則為僧人自置私產無疑,”但是平政院經核查認為“善寺內已廢毀之金剛殿基地既于前清光緒三十一年,經舊山陰縣知縣勒碑示禁,載明是項基地永遠不準建筑屋宇”,因此判決不支持原告之主張。平政院積極查核原被告證據的真實性與關聯性,以調查結果為依據作出的裁判是具有科學性的。
四、廟產糾紛產生的原因
法律的近代化本質上是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一種交織與轉化的歷程,現代法律取代傳統法律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它總是呈螺旋式的,傳統法下的遺留問題存留下來成為法律現代化的注腳。清末興起的廟產興學運動使寺廟的廟產權益受到極大損害,各寺廟無從通過適當途徑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正如如孔飛力所指出的那樣“在舊制度的議程上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肯定會在現代中國的公共生活中表現出來”,民國建立后,著力建設法治國家,設立平政院受理行政訴訟案件,廟產糾紛這一前清時期留下的問題,在民國初年突顯出來,為社會所關注,它的出現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民初興起的法治思潮
民國建立以后,社會各界熱忱于法治國家建設,尤其是《臨時約法》以憲法性文件的形式,規定人民的一系列權利,促使社會上興起了一股法治思潮,民初政論家張東蓀指出“中國之當為法治國,已為全國上下所共認,謂會議正式大總統就職之宣言日:西儒恒言,立憲國重法律,共和國重道德……共和定義日,采大眾意思,制定嚴格法律,而大眾嚴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則共恥之。誠如大總統言,特法治國者,不僅恃人民之守法,尤必以國家各機關之行動,一一皆以法律為準繩”。在這種思潮的推動下,僧尼對行政機關的違法行政行為,選擇以行政訴訟方式維護權益,自不為社會輿論所排斥。
行政訴訟是一種“民告官”的法律行為,目的在于保障民權,防止政府權力的專斷和恣意,是現代法治社會的象征。但僧是否屬于“民”,行政機關能否作為被告參與到訴訟中?這些都是有待澄清的問題。佛教傳人中國已經有千年時間,幾乎跨越了整個封建時代,寺廟因其屬于宗教事務管理范圍而長期受到政府優待,寺廟僧人也不同于普通民眾。隨著清政府滅亡和民國政府的建立,中國人的公民意識開始覺醒,法治思潮風起云涌,僧人也受到這種思潮影響,他們“積極爭取僧尼的公民權利和身份地位。如太虛法師曾多次強調僧人亦為國民之一員,同享公民權利與平等地位。對于在歷史中已經習慣了享受封建統治者所給予的僧尼免服役調的僧人來說,這是僧人身份認同中一個很大的轉變”。《寺廟管理條例》第二條明確指出“凡寺廟財產及僧道,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與普通人民受同等之保護”,因此民初廟產糾紛案件的頻繁發生,僧尼得以通過行政訴訟手段維護自己的權益,正是受這種身份認同轉變的影響。而政府能成為行政訴訟的被告,這本身也代表著行政機關由傳統父母官的身份向著行政訴訟中平等主體身份的轉變,傳統法下,中國古代官員是作為君主的代表,為民父母,并治理國政,有學者指出“為民父母行政是中國傳統政治和行政制度的最基本立足點或出發點,是中國傳統政治和行政制度的靈魂”。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自然不存在行政訴訟制度孕育的土壤,固然出現了少量的民告官的現象,也僅是作為廉政監督的一種方式,在形式上是“告官員”而不是“告官府”,決不允許以官僚集團和官僚機構本身為控告對象,否則即被認為是叛逆的行為,在責任承擔上,亦是由違法官吏個人而非違法機關來承擔責任,這與西方法治國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相去甚遠,清末民初移植西方法律以建設法治國家,《臨時約法》的施行及平政院的成立,宣示著在法律上身份轉變的開始。
(二)民初法律制度的缺陷
民國初期雖承繼了清末修律的結果,但許多法律如法人制度仍不完善。各寺廟難以通過民事訴訟方式獲得完全救濟,須借助行政訴訟保護僧尼權益。民國初年對于廟產的法律地位,也一直處于搖擺不定的狀態,從1912年《管理寺廟條例》到1915年的《寺廟管理條例》,其中對于廟產是從屬于寺廟本身,獨立于政府管理之外,還是從屬于國家,并未予以明確規定,各地判例亦多有不同。而廟產問題得以行政訴訟方式出現,是因為“從1911年以后,始終未能正常、持續召開的國會導致廟產制度的上位法——法人制度遲遲無法通過頒布民法典確立,也就無法為廟產中屬于法人一般問題的制度提供全面系統的依托”。基于法律規定的漏洞,各地政府也就只能通過行政手段作出對于廟產的處分。
(三)廟產興學的政策推行
廟產興學政策刺激了寺廟為維護廟產權益而進行聯合,依靠團體的力量保護自身權益,1912年中華佛教總會及后來各宗教團體的成立,積極尋求法律手段維護寺廟權益,這也是當時廟產糾紛不斷出現的主要原因之一。早在1904年以八指頭陀敬安為代表的僧人代表團為維護廟產權益入京請愿,請求清廷保護廟產,清廷迫于壓力于1905年4月12日下詔地方政府保護寺廟,“前因籌辦捐款,迭經諭令,不準巧立名目,苛細病民。近聞各省辦理學堂工廠諸端,仍多苛擾,甚至捐及外方,殊屬不成事體。著各該省督撫飭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眾產業,一律由官保護,不準刁紳蠹役,藉端滋擾。至地方要政,不得捐勒廟產,以端政體”,要求禁止地方劣紳侵占廟產,但為時晚矣,提充廟產辦學已經成為趨勢,保護廟產的命令收效甚微。
民初政府受困于貧瘠的財政狀況,為發展教育事業不得不繼續施行清末的廟產興學政策,混亂的社會秩序與軍閥勢力的崛起導致廟產興學運動再次達到高潮,據《上海縣續志》載,上海一地,1903年至1918年,該縣辦學校143所,其中標明占據廟產開辦的學校就有50所。持續施行的廟產興學政策,使得許多僧尼因此喪失安身立命之所,也極大地傷害了他們的佛教信仰,引起了各地寺廟的強烈反感,現實促使各寺廟認識到必須聯合成立宗教團體保護自身權益。1912年2月,中華佛教總會成立,其宗旨是對于“凡會中各寺庵所有財產,無論檀越施助、寺僧苦積,外界如有藉端攘奪,本會得據法律實力保護,以固教權”,各地紛紛設立分會,參與保護廟產的行動,通過法律手段等表達自己的訴求,以期維護自己的廟產權益。在民事領域,根據章一博士的統計,1912-1928年民事最高審判機關大理院審理的關于寺廟的糾紛案件一共十四起,是各類型訴訟中最多的,而在行政訴訟領域,平政院亦審理了這19個有關廟產的糾紛,足可見當時廟產糾紛問題的嚴重性。
四、結語
《臨時約法》規定了廣泛的人民權利,極大地促進了近代公民意識的覺醒和行政機關主體身份的轉變,但正如盧梭所言:“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里。”權利的實現主要在于實踐,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法治諾言只是空中樓閣,對人民權利的諾言要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得到檢驗。
民國初年新舊交替的歷史環境,廟產糾紛案件自然出現了時代性和復雜性。因緣際會,平政院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行政訴訟審判機關,充當起廟產糾紛處理機關的角色,這得益于相對完善的制度設計和高素質的評事隊伍。在政局動蕩、戰亂頻仍的民國初年,平政院能夠做到不因人廢事,對廟產糾紛依法論斷,為力圖將肇建之初的民國引領到建設法治國家的正途之中所做的努力著實難能可貴,正如蔡志方教授所言“平政院在我國行政訴訟萌芽之時擔當裁判者之角色,于法治及法制均不甚發達之際,能有此成績尚屬難能”,可以看出,民初平政院對廟產糾紛的審理反映出法治觀念已經開始在民國初年深入人心,而中國的法治近代化之路也在不斷前進。
本文責任編輯:龍大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