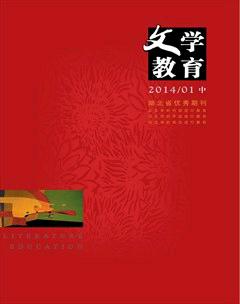民族傳統文化影響下的審美差異
[摘 要] 審美具有民族性,體現在宗教、文學、思想的各個方面,不同的民族傳承下不同的文化,久而久之造就了其獨特的審美視角和視野。盡管中國與日本兩國文化同出于東方一源,但在發展過程中不斷適應本土需要,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美學觀。本文試以“恩情”一詞為例,從審美定義、審美表現等方面闡述兩國賦予它的不同內涵以及由此所折射出的審美差異。
[關鍵詞] 民族;傳統文化;審美;差異
不可否認,日語中的“恩情”一詞來源于中國,但是當它一旦脫離了本土文化,融入另一個民族的傳統時,它的詞義便被賦予了新的審美內蘊,注入了新鮮的血液。《說文解字》中如此解釋:“恩”,從心因聲,惠也;“情”,從心青聲,人之陰氣有欲也。“恩情”一詞本義指深厚的情義,也可以引申為負恩者感念遇到困難時得到幫助的這份情義。
一、“恩情”的審美定義
在中國,恩情即恩惠、情誼,深摯的感情。最早見于漢朝班婕妤的《怨歌行》:“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后來三國時期魏國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尤姻媾之意,恩情已深。”①唐朝時期,鑒真東渡為日本帶去了大量的漢文書籍,日本人在漢字的基礎上仿照創制了自己的文字。當時傳入日本的“恩情”一詞,被日本賦予了兩層含義:一是感恩不及,披恩戴德;二是因給對方造成麻煩而感到內疚。②對日本人而言,“恩情”是接受恩惠,同時并對他人負起某種義務,代表著一種高度責任感的美德。擔負了人情債,因而,日本人要求自己牢記恩情并回報恩情,毫無怨言甚至不顧一切,他們甚至把極端的自我犧牲精神也納入這種美的顯現。“萬勿忘恩”是對恩情的真誠贊美也是負恩者謹慎奉行的道德圭臬。日本歷史上的明治天皇駕崩時,一代陸軍名將乃木希典選擇在這一天自殺殉國。他在遺書中寫道:“明治十年之役丟失軍旗后,即欲死得其所而不得,反蒙殊譽沐浩蕩皇恩茍活至今。現日漸老衰再無一用,故借此圣上大變之機,雖則惶恐,然決意了此余生。”③乃木希典具有報恩情結的自殺壯舉至今還被日本人奉為武士道德楷模大加頌揚。
反觀中國的土地上,“恩情”是對施予恩惠者的慷慨高尚的美德的一種贊揚。至于如何對待這份“恩情”,受恩者卻有多種選擇方式,古語有“滴水之恩,涌泉相報”的訓釋,也有“大恩不言謝”的說法。回報恩情,的確是受恩者懷有感恩之心體現,但不同于日本將報恩直接依附于“恩情”,具有強制性和絕對性,在中國人看來,它不是“恩情”的組成部分,而是接受恩情后的另一回事。《水滸傳》中一百零八條好漢中的首領宋江號稱“及時雨”,小說里的他從不吝嗇自己的幫助,竭盡全能給他人帶來惠利,廣泛贏得了民心,至于有沒有人回報他的恩情,有多少人回報他的恩情,怎樣回報他的恩情,作者施耐庵并不著力描繪。可見“恩情”在中國,因為它的無條件而顯得難能可貴,因此具有了美感。
二、“恩情”的集中體現
不論在中國還是日本,“恩情”最主要集中體現在君主(包括天皇、藩主或城主)恩澤和父母情深兩個方面。
日本人認為,他們得以生于這個國家,得以如此生活,得到大大小小的關懷,這一切不能不歸功于天皇的恩惠。因此,每一個人都應該誓死盡忠報答天皇的恩情。每一支以天皇名義分發到前線軍隊的香煙都是士兵領受的皇恩,出征前將士們所酣飲的每一口酒更是一種皇恩;而為了奪得二戰的勝利奮勇殺敵乃至犧牲,即使戰爭本身具有非正義性也必須執行。在這里,偏激的盡忠和極端的自我犧牲都是美的,它們只為轟轟烈烈回報皇恩。除開效忠天皇,對待自己的藩主也應該竭心盡力。藤澤周平的小說《生瓜與右衛門》中三栗與助藏奉藩主之命刺殺勢力強大的反賊平松一派,任務執行起來萬分艱難,最終以助藏犧牲,三栗負傷的代價消滅了平松的黨羽,沒有辜負藩主的囑托。日本的“忠”是不計條件的,而中國人則認為個人的效忠應該以“仁德”為前提條件,如果統治者昏庸無能,子民可以有揭竿而起反對統治的權利。“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④既然國家混亂、君主無能,自己又有什么必要去盡忠呢?中國人對日本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感到憤恨,靖國神社里供奉著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軍國侵略主義戰死的軍人及軍屬,在這些非正義的戰爭中戰死的將士居然還能得到眾人愛戴,甚至歷屆的日本首相也去參拜,中國人以自己慣常的思維方式去打量日本人的行為,認為這是罪惡的淵藪,暗指日本人至今不肯承認曾經的侵略行徑,是不知悔改的表現。其實不然,在日本,國民絕不能大逆不道地質疑天皇,忠君報主是他們的使命也是他們的美德,知恩圖報的將士們當然值得日本國民的緬懷。
報答父母恩情稱為“孝”,日本的“孝”相比中國的“孝”范圍大大縮小,它既不包括幾個世紀以來的祖先,也不包括一代代繁衍下來的巨大支系。日本的祖先崇拜僅限于近祖,孝道僅限于在世的人。對日本人而言,回報父輩恩情的最好方式是把自己受到的照顧轉移給子女,對自己的孩子悉心照顧就是回報自己年幼時曾經得到的父母之恩。人們像父母當年細心照顧自己一樣對待自己的子女,甚至照顧得更好,這也就部分地報答了父母之恩,總之,對孩子的撫養從屬于“父母的恩情”。而在中國,“贍養”和“撫養”是一對不同的概念,牢記父母的養育之恩不過意味著盡心贍養老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儒家經典《孝經》中規范了侍奉父母的一言一行。
三、對“恩情”的態度
“恩情”意味著重負,日本人在受恩時通常懷有矛盾的情緒:一方面,巨大的恩情推動著人們全力以赴地回報,另一方面,無論多么微薄的恩情債,都使自己感到痛苦難耐,而只有心存不快才稱為一種美德。這種矛盾心理決定了日本人在“恩情”面前慎重地選擇,受到生疏的人所施予的恩情則是最令他們生厭的事情,甚至可以全然不顧后果,斷然拒絕這種“恩情”。夏目漱石的小說《哥兒》中形象地描繪了日本人這種對待恩情的反感態度。哥兒與一位自己戲稱為“豪豬”的同事交好,一次出游時朋友請他喝了一杯價值一錢五厘的冰水。不久之后,他又聽其他同事說,朋友在背后指責自己,念起“豪豬”曾經予以自己的恩情,他痛苦萬分。第二天,哥兒把錢丟在朋友的辦公桌上,他必須把那杯冰水的“恩情”歸還,才能再清算兩人間的其他問題。對小事如此敏感,在中國他一定是個有點神經質的異常人,但這恰恰卻是日本人的美德。日本評論家談及“哥兒”,認為他是“一個脾氣暴躁,純潔如水晶,為正義而戰的都是。”受人恩情,即使微不足道也看作“百萬元”的價值,只有如數奉還,才能使自己擺脫“負恩”的境地。另一方面,“恩情”的復雜含義對施恩者也無形做出了限制。明治維新之前,日本有一條法令:發生吵架爭端時,旁人不可無端插手。⑤我們中國人看這無疑是人情冷漠的惡劣社會風氣,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因為日本人都知道給予幫助會使當事人“負恩”,所以都不便積極插手,而是慎重對待。一個濫施“恩情”的人會被懷疑居心叵測、圖謀不軌。即使是一支香煙,如果與遞煙者毫無瓜葛,日本人都會感到不舒服。這對于中國人的確比較匪夷所思,我們推崇助人為樂的風尚和無私奉獻的美德,“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⑥本是一首愛情詩,卻被后世引申為不計回報、慷慨付出的精神之美的最高境界。
結語:同是“恩情”一詞,在它的源地中國,展現出的是一種慷慨奉獻的美,無所謂回報,受恩者量力而行。而當它越過太平洋,東渡日本,“恩情”則被賦予了另一種全新的美。在那里,它代表著謹慎之美,感恩之美,當這種美展現到極致,死亡也被包含其中。
相異的民族文化造就了全然不同的審美向度,這正是中國人難以理解日本人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難以切身體會日本文學藝術的美感的重要原因。
注釋:
①摘自《辭源》,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②摘自《日本常用語詞典》,五南圖書,2012年版.
③摘自《為天皇“殉死”與“殉國”——乃木希典》2009年6月19日,日本新華僑報網.
④摘自《論語·衛靈公》:“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⑤引用《菊與刀》中的資料
⑥來自李商隱《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曉鏡但愁云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參考文獻:
[1]本尼迪克特:《菊與刀》,呂萬和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
[2]戴季陶:《日本論》,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簡介:覃芷荻(1993—),女,湖北宜昌人,湖北大學本科在讀,中國語言文學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