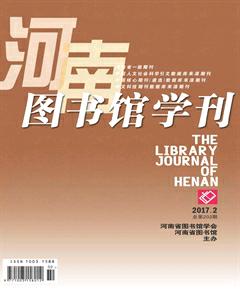一本圖書館社會形象理論的創新之作
孔德超
摘 要:文章肯定了《圖書館社會形象定位與發展》一書出版的意義,分析了該書在圖書情報學理論研究方面的重要性,并對其特點予以歸納,同時也指出了存在的問題。
關鍵詞:圖書館社會形象定位;圖書情報學;理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G25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1588(2017)02-0002-03
在當今這個重視“實際”、強調“應用”、尊崇“技術”的時代,學術研究,尤其是理論性比較強的學術研究,枯燥而艱難,在學術界常常是費力不討好的,在圖書情報學界也同樣如此。于是我們看到,各種打著“信息”“網絡”“數據”“智能”旗號的文章和論著蜂擁而出、鋪天蓋地,各種應用性研究成果大行其道、充斥其間。反觀比較純粹的理論研究,因為無法快速成文,難以獲得可觀的“收益”,需要坐冷板凳,從而越來越陷入“式微”的尷尬境地,甚至幾年都難得一見一本像樣的、有較高理論功底和學術水平的著作面市。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欣喜地看到由周九常等人撰寫、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專著《圖書館社會形象定位與發展》問世了,展讀此書,可以看出作者的“匠心”,不難發現其中的精彩。夸張一點兒說,它給當下沉悶的圖書情報界理論研究增添了一抹亮色。
圖書館社會形象定位問題(主要指公共圖書館社會形象定位)是一個涉及圖書館學、管理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學科交叉的復雜的研究課題,不是一個小問題,更不是一個人“閉門思考三五日,伏案動筆一兩篇”就可以解決的。作者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和河南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學者資助計劃的支持下,組成研究團隊,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研究,歷經四年有余,終成此書。
綜觀全書,其理論建樹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在理解公共圖書館社會形象的概念、構成因素及其相互關系的基礎上,構建出一個由十一個因素組成的公共圖書館社會形象體系模型。二是提出了公共圖書館的整體社會形象定位——以知識存取為核心的公共文化殿堂。三是在公共圖書館社會形象體系模型和整體社會形象定位的基礎上,分別提出了不同層次、不同類型、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公共圖書館的社會形象定位。四是以社會角色為切入點,分析了其與圖書館社會形象的相互作用與聯系,總結了不同歷史時期我國圖書館的社會形象演變的規律。五是從貼心服務(構建了價值導向型貼心服務模型)、新媒體技術應用的角度提出了公共圖書館社會形象塑造的新舉措,為公共圖書館的社會形象建設和管理提供了一條有別于前人、他人的思路和方法。六是系統提出了“最美圖書館”的評選標準和原則,并據此推舉出國內18個最美圖書館。
歸納起來,該書具有以下幾個突出的特點。
1 為圖書館社會形象塑造、建設和管理筑牢理論基礎
公共圖書館的社會形象定位是其社會形象管理和建設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是一個基礎性或前提性的問題。但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學術界幾乎不約而同、無一例外地忽略了這個問題,具體表現為研究圖書館社會形象塑造、社會形象建設的論文數量很多(尤其是關于圖書館社會形象塑造和建設的方法、措施方面的論文數量很多),而直接涉及和面對公共圖書館社會形象定位問題的文獻卻非常罕見。也就是說,大家多是“直奔主題”而來,研究圖書館如何進行形象塑造,通過哪些辦法、措施來改進圖書館的社會形象。而對于其首要問題或基本問題——形象定位問題——卻避而不談,可能是無心之失,或者是力有不逮,造成圖書館社會形象理論研究的先天不足。這是圖書館社會形象理論研究上的一個明顯疏漏,或者說是圖書館社會形象理論研究中的一個薄弱環節。這就如同建樓房,地基不牢就建起了樓房,樓房自然會出現問題。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該書無疑填補了圖書館社會形象的管理和建設理論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空白,彌補了其中的一個關鍵薄弱環節(據說這個“空白點”和“薄弱環節”正是促使作者加以思考、展開研究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樣一來,該書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種原始創新的性質。這種創新的特點在筆者這里也得到了部分印證——經過全面、系統的查詢、梳理,不僅國內沒有發現主題為“圖書館社會形象定位”的專著,而且國外也沒有發現同類的著作。此外,把該書放在國內整個圖書情報學界2016年所推出的專著群體中,也依然不掩其色,甚至可以說是其中顯得比較突出的一種。
2 初步形成圖書館社會形象定位基本框架,建立起圖書館社會形象定位的理論體系
該書通過系統研究,以基本概念(圖書館社會形象定位及其相關概念)和公共圖書館社會形象體系以及圖書館整體社會形象定位為“頭”,以實證研究,即對公共圖書館社會形象的調查分析(包括面向圖書館工作者的調查分析和面向社會人士的調查分析)和媒體報道中的公共圖書館社會形象調查為“尾”;以不同歷史階段的圖書館社會形象為“經”,以不同類型圖書館(主要是兒童圖書館和社區圖書館)和不同層級圖書館(主要是國家圖書館、省級圖書館、地市級圖書館和縣級圖書館)的社會形象為“緯”;以公共圖書館的社會形象定位“為體”,以公共圖書館社會形象塑造方法(主要表現為通過貼心服務和利用新媒體技術)“為用”,縱橫交錯地展開研究。最后,該書分析了實踐中“最美圖書館推選”或“尋找最美圖書館”活動與圖書館社會形象建設的關系,以及此類活動對圖書館社會形象定位、塑造造成的影響,可以看作是全書的“余響”。這樣,全書內容中所包含的圖書館社會形象定位理論體系的基本框架就隱然成型了。實事求是地說,這一基本框架和理論體系具有典型的開拓性和指引性,也就是說,后來的同類研究對它不可跨越,無法忽視。該書構建了圖書館社會形象定位的理論體系,為圖書館社會形象理論的研究提供了新鮮血液,帶來了新的生長點,拓寬了研究領域,深化了研究內容,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對圖書館社會形象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推動了其進一步完善。
除了上述兩個方面的理論創新價值外,該書也具有一定的應用價值,可以為我國公共圖書館的建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優化提供參考和指導。說到底,圖書館社會形象定位既是一個理論問題,又是一個實踐問題,該書提出了改善圖書館社會形象的關鍵舉措,假以時日,如果其思想、方法和措施能在圖書館實踐中加以貫徹、應用,將使圖書館管理者和館員可以以更加清醒的思路和穩健的姿態推動圖書館的健康發展,也使圖書館與讀者、公眾之間的關系更和諧。
3 邏輯性、系統性強
這一特點通過內容的時間順序(從古到今,從現在到未來)、層級順序(從頂級到高級再到中級,最后到基層)、重要性順序(從公辦到民辦,從國內到國外等)和學理順序等反映出來。僅就學理順序而言,按照邏輯關系和邏輯順序,首先,該書給出圖書館社會形象定位及其相關概念,從而為全書內容建立起必要的概念基礎;其次,系統搜集、梳理和分析國內外的相關研究成果,從而為該書寫作的必要性和內容的價值提供了注解和依據;接著,對公共圖書館的社會形象與社會角色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指出了圖書館社會形象的關鍵來源;之后,建立圖書館社會形象體系模型,給出了當前我國公共圖書館的整體社會形象定位,為后來不同類型、不同層級的公共圖書館的社會形象定位奠定基礎;再往后,對我國圖書館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形象進行了考察與分析總結,論述了新技術環境和社會需求下公共圖書館社會形象定位的未來發展;隨后,對不同類型、不同級別的公共圖書館的社會形象定位進行了研究;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順理成章、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地提出了改善公共圖書館社會形象的策略,即貼心服務和新媒體技術應用,并對國內最美圖書館進行推舉和分析。幾種不同的邏輯順序并行不悖,復合一體。在此情況下,全書邏輯思路清晰,邏輯順序分明,層次結構合理,系統性、邏輯性強。
此外,該書研究視角寬廣,從社會學、心理學、管理學、預測學等多個學科,或者說通過多學科交叉,從不同學科側面來關照公共圖書館的社會形象定位問題,這樣既增強了內容的豐富性,也提高了研究的科學性與嚴密性。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明,該書是一本具有一定理論高度和理論深度的不可多得的學術專著。
同時,該書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其理論部分和實證部分二者之間不是無關聯地拼湊,不是“水是水,油是油”,不是“兩張皮”那樣的關系,而是有機、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符合“事實上需要,邏輯上一致”的原則。理論部分是該書的主體,是全書的精華所在,是其創新之處,實證部分是其輔助、支持的部分,后者對前者有著增光添彩的作用。
當然,在個別地方,該書也存在一些問題。一般而言,創新有多大,問題就有多大,風險就有多高。該書的創新性顯而易見,自然也帶來一些可能不成熟或容易帶來爭議的問題:第一,盡管力圖多視角、多主體地研究公共圖書館的社會形象定位,但是該書主要還是從“圖書館”或者“圖書館人”的角度,即“本位主義”的視角進行研究,具體來說就是從“主動”的角度來研究公共圖書館的社會形象定位,而較少從讀者、公眾的“心理接受”或者“感覺印象”角度來進行研究,導致“研究視覺”或“研究立場”上的不平衡。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因為全方位、多視角的研究才是最理想的結果。第二,書中對18個中國最美圖書館的推選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結果可能不符合一些人的心理預期(尤其是讓那些層級較高、知名度較響亮、規模較大的圖書館或圖書館的管理者難以接受,因為在他們的心里,可能早已把自己認定為“最美圖書館”之一了,這樣難免會讓他們產生心理落差。當然,這種最美圖書館的推選很難讓所有的人認同,甚至產生一定的爭議。事實上作者在選擇中也面臨“兩難選擇”甚至“多難選擇”的困境,因為選擇標準的客觀性、同一性存在不足,不能把高層級圖書館與基層圖書館完全用同一標準衡量,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多少有些無可奈何的問題。第三,雖涉及個別私立圖書館或民營圖書館的社會形象定位,但是畢竟“著墨不多”,而隨著我國公共文化事業和圖書館事業的發展,私立圖書館和民營圖書館也將越來越多,并且它們也開展免費服務,越來越成為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越來越成為我國圖書館事業的一個發展趨勢,從這一點來看,該書的研究似乎對于“未來前景”把握不夠。第四,書中有的地方存在一些不一致的現象。比如第二章“公共圖書館社會形象研究述評”部分,對國內的研究現狀寫得比較詳細,掌握資料比較全面,所用方法比較“科學”,顯得技術性強;但是在寫國外的研究現狀的時候,可能由于對國外的相關研究資料掌握比較少,導致寫得比較粗略,而且所用的主要是歸納、分析等“科學性”較差的方法,出現了明顯的不對應現象。第五,關于數字的書寫或表達,該書有的地方采用阿拉伯數字的形式,有的地方采用漢字書寫方式,顯得不夠統一。此外,在圖書館社會形象調查中,個別“問項”存在不夠合理的問題。凡此種種,都有待于他們在后續研究中加以糾正、補充和完善。
(編校:崔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