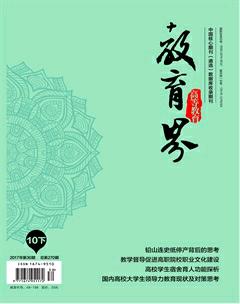高職學生的移動媒介的使用、批判與參與
洪曉彬

【摘要】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革新與普及,移動媒介素養成為新的研究熱點。文章通過調查發現,高職學生是移動互聯網的深度用戶。他們圍繞日常生活場景,通過移動終端實現自身社交、娛樂和信息獲取的需求。然而,高職學生的批判認知薄弱、批判行為尚未養成,而參與意向也處于中等水平。
【關鍵詞】高職學生;移動互聯網;媒介素養
一、引言
媒介素養思想最早起源于英國。1993年,學者F.R.Leavis和D.Thompson合作出版了《文化與環境》一書,提出了“文化素養”的概念,倡導媒介教育,反對傳媒中的流行文化價值觀念,訓練青年人抗拒大眾媒介中提供的“最低水平的滿足”。媒介素養自誕生起,就打下了“媒介批判”的烙印。此后,研究者不斷結合媒介技術發展對媒介素養的具體內容進行豐富拓展。每當新的媒介出現,就會引發研究者的興趣、警惕和批判,新一輪的媒介素養研究也隨之出現。1992年12月,在美國召開的“全國媒介素養領導人會議”,提出了簡練的媒介素養定義:“具有能夠獲取、分析、評價、制造印刷與電子媒體能力。”明確將媒介素養界定為一種能力體系。
從20世紀90年代起,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大眾媒介、網絡媒介的普及推廣,國內開始關注媒介素養研究,學術界經歷了國外研究引入、媒介素養理論探討、立足中國語境開展媒介素養實證研究等階段,媒介素養作為大學生綜合素養的一部分也逐漸成為研究者的一種共識。2011年以來,隨著中國移動互聯網的興起和普及,手機、平板等移動終端成為大學生使用網絡的新平臺。基于手機端的移動互聯網的媒介素養研究成為新的研究趨勢。
二、研究問題與方法
(一)研究問題
本文立足當前中國移動互聯網語境,對高職學生媒介素養進行實證探討,主要探討以下三個問題。
1.高職學生移動媒介使用的情況如何,是否具備日常使用的基本能力?
2.高職學生對媒介建構功能的認識如何,是否具備批判行為習慣?
3.高職學生的媒介參與意向如何,面對正面媒介行為與負面媒介行為,參與意向是否存在差異?
(二)調查問卷
本文使用網絡問卷對筆者所在學校學生進行調查,共發放問卷192份,回收有效問卷183份,有效率95.31%。
(三)調查內容
第一部分是學生使用移動互聯網的基本情況調查, 包括學生基本信息、使用時長、接觸移動網絡時間等,第二部分則圍繞媒介批判認知、行動及媒介參與意向進行調查。
三、數據分析
(一)受訪高職學生基本情況
本次共訪問學生183名,其中男生79名,女生104名。從受訪學生年級分布來看,高職2016級(即大一學生)95名,高職2015級(即大二學生)74名,高職2014級(即大三學生)14名。
(二)移動媒介使用現狀
1.超四成學生在線時間超5小時,女生在線時間更長。調查發現,79.3%的受訪學生表示每日使用移動終端上網時長超過3小時,45.4%的受訪學生每日上網時長甚至超過5小時。
對“在線時間”與“性別”進行交叉相關分析發現,Pearson卡方P=0.012<0.05,具有統計學意義,說明男女生每天使用手機上網的時間長度存在差異。超過55.9%的受訪女生每天使用手機上網時間超過5小時,而受訪男生中同樣情況的只有33.8%。綜合而言,女生使用移動互聯網的時間更長。
2.超四成學生初中期間接觸移動網絡。調查發現,初中期間開始使用移動互聯網的學生達43.2%,遠遠超出高中期間(34.4%)和大學期間(10.4%)開始使用的學生人數。
3.最熱衷的三大功能:社交、娛樂和信息獲取。對受訪學生使用移動互聯網的情況進行調查發現,社交功能最凸顯,娛樂功能其次,信息獲取第三。社交功能:86.3%的受訪學生使用移動終端實現即時通訊聊天(如微信、QQ),56.3%的受訪學生進行網絡社交(如貼吧、朋友圈、微博)。娛樂功能:超過六成的受訪學生表示使用移動端觀看影視節目(占受訪學生的65%)和聽音樂或唱歌(占受訪學生的61.2%)。信息獲取:超過四成的受訪學生(占受訪學生的44.8)表示使用移動終端瀏覽新聞資訊和搜索、查閱信息。
4.男女學生使用的喜好差異。對“移動互聯網的使用功能”與“性別”進行交叉分析,具有統計學意義,發現女生更熱衷于網絡影視節目、聽歌唱歌等娛樂方式,男生則更熱衷于網絡游戲,具體見表1。
此外,在網絡購物、參與觀看網絡直播等方面,性別差異也具有統計學意義,超過50%的女生使用移動終端進行網絡購物,而這一比例在男生中僅有21%,說明女生更偏愛于網絡購物。
(三)媒介批評認知與批判行為
1.批判性認識不強。對于“我偶像代言的產品質量更好”“手機音樂排行榜的上榜歌曲是最優秀的”“女性司機常被報道是因為她們駕駛車輛時更容易出現事故”等問題,以5級李克特量表的方式進行調查,受訪學生對這3個問題的態度均值分別為2.8、3.46、3.11,總體均值為3.12(1分表示非常不贊同,5分表示非常贊同)。可見,高職學生對媒介所呈現的信息真實性表現出迷惑與不解,對媒介建構現實的識別能力屬于中等水平,對于媒介信息的批判性認識還有待提高。
2.批判性行為較弱。對于“尋求信息的弦外之意”“質疑信息”“拒絕接受”“核實觀點”等4個題項,以5級李克特量表的方式進行調查,受訪學生對這4個問題的態度均值分別為2.45、2.26、2.13、2.09,總體均值為2.23(1分表示十分不符合, 5分表示十分符合)。可見,高職學生在使用網絡媒介時,尚未形成對媒介信息的批判,即面對媒介信息存在“讀不懂”“不質疑”“不拒絕”的狀態。換言之,高職學生在媒介信息面前不具有“免疫系統”,對媒介信息的批判能力屬于中下水平,對于媒介信息的批判能力還有待提高。
(四)媒介參與意向
1.參與意向整體不高。媒介素養的另一重要核心內涵,即媒介參與意向。調查受訪學生面對不同場景的網絡信息,對于“參與網絡爭論”“不猶豫地轉發信息”“參與校園環境建設的討論”“對涉黃涉暴信息的投訴舉報”等4個題項,以5級李克特量表的方式進行調查,受訪學生對這4個問題的態度均值分別為3.10、3.37、3.55、3.76(1分表示十分不符合, 5分表示十分符合)。
2.參與正面媒介行為略高于負面媒介行為。其中,前面兩道題目調查了受訪學生對于負面消極的媒介行為參與意向,均值3.24,表明受訪學生對于負面媒介行為的辨識能力較弱,自覺抵制的意識不強。后兩道題目調查了受訪學生對于正面積極的媒介行為參與意向,均值3.66,高于負面消極的媒介參與意向,對正面媒介參與意向均值T檢驗,具有統計學意義。可見,高職學生總體媒介參與意向處于中等水平,但是作為正面積極媒介行為的參與意向明顯高于負面消極的媒介行為的參與意向。
四、結論與討論
移動媒介為高職學生進一步參與社會實踐提供了新平臺。從使用年齡、在線時長、功能使用等方面分析,當前高職學生對移動互聯網的使用與駕馭已經嫻熟,是移動互聯網用戶中的重度用戶,已經具備基本的媒介使用能力,能夠使用移動互聯網技術,實現自身對社交、娛樂和信息獲取等方面的需求。然而,他們對移動互聯網的使用缺乏科學理性,對媒介建構社會真實的認知不足,對媒介信息存在“讀不懂”“不質疑”“不拒絕”的現象,尚未形成有效的“免疫系統”。高職學生對媒介的批判意識還很薄弱,還不具有獨立思考的批判思維。調查還發現,高職學生參與意向整體不高,對正面媒介行為的參與意向高于負面媒介行為。移動互聯網技術為高職學生參與社會實踐提供了便捷而且有效的渠道,然而其主動、理性參與網絡事件的熱情并不強烈。
本文通過問卷調查,對高職學生媒介素養現狀進行了初步探討,對高職學生媒介使用情況、批判意識和參與意向進行了量化統計。但仍然有很多問題需要深入探討,比如高職學生的媒介素養教育與實踐,這也是未來應該繼續努力的方向。
【參考文獻】
[1]陸曄.媒介素養:理念、認知、參與[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
[2]卜衛.論媒介教育的意義、內容和方法[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1997(01):29-33.
[3]蔡騏.論媒介認知能力的建構與發展[J].國際新聞界,2001(05):56-61.
[4]陳龍.媒介全球與公眾媒介素養結構的調整[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04(04):26-29.
[5]董雪.新媒體時代的大學生媒介素養研究——以廈大學生群體為例[D].廈門:廈門大學,2014.
[6]陸曄.媒介素養的全球視野與中國語境[J].今傳媒,2008(02):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