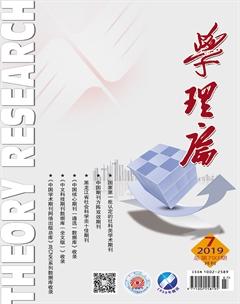梁啟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轉化
段瀾濤
摘 要:梁啟超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早年積極提倡西學,晚年回歸中國傳統文化。但梁啟超前后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是一致的,即倡導中西文化的“結婚”,對中國傳統文化既有批判也有傳承,尤其提出了“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的轉化中國傳統文化的觀點,對于我們今天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關鍵詞:梁啟超;中國傳統文化;轉化
中圖分類號:B259.1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2-2589(2019)07-0059-02
梁啟超雖然在游歷歐洲前后的思想有所變化,后期與前期相比宣傳中華傳統文化優越性的成分偏多,但對中華傳統文化既批判又傳承的基本態度始終沒有變。梁啟超中西文化觀的實質是“擷實咀華”“融會貫通”,對中華傳統文化主張“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即“掘井及泉”,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源頭活水”,并嘗試對陽明心學進行了轉化。
一、對中西文化的基本態度
在中西文化的關系上,梁啟超既反對全盤西化,也反對民族文化本位論,主張對中西文化“擷實咀華”“融會貫通”。
在論述新民的問題時,梁啟超曾說:“吾所謂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風者流,蔑棄吾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紙者流,謂僅抱此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表明了他對“心醉西風者流”和“墨守故紙者流”均持否定態度。梁啟超說:“大地今日,只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二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吾欲我同胞張燈置酒,迓輪俟門,三揖三讓,以行親近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也。”梁啟超這里用“結婚”的形象說法表達了他對中西文明關系相互融合的看法,隆重歡迎西方文明,以繁榮我中華文明。概括地說:“于彼乎,于此乎,一一擷其實、咀其華,融會而貫通之”,對中西文化都要“擷實咀華”“融會貫通”。
梁啟超雖然主張中西文化“融會貫通”,但更強調了學習西學以創新的重要性,他下面這段話表達了他的“新舊”觀:“新舊者,固古今盛衰興滅之大原哉!故衣服不新則垢,器械不新則窳,車服不新則敝,飲食不新則餒敗傷生,血氣不新則槁暴立死。天之斡旋也,地之運轉也,人之呼吸也,皆取其新而棄其舊也。”梁啟超在這里所說的“取新棄舊”指的是新陳代謝,突出強調了“新”的價值,而“棄舊”并非完全拋棄,而是指“變數千年之學說”。那么,怎么變呢?這就進入到他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轉化范圍。
二、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態度
梁啟超首先強調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所具有的“特質”的重要,認為它是立國的基礎,不能隨意放棄。他說:“凡一國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質,欲自善其國者,不可不于此特質焉,淬厲之而增長之?……諸君如愛國也,欲喚起同胞之愛國心也,于此事必非可等閑視矣。”梁啟超在這里強調了“特質”的重要,它是人們愛國的重要表現,應該對其改造使之增長。這個“特質”是什么呢?梁啟超說:“凡一國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字,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后群乃結,國乃成,斯實民族主義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數千年立國于亞洲大陸,必其所具之特質,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異于群族者,吾人所當保存之而勿失墜也。”這是梁啟超對上段話的具體展開,“特質”即“一種獨立之精神”,貫穿于道德、法律、風俗、習慣、文字等,是“民族主義之根柢源泉”,我們應當“保存之而勿失墜”。這種“特質”或“獨立之精神”應該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
其次,梁啟超談到了中華傳統文化的轉化方法及未來展望。張錫勤指出,梁啟超認為“新”應從兩個方面同時進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其實,這既是他新民的方針,也是他進行文化革新的方針。所謂“淬厲其所本有”,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民族精神有價值、可繼承的精華部分,“濯之、拭之,發其光晶;鍛之,煉之,成其體段;培之、浚之,厚其本源”。即對它作加工提煉、充實改造的工作,使之萌發新芽、涌出新泉,“繼長增高”,日新光大。所謂“采補其所本無”,就是“博考各國民族所以自立之道,匯擇其長者而取之,以補我之未及”。就是說,對西方文化也不能簡單照搬,必須下一番考察、選擇的功夫,取其精華,為我所用。
再次,梁啟超提出了中國文化建設“四步走”的設想:“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一個新文化系統。第四步,把這新系統往外擴充,叫人類全體都得著他好處。”梁啟超所說的第一步,就是讓人們加強民族文化的自覺性,以同情、敬意、誠意對待中華傳統文化;第二步類似于胡適所說的“整理國故”,用科學、邏輯的方法厘清中華傳統文化的原貌;第三步就是綜合創新,不僅整合中國傳統不同流派、不同類型、不同風格的文化,還要“輸入學理”,借鑒他山之石以攻玉,從而在不同文化之間產生一種“化合”作用,形成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即“再造文明”。第四步是讓中華民族新文化沖出國門,走向世界,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可以說,梁啟超有關中華傳統文化的觀點值得我們借鑒。他有關中西文化“融會貫通”“結婚”的說法是正確的,這是在“西學東漸”背景下多數中國思想家的選擇,我們今天傳承、弘揚、轉化中華傳統文化依然應該如此。尤其是梁啟超“淬厲其所本有”,即對中華傳統文化作加工提煉、充實改造、日新光大的觀點對今天探討中華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具有直接的意義。另外,梁啟超所說的加強民族文化的自覺性,用科學方法厘清中華傳統文化的原貌,對不同文化資源進行“化合”從而形成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并讓中華民族新文化沖出國門,走向世界,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應有貢獻的文化設想對于我們今天建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文化具有主要的借鑒意義。
三、對佛學和陽明心學的轉化
推崇陽明心學是中國近現代以來思想文化界的一個突出特征,梁啟超亦不例外。梁啟超稱王守仁為“千古大師”,認為“王學為今日學界獨一無二之良藥”,而致良知說是“千古學脈,超凡入圣不二法門。”他自稱,“吾生平最好言王學。”梁啟超認為佛學是“最高尚”的宗教信仰,而且,“自來言哲理者”,也“以佛說為最圓滿”。他將佛學置于古今中外一切學術之上,認為“佛教是全世界文化的最高產品”,給予了最高評價。
不僅如此,梁啟超還為闡釋、弘揚、轉化佛學思想和陽明心學做過積極的努力,突出表現在他自己的心境學說中。
梁啟超1900年發表了《惟心》一文,提出了心境說。他說:“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虛幻,惟心所造之境為真實。”梁啟超在這里提出兩種“境”:一是物境,一是心境。物境為虛幻,心境為真實。面對同一物境,會產生千差萬別的心境,“有百人于此,同受此山、此川、此春、此秋、此風、此月、此花、此鳥之感觸,而其心境所現者百焉;千人同受此感觸,而其心境所現者千焉;億萬人乃至無量數人同受此感觸,而其心境所觀者億萬焉乃至無量數焉。”比如,“同一風雨也”,“三兩知己圍爐茅屋,談今道故,飲酒擊劍,則有余興”;反之,“獨客遠行,馬頭郎當,峭寒侵肌,流潦妨轂,則有余悶”。“同一黃昏也”,當“月上柳梢頭”之時,熱戀中的情人依約幽會,則感此黃昏無限美好;反之,閨中怨女“欲黃昏,雨打梨花深閉門”,則感此黃昏無比愁慘。“同一江也,同一舟也,同一酒也”,當曹操統大軍南征之時,“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則感此江景極為壯麗;反之,當白居易“潯陽江頭夜送客”之時,則感此江景無比凄涼。梁啟超這里是說,面對同一物境,由于人們的處境不一樣,會產生不同甚至南轅北轍的感覺認知和情感體驗。面對同樣的風雨,有的人“有余興”,有的人卻“有余悶”。換一種說法,比如“戴綠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綠,戴黃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黃;口含黃連者所食物一切皆苦,口含蜜飴者所食物一切皆甜。”“果為何狀”?“一切物非綠非黃、非苦非甜;一切物亦綠亦苦、亦黃亦甜;一切物即綠即黃、即苦即甜。”“綠也、黃也、苦也、甜也,其分別不在物而在我。”即是說,顏色、味道不在物,而在我。離開我無所謂綠黃苦甜。“全世界者,全世界人類心理所造成;一社會者,一社會人之心理所造成;個人者,又個人之心理所造成也”,心理造成個人、社會乃至全世界。
在談到認識論的時候,梁啟超關注到認識客體的存在,但強調的是認識客體對認識主體的依賴性。他說:“須知認識之成立,必由主客兩觀相對待,無主觀則客觀不能獨存。外而山河大地,內而五官百骸,茍非吾人認識之,曷由知其存在?既已入吾識域而知其存在,則知其絕不能離吾識而獨立,故佛家之謂此為識所變”。
在思想、理論與事實、實事的關系上,梁啟超強調了思想、理論的優先性。“思想者,事實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實,必先養成何等之思想。”“天下必先有理論,然后有實事。理論者,實事之母也。”
梁啟超十分重視心力的功能,認為“心力是宇宙間最偉大的東西,而且含有不可思議的神秘性,人類所以在生物界占特別位置者就在此。”心力偉大,是人之優越于其他生物的依據。梁啟超贊揚宗教和唯心論能培養、激發人們舍身救世的精神,有助于培養、激發人們的心力。而“報大仇,雪大恥,革大難,定大計,任大事,智士所不能謀,鬼神所不能通者,莫不成于至人之心力。”
1924年,梁啟超發表了《非“唯”》一文,對以前的觀點有所修正。他說:“有客觀方有主觀,同時,亦有主觀方有客觀。因為主觀的意不涉著到客觀的物時,便失其作用,等于不存在;客觀的物不為主觀的意所涉著時,便失其價值,也等于不存在。”“蓋在心物合一的前提之下,不獨物要靠心乃能存在,心也要靠物乃能存在。”梁啟超在這里肯定了物的存在,注意到了主客觀的相互依存,但從總體傾向而言,依然強調的是客觀對主觀的依賴。
梁啟超的心境說顯然是對王陽明心外無物和唯識學境隨識轉等思想的傳揚,但梁啟超闡述得更為現代、平實、細致,并主要從認識論的意義上對其進行了轉化和創新。在梁啟超的心境論中,似乎隱含著一個邏輯前提,如果物境不是虛妄的,那同一物境應該產生同樣的感覺認知和情感體現,但事實上同一物境卻產生了不同甚至相反的感覺認知和情感體驗,足見物境是虛妄的,真實的只是面對同一物境所產生的千差萬別的心境。梁啟超的心境論與后來胡適的“實在論”、梁漱溟的“現量論”、熊十力的“量論”等傾向一致,雖然有陽明心學和唯識學的影響,但也明顯地受到了西方近現代哲學中感覺論的影響。盡管晚年梁啟超關注到主客觀的內在關聯,但重心依然放在認識主體上。在這里,我們應該肯定梁啟超的心境說具有現代哲學的色彩,他所說的“心”既是宇宙本體,又是認知主體,是本體與主體的合一。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凡是能夠成為認知客體的東西必然與認知主體密不可分,沒有認知主體無所謂認知客體,就此而言,梁啟超的境由心造包含合理性,與熊十力心境融本體論和認識論于一體,強調認知客體與認知主體的統一是一致的。然而,從常識和基礎上來講,無論何種意義的“心”都無法否定、左右作為事實存在的“物”的真實性和獨立性,即使在認識論的領域,我們也不能否定認識客體與存在客體的相關性。
參考文獻:
[1]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2,4,13,23,26,54[M].北京:中華書局,1989.
[2]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2,5,6,7,22,39,41,42,43[M].北京:中華書局,1989.
[3]張錫勤.梁啟超思想平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責任編輯:許廣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