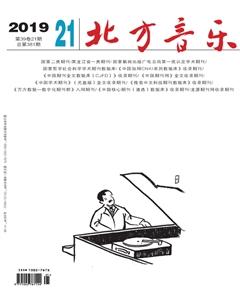“政教型”音樂美學模式下的審美意識研究
【摘要】《論語》與《儀禮》屬于儒家經典著作,也都屬于中國古代音樂美學研究的重要范疇。解讀兩者的審美意識不能脫離其發生(主觀邏輯上系統的產生,不同于起源的概念)的“政教型”音樂美學模式,其中,孔子的音樂美學觀念與士大夫階層儀式用樂體現的音樂審美為主要論域,以求多視角的貫穿既有的音樂美學模式,從“十三經”等更多領域拓寬研究視域。
【關鍵詞】音樂美學;審美意識;論語;儀禮
【中圖分類號】J60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政教型”音樂美學模式是指禮樂與教化并舉,以樂施教、禮樂相輔、以樂佐政,音樂在其中合乎禮的制約,同時也形成了規范的音樂審美意識。進而,中國古代音樂美學是以理論形式的審美意識研究為基本內容,儒家典籍又為其核心論域。故此,儒家論著中的審美意識研究也處于“政教型”音樂美學模式下,主要體現在音樂的功能性上。《論語》中有大量的論樂文字,是孔子音樂美學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深入探討禮樂相輔下的音樂審美問題。《儀禮》為“十三經”中的重要代表,與《周禮》、《禮記》合稱為“三禮”,其中只有四個章節述及音樂的內容,主要是記錄了士大夫階層用樂的儀式活動,在不同場合體現了用樂的特殊性。
一
《論語》是記錄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創始人孔子及其弟子或再傳弟子之言行的儒家經典,其中,述及“樂”的有二十幾個章節,可見“樂”在孔子,或者換言之,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一)禮樂規范下的用樂制度
儒家思想的核心觀點是“仁”,所以在《論語》中也體現了音樂中的“仁”。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
孔子想說明的是音樂的存在需要“仁愛”、“仁德”,不然音樂就沒有了根基和意義,禮也是如此。可見“仁”在孔子眼中不僅僅是禮的根本,也不僅僅是音樂的根基,而是可以用來衡量一切客觀事物的基準。
這段話也引出了儒家對于“禮”與“樂”的論述,舉個例子: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
所以進一步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禮樂”?“什么樣禮和什么樣的樂才能符合孔子期望的禮樂?”通過分析孔子的身份可以得知,孔子是一個落寞的奴隸主貴族,他崇尚的是封建等級制度,用以穩定社會秩序和保護各個等級,尤其是高等級的貴族。可以說“禮”的等級劃分實際上是在為統治者服務,所以他想要的禮是可以區分貴賤等級且不相互逾越的禮。所以,孔子認為“樂”符合為政治服務的要求,認為“樂”是非常好的為“禮”服務的工具。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
描寫季氏用天子之樂的場景。古代奏樂舞,佾是指行列,一佾是八人,八佾是天子用樂的陣容。周代的禮樂制度體現在嚴格的用樂和繁復的音樂禮儀上,不可僭越。又有,《周禮·春官宗伯》“小胥”:
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
上文中季氏用了八,也就是逾越了天子的等級地位,孔子譴責用樂的不規范,是對明目張膽濫用天子的禮樂的“不可忍”,可見當時通過用樂可以察覺“禮崩樂壞”的社會現象。
(二)功能性中體現的音樂審美
孔子述及音樂審美問題時也有一套標準,他所認為的“盡善盡美”絕對不是僅僅指好聽的音樂,而是暗合了禮、政治、樂教等多個方面且具備具體功用的音樂,欣賞的同時可以潛移默化地彰顯其功能性。
孔子精通音律,對音樂也是特別的喜愛。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興與《詩》,立于禮,成于樂。”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論語·泰伯》)
1.孔子熱衷于古代優美的旋律
沉醉在音樂營造的美好意境中;認為“成于樂”,是指音樂能使人向善,孔子論述音樂的功用,即促進人完成修養、事業成功,音樂可以修身;在欣賞音樂的時候是懷著愉快的心情,暢快而滿足。《關雎》作為《詩經》的一部分在書中被提及和演唱。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
孔子認為音樂也應當具有詩一般的情操,《關雎》中雖然有哀怨的情緒,但也有所節制,不用于悲傷,沒有放任悲傷的情緒在詩中展露。音樂要有“節”,“和”的音樂才是好的音樂,這也是一個重要的音樂審美觀念。“和”體現在情感上的適度,也體現在音樂形式和內容的適度。
2.“盡善盡美”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矣。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孔子認為音樂審美的標準是美與善的統一,既要好聽有節制,又要積極向善傳達仁愛的思想。
3.“崇雅貶鄭”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論語·衛靈公》)
孔子認為鄭聲是傳播不好思想的音樂,使人過度沉迷和追求,精神萎靡不振,長此以往會敗壞社會風氣,就如如同花言巧語的佞人一般。若想真正地治理國家就要聽雅樂,欣賞《韶》、《武》。
綜上,儒家思想中的音樂審美已經不僅僅停留在欣賞的層面,從對于“鄭聲”的描述,甚至完全否定鄭聲的美而直接將其推向了雅樂的對立面。可見,儒家思想中“樂”不只是單純的審美而已。從中也可以看出,孔子是一個在音樂使用方面較為“復古”的一個人,他的樂對于自身是作為一種欣賞和修煉,對于鄭聲是一種抵制和抗衡,對于社會制度是一種方法和途徑,對于統治者它更是一種手段和工具。
二
上文論述到音樂需要符合一定的禮儀、政治規范,它是如何具體體現在音樂活動中的呢?《儀禮》中有載,周代有八種重要的音樂禮儀:祭天地、祭宗廟、大饗、燕禮、大射、養老、鄉飲酒、鄉射。《儀禮》共17篇,其中明確描寫用樂活動的有4篇,分別是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
(一)儀式活動中的用樂流程
鄉飲酒禮是鄉射禮之前的一個儀式活動,通過《儀禮》中記載的鄉飲酒禮,可以整理出當時用樂有四個環節,分別是工歌(升歌)、笙歌(下管)、間歌、合樂,具體的每個環節有其象征意義和特定內容的選取和行樂方式。
1.工歌(升歌)
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后首,挎越,內弦,右手相。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受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儀禮·鄉飲酒禮》)
鄉射禮中的工歌相較于其余三篇是最為完備的,其中可以體現很多用樂的規范。首先,周禮嚴格規定樂工的規格,“天子有八人,諸侯六人,卿大夫四人,士當二人。”可見用樂不能脫離等級制度,樂官有大樂正、小樂正,樂工有大師、少師、上工。《鄉射禮》中“工四人”符合要求,到了《大射》中即為“工六人”,因為《大射》為諸侯之禮。那么,是否所有的用樂都要如此按部就班?實則不然,還需要進一步考量禮儀的活動內容。例如燕禮,也屬于諸侯之禮,原則上應該使用“工六人”,然而,《儀禮·燕禮》中載,“工四人”,因為諸侯與群臣只宴飲而不論國事、政事。
2.笙歌(下管)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儀禮·鄉射禮》)
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儀禮·燕禮》)
笙歌是用樂的第二個環節,純器樂演奏環節,用樂選自《詩經·小雅》。
3.間歌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儀禮·鄉射禮》)
間歌采取“一歌一奏”的表演形式,內容來自《詩經·小雅》。
4.合樂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告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儀禮·鄉射禮》)
合樂是用樂的最后一個流程,笙、磬、歌等眾聲齊作,將整個儀式活動的氣氛推向高潮,選曲取自《詩經·國風》。
綜上,儀式用樂中的樂人、方位、表演形式、出場順序、選曲等都需要合周禮,例如《鄉射禮》和《大射》的用樂就截然不同。射禮中的用樂比較特殊,這種場合用樂是為了“用樂助射”。首先,不同的等級用樂不同,《鄉射禮》中用《騶虞》,《大射》中用《貍首》;其次,這樣的用樂有它使用規范。
司射遂適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鼓不釋。”(《儀禮·大射》)
射劍如果不和音樂的節奏相應,就不算數。從中,可以看出音樂被賦予了把握射箭節奏的功用,是引領整個射箭儀式活動的內在核心。
(二)《儀禮》中的音樂審美意識體現
從《儀禮》中描寫的不同儀式中的用樂可以看出,當時的選曲是有選擇性的,都是從《詩經》中的“風”、“雅”中選取,且在固定的用樂環節使用固定的曲目。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詩經·小雅》);
笙歌。《南陔》《白華》《華黍》(《詩經·小雅》);
間歌。《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詩經·小雅》);
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詩經·國風》)
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皆屬嘉禮,嘉禮所用的樂曲主要是用短小的詩樂的形式貫穿,體現了世俗的形態,對于不同儀式場合也出現多曲多用的現象,這也是符合等級制度要求的。
在《儀禮》中,對樂官、樂工的所有的描寫,包括出場順序、樂器使用、演奏次序、演奏曲目等各個方面,體現了當時的儀式用樂已經十分完善了。再進一步思考,從上文的分析來看,難以將音樂脫離當時的等級制度來談。那么,音樂是不是禮的附庸?筆者認為,在周代的時代背景下,分析“樂”不可避免要在禮的框架下來解讀。可是除去禮的約束,音樂在有“節”的行樂過程中,也是有愉悅的審美體驗的。這一點不能避而不談,尤其在宴飲享樂的過程中,樂在教化方面的功能性削弱,在審美娛樂方面的功能被加大,這也是研究儒家音樂思想時需要被考量的問題。
在審美娛樂性上最好的體現是“無筭樂”。
說履,揖、讓如出,升,坐。乃羞。無筭爵,無筭樂。(《儀禮·鄉飲酒禮》)
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無筭樂。(《儀禮·鄉射禮》)
士終旅于上如初。無筭樂。(《儀禮·燕禮》;《儀禮·大射》同)
這里的“筭”通“算”,是指在宴飲的過程中不計其數的依次酬酒的同時,音樂也不計數的一遍一遍演奏,盡歡為止。觥籌交錯,沒有計算,沒有節制,是宴飲到了酣暢階段的表現,音樂也是如此。一遍一遍的演奏,體現了音樂的享樂功能、娛樂功能,這時的音樂它如何附庸在禮之下?換言之,這時的音樂怎樣體現儒家思想中的樂教功能?可能都不大合適。
那么,是不是這時的樂就直接導向“禮崩樂壞”?《儀禮》的成書時期有諸多爭議,不過通過分析整本書可以知道它很接近“禮崩樂壞”的前期,但是否直接導向?筆者認為并不是這樣。因為音樂中的“節”在整個儀式過程中都有體現,有“節”就是在遵循禮的制約和指導。例如《陔夏》。
賓出,奏《陔》。主人送于門外,再拜。(《儀禮·鄉飲酒禮》)
賓降,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眾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儀禮·鄉射禮》)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內溜,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儀禮·燕禮》;《儀禮·大射》同)
在《燕禮》和《大射》中都明確指出“賓醉”,而這時的用樂一方面是禮貌的送客;另一方面“賓醉”容易失態,此時奏《陔夏》也是為了提醒賓客不要酒后失德。故此,從請賓到送賓音樂起到引領儀式活動的作用,輔助著禮施行的全過程。
結語
《論語》中具體體現孔子的音樂美學觀念,有“和”“盡善盡美”等,這里的音樂是嚴格符合禮的要求,禮樂相輔。音樂被賦予一定的教化功能,用樂的規格、選曲都要符合禮的內容。然而,《儀禮》中主要記載了較為完善的宴饗用樂,在用樂的過程中既要符合禮的約束,又要通過音樂的節奏、曲目變化來引導整個儀式的順利開展。所以,“政教型”音樂美學模式的具體表現是在禮樂關系,而其中的音樂審美意識研究不僅僅是孔子音樂美學觀念,也不僅僅是周禮附庸下的各種音樂規范。除此之外,通過分析《儀禮》也可以看出除了功能性審美以外的純娛樂性的音樂審美,然而,這樣的審美歸根結底還是要有“節”。
參考文獻
[1]朱靜.《論語》中孔子的音樂美學思想[J].西安聯合大學學報,2004(4)
[2]劉承華.中國古代音樂美學的理論特點[J].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2011(3).
[3]楊天宇.儀禮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漆子揚.《儀禮》樂制初探[J].社科縱橫,1993(4).
[5]十三經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2002.
[6]高亨.詩經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7]李安宅.《儀禮》與《禮記》之社會學的研究[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
[8]胡承珙,郭全之.毛詩后箋[M].合肥:黃山書社,1999.
[9]楊寬.西周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0]傅斯年.詩經講義稿[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11]漆子揚.從《儀禮》樂制的變通看周代樂禮的文化屬性[J].中國文化研究,2008(1).
作者簡介:汪茹婷(1992—),女,漢族,安徽銅陵,碩士研究生,江蘇師范大學科文學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國音樂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