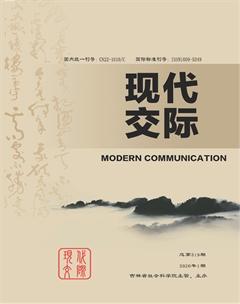戴震的科學精神
單曉宣
摘要:戴震作為清代著名的思想家,其學術著作和主要思想對之后很長一段時間的思想史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梁啟超在其著作《清代學術概論》中對戴震的思想大為褒獎,戴震抨擊宋明理學的《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更是被梁啟超盛贊可與文藝復興類比;其善疑、求真的治學思想更是被梁啟超冠以“科學精神”。戴震的科學精神一直到今天仍對青年人有著重要的影響。
關鍵詞:戴震 實事求是 科學精神 梁啟超
中圖分類號:K2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20)01-0230-02
戴震生于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字東原,又字慎修,號杲溪,休寧隆阜(今安徽黃山屯溪區)人。戴震于訓詁學、哲學、考據學、自然科學等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僅如此,其藝術成就也卓越斐然,音韻、文字、歷算、地理無不精通,可稱之為“通儒”。戴震對理學家“去人欲,存天理”之說有所抨擊,其批判程朱理學的舉動、“善疑”“求真”的科學精神,不僅對當時的學人進行啟蒙,也對當今年輕人無論治學還是生活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梁啟超稱之為“前清學者第一人”,在其著作《清代學術概論》中用了很大篇幅對戴震的科學精神進行解讀,并稱之為“中國近代科學界的先驅者”。
一、作風嚴謹,追求真理
戴震幼年在學習《大學章句》時曾向老師發問:“次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1]51在得到老師的回答后仍不滿意,仍繼續追問,直到老師無以為應,只能夸贊其“此非常兒也”。這一件短短的記載戴震幼時求學經歷的小事,卻能夠體現出戴震整個治學思想的出發點——善疑與求真。梁啟超對此事曾說道:“蓋無論何人之言,決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并稱贊:“此種研究精神,實近世科學所賴以成立。而震以童年具此本能,其能為一代學派完成建設之業固宜。”[1]52認為戴震幼年便具備善于質疑的能力,產生了其實事求是、善于追根溯源的治學思想萌芽,無論什么人說過的話,絕不輕易信服,必定要找到根據,知其然的同時必要知其所以然,若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根據,即使是圣父先人之辭,亦不可信。戴震曾說:“學者當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為一時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1]52這種單純的為了治學而治學的態度,實為后世稱道也。而其為探索真理、實事求是的治學過程自然也是歷經困苦。戴震為破除“人蔽”和“己蔽”的桎梏,弄清楚“所謂十分之見”與“未十分之見”,真正做到了“有一字不準六書,一字不通貫群經,即無稽者不信,不信必反復參證而后即安。已故胸中所得,皆破出傳注重圍”[1]54。雖承襲當時考據學“凡立一義,必憑證據”[1]69之學風,但其嚴謹的作風和對真理的追求,于今天的青年學者而言也是極具意義的。
二、辯證的思考情感與理性
抨擊程朱理學是戴震思想上的一次大的突破與轉變,而其思想發展與轉變離不開當時特殊的社會背景和治學風氣。戴震成長于康乾盛世之際,出生于較為閉塞的徽州休寧縣,程朱理學思想在當地有絕對的權威。戴震的老師江永亦是程朱理學的忠實擁護者,早年的戴震便深受程朱理學的影響,對程朱理學的許多觀點都十分推崇。后來戴震由于種種原因,多次居住在揚州。與相對封閉的徽州府不同,揚州的學術風氣、經濟環境皆是一片繁榮景象,戴震也在此地結交了惠棟等一眾志同道合且具有啟蒙精神的“學友”,治學思想深受影響。而揚州地處長江中下游地區,正處于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經濟較為繁榮的階段,戴震親眼見識到揚州與家鄉的區別后,難免對之前的舊思想產生了強烈的沖擊,這些都為戴震日后推崇“經世致用”的實學,堅定地反對程朱理學,甚至“背師棄祖”奠定了基礎。其晚年最得意的代表性作品《孟子字義疏證》便是對程朱理學的理論批判。書中戴震對于理與欲、情感與理性進行了辯證的思考和討論,認為“理”與“情”是不可分離的,二者相互依存,脫離了現實人情的“理”就不再是什么所謂的圣人之道,而是用來禁錮人的殘酷武器,是維護統治與秩序的工具。而戴震對宋明理學并沒有全盤否定,在一些著作中依舊能看到一部分宋明理學所包含的哲學理念,可以說戴震只是摒棄了宋明理學的糟粕。梁啟超認為縱覽《孟子》字義疏證全書,無外乎用“情感哲學”代替“理性哲學”,此觀點可以說與歐洲文藝復興的思潮非常相似。程朱理學對中國人的禁錮,和當時基督教的絕對禁欲主義對歐洲人的思想束縛大體類似,而一旦遇到了解放思潮,則如雨后春筍一般呈現出勃勃生機。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便產生了這一作用,其蘊含的平等的精神,對宋明儒學的抨擊雖言語含蓄卻義正辭嚴,“隨處發揮科學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實三百年間最有價值之奇書也。”[1]60雖在當時的學術正統看來《孟子字義疏證》是為異說,在論清學正統派之運動時,不得不將此書除外,但在梁啟超看來,正是因為拋棄了戴震的此作,“清代學派的運動”的成就才遠不如歐洲文藝復興的成就大。直到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面世,學界才重新對戴震的學說給予足夠的重視。
三、梁啟超對戴震科學精神的認識
梁啟超作為近代思想啟蒙的領軍人物,也是最早一批深受西方科學精神影響的“有識之士”。于是在西方科學的影響下,梁啟超對戴震治學思想的解讀也難免結合了西方科學精神色彩。在戴震那個還不確定是否有“科學”這一概念傳入中國的年代,梁啟超便將這種務實的,具有理性色彩的“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的思想冠以“科學精神”加以推崇,認為這是科學家所具有的素質,賦予了此種中國舊學以近代科學的靈魂,其對戴震的欣賞之情,可見一斑。任公亦認為戴震的治學精神與西方實證哲學派的思想是相通的,并且十分惋惜地表達了這種精神應不僅僅應用于博古考據,更應該應用于自然科學,可惜因為年代的限制,未能達成,實為遺憾。在《戴東原生日二百年紀念會緣起》中,梁啟超再次強調戴震之研究法的重要,說:“東原本人自己研究出來的成績品,可寶貴的雖然甚多,但他同時或后輩的人有和他一樣或更優的成績品的也不少。東原在學術史上所以能占特別重要位置者,專在研究法之發明,他所主張‘去蔽、‘求是兩大主義,和近世科學精神一致。他自己和他的門生各種著述中,處處給我們這種精神的指導。這種精神,過去的學者雖然僅用在考證古典方面,依我們看,很可以應用到各種專門科學的研究,而且現在已經有一部分應用頗著成績。”[2]38在梁啟超看來,戴震的治學精神所蘊含的科學意義對清末學界的影響,遠大于其學術成就本身,但這也恰恰說明了,戴震的科學精神是超越了時間限制的。
四、結語
對于今天的青年人而言,戴震的科學精神中所包含的懷疑精神、實證精神和理性主義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素質。隨著網絡技術的發達和大數據時代的來臨,造成我們越來越麻木被動地接受信息而不是主動吸收于自身有益的經驗。而作為依舊在校園里從事學術研究的青年學生,有時會被所謂的權威擾亂自己的判斷,一方面由于自身知識儲備的確不足,以至于思考的深度和廣度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就是缺少質疑的勇氣,有時候迫于一些所謂的主流聲音的壓力,擔心自己孤掌難鳴,擔心自己的聲音不會被別人聽到,諸多擔心使許多青年學生變得畏首畏尾,缺少懷疑精神就會直接影響研究的熱情。敢于懷疑才能引發思考與研究,而在這個研究的過程中,如若能依照戴震破除“人蔽”和“己蔽”的思想,保持觀點中立,不去以個人的價值觀作為標準衡量,并且所引用的任何觀點都可以找到引征出處,不能為了得出所謂的研究成果捏造事實,這樣所得出的結論才是真正科學的結論。
參考文獻:
[1]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M].北京:中華書局,2010:51,52,54,60,69.
[2]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之四十[M].北京:中華書局,1936:38.
責任編輯:趙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