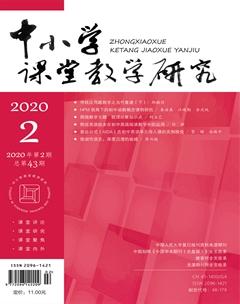傳統(tǒng)應(yīng)用題教學(xué)之當(dāng)代重建(下)


【摘要】傳統(tǒng)應(yīng)用題教學(xué)之當(dāng)代重建(下)鄭毓信(南京大學(xué) 哲學(xué)系,江蘇南京 210093)[=]【摘 要】傳統(tǒng)應(yīng)用題教學(xué)之當(dāng)代重建并非是相關(guān)傳統(tǒng)的簡單回歸,而是如何能夠依據(jù)數(shù)學(xué)教育目標(biāo)的現(xiàn)代認(rèn)識對此做出認(rèn)真的總結(jié)與反思,并能通過新的研究做出進一步的發(fā)展。研究者以“努力提升學(xué)生的核心素養(yǎng)”作為分析的基本立足點,主張數(shù)學(xué)教育的主要任務(wù)是促進學(xué)生思維的發(fā)展,特別是幫助學(xué)生逐步學(xué)會更清晰、更深入、更全面、更合理地進行思考,并能由“理性思維”逐步走向“理性精神”,從而真正成為一個具有高度自覺性的理性人。
【關(guān)鍵詞】應(yīng)用題教學(xué);理性精神;數(shù)學(xué)教育;當(dāng)代重建
(續(xù)上期)
三、應(yīng)用題教學(xué)與學(xué)生思維品質(zhì)之提升
前面已經(jīng)提到,學(xué)習(xí)的程式化與機械化是傳統(tǒng)應(yīng)用題教學(xué)的又一常見弊病。但是,如果認(rèn)定我們只需盡早引入代數(shù)方法就可解決這一問題,則是“看錯了病,號錯了脈”。因為,通過“列方程、解方程”解決問題事實上也是程序或算法的應(yīng)用,如果學(xué)生缺乏足夠的自覺性,就可能導(dǎo)致機械的學(xué)習(xí),甚至更可能因此喪失促進學(xué)生思維發(fā)展的一個良好契機。
為了清楚地說明問題,在此還可特別提及這樣兩個事實:(1)代數(shù)方法的應(yīng)用并不能被看成解決問題的“萬能方法”。例如,有很多提前學(xué)習(xí)了方程方法的學(xué)生,在面對“面積問題”時仍然有較大困難,因為后者的求解往往需要用到“割補”等其他方法。(2)平面幾何(“綜合幾何”)的學(xué)習(xí)也有很多難題,其中的一些如果用解析幾何的方法求解則會變得比較容易,也即只需按照一定的程序或方法(代數(shù)化、方程化)就可獲得解決③。那么,我們是否也應(yīng)盡早離開“綜合幾何”去引入解析幾何呢?應(yīng)當(dāng)指出的是,這事實上也正是數(shù)學(xué)教育改革運動經(jīng)常提到的一個口號:“打倒歐幾里得”。但是,中外的相關(guān)努力應(yīng)當(dāng)說又未能夠都取得成功,從而也就使人們更清楚地認(rèn)識到了這樣一點:學(xué)習(xí)綜合幾何的目的不只是獲得相關(guān)的知識,我們更不應(yīng)以單純的解決問題作為求解幾何題的主要目的,而應(yīng)清楚地看到其對于促進思維發(fā)展的重要作用④。
總之,我們應(yīng)當(dāng)超出單純的問題求解并從更廣泛的角度認(rèn)識應(yīng)用題教學(xué)的意義,也即應(yīng)當(dāng)通過應(yīng)用題的教學(xué)努力促進學(xué)生思維的發(fā)展。
⑤ 由此可見,將應(yīng)用題的教學(xué)歸結(jié)為由“典型應(yīng)用題”過渡到“復(fù)合應(yīng)用題”,也只是抓住了其中的一方面。 應(yīng)當(dāng)強調(diào)的是,上述分析事實上也為我們應(yīng)當(dāng)如何開展解題策略的教學(xué)提供了重要啟示。也就是說,我們應(yīng)由唯一強調(diào)各種具體解題策略(更一般地說,是數(shù)學(xué)思維)的學(xué)習(xí)過渡到普遍性思維策略的學(xué)習(xí)與思維品質(zhì)的提升。特別是,我們應(yīng)努力幫助學(xué)生通過解決問題的具體實踐逐步學(xué)會更清晰、更深入、更全面、更合理地進行思考,并能努力提升思維的綜合(整體)性和靈活性、自覺性和創(chuàng)造性,等等。(當(dāng)然,我們又不應(yīng)將“具體解題策略的學(xué)習(xí)”與“普遍性思維策略的學(xué)習(xí)與思維品質(zhì)的提升”絕對地對立起來,這即為我們改進教學(xué)指明了進一步的努力方向。)
以下圍繞普遍性思維策略的學(xué)習(xí)與思維品質(zhì)的提升,對我們應(yīng)當(dāng)如何從事應(yīng)用題教學(xué)做出進一步的分析。
具體地說,應(yīng)用題教學(xué)的深化決不應(yīng)被理解成形式的變化,即如由所謂的“一步應(yīng)用題”過渡到“多步應(yīng)用題”,而主要是指“由簡單走向復(fù)雜,化復(fù)雜為簡單”。其中,后者不僅可以被看成數(shù)學(xué)發(fā)展的主要線索,也為學(xué)生具體學(xué)習(xí)各種解題策略特別是普遍性思維策略,包括努力提升思維的品質(zhì),提供了重要途徑。
以下是這方面特別重要的幾個環(huán)節(jié)。
第一,辨識與求變。
前一節(jié)中已經(jīng)提到了題型的“辨識”對于解題活動的特殊重要性,但就大多數(shù)情況而言,我們顯然不可能通過簡單的問題辨識與相關(guān)方法或解題模式的直接應(yīng)用就可順利地解決問題,而必須針對具體情況做出適當(dāng)?shù)恼{(diào)整或變化。由此可見,對于這里所說的“辨識”我們應(yīng)做更廣義的理解,也即應(yīng)當(dāng)更加重視新問題與基本題型的對照比較,特別是要很好地弄清兩者的同與不同,這樣就可通過適當(dāng)?shù)淖兓ソ鉀Q問題。
也正因如此,對于這里所說的“求變”,我們就不應(yīng)混同于前面所提到的“變式理論”。因為,我們在此所關(guān)注的已不是如何能夠通過引入更多的變式幫助學(xué)生很好地掌握相關(guān)的題型與解題方法,而是如何能夠提高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特別是思維的靈活性與創(chuàng)造性。例如,就“和差問題”的求解而言,學(xué)生往往首先需要依據(jù)題目中的條件求得所說的“和”與“差”,或是必須對已求得的結(jié)果做出一定調(diào)整才能最終解決問題。另外,問題中所涉及的未知數(shù)也可能不是兩個而是增加到了三個或更多。
以下是更復(fù)雜的一些情況,如要求學(xué)生就某一特定情境自己去發(fā)現(xiàn)相應(yīng)的條件或限制,或是通過若干基本題型的組合得出新的問題⑤。例如,面對“年齡問題”,我們不僅應(yīng)幫助學(xué)生清楚地認(rèn)識此類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可看成“和差問題”“和倍問題”與“差倍問題”的變形,而且也應(yīng)幫助他們很好地認(rèn)識此類問題的特征:盡管其中所涉及的年齡處于不斷變化中,但不同成員之間的年齡差又始終不變,這往往也是順利解決“年齡問題”的關(guān)鍵。再例如,“水流問題”顯然可被看成是由“和差問題”與“路程問題”組合而成,因為這正是此類問題的主要特征:船的順?biāo)俣仁谴撵o水速度與水流速度之和,其逆水速度則是兩者之差。
總之,為了切實提高學(xué)生解決問題的能力,關(guān)鍵并不在于引入更多的題型,而是應(yīng)當(dāng)引導(dǎo)學(xué)生積極地進行思考,并能切實提升學(xué)生思維的靈活性和創(chuàng)造性。再者,上面的分析顯然也可被看成這樣一個原則的直接應(yīng)用:“數(shù)學(xué)基本技能的學(xué)習(xí),不應(yīng)求全,而應(yīng)求變”,盡管我們所關(guān)注的并非基本技能的學(xué)習(xí),而是學(xué)生思維品質(zhì)的提升,特別是,能夠很好地掌握“求變”這樣一個普遍性的思維策略。
第二,整體分析與序的把握。
這是面對復(fù)雜問題時應(yīng)當(dāng)特別重視的又一環(huán)節(jié):相對于細(xì)節(jié)而言,我們應(yīng)當(dāng)更加重視整體的分析,包括確定解決問題的關(guān)鍵,并能按照合理的順序一步一步地解決問題。
由法國著名科學(xué)家、數(shù)學(xué)家彭加萊的以下論述,我們可以清楚地認(rèn)識到“整體分析”與“序的把握”兩者之間的重要聯(lián)系,以及這對于思維的清晰性和條理性的特殊重要性:“一個數(shù)學(xué)證明并不是若干三段論的簡單并列,而是眾多三段論在確定的序之中的安置。這種使元素得以安置其中的序要比元素本身重要得多。一旦我感覺到,也可以說,直覺到這個序,以致我一眼之下就領(lǐng)悟了整個推理,我就再也不必害怕會忘掉任何一個元素,因為每個元素都將在序中各得其所,而這是不需要我付出任何記憶上的努力的。”[9]
也正因如此,善于整體分析包括對序的很好把握,就應(yīng)被看成又一重要的思維品質(zhì)。進而,相對于這方面的專門教學(xué)而言,我們又應(yīng)當(dāng)更加重視這一思想在求解各類應(yīng)用題時的具體應(yīng)用。這顯然是我們在開展“握手問題”等與排列、組合密切相關(guān)的問題,以及“一一列舉”等解題策略的教學(xué)所應(yīng)特別重視的一點,包括我們?nèi)绾文芎芎玫刈龅郊葻o遺漏也無重復(fù),既非雜亂無章也非瑣碎、煩人。
在此,還應(yīng)特別重視“幾何圖示”(“結(jié)構(gòu)圖”)的作用。例如,為了用圖形表示出全部的解題過程,可以用“點”表示其中的已知及未知成分,用“線段”表示它們的聯(lián)系。顯然,按照這一做法,整個解題過程就被表示成了由已知點到未知點并由多條線段組成的一個幾何圖形,從而也就十分有益于解題者建立對于全部解題過程的整體性認(rèn)識和直觀把握。
以下是這方面的一個具體實例。
最后,依據(jù)上述分析,可更清楚地認(rèn)識到這樣一點:我們確實不應(yīng)特別強調(diào)解題過程中究竟包括幾個步驟,而應(yīng)更加重視問題的整體把握與思維的條理性。
第三,由“解題策略”轉(zhuǎn)向普遍性思維策略。
這是具體判斷一個策略能否被看成普遍性思維策略的主要標(biāo)準(zhǔn),即其是否具有超出數(shù)學(xué)的普遍意義。顯然,就應(yīng)用題的教學(xué)而言,這也意味著我們不應(yīng)單純地從解決問題這一角度去認(rèn)識各個解題策略的作用,將它們看成純粹的“解題術(shù)”,而應(yīng)注意分析它們是否具有更廣泛的意義。
例如,“畫圖”與“列表”顯然可被看成兩種具有廣泛意義的普遍性方法。另外,我們也可從同一角度對“假設(shè)法”的教學(xué)做出更深入的分析。“假設(shè)法”是指,教學(xué)中我們應(yīng)當(dāng)更加突出“嘗試與誤差糾正(try and error)”這樣一個方法。因為,后者相對于單純的“假設(shè)”顯然具有更普遍的意義,特別是在科學(xué)研究中具有廣泛的應(yīng)用。
⑥ 不難看出,上述分析對于“問題解決”也是基本適用的,而這事實上也正是國際上關(guān)于“問題解決”的一點共識:由于我們在此所面對的并非是簡單的練習(xí)題(nonroutine problem),從而就必須通過各種相關(guān)的知識與技能的綜合和創(chuàng)造性的應(yīng)用去求得問題的解答。詳見另著《問題解決與數(shù)學(xué)教育》,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第40頁。
再者,從更高的層次進行分析,我們又應(yīng)當(dāng)特別強調(diào)兩種普遍性的思維策略:“聯(lián)系的觀點”與“變化的思想”。另外,在一些學(xué)者看來,對于“特殊化與一般化”,也應(yīng)予以特別的重視。在筆者看來,教師也可聯(lián)系自己的教學(xué)實踐對此做出概括和總結(jié)。這直接關(guān)系到了這樣一點,即我們能否在學(xué)生離開學(xué)校以后給他們留下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當(dāng)然,為了實現(xiàn)這樣一個目標(biāo),我們在教學(xué)中應(yīng)始終堅持這樣一點——“基本思想的學(xué)習(xí),不應(yīng)求全,而應(yīng)求用”。
第四,突出數(shù)量關(guān)系的分析。
在此應(yīng)再次強調(diào)一點,即應(yīng)當(dāng)將“數(shù)量關(guān)系的分析”很好地滲透、落實于應(yīng)用題教學(xué)的全部過程之中。
還應(yīng)強調(diào)的是,從上述角度我們也可更清楚地認(rèn)識到“應(yīng)用題”與一般所謂的“練習(xí)題”之間的重要區(qū)別。后者的反復(fù)演練主要是為了幫助學(xué)生很好地掌握相應(yīng)的基本技能,包括養(yǎng)成較強的計算能力。也正因如此,就相應(yīng)的教學(xué)工作而言,強調(diào)的往往是“程序性觀念”,也即如何能夠按照指定步驟快而準(zhǔn)地進行計算從而獲得所要求取的答案。與此相對照,應(yīng)用題教學(xué)則具有不同的性質(zhì):此時我們并沒有直接告訴學(xué)生應(yīng)當(dāng)通過哪些計算并按照怎樣的順序去求得答案,而是必須依靠他們自身的努力發(fā)現(xiàn)具體的解題途徑。也正因如此,就應(yīng)用題的求解而言,我們應(yīng)特別關(guān)注問題中數(shù)量關(guān)系的分析,也即應(yīng)當(dāng)更加突出“結(jié)構(gòu)性觀念”。也就是說,對于應(yīng)用題,盡管我們?nèi)钥蓞^(qū)分出多種不同的類型,但是又必須通過問題中未知量與已知量之間關(guān)系(特別是等量關(guān)系)的分析發(fā)現(xiàn)具體的解題途徑,而“快而準(zhǔn)地進行計算”則已退居到了次要的地位。當(dāng)然,應(yīng)用題教學(xué)主要是為了促進學(xué)生思維的發(fā)展,而不只是學(xué)生計算能力的培養(yǎng)⑥。
最后,突出數(shù)量關(guān)系的分析也可被看成小學(xué)數(shù)學(xué)教學(xué)很好地滲透代數(shù)思想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因為,后者并不應(yīng)被理解成在小學(xué)盡早地去引入代數(shù)方法或其他一些明顯屬于代數(shù)范圍的內(nèi)容,而主要是指代數(shù)思想的滲透,“等量關(guān)系”(或者是“結(jié)構(gòu)性觀念”)則又正是后者十分重要的一個內(nèi)涵。另外,這顯然也為學(xué)生學(xué)習(xí)方程提供了重要基礎(chǔ)。
第五,注重優(yōu)化。
正如人們普遍認(rèn)識到的,與知識的簡單積累或不斷糾錯相比較,優(yōu)化更應(yīng)被看成數(shù)學(xué)學(xué)習(xí)的本質(zhì)。而這又正是“通過數(shù)學(xué)學(xué)習(xí)努力優(yōu)化思維”十分重要的一個含義,即思維品質(zhì)的提升。特別是,學(xué)生如何能夠逐步學(xué)會更清晰、更深入、更全面、更合理地進行思考,包括努力提升思維的綜合(整體)和靈活性、自覺性和創(chuàng)造性,等等。
在此,還應(yīng)特別強調(diào)一點(這也應(yīng)成為應(yīng)用題教學(xué)的一個重要目標(biāo)):努力幫助學(xué)生養(yǎng)成“長時間思考”與“反思”的習(xí)慣與能力。具體而言,由于無論是解題策略、方法的學(xué)習(xí),或是思維品質(zhì)的提升,往往都有一個較長的過程,因此在教學(xué)中我們應(yīng)特別重視幫助學(xué)生逐步學(xué)會長時間的思考,包括努力創(chuàng)設(shè)必要的外部環(huán)境或課堂氛圍,以及對學(xué)生的不同意見采取更加寬容與理解的態(tài)度,等等。更重要的是,我們還應(yīng)努力使之成為學(xué)生的自覺行為,而不只是由于外部壓力的被動行為。也正因如此,我們在教學(xué)中就應(yīng)對于總結(jié)與反思予以特別的重視,包括從整體高度對已建立的知識做出必要的“再認(rèn)識”。
顯然,按照上述的要求,應(yīng)用題教學(xué)將上升到一個更高的水平。當(dāng)然,就這方面的具體工作而言,我們又應(yīng)十分重視相應(yīng)的教學(xué)行為對于學(xué)生的可接受性。
具體而言,筆者認(rèn)為,小學(xué)中年段特別是四年級是開始應(yīng)用題教學(xué)較為合適的一個時期。 但在做出相關(guān)努力的同時,我們又應(yīng)特別重視學(xué)生興趣的培養(yǎng),而不要因為不適當(dāng)?shù)靥岣唠y度而使學(xué)生完全喪失了數(shù)學(xué)學(xué)習(xí)的興趣。另一方面,這是學(xué)生成長更為合理的一個軌跡,從而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基礎(chǔ)教育階段數(shù)學(xué)教育乃至一般教育所應(yīng)實現(xiàn)的主要目標(biāo):習(xí)慣—興趣—品質(zhì)—精神。
筆者衷心希望能有更多教師積極投入此項工作,從而真正做好傳統(tǒng)應(yīng)用題教學(xué)的當(dāng)代重建。
參考文獻:
[1]唐彩斌.怎樣教好數(shù)學(xué):小學(xué)數(shù)學(xué)名家訪談錄[M].北京:教育科學(xué)出版社,2013.
[2]鄭毓信.數(shù)學(xué)教育視角下的“核心素養(yǎng)”[J].數(shù)學(xué)教育學(xué)報,2016(3):1-5.
[3]鄭毓信.關(guān)于“問題解決”的再思考[J].數(shù)學(xué)傳播,1996(4):63-69.
[4]馬云鵬,朱立明.從應(yīng)用題到數(shù)量關(guān)系:小學(xué)數(shù)學(xué)問題解決能力培養(yǎng)的新思路[J].小學(xué)數(shù)學(xué)教師,2018(6):4-7.
[5]波利亞.數(shù)學(xué)的發(fā)現(xiàn):第一卷[M].劉靜麟,曹之江,鄒清蓮,譯.呼和浩特:內(nèi)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6]鄭毓信.新數(shù)學(xué)教育哲學(xué)[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5.
[7]張奠宙.張奠宙數(shù)學(xué)教育隨想錄集[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3.
[8]顧亞龍.題組模塊:給數(shù)學(xué)課堂以生成的力量[J].小學(xué)數(shù)學(xué)教師,2019(1):34-40.
[9]彭加萊.科學(xué)的價值[M].李醒民,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